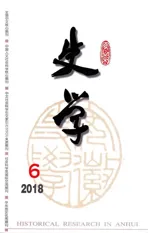北洋海军购置蚊船、铁甲船史实补正
2018-01-23陈先松
陈先松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清政府因为对方2只铁甲船的威胁而以求和告终。在这一背景下,李鸿章建设北洋海军之初,重点购置“敌有我无”的铁甲船,以及据说可以击沉铁甲船的蚊船。学术界对此多有研究,但主要探讨赫德等经办人的具体作用,相对忽略李鸿章这一核心人物的购舰决策。部分学者在一些史实叙述和结论方面,亦有补充、商榷之处,譬如认为:第一批蚊船的订购,是赫德与总理衙门的共同决策,出现任何问题,不应归罪于李鸿章;李鸿章对蚊船的信心产生动摇,始于光绪五年或光绪六年;李鸿章至光绪五年下半年后,已意识到购置蚊船吃亏,却指使山东等省继续购置蚊船,是遮掩之前购船错误、玩弄权术的结果;丁日昌《海洋水师章程》中提到的大兵轮船即铁甲船;李鸿章最初不愿购买铁甲船,并以日意格购船事件为例,说明其理由之一,源于巨炮威胁论;李鸿章最初几年放弃购买铁甲船的另一原因,是赫德的阻挠;李鸿章光绪五年之前对铁甲船的态度是观望、查询或阻挠,之后才紧锣密鼓地购买;丁戌奇荒对李鸿章购置铁甲船的负面影响,是北洋海防专款的大量挪用;李鸿章光绪五年初决定购置铁甲船,源于赫德呈递《条陈海防章程》进而染指海防权力的威胁;李鸿章光绪五年十月停购铁甲船,是担心购船后会并入南洋,故“有钱不愿让南洋分沾”,直至南洋大臣沈葆桢逝世,才又开始购置等等。[注]参见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增订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7—130页;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6—140页、153—162页;罗肇前:《李鸿章是怎样购买铁甲舰的》,《福建论坛》1993年第4期;刘振华:《赫德、金登干与晚清舰船的购买》,《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等;曾志文:《西方铁甲舰议购与晚清海疆筹防——以李鸿章私函为中心》,《学术研究》2017年第3期。本文拟充分利用新版《李鸿章全集》《清代孤本外交档案》《李星使来去信》等文献,以时间为线索,全面梳理李鸿章购舰心态的演变历程及影响其购舰决策的相关因素,并就学术界已关注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一、李鸿章与第一批蚊船的购置
蚊船是一种守口的浮动炮台,以较小的舰体装置一门巨炮,靠调整船体来瞄准射击目标,在港口防御时与岸上炮台机动配合,以击退敌人的进攻。[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第120页。在清末中国,蚊船可以音译为“根驳船”(gunboat),也可根据外形特征、作战形式等直译为“守口大炮铁船”、“水炮台船”、“铁炮台船”等。
早于同治九年(1870年)、同治十年,李鸿章已听闻蚊船的音译名称——根驳船,但他缺乏了解,以为船体可装载数门大炮。[注]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3、352;163页。甚至在接下来的数年内,也将根驳船与蚊船的直译名称——守口大炮铁船、铁炮台船等相混淆,称中国除30只根驳船外,还需添置名异实同的守口大炮铁船20只。[注]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3、352;163页。
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犯台湾,沿海各省纷纷设防,洋商也借机兜售蚊船、铁甲船等。李鸿章始对蚊船有所关注,并建议江苏巡抚张兆栋放弃铁甲船,添置价格相对低廉的蚊船,称:“吴淞炮台……若添守口铁炮船,较有依恃……海口只宜铁炮台船也。”[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89、83、89、95页。文中的“守口铁炮船”、“铁炮台船”等,即指蚊船。李鸿章虽认识到蚊船的守口价值,但限于经费,并无购置意图,称:“敝处欲添置枪炮,不名一钱,遑论其它。奉天海口极多,一无防备,诚如尊示,是以中外无不冀事之速了,一了则百了,更不计及此后如何整备也。”[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89、83、89、95页。
北洋海军第一批蚊船的购置,最初由总税务司赫德和总理衙门商议、推动。学术界相关成果,通过《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等文献,对赫德购船的过程,已有充分研究,但甚少提及赫德通过何种渠道推动蚊船的购置。
查日本侵台事件以后,赫德与总理衙门多有接触。同治十三年五月,赫德建议中国不宜购置西洋铁甲船,“价廉者不合用,合用者价不廉,各国合用者不肯出售,出售者不能合用”,且铁甲船价格昂贵,每船约银120万两,“一经遭损,修理更难”。[注]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7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2640、2679—2680、2850—2851、2851—2852页。六月,向总理衙门集中反映洋人、洋行兜售军火的弊端,譬如推荐铁甲船的某洋行,信誉不佳,历史上曾两次倒闭;某洋商代日本购买枪支,打算将质量低劣者转售中国。总之,“贱价买贱货耳”。[注]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7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2640、2679—2680、2850—2851、2851—2852页。八月,正式提出蚊船巨炮的设计理念,称英国新造大炮,可在3里外击破甲厚24寸的铁甲船,以致“英国不另造铁甲船,专做此炮”,而负载此炮,“闽船恐不能支”,需在外洋另求坚固船体。[注]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7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2640、2679—2680、2850—2851、2851—2852页。
赫德与总理衙门的频繁接触,产生积极影响。总理衙门后来奏称:“赫德自上年(同治十三年)日本扰台事起,屡在臣衙门议及购买船炮各事,经臣等详细询究,拟即量力先行购办,责令该总税务司经理,以视各口洋行经手购办者较有责成。”[注]总理衙门片,光绪元年四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381-30。本文所引军机处录副奏折,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总理衙门此奏,与其当初所想,尚有一定距离。赫德阐述蚊船理念后,总理衙门犹豫不决,称“诚恐一时难于备办”,要求李鸿章就南洋、北洋的海防实际等,讨论赫德所述各节,以供参考。[注]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7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2640、2679—2680、2850—2851、2851—2852页。自此,李鸿章成为是否订购蚊船的重要决策者。
同治十三年八月,李鸿章复函总理衙门。虽然洋商的报价从八月初的每船炮“十余万内外”[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89、83、89、95页。,虚涨到“五六十万元至百万元不等”,但出于北洋自身利益,李鸿章赞成由总理衙门代置蚊船,称赫德所述巨炮,“即系铁炮船上所用,又名蚊子船,又名水炮台,守海口最为得力……将来南北洋必须订购二三只,分布要口,认真操练,庶各国兵船不敢觊觎。”[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89、83、89、95页。
九月初二日,总理衙门收到李鸿章复函后,坚定了购置决心,嘱咐后者“筹复商办”。初九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进一步强调蚊船的海防价值,认为驶近中国口岸的铁甲船,“铁甲不过数寸,有此巨炮小船守口最为得力,较陆地炮台更为灵活”,并赞成由赫德代购,“总税司经办当较洋行行为可靠”,每船仅银10万两。[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04—105;197—200、202—203;203页。在总理衙门、李鸿章同意下,赫德委托海关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具体负责蚊船的订购事宜。
光绪元年(1875年)春,赫德携带金登干有关蚊船信函以及自己草拟的购置合同,与李鸿章“连日接晤,逐细讨论”,议定于英国阿姆斯特朗厂订购38吨巨炮蚊船、26.5吨巨炮蚊船各2只,相关经费共45万两,由江海等关洋税项筹拨。[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04—105;197—200、202—203;203页。这4只蚊船即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号。
二、李鸿章与后续蚊船的购置
李鸿章对蚊船颇为期待,称总价不及铁甲船1只之费,若真能制伏铁甲船,则“日后添购为费尚省”,即使不确,而“巨炮已为中国所无,船只亦能随时修理,出入各口,战守皆宜,似不至糜费无益”。[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04—105;197—200、202—203;203页。至光绪二年,李鸿章检阅先期抵达的龙骧、虎威号,甚是满意,“所有炮位轮机、器具等件均属精致灵捷……运炮装子全用水力机器,实系近时新式,堪为海口战守利器”。[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7册,第211—212页。
光绪三年底,李鸿章对蚊船的信心有所动摇。因为蚊船的船底铁板“久浸盐水,均生茜草”,进而影响航速,李鸿章令福州船政局修理。至光绪四年正月,新闻报纸传言蚊船到福建后,“有行走不动之说”,时速从原先30里,降到不及10里,引起总理衙门、李鸿章疑虑,“来华未久,行走亦不如从前之速,倘历有年所,岂不又蹈绿营兵船积习”,“何以阅时未久,相去如此悬殊”。为此,李鸿章致函福州船政局,要求出洋试验,“据实禀报”。[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239页;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15册,第5749—5750页。
至光绪四年三月,总理衙门、李鸿章对蚊船的担忧,得到很大缓解。这源于两个因素。其一,赫德的有力解释。总理衙门发现问题后,召集赫德咨询,得出“此等船只似宜动不宜静,驾船之人似宜劳而不宜逸”的结论,并告之李鸿章[注]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15册,第5751、5820—5821、5842—5844页。,后者赞为“极是笃论”。[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240、293、304、304页。其二,福州船政局的出洋试验报告。该报告内容,已不可考,但李鸿章阅后,十分满意,称“极为周详”。[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240、293、304、304页。参考数月后李鸿章亲自检测的结果,蚊船时速至少达到21里,非报纸所谓的不及10里,“轮机、器具等件均尚精致灵捷,演试大炮亦有准头”。[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109页。
不久,总理衙门、李鸿章对蚊船的一点猜疑,即为英国回购事件一扫而空。四月二十三日,英国驻华使馆署汉文正使璧利南拜访总理衙门,商议购回龙骧等4只蚊船。[注]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15册,第5751、5820—5821、5842—5844页。总理衙门、李鸿章认为英国此举与英俄边事紧张有关,并以局外中立的原则加以拒绝。然在这一事件中,英国既愿购回,充分说明蚊船的海防价值。李鸿章还打听到英国亦以此船“专防本国海口,以作水炮台,抵御铁甲最为得力”,不仅造有20余只,还打算添造50余只。[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240、293、304、304页。
英国回购事件,间接促成了北洋海军第二批蚊船的购置。
其时,清政府划拨的南北洋海防专款,由于南洋大臣沈葆桢的谦让,全归北洋近3年[注]参见沈葆桢折,光绪四年二月初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382-38。,以致南洋“海防、江防,一无措置”。[注]林海权点校:《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4页。李鸿章应沈葆桢的请求,拟光绪四年初为南洋再购2只蚊船。[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240、293、304、304页。在英国回购事件中,李鸿章暗示船少,“不敷调拨”,总理衙门认为英国的购船动机“固难尽测”,而蚊船“足适于用可知”,希望李鸿章从海防专款内购置4只。[注]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15册,第5751、5820—5821、5842—5844页。李鸿章表态赞同。此4只蚊船即北洋海军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号,船炮38吨,由赫德具体购置。[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109页。
可于海口制伏来犯的铁甲船,是李鸿章一再购置蚊船的重要依据。然至光绪五年,李鸿章日渐清醒:蚊船船小,只能布置于海口,而外国铁甲船吃水过深,多行驶于大洋之中,两者直接对敌的可能性很小。若谓守护海口利器,尚属勉强;若谓足制敌国铁甲船,则没有可能。
这在光绪五年赫德向总理衙门自荐总海防司的事件中有明显体现。赫德自荐的前提条件是:只要假以事权,雇佣西人,认真操练,仅需蚊船、碰快船,“即可以制铁甲”。[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页。对此,李鸿章八月十一日致函沈葆桢称“前定蚊船,原议明可以出海接战,若徒守口,各口多浅,铁甲不能深入,殊为无用”[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页。,九月初五日致函曾纪泽称“赫德谓可海战,攻破铁甲,似非确论……(蚊船)既不及铁甲之乘风破浪,行驶至速,又恐大洋浪战被炮击沉,自蹈危险”。[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页。
李鸿章对蚊船不能制伏铁甲船的新认识,并非否认蚊船海口设防的巨大价值,前致曾纪泽函即认为“金登干代购蚊子船,经执事查验,诚为防御海口利器,洵然”。[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页。九月十一日,李鸿章进一步向总理衙门肯定为“守港利器”,南北洋海口众多,“若财力有余,尽可添购”。[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页。与此相关,李鸿章推动了北洋海军第三批蚊船的购置。
光绪五年十月,因清政府饬令筹议海防,李鸿章称蚊船“防守海岸最为得力”,要求沿海各省皆自筹经费,购置一两只,获得清政府允准。[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511—512页。按照李鸿章原奏,山东省原只需购置1只,然李鸿章借口浙江、广东等省未有回音,若仅订1只,“似难向西厂定造”,劝说山东巡抚周恒祺购船2只,分布烟台、登州两处。[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页。周恒祺欣然允从,于光绪六年初奏请定购38吨巨炮蚊船2只。[注]周恒祺片,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奉旨日期,军机处录副奏折,3-9384-8。此即镇中、镇边号,后归北洋海军统一训练、管理。
三、李鸿章对铁甲船的态度分析
铁甲船,是在木质兵轮水线以上部分配以装甲带,建一装甲的中心堡垒,以保护主要武器的安全,具有强大的攻击和防卫能力。[注]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第155页。
同治七年,丁日昌草拟《海洋水师章程》,提及可在外海剿匪、“兼用风帆行驶如飞”的大兵轮船。[注]参见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页;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39页。此兵轮船并非铁甲船。丁日昌将两者区分开,认为铁甲船视质量等因素,“往往有价贱于兵轮船者”。[注]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225、163页。
李鸿章听闻铁甲船的时间,始于同治十年,认为其用在“防守海口”,接下来的两年中鲜有提及。[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第229、247页等。李鸿章对铁甲船真正有所认识,源于同治十三年的日本侵犯台湾之役。因为日本两只铁甲船的威胁,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沿海各级官员频繁探讨铁甲船的购置问题,参阅了洋商送来的相关图纸式样等。[注]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39、41、48、58、77、80、83、95、105页。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的海防奏议,是这一时期李鸿章海防思想的集中体现。李鸿章肯定铁甲船的海防价值,即在洋面“专为游击之师”,与重视守口的蚊船有别。在海军建设思想上,李鸿章希望优先购置铁甲船,东洋、南洋、北洋各2只,“其有余力再置他船”,建议派中国官员亲赴外国各厂考究等。[注]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225、163页。
光绪元年四月,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仍坚持应该购置铁甲船,五月致函总理衙门称“约计一军须兵轮船二十只,内应有铁甲船一两只,声势稍壮”,七月致函山东省称“洋面散漫,诚如来示,防不胜防,亦防不能防,将来集有巨款,须照总署原议,创立水师一军,约铁甲及大小兵轮船十数只,驻扼庙岛、旅顺口之间,以固北洋门户。”[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为购置铁甲船,李鸿章支持福州船政局学生,“带往英德铁甲船学习”,赞为“此举最为紧急,愈速愈妙”[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以培养驾驶人才。
光绪元年底,曾在福州船政局供事的法国人日意格积极兜售铁甲船,李鸿章却致函南洋大臣沈葆桢称:“各处新闻纸佥谓,德之克鹿卜、英之阿摩士庄新制巨炮,实可洞穿二十余寸铁甲,而铁(甲)船转虑无用,果尔则此事更宜斟酌。”[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这仅是李鸿章婉拒日意格售船的借口。究其实,早于同治十三年八月,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信函,已了解到巨炮可以击沉铁甲船[注]参见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7册,第2850—2851页;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94—95页。,但如上文所述,并未因此而显示出对铁甲船的退缩之意。李鸿章婉拒日意格的真实意图,一在于对日意格的不放心,“总署惑于浮言,尝疑日酋(日意格)贪利欺骗,外人亦有附和其说者”,如果购置,需派中国官员出洋,“就便监察,以祛众疑”[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另在于经费的制约,李鸿章称北洋海防专款“迄今一年之久,统计各省、关仅解到银六十余万,屡催罔应,实解尚不及十分之二……是以幼丹(沈葆桢)函属(嘱)日意格回华商订铁甲船一只,尚未敢率允定购。”[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
事实上,海防专款收数有限,以及在此基础上购船经费的难以筹措,是李鸿章最初愿意而不能购置铁甲船的主要考虑。光绪元年,清政府为南洋、北洋划拨海防专款,每年约“四百数十万两”,但筹议时未能解决财源问题,划拨之始即已种下拖欠的恶果。[注]参见陈先松:《晚清海防专款筹议述论》,《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与此相对应,清政府劝李鸿章体谅国家财政困难,对北洋“不云暂缓海防,乃云从容筹备”[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李鸿章不得不表示“能得若干款项,再办若干兵船,较为稳妥”。[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至光绪三年八月,北洋海防专款仅收存100余万两,据当时估算,1只铁甲船约价100万两,连其养兵之费、新建船坞经费等,“统足以举事”。[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21;429;96、97页。李鸿章向前福建巡抚丁日昌自嘲为:“无钱逼倒英雄汉,大才将何以处之,时局似急尚缓,务祈从容擘画,勿过躁迫是幸。”[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21;429;96、97页。
李凤苞的建议,是影响李鸿章购置铁甲船的另一因素。
李凤苞,字丹崖,江苏崇明人,“究心历算之学,精测绘”,同治年间先后调入江苏舆地局、江南机器制造局、吴淞炮台工程局工作,接触近代物理、化学、军事等书籍,西学知识丰富。[注]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44页。光绪元年四月,李鸿章慕名召见,赞其“精于舆图,勤能耐苦,确是有用之材”。[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光绪二年三月,因李凤苞委带船政学生出洋,李鸿章令其就近酌购铁甲船,“较之数万里外贸贸然徒听外人指挥者,必更核实节省”。[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至该年八月,李鸿章致函丁日昌,称铁甲船应购与否,“须俟丹崖(指李凤苞)到英后,探讨底细,再行定购”。[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由此,李凤苞成为李鸿章购置铁甲船的主要参谋。
光绪二年十二月,对铁甲船多次发表负面评价的赫德,曾正面推动北洋海军购置铁甲船,然为李凤苞所阻挠。赫德向李鸿章所推荐者,系土耳其2只铁甲船,马力3600匹,时速72里,25吨大炮4门,铁甲厚至10寸,每只原需100余万两,现因土耳其国“限于资财……情愿亏价相售”,只需银80万两。[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经探询,李凤苞认为该船炮位只有4尊,略嫌其少;炮重25吨,却不用汽机,“自难十分灵捷”;此外还有不合用者数端,例如“机器不用康邦,一也;药库近船尾,二也……桅上不装横杆,五也;烟通及水锅之半俱在八角台外,六也”。不仅质量堪忧,李凤苞还明确指出,土耳其国在英国另造新船,并非财力匮乏,该二船“久欲求售,并非便宜”等等。光绪三年七月,李鸿章致函李凤苞,称其“所议各节,极有见地”,“自应暂作罢论”。[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21;429;96、97页。
光绪三年底,李凤苞在欧洲历观英法诸国20余只铁甲船的基础上,考虑到中国海岸水深多在20尺以内而西洋铁甲船可进入者甲厚至10寸,建议应在英国缪答厂购置铁甲船,“以甲厚十二寸、入水十七八尺为率”。李鸿章甚感兴趣,十二月十七日致函李凤苞,要求与该厂协商,若“果有新式坚利、吃水不深……价值较廉”的铁甲船,则“再行议请订造”。[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页。与购置决心相对应,李鸿章于光绪四年派遣员弁勘探北洋各口的入水深度[注]参见蔡少卿、江世荣主编:《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以为铁甲船驻地的选择提供准确数据。
光绪三年底、光绪四年初,正值华北丁戌奇荒。李鸿章英国缪答厂购船的失败,与此有很大关联,但并非因为北洋海防专款的大量挪用。事实上,北洋海防专款用于丁戌奇荒者,大多为借款,约有43万两,可由“练饷制钱提还,或议(山西、河南等省)分年解缴”。[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29页。因借而未还者仅7万余两,连同无需偿还者,被挪用的总数共32万余两。其中,至少约20万两于光绪三年秋被挪用,并未阻碍李鸿章光绪三年底的购船决心[注]参见陈先松:《北洋收存海防经费的挪用问题(1875-1894)》,《安徽史学》2013年第2期,第32—35页。;其余12万两,数额较小,对“非存银三四百万”不敢购置铁甲船的李鸿章来说,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丁戌奇荒,对李鸿章购船真正的影响,是购船经费筹措计划的破灭。如前文所述,李鸿章建设北洋海防之初,秉持“能得若干款项,再办若干兵船”的方针。在北洋海防专款仅收存100余万两而铁甲船“非存银三四百万不足以举事”的情况下,李鸿章敢于光绪三年底购置,其关键就在于“议请订造”,即与清廷中枢商议、请拨购船经费。但光绪四年初华北灾情加重,李鸿章在清政府的再三垂询下,自保北洋海防专款尚且吃力,自难以再“议请订造”。[注]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29—30页;第32册,第452页。光绪五年六月,李鸿章致函李凤苞,将光绪三年底英国缪答厂购船的失败,归咎于“嗣因筹款维艰中止”。[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页。
从北洋购船史的角度来说,李鸿章光绪三年底购置铁甲船的努力,具有另外一层意义,即开始在海防专款收数有限的情况下,打破“能得若干款项,再办若干兵船”的购船思路,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以筹措大宗购船经费。这为后来定远、镇远号铁甲船的购置,埋下了伏笔。
四、李鸿章与定远、镇远号铁甲船的购置
光绪五年,李鸿章再次倡购铁甲船。这与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条陈海防章程》无关。查李鸿章阅知赫德章程的时间,是光绪五年七月初十日。然早于六月初九日,李鸿章即已致函李凤苞,令觅购“于中国海口相宜,能制日本之船”,并查明每船需银若干、分几批兑付及相关的船坞建设费用,以便与沈葆桢等商量核办。[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页。
李鸿章光绪五年六月的购船决心,源于清廷谕旨的授意。该年初,日本废灭琉球,“举朝惶遽无措”,李鸿章在京陛辞慈禧时,建议购置铁甲船,“但有二铁甲,闯入琉球,倭必自退”。[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页。此议终被采纳。五月十七日,清政府谕令李鸿章等:“至购买铁舰等物,需用浩繁,应如何筹集巨款,并著该大臣等设法商办”。[注]《清实录》第53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3页。这为铁甲船购置经费的再次“议请”,提供了可能。
然而,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户部“议请”购船经费的进程并不顺利。按李鸿章原拟计划,至少需购2只铁甲船,连新建船坞等约需300余万两,时北洋只收存100余万两,其余不敷200余万两,不论是借洋债还是借户部存款,“皆非中朝大官所愿闻”。[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页。九月十一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拟尽北洋海防专款的全部购置铁甲船1只,“来华操演,以为始基”。[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页。李鸿章之意,更多的是逼迫总理衙门表态:若同意购置,则北洋海防专款已无剩余,铁甲船购置经费的缺口、建坞经费以及蚊船日后相关费用等,需由总理衙门承摊,或者总理衙门另筹铁甲船购置经费。九月十六日,总理衙门函复:“筹办海防若先购铁甲船一只,只能专顾一口,应另购他项战舰。”[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页。
至此,李鸿章购置铁甲船的计划,已陷入绝境。十月初五日,李鸿章收到李凤苞八月初十日的信函。李凤苞认为北洋现在购置铁甲船,可仿照光绪二年赫德推荐的土耳其铁甲船样式,前往欧洲各厂考核订购。然就李凤苞本意来说,他反对操之过急,认为各国“纷议停造铁甲,如可缓办,尤为合算”,况且购置铁甲船需同时举办四事:一为炮台庇护,吴淞等处炮台不足庇护;一为船坞修理,江南制造局船坞太浅,且离海太远;一为快船,若铁甲无快船辅佐,“则孤注而已”;一为水雷,有行雷可以出奇,有伏雷可以堵守,然后铁甲船不为快船所困等。[注]《李丹崖自德国柏林发来第二十四号信》,《李星使来去信》卷4,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抄本。因为李凤苞的建议,加之购船经费难以筹措,李鸿章于十月十七日复函总理衙门,正式停止铁甲船的购置。[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页。
铁甲船购置计划的转机,源于清廷谕旨的促成。因为之前“预筹海防事宜,尚未定议”,清政府颇为不满,令总理衙门、李鸿章等再“分别妥议具奏”。[注]《清实录》第53册,第505页。总理衙门不得不转变态度,令李凤苞就近查明土耳其两只旧铁甲船,“如尚未出售,而价不甚昂,自应购备”。[注]总理衙门折,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383-33。李鸿章得知船已归英国、而英国愿以单价100万两转售时,便力劝总理衙门:“既奏明购备,亦未便置而勿论”。[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页。
前文已述,土耳其铁甲船3年前的售价仅银80万两,现在涨幅25%,且质量低下。李凤苞回复总理衙门,称“不能出洋交战”。然而,李鸿章却力主购买,认为与中国海口最为相宜,甚至辩称李凤苞的反对意见是“手书匆促,未暇择言”的结果。[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页。李鸿章之所以罔顾事实,购置3年前就被自己否决过的劣质铁甲船,最根本的原因是遇到了一次难得的筹款良机。
其时,在李鸿章、总理衙门主持下,山东、广东、浙江等省需筹措5只蚊船购置经费,单价15万两,共约75万两;南洋需筹措2只碰快船购置经费,单价32.5万两,共约65万两;福建省需筹措4只蚊船、2只碰快船的购置经费,共约125万两。[注]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512页;第32册,第516页。李鸿章建议“先其所急”,各地“未定之蚊船、碰船皆在可以稍缓之列”。[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页。经与总理衙门反复协商,李鸿章奏准购置土耳其铁甲船,一只归属福建,另一只南北洋共有,除挪用福建、南洋的“蚊、碰船之款”外,余款可从出使经费内续拨或由各方匀凑,“尚易为力”。[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页。
不久,土耳其铁甲船因英国“海部换人”而“作罢论”。对于铁甲船的购置来说,经费是最大难题,而现在各省已凑拨大宗现款,“尤属难得机会”。[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页。李鸿章不愿放弃,奏准李凤苞从西洋各厂中“查照新式”订购2只铁甲船。[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页。
按照李鸿章原奏,所订铁甲船,一归福建,一归南北洋共有。李鸿章并不满意。其时,在户部和李鸿章的策划下,两淮盐商捐款100万两,轮船招商局需归还各省解拨的官款170余万两。李鸿章遂利用光绪六年初中俄伊犁交涉、沙俄兵船在太平洋时有调动的传闻,从上述两笔经费中各“议请”100万两,为北洋单独添置2只铁甲船。[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页。
李鸿章的购船计划,系按每只100万两估算。然南洋、福建最终解交的购船经费仅150万两,李凤苞在欧洲各厂“择善订定”[注]《来信第五十一号》,《李星使来去信》,卷8。的2只铁甲船却涨至326万余两。光绪七年,李鸿章不得不将两淮盐商捐款100万两,“挪后就前”,另从自己掌管的淮军军饷等款中凑拨购船经费。[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页。这两只铁甲船,即定远号、镇远号。
至于第二批铁甲船的购置计划,终被李鸿章放弃。这与两个因素有关。
其一,购船经费的难以筹措。在定远、镇远占用了两淮盐商捐款100万两后,第二批铁甲船的购置经费仅剩轮船招商局官款100万两。李鸿章于光绪七年称:“俟二三年后伊犁偿款归清,各省财力稍宽”,再“请旨敕下总理衙门、户部筹拨的款”。[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页。然至光绪八年日本发起朝鲜事端时,李鸿章借机“议请”购船经费[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83页。,却遭到户部的委婉拒绝。[注]参见蔡少卿、江世荣主编:《薛福成日记》,第403页。
其二,定远、镇远号被纳入北洋海军序列。这两只铁甲船原归福建、南洋,但挪用了北洋购船所需的盐商捐款等,且系李鸿章所订,为其收编提供了便利。至光绪八年,李鸿章已隐含此种意图,称定远、镇远号返华后,将由自己“选将练兵,精心教练”。[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83、83、158页。在达到北洋海军2只铁甲船的既定目标后,李鸿章对续购已不再急切,仅以商量的语气奏称:“如有余力,亦宜添置。”[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83、83、158页。至光绪九年初,李鸿章借口“铁船来华,必有精利快船辅佐巡洋,或作先锋,或为后应”[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83、83、158页。,将购船的重点转移至巡洋舰方向。
结 论
从海防思想上来说,蚊船以近海口岸的防御为目标,突出守的功能;铁甲船以“大洋游击”为目标,突出战的功能。李鸿章作为传统文人,曾错误地认为蚊船可与铁甲船直接对敌,但他自同治十三年底开始,对两者主要的海防价值已有清醒认识。赫德、李凤苞等人对于李鸿章购置舰船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购船时机、质量选择,而非应否购置的判断。
李鸿章最初选择以口岸防御为目标的蚊船巨炮,主要是购船经费的制约。光绪元年之前,李鸿章“添置枪炮,不名一钱”,自愿推动清政府为北洋置办蚊船。之后,虽收用北洋海防专款,但数额有限,李鸿章在“能得若干款项,再办若干兵船”的方针下,只能购置价格相对低廉的蚊船巨炮。但这不代表李鸿章忽视铁甲船。事实上,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底就已确定2只铁甲船的建设目标,直至定远、镇远订造之后,才将购船重心转移至铁甲船舰队的辅佐舰船——巡洋舰方向。
李鸿章能从蚊船守口的近海防御体系,转向以铁甲船为中心的大洋海军建设,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摆脱了海防专款收数有限的制约,积极向上“议请”购船经费,并于光绪六年大获成功。这也是定远、镇远号铁甲船能够顺利订造的基础。然在晚清财政整体困窘的情况下,李鸿章的“议请”往往需要海疆危机的刺激,以及在此基础上清廷最高统治者的积极干预,这并非海军建设的正常轨迹。从这个角度来说,甲午战前10年中外交往相对和平安定,北洋海军尚需扩充而又未能及时扩充,也就成了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