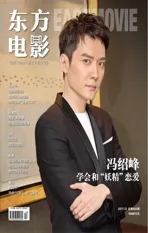鲁本·奥斯特伦德我是唯一说实话的人
2017-12-13甘琳尧黎
文/甘琳 尧黎
鲁本·奥斯特伦德我是唯一说实话的人
文/甘琳 尧黎
11月末,上海欧盟电影展放映的压轴之作是鲁本·奥斯特伦德的《广场》,开票之初就被销售一空,观众们都对这部出自金棕榈新人之手的作品充满期待。今年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带着自己的《广场》首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就意外爆冷获得了金棕榈大奖,在此之前,瑞典电影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了。在《广场》的场刊评分接近两极化的情况下,媒体都以为酷儿电影人阿莫多瓦带领的评审团会将最后的大奖颁给同样是酷儿电影的《每分钟120击》。但当颁奖嘉宾法国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深情朗诵了一首诗并宣布金棕榈属于瑞典电影《广场》时,戛纳电影节就向我们证明了奥斯特伦德的魅力—奥斯特伦德电影的政治性契合了当下艺术政治的潮流,就像是一个社会实验室,他的电影始终不变地在对中产阶级的社会族群进行犀利的讽刺和批判。
电影的社会实验室
2015年,奥斯特伦德曾经在YouTube上发布过一支名为《瑞典导演因错失奥斯卡提名而痛哭流涕》的反讽视频。2017年奥斯特伦德凭借《广场》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他在严肃的领奖台上一度蹦跳狂奔而放飞自我。“每个人都关心奖项,我是唯一一个说实话的人”,相比于萨特以“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戈达尔直接抨击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含金量,奥斯特伦德对奖项的着迷直接打破了艺术家与荣誉之间那层模糊暧昧的玻璃窗。反归到他自己的电影,也总是以客观甚至疯癫的荒谬和嘲讽之势揭露当下社会各种一点就破的窗户纸。
奥斯特伦德90年代以拍摄滑雪电影和纪录片发家,之后便在瑞典哥德堡进行电影方面的深造。在那里他遇到了对自己影响很大的罗伊·安德森,安德森向其推荐的《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和《偷自行车的人》成为影响奥斯特伦德创作生涯的重要作品。《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里对中产阶级无处不在的讽刺和挖苦,《偷自行车的人》里固定镜头的冷静客观都成为奥斯特伦德后来作品里两个重要的母题和元素。
奥斯特伦德的创作以《游客》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以固定机位长镜头为主,叙事松散,故事性不强,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采用多条线索平行叙事。无论是《吉他蒙古人》中互不相干的几组人物,还是《身不由己》里五个独立情境下的故事,这些电影都不具备传统电影的起承转合。另一方面,固定镜头虽然客观,但是却限制了观众从多方位去感受剧中人物的情感和行动,而奥斯特伦德表示,他之所以拒绝提供观众更多的角度去看,是因为不想让观众成为“被喂食者”。他强迫观众自行去思考影像呈现之物,一景一镜的场面调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片中人对环境刺激毫无中介的第一反应。

在奥斯特伦德的第二阶段创作中,叙事开始集中,围绕着一条主要的叙事线索开始展开,情节性加强。《游客》中剧作严谨,趋向常规叙事,在电影十分钟的时候,就发生了雪崩,夫妻关系埋下了最大的隐患,在接下来的四天里,冲突层层递进,结构十分工整。《广场》则围绕着本片的主角—博物馆策展人克里斯蒂安而展开,在电影开场便陷入困境之中:私人生活上因为丢手机和钱包而引来了一系列麻烦,工作上策划“广场”这一现代艺术装置又使其陷入了社会舆论危机。
戛纳荣誉之后,奥斯特伦德正在筹拍一部以时装行业为背景的暂定名为《悲伤三角》的作品。奥斯特伦德解释“三角区”是眼睛周围最容易堆积皱纹的地方,但是人们可以通过整形外科手术在50分钟内用肉毒杆菌给自己的“悲伤三角”去皱。电影的男主角是一个即将秃顶的男模,过去的他经常用自己的美貌去获取社会资源,如今美丽即将消逝,他必须采取各种“整形”措施去补救自己的身份,而其中一条办法就是和一个著名的女星相恋,为自己打造新的时尚圈烙印。
性和权力一直是奥斯特伦德电影中穿插的讨论元素。“我认为女性的性吸引力一定程度上与经济相关,而有些女性也在利用这点。我们对忠诚的看法始于人们拥有土地,因为这时人们才开始从父辈继承土地,也是从这时开始父辈对于女性性吸引力的控制变得非常重要,这样才能保证是他的后裔继承了他的财产。所以,女性的性吸引力开始与经济联系起来,才有了不同的地位。而有些女性便开始利用这一特点,有些男性也是,所以才会经常出现这样的设想。”《广场》里女记者和克里斯蒂安两性关系的逐力将在《悲伤三角》中被放大,所有个人层面的美貌和恋情因素都会被奥斯特伦德放置在权力和社会的考量中进行展现。
核心家庭的破裂
家庭作为社会单位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已久,现代社会的产生与中产阶级文化的兴起,往往会赋予家庭不同以往的象征意义。瑞典学者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曾综合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方法,专注于瑞典中产阶级兴起的历史阶段1880-1910年,其研究指出,家庭在中产阶级“美好生活”的神话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家庭开始从社会景观中脱颖而出,建立在一个三角基础之上—恩爱夫妻、慈爱父母、美好家屋。中产阶级将自身的文化强调为进步的、普世性的,企图通过本阶层的日常生活规范建构起一整套文化霸权,一旦违背了核心家庭的“和睦美景”就会被排除在社会主流进步的阶梯外。从小就父母离异的奥斯特伦德,显然已经被排除在了和睦核心家庭的框架之外,他甚至在《游客》的采访中笑称:自己最大的两个目标,一是制造电影史上最大的雪崩,另外就是提高离婚率。
奥斯特伦德获得2014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大奖提名的《游客》就是一部不紧不慢地撕裂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所谓美好表面的“反家庭电影”。衣冠楚楚的一家四口在电影开头其乐融融地围在五星级酒店的洗漱间,电动牙刷、统一的蓝色睡衣、明亮的镜面……一切有条不紊的存在都被一场不可抗的雪崩颠覆了。一家四口在餐厅突遇雪崩,丈夫托马斯在危险发生时却扔下妻子孩子一人逃跑,事后还懦弱虚伪地不肯承认。
《游客》的剧本创作来自于奥斯特伦德看到的两个婚姻调查研究:一项调查显示,经历过飞机劫持的夫妻在之后离婚的可能性更大;而另一调查则是关于海上灾难的幸存,从泰坦尼克号到爱沙尼亚号,某个年龄段的男人就是比女性更容易幸存下来。在奥斯特伦德看来,电影历史的主角或英雄总是男人,但当涉及现实和危机的情况下,死亡的又总是妇女和儿童,“当人们说我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时,我可以肯定地说,男人比女人更容易逃跑。”所以在奥斯特伦德的《游客》里,作为核心家庭一家之主的托马斯,在遇到危险的情况下选择了动物本能的逃跑,在危险过后又选择性遗忘自己的所作所为,否认自己逃跑。
奥斯特伦德并没有对托马斯给出直接的道德和情感批判,他用早期实验电影的客观视角创造了一种视觉受限的人物面向,镜头并没有多少主观记录托马斯和妻子情绪反应的部分,反而出现了许多游离于叙事之外的“旁观者”视点,使影片呈现出一种冷漠而疏离的气质。三次莫名在酒店走廊出现的酒店工作人员,他就像一个叙事的旁观者,也像一个怜悯的上帝,默默注视托马斯一家脱节事情的发展;在后半段出现的莫名其妙的男子狂欢聚会,也与托马斯一家内部暗流涌动的破碎感形成了鲜明反差。在音乐上,奥斯特伦德使用了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中的G小调第二协奏曲“夏”,原曲是表现夏天的疲乏和恼人,疲惫的夏与《游客》的冬形成了反讽式的并列。
奥斯特伦德并不想用当头棒喝式的道德批判粉碎这个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他没有让托马斯在家庭这个封闭的私人空间里进行自我救赎。他拉入了很多外力的观看和参与,让本来只想在私密家庭层面解决问题的托马斯被迫又要面对外在社会的审视。在一个快速变迁的世界里,个体需要寻找别的社会依托,而不是之前由自己邻居和所处集体为自身提供的社会位置,核心家庭的存在正好能够给个体一个休息的港湾。但是,一旦核心家庭出现裂痕,个人又不得不返回到社会进行可能“无解的解围”。托马斯在妻子面前否认自己雪崩时逃跑的行径,妻子被逼在朋友和丈夫面前赤裸裸播放丈夫逃跑的视频,“家丑不能外扬”变成了“家丑必须外扬”,封闭家庭的问题最后又回归到了公共空间。
《游客》的最后,托马斯和妻子又开始在大巴上重演雪崩的情景,只不过逃跑的人变成了妻子。不可抗灾难的发生和上次一样又是出现在公共空间,而且这次作出逃避行为的人变成了整车乘客。所有离开公共汽车的人都羞于夸大自己的情绪。但过了一会儿,当他们一起走在路上时,他们感觉到了一种联系,这就是个人和集体的联系—集体里的个人试图伪装自己,试着摆出一副害怕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样子。
我没有“杀死”我的人物
公共空间是奥斯特伦德电影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空间意象,在这里个体、家庭与集体总是不停碰撞出各种冲突。广场、商场、公交车、公园、旅游大巴等在他的电影中频繁出现,并且总是承担着叙事任务的重要载体。《吉特蒙古人》里患唐氏综合征的小孩在广场上弹吉他卖艺,多次与另一青年一起坐公交车;《游戏》中的黑人小孩对白人小孩的欺凌,发生在商场里,以及两组小孩漫无目的坐公交车在城市里游荡;获得第6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短片金熊奖的《银行事件》索性把所有的叙事都发生在银行前的广场内。

拍摄滑雪影片起家的奥斯特伦德,对当代科技全面入侵影像领域,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滑雪影片本身就是拜科技之赐的产物,摄影师必须一边滑雪一边拍,因此摄影机一定得超轻便)。因此,在奥斯特伦德的大部分电影中,在现代公共空间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媒介被赋予了独特的叙事功能,成了奥斯特伦德电影中叙事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身不由己》中两个女孩对着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调整姿势拍照;《游客》中记录下丈夫在雪崩时独自逃生的手机视频,在托马斯否认时成为重要证据;《广场》中的当代艺术装置、多次出现的“大猩猩”表演录像,以及使克里斯蒂安陷入危机的病毒营销视频等等媒介都成为影响电影叙事的重要环节。媒介之下,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某个群体或者是整个社会大环境下,甚至,媒介正发挥着对人类的异化作用,他的电影试图讽刺媒介如何影响我们当代的生活,争夺大众的注意力。

奥斯特伦德的父亲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长大,他小时候经常被父母送到市中心独自玩耍,只在脖子上挂了一个自家地址的标签。在父亲的讲述里,20世纪50年代斯德哥尔摩的成年人被看作是可以帮助孩子的有心人。但现如今,所有的成年人都被视作潜在的掠食者,他们会给孩子带来麻烦,会给社会制造困境。奥斯特伦德认为,这些本质上是一种态度的改变,社会并没有变得危险,社会同样安全,有时甚至更安全。态度的改变源于人们对于公共空间的怀疑,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横行的社会里,人们越来越无法负起自己的责任。社会契约该如何遵守,个人如何才能在困境中真正拔足而不深陷,成为奥斯特伦德获得201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广场》所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
《广场》中男主角克里斯蒂安策展的艺术装置“广场”主要用来探讨社会学中的“旁观者效应”,艺术家希望以此来检验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选择信任他人的观众可以将手机、钱包等物品放置在装置中并离开。作为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必须在怀疑徘徊的参观者面前带头打破“旁观效应”,但正是他给出的信任和善意,让自己的钱包和手机被偷。随后,围绕着这个博物馆内自造的社会契约而产生的麻烦和困境一直影响着克里斯蒂安:他与一位美国女记者在派对后发生一夜情,之后被女记者指责;它策展的装置艺术因为宣传团队的病毒营销视频而陷入危机,自己被迫辞职……
个人要承担社会责任,但是该怎么承担,承担后如何面对,都是“旁观者效应”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都关心我们生活在表面上的世界,但是一旦你越过了那个表面,我们都会被更多的自我导向的动机所支配。奥斯特伦德曾经拿瑞典人对待乞丐的看法概括了当下人们是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问题的:一方面人们在面对乞丐时会从自我个人的身份产生内疚感—帮还是不帮,但是个人永远也不能完全解决乞丐问题。另一方面,当我们在社会层面讨论乞丐问题时,比如提出向富人增税等解决办法,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而不是独自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该如何正确地把这么多的社区和社会问题带到个人层面。个人在承担压力的同时该如何面对那些尴尬困境的捆绑,成了奥斯特伦德电影一直关注的焦点。
奥斯特伦德的《游戏》曾经掀起轩然大波,很多观众都觉得刻意让黑人小孩主导的抢劫事件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种族偏见。面对质疑,奥斯特伦德用此片创作的缘由回应大家,影片原型出自奥斯特伦德一直关注的一个真实案例:在哥德堡的一个商城,一群小孩曾连续三年抢劫同龄男孩。在这个成年人为主的商场里,被抢小孩很少发出求助,成年人也很少阻止小孩们的抢劫行为。施害者作出侵略行为后,受害者和旁观者反常的“不反抗”行为才是奥斯特伦德真正寓意批判的。个人陷入困境,却因一些外在的政治、种族和社区原因而让事情的解决变得更加繁杂。电影里抢劫男孩被设置为移民黑人族裔,种族和年龄让这群小孩在社会中的身份变得愈加敏感,也更容易让电影的母题凸显出来。如果真正关注奥斯特伦德的电影,我们就能轻易发现,奥斯特伦德电影里人物的身份其实各有不同,并没有刻意针对哪个阶层,电影里的角色几乎囊括瑞典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长篇处女作《吉他蒙古人》中把脚踏车挂上路灯的狂野少年、患有強迫症的女人和在广场上卖唱的唐氏症少年都有着各自的尴尬困境;《身不由己》中不敢承认错误的女演员、坚持己见的司机、不肯就医的男子和揭发同事的女教师也都在做着一些为了面子而让自己置公共契约而不顾的事情。
最后,在经历了一系列困境之后,奥斯特伦德电影中的人物都留下了无法痊愈的伤痛,先不说是否修复了公共空间的共同契约,在个人方面,人们就已经回不到之前的生活了。《游客》的第五天的叙事时间里,丈夫救回了遇到危险的妻子,表面上挽回了丈夫作为男人和家长的形象,看似一切完美,但是在镜头的后半段妻子背对着丈夫孩子走向雪山,暗示着这场挽回家庭的“人造营救”最终还是失败了,妻子仍然无法原谅丈夫的所作所为,这个家庭再也回不到从前。奥斯特伦德曾在采访中笑称:“虽然我经常让我的人物遇到困境,但我从来没有杀死我的人物,我感到非常自豪。”死亡并不是结局的唯一评论标准,其实,在奥斯特伦德的电影里,每个人在最后都失去了他们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