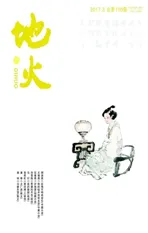现代世界的隐喻
——读第广龙诗歌《石油曰》
2017-11-25宋宁刚
■ 宋宁刚
现代世界的隐喻
——读第广龙诗歌《石油曰》
■ 宋宁刚
《石油曰》是第广龙的一首约百行的长诗,也是一首有经典气质的杰作。读这首诗,看到其中的诗句从“死”这个意象对现代世界的死与活、有与无、埋葬与出生……的深度辩证和书写,会让人想起T·S·艾略特,想起痖弦。在我看来,《石油曰》对现代世界的书写,和前述两位大诗人的经典之作,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特别是,诗人以“死”来切入对石油的书写,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以 “死”来命名石油,以带着浓烈腥味的、生与死的思辨书写石油,以切近的感受和在此基础上超拔之后的抽象观照石油,进而观照人世、地球、宇宙的生灭,与艾略特和痖弦对现代世界的命名——“荒原”“空心人”“深渊”,实在有着鲜明的可比性。在《石油曰》中,第广龙的笔触大开大阖,紧张凝练,如石油一般,仿佛是长久的埋藏和高度的凝缩才有的结果。如此书写,恐怕只有做了几十年石油工人的诗人,才写得出。
不过,也正因此,我们对它的要求似乎就更为严苛一些。尤其是在与前述两位诗人作品的比照中,我们看到 《石油曰》的缺点似乎也更多一些。如果能改掉这些缺点,它的整体品质也会大大地得到改善。——它们部分地是可以通过删削来达成的,正如经庞德删削和修改过的《荒原》。举庞德删改《荒原》的例子,当然并非是要大言不惭地自比庞德,而只是想说,以此方式让诗得到改观,是可能的。
说到删削,首先,我觉得这首诗每一节后面的 “附记”是可以删掉的。因为从诗本身来看,诗人的站位是很高的,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普遍性的角度来写这首诗的。但是“附记”却与此并不相应,它要么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回忆、记录 (比如“附记”一、二、七、九),要么表达的是个人的一点想法和感慨 (比如 “附记”三、四、五、六、八、十),即使个别“附记”的文字与诗的主体有一定的相应性 (比如 “附记”五和六),也还是不够致密和紧凑,有损这首诗的整体。
或许有人会质疑:诗的声音是普遍性的,“附记”的声音是个人性的,不正好形成对照和补充么?实际上,“附记”作为这首诗的一部分,难以起到补充的作用,而只会稀释整首诗的密度,破坏整首诗在语调上的一致性。如果说非要有这些文字,我宁愿它们以关于这首诗的 “创作谈”或“访谈录”的形式出现。
所以,下面的讨论中,我们略去这些 “附记”,只讨论这首诗的正文。
先看第一节:
如此之深的埋葬,也被挖开
如此之深的死,也会暴露
大地上,一口口井
喉管,食道,直抵地底
也许一千五百米,也许两千米三千米
抵达这埋葬之处
抵达这死
不是复仇,不是折腾也不是恶作剧
甚至没有和死
和埋葬联系在一起
人们寻找的,是
有用的物质,已经沉睡了亿万年
就像挖掘铜,挖掘石膏和稀土
人们用这样的器官
把石油抽取了出来
非常精彩的开场——“如此之深的埋葬,也被挖开/如此之深的死,也会暴露/大地上,一口口井/喉管,食道,直抵地底”,不仅充满气势,而且具有切实、丰富的内容,同时,又饱含思辨的张力。
这首诗好就好在,诗人从一开始就抓住了石油是生物的尸体、是被埋葬的东西、是如此之深和如此之久远的死,这样一组极为恰切,同时又具有震惊效果的意象。并且,作为全诗的线索、乃至灵魂,贯穿整首诗的始终。死本来是抽象的、看不见的,但是在生物尸体被深深埋葬亿万年之后被转化为石油这一点上,它显示出了自身具象的一面。因而让人觉得特别巧妙,特别具有说服力。
接下来的一行,“也许一千五百米,也许两千米三千米”其实可有可无。无论多少米,都是或然性的,可以更改。之前和之后的诗行则不同。它们都是必然性的:“一口口井/喉管,食道,直抵地底……/抵达这埋葬之处/抵达这死”。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就伸展开的张力感,以一种饱满、均衡的状态,一直持续着。
下面:“不是复仇,不是折腾也不是恶作剧/甚至没有和死/和埋葬联系在一起/人们寻找的,是/有用的物质”。
“不是复仇”,没有问题,后面的 “不是折腾也不是恶作剧”,从语势、语态上看,有油滑和 “串味”的嫌疑,从内容上看,也不完全能够经得起推敲。但是,如果直接删掉,前后读起来又不甚连贯,从语势上看,也有些促迫,与整体的气势不大一致。因此,我觉得最简捷可行的方式,是删去“不是折腾”几个字。
此外,这一节的内容,似乎也可以到此为止了。下面几行,无论“已经沉睡了亿万年”,还是“就像挖掘铜,挖掘石膏和稀土/人们用这样的器官/把石油抽取了出来”,都可以不要。前者,是常识,并且在后面的诗行中,会以更必要的方式再次出现。后者,其实在前面的诗句中也早已经蕴含了“石油被抽取出来”的意思。删掉这些可有可无的诗行,这一节诗不但没有损失什么,反倒显得更为紧凑。
下面看第二节:
石油,喷涌出来
气味浓烈
这是腥味,臭味
这是窒息造成的味道
随着灼热的雾气
持续向四周扩散
这是石油特有的味道
也是死的味道
这八行诗是非常出色的。第一节说,“大地上,一口口井/喉管,食道,直抵地底”,寻找“有用的东西”,这一节承接前一节,以“石油,喷涌出来”这样有力的诗句开头,气势丝毫不减。接下来的六行都在描述石油的“气味”“味道”。同样是描述,上一节的部分描述我们认为可以删掉,因为它使诗显得散漫,整个节奏也有些拖沓了。这里却不同,它的描述是有力的,六行诗保持了均衡的“浓烈”,并以最后一句更为“浓烈”的“也是死的味道”作结。这个结尾使这一节诗由实转虚,用“死”这个看不见却对石油来说极为具体和恰当的词提升了诗境,同时,又与上一节 “如此之深的死”构成了诗意上的接续与呼应。
第三节:
大地上,运尸的队列
就是死的动力,在驱使
使车轮滚动,加速
道路,也是这死身铺就
多么平坦和耐压
进入城市,进入加油站
天上地下,都在消费这死
这死换了名字,叫燃料
第一节写石油被从深深的埋葬中挖开、暴露出来,第二节写石油喷涌而出,第三节写石油的运送。不过,诗人却没有用“运送石油”这样普通的字眼,而是代之以“运尸的队列”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诗句。这么写,并不是诗人想要刻意地哗众取宠,而是他从一开始就洞悉了石油与死之间高度亲密和本质性的关系,并且在每一节的诗中贯穿这种本质性的书写。因此,读来就会让人觉得格外醒目,甚至刺激。
如果说 “运尸的队列”本身带来的只是醒目和刺激,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诗句——“死的动力,在驱使”中看到的,就是悖论、反讽和辩证。死,本来意味着丧失生命、僵直、不再有动力,可是,面对石油——死的结晶物、甚至就是死本身,我们看到的却是,它成了动力,“在驱使”。不仅如此,它不光是在一般性的驱使,即驱使其他车辆,“使车轮滚动,加速”,还在驱使着运送它自身的车辆,也就是说,通过“死的动力”,它在运送自身。不仅如此,连汽车行驶在其上的“道路”,“也是这死身”铺就。也就是,死不仅运送自身,还为自己铺设运送的道路。顺着这个思路展开来想的话,包括油井的架设、勘探、钻井、采油……几乎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以石油为动力,也就是说,石油作为一种死(的产物),既使自身的再见天日,也即,使自己的重生 (重新发挥作用),也使自己再次死亡(被消耗),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在任何一个环节上,都是自己为自己送葬。这就太有意思了!
第五行,“多么平坦和耐压”——这种散文式的对于道路的描述,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其实也可以删去。因为这样的修饰显得有些松散了,于诗歌整体的紧致、密集的气氛稍稍有伤。
最后三行:“运尸的队列”——“进入城市,进入加油站/天上地下,都在消费这死/这死换了名字,叫燃料”,尤其 “天上地下,都在消费这死”一句,显得分外刺眼。“天上地下”,当然是包括天上飞的飞机,地上跑的汽车。我自己以前不曾留意过,看过柴静的《穹顶之上》,才知道我们坐的飞机,“一起飞,一吨汽油没了,一落地,一吨汽油没了”。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飞机有多少?得多少吨汽油?每天奔跑在城市里的又有多少汽车?得多少吨汽油?这都是消耗啊。如诗人所说,“都在消费这死”。只不过“这死换了名字,叫燃料”。
第四节:
死也是一次性的
死也会用完
亿万年前的死
被一次性使用
因为没有第二次
没有第二次的生成
不会再有汽油,柴油
不会再有沥青和甲醇
一次性使用了
也就一次性消失了
这同样是死的宿命
哪怕死在亿万年前
这是在前一节 “运送”的基础上,写石油的使用。与之前一样,这一节诗以 “死”作为“石油”的替代,从二者间共同的 “一次性”这个特点展开诗的叙述。“死也是一次性的/死也会用完”——称“死”是“一次性的”、“也会用完”,既符合“死”的本性,也有触目惊心的效果。“亿万年前的死/被一次性使用”——将“亿万年”与“一次性”对置,两者之间鲜明的比照性和张力效果呼之欲出。接下来的 “因为没有第二次”,作为一个解释性表述,本来是散文式的,效果并不突出,甚至算不上积极。但是,它与接下来的第六行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没有第二次/没有第二次的生成”,这样一来,它就成了第六行在语势上的铺垫。作为第六行的“垫脚石”,它的效果却是积极的。“没有第二次生成”,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它与整首诗既具象又抽象的总体表述相一致。
接下来的七、八两行——“不会再有汽油,柴油/不会再有沥青和甲醇”,是对第六行的解释、展开和具体化。从第九行到第十二行——“一次性使用了/也就一次性消失了/这同样是死的宿命/哪怕死在亿万年前”,则是升跃和超拔式的总结。它突出的是“一次性”、不可重复、不可再生等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具有警示效果的特点。其落脚点,则是“死”这个“宿命”性的、即不可抗拒的规律性的特点。“哪怕死在亿万年前”——这一句细究起来,似乎有点“绕”,因为“死在亿万年前”的是生物,它们在亿万年前死后的生成物,才是现在的石油。所以,严格来说,并非亿万年前生物的死,而是作为死后之生成物的石油的死——消耗,才是这里的主语,也即这里叙述的主体。当然,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这一次性的死。虽然这个“死在亿万年前”的“死”与“死的宿命”的“死”,并非同一个东西,但是“死”本身是一样的。诗人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一样的“死”,意在突出“一次性”和“亿万年”之间的比照。
第五节:
如果相信物质不灭
那么,这么多的死
在第二次死之后
是否在另一个空间
又聚集在一起
还是原来的形态,原来的死?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条件下,在什么样的场合
才能重现,还携带着自身的能量?
上一节写到死——石油“被一次性使用”之后,就一次性地“消失”和“死”去了,这一节,紧承前面的内容,转入诗人的另一重思考和问寻:“如果相信物质不灭”,就不会有什么白白地死去而不留下什么痕迹——“那么,这么多的死/在第二次死之后/是否在另一个空间/又聚集在一起/还是原来的形态,原来的死?”
“这么多死”中的 “死”应当指石油,这么多的石油;“第二次死”应当指石油的被消耗、在消耗中散尽。诗人问,“在第二次死之后”,也即在石油被消耗掉之后,“是否在另一个空间下/又聚集在一起”,并且,还是“原来的形态,原来的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条件下,在什么样的场合/才能重现,还携带着自身的能量?”
我们当然知道,石油被消耗之后,一部分转化为动能,一部分以尾气的形式被排放。它们不会在另一个空间下,“又聚集在一起”,更不会以 “原来的形态”聚集。因此,诗人后面的 “天问”,只会落空。
这个落空了的疑问并不是无意义的。它调整了整首诗的叙述节奏。前面四节诗,从石油的开采,到石油的气味,再到石油的运送和消耗,讲的是石油从发掘到消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后,转入向内的思索与问询,无论从诗思,还是从情理上看,都是再自然不过的。读到这里,我们或许会好奇,甚至猜测,接下来诗人会写什么呢?
请看第六节:
石油里有多少死
多少死,曾经的肉体,灵魂
死了,甚至已成为死本身
遍布大地的生命
以一个纪元的生命
一起死,在同一时刻
那是近乎一个星球的死
星球崩塌,沸腾
这宇宙的悬浮物
表面的热度
呼应内里的热度
所有生命,都被挤压了一次
已死的,再死一次
和活着的,一起死
一起叠加,交织
压在石头下面,岩层下面
那个时候的时间,太阳
都归于地下
以为从此与地上失去联系
以为从此永远安宁
第一行要和第二行的前半句连起来看:“石油里有多少死/多少死”。第二行的 “多少死”,是通过重复增加感慨、慨叹的氛围和语气。它与上一节的思考和问询的语气是一致和贯通的。接下来,“曾经的肉体,灵魂/死了,甚至已成为死本身”——这样的诗句是很“狠”的。曾经的死亡那么长久,那么深远,不仅肉体死了,连灵魂也死了——“灵魂死了”当然是个形象的说法,意在强调死的深沉。不仅肉体和灵魂死了,“甚至已成为死本身”——肉体和灵魂的死如何成为 “死本身”?甚至,何谓“死本身”?一如前面所说,“死”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死本身”,更是抽象的,看不到摸不着的。肉体和灵魂之死“甚至已成为死本身”,这样的诗句虽然细想起来有点困难,但是它所传达的对“死”的某种带有形而上意味的表达及其力道,我们却是能够感受到的。
“遍布大地的生命/以一个纪元的生命/一起死,在同一时刻”——这是在讲石油的 “前史”,即石油形成之前亿万年所发生的事情:受突发的地质运动影响,成片的、可能生长了几百年的森林被埋在地底——“一起死,在同一时刻”。诗中的表述所突出的还是“死”的过程,“死”的陡然出现,以及瞬间对广大生命体的改变。诗中说,“那是近乎一个星球的死/星球崩塌,沸腾/这宇宙的悬浮物/表面的热度/呼应内里的热度/所有生命,都被挤压了一次”。这个描述也可以,但是并非对形成石油的“遍布大地的生命”“一起死”本身的描述,而是对“星球坍塌”的描述,以后者的变化之剧烈作为参照,烘托和引导我们想象“遍布大地的生命”“一起死”的场面。在我看来,这个描述本身也是可以删去的。这是因为,第一,如前所说,它不是对形成石油的“遍布大地的生命”“一起死”本身的描述,而是对他物的描述,期望通过对这个他物的描述来引导读者想象“遍布大地的生命”“一起死”的情形。这个“弯”绕得似乎有些远。第二,对于“星球的崩塌”,除了从影视节目中看到,其实我们也没有切身的经历,因而它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抽象的,不见得会有多少效果。第三,这一节以石油为主题的总共二十行的诗中,用六行的篇幅来写 “星球的崩塌”,不仅有喧宾夺主之嫌,而且对主题造成了巨大的离心力。因此,我觉得可以将这里 “星球的死”以下的五行都删掉,只保留作为总结的最后一行——“所有生命,都被挤压了一次”,因为它对于描写石油形成之前“遍布大地的生命”“一起死”,也是适用的。
再往下看:“所有生命,都被挤压了一次/已死的,再死一次/和活着的,一起死/一起叠加,交织/压在石头下面,岩层下面”——这里写得也是很“狠”的,尤其“已死的,再死一次/和活着的,一起死”。如此表述及其句式,仿佛把那种不由分说、不分青红皂白的,带着荒蛮之力、发乎于瞬间的剧烈的“死”的过程,推到我们面前,那种汹涌的气势,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感。
最后四行,其实也可以删掉。因为它更多是感慨,而不是外在描述。如果这一节将这四行删掉,而从 “所有的生命”“压在石头下面,岩层下面”这个有力的句子作为结束,仿佛电影镜头,一次埋葬式的剧烈坍塌、掩埋,镜头最终显示出一片死寂的黑,即使不算更好,也是相当不错的。
第七节:
失去空间,空气
失去呼吸
多少死,多少毁灭
要多深的深埋
要多久远的时光
才有如今这死的形态
并呈现出来
在第六节中,诗人以想象重构了石油产生之前的亿万年前,“遍布大地的生命”“一起死”,“所有生命,都被挤压了一次”,最终被压在“岩层下面”。第七节,接着第六节的话题,叙写被压在岩层下面的生命,“失去空间,空气/失去呼吸”。诗人自问——同时也感慨:在这挤压和掩埋中,有“多少死,多少毁灭”!
接下来,同样像是在问询和感慨:“要多深的深埋/要多久远的时光/才有如今这死的形态/并呈现出来”。这同时也是诗人对生命被深埋之后最终变为石油这一事实,感到惊奇甚至觉得不可思议。的确,这个过程是常情难以揣测和想象的。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这一节的最后一行,似乎也可删掉。因为倒数第二行中的 “死的形态”已经包含了从久远的生命最终转化为石油这一事实。这“死的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呈现。当然,这里的“呈现”,也可以指石油被开采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最后一行就应当保留。
下面看第八节:
多少黑暗的集合
才有如此的黑
多少黑暗的分解
才有如此的液体
如此的黏稠
多少死已不辨面目
形状,轮廓,和性别
和族类,和进化
和基因突变
多少死忘却了死
多少死才有如此的黑
如此黑的液体
成为石头的一部分
又区别于石头
成为地狱的一部分
又区别于地狱
沉默,成为分子结构
成为可降解物
和不可降解物,只是沉默
不存在一样,有如同没有一样
成为这么多的死
这么多的黑
是肉体,还是灵魂
已无从辨认,无从分离
这又是极为出色的一节。在总共二十四行的这一节诗中,前面十一行是五个以 “多少”打头的形式松散的排比句:
多少黑暗的集合/才有如此的黑
多少黑暗的分解/才有如此的液体/如此的黏稠
多少死已不辨面目/形状,轮廓,和性别/和族类,和进化/和基因突变
多少死忘却了死
多少死才有如此的黑/如此黑的液体
这些诗句,不仅在形式上显得有气势,在内容上也是如此,意象迭出,对比不断,带给人强烈的冲击。其中,前两个排比句中“黑暗的集合”与“黑暗的分解”之间的张力就是如此。“多少死已不辨面目”,也是如此。而像“多少死忘却了死”这样自我指涉的诗句,跟第六节中“曾经的肉体,灵魂/死了,甚至已成为死本身”一样,不仅读起来因为其“狠”而觉得过瘾,仔细思之,更会觉得其中意味无穷。死得那么深、那么久远,竟忘却了死——这是怎样一种情形的死呢?也是超乎我们想象,而又吸引人去深思的。
第十一行,“多少死才有如此的黑”,与第一、第二行 “多少黑暗的集合/才有如此的黑”在形式上是重复的,但是其内在意蕴,却大大地提升了。“黑暗的集合”变成了 “死”,用词更为决绝,更为刺目,更有具体和抽象——这听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实际的情形却正是这样既矛盾又谐和一致。
接下来的第十二行——“如此黑的液体”,应该和前一行结合起来看呢,还是应该与下面结合起来看?似乎都可以。如果与前一行结合起来看,“多少死才有如此的黑/如此黑的液体”,那就是对前一行的具体化:将之前的“黑”具体化为“黑的液体”。但是这样读起来,在语气上似乎稍有不顺。另外,与这一节前两行的呼应性也就有所减弱。更突出的问题是,虽然“如此的黑”没有 “如此黑的液体”这么具体,但实际上这里可以不必这么具体。在诗中,相比“如此黑的液体”,“如此的黑”因为其抽象性、概括性和留给人的巨大的思考空间,而更为有力。
如果将第十二行与下面的诗行联系起来看,“如此黑的液体/成为石头的一部分/又区别于石头”,“成为地狱的一部分/又区别于地狱”。在句式上,它就更像是接下来的四行(第十三至第十六行)——它们也是两个排比句——的主语。这两个排比句也是充满辩证色彩,意味无穷的。“如此黑的液体/成为石头的一部分/又区别于石头”——很明显,“如此黑的液体”是指石油,石油是石头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叫“石—油”?如果是,为什么又是液体?是“油”?石油深埋在地下,仿佛地狱的一部分,然而又不是地狱本身。这种是又不是,带着相似又存着差异的关系,是意味深长的。诗人之能写下这些微妙的诗句,不能不说他的思考和感受之深妙。
接下来,又楔入石油的另一特点——“沉默”:
沉默,成为分子结构/成为可降解物/和不可降解物,只是沉默/不存在一样,有如同没有一样/成为这么多的死/这么多的黑
从石油的“如同没有”的“沉默”,又回到这首诗的主线索,即之前一直写到的“死”与“黑”。最后两行:“是肉体,还是灵魂/已无从辨认,无从分离”算是余音。不过,这个余音,也不是随便凑行的,它仍然是意味深长的:这么多的黑,已经无从区分“肉体”与“灵魂”,换言之,“肉体”与 “灵魂”已经合一,灵魂即肉体,肉体即灵魂,“无从分离”,无从区分。
到这一节为止,这首诗实际上已经升跃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越是在一个制高点上,就越难写。想要接着这个高度写下去,相当困难。这首诗的问题就在这里。后面的九、十两节,在我看来——说严重一点,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它缺少了之前深刻的洞察、思辨,以及有着坚实内核的东西,变成了缺乏实在内容、有些流于散文化的慨叹的稀松的表达,尤其第九节的 “这的确不可思议”、第十节的假设,都是如此。如果说还有什么有价值的内容,那就是第九节的最后几行,地球让生命繁衍,“也让死,以石油……保存了下来”,以及第十节的 “如果经历一次大毁灭”能否把死再转换成石油这个想象式的疑问。因此,最后两节要么需要进行大幅修改,要么可以径直删去。作为读者,我们无从大改,那么就当是删掉了,看到这里为止吧。
现在,回过头来整体地看一下这首诗。它的一至四节,写了石油被挖掘、开采、运送、消费的过程。这也是现在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过程。从第五节,诗人转入自我的思索与问寻。在这思索与问寻中,他又试图通过想象来再现石油的 “前史”,也即通过诗句勾勒亿万年前的生物被压在岩层下面,经过难以想象的岁月和深埋,最终呈现为现在的样子(第六、七两节)。在此基础上,对石油——“黑暗的集合”,进行了聚焦式的观照和书写。正如我们看到的,这首诗可以分为前四节和后四节为单位,分成两个部分。它们总体上是对应、对称和均衡的,但是从叙述的顺序上,(后四节)又是倒叙的。
最后,说一下这首诗的题目。《石油曰》这个题目似乎并不那么恰当。因为在诗中,石油本身并没有说什么,而是有外在于石油的一个类似站在普遍意义上的第三者的声音在说。所以,严格来说,谈不上 “石油曰”。从文题一致的角度看,题为“石油”,也会比 “石油曰”更恰当一些。当然,这个题目本身并不好。起标题是一个堂奥很深的艺术,不能随便将就。
不过,这里虽然说了许多问题,但是,正如我们一开始就说过的,第广龙的 《石油曰》是具有经典气质的诗 (之所以说 “经典气质”,而不是 “经典”本身,正是因为这首诗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也是浓缩了第广龙多年生活经验与思索的生命之诗。它有成为经典的质素,也起到了为作者代言和创造意象的作用。张清华教授曾说,郑小琼的诗通过对“铁”的书写,为这个时代提供了最具隐喻的扩张性意义的意象,为我们这个冷硬的工业时代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关键词 (参见 《郑小琼诗选》,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封底),我们也可以说,第广龙的诗,通过对石油与死的辩证书写,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极其重要的意象,甚至比“铁”的意象要更为本质,更为深刻。它不仅是关乎个人、社会、生活和命运的,更有超越于命运之上的极度书写。
作为一个石油工人,第广龙在这首关于石油的诗中,没有对石油大唱赞歌,而是在多年感受和思索的基础上,抓住石油的“黑”与“死”这两个本质性的特征,既是书写了石油,也观照了我们建立在石油的消耗之上的现代社会,包括对它建基于 “死”、会不会归于“死”的隐忧。这是诗人的洞见,也是诗人的道德和良心。
附:
石油曰
一
如此之深的埋葬,也被挖开
如此之深的死,也会暴露
大地上,一口口井
喉管,食道,直抵地底
也许一千五百米,也许两千米三千米
抵达这埋葬之处
抵达这死
不是复仇,不是折腾也不是恶作剧
甚至没有和死
和埋葬联系在一起
人们寻找的,是
有用的物质,已经沉睡了亿万年
就像挖掘铜,挖掘石膏和稀土
人们用这样的器官
把石油抽取了出来
附记:我1981年来到一个油田,穿上油工衣,坐大卡车在山路行进三个钟头,到达一个山坳里的井场,油井编号,井号是里10排五井。那是一个冬夜,我们在山里搬动油管,是要下入油井里的。那天奇冷,18岁的我,汗水湿透了油工服。
二
石油,喷涌出来
气味浓烈
这是腥味,臭味
这是窒息造成的味道
随着灼热的雾气
持续向四周扩散
这是石油特有的味道
也是死的味道
附记:我第一次闻到石油的味道,差点呕吐。小时候,我爱闻汽油的味道,曾经追逐汽车,就是为了闻一口尾气。可是,石油的味道,我接受不了。后来,慢慢地,我也习惯了。站井口操作时,石油喷涌,浇淋到我的头上,钻进了裤裆里。粘,清洗难,用汽油洗衣服才能洗净。
三
大地上,运尸的队列
就是死的动力,在驱使
使车轮滚动,加速
道路,也是这死身铺就
多么平坦和耐压
进入城市,进入加油站
天上地下,都在消费这死
这死换了名字,叫燃料
附记:人类社会发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如今,所有成果,还是离不开远古的积存。石油更是早于创世的物质,原来被埋葬,现在被火葬。
四
死也是一次性的
死也会用完
亿万年前的死
被一次性使用
因为没有第二次
没有第二次的生成
不会再有汽油,柴油
不会再有沥青和甲醇
一次性使用了
也就一次性消失了
这同样是死的宿命
哪怕死在亿万年前
附记:石油总有用完的一天。据说,永远也用不完。理由是当石油稀缺,价格上涨,人们用不起时,就会寻找替代能源。这样,石油总是保持相应的存量。
五
如果相信物质不灭
那么,这么多的死
在第二次死之后
是否在另一个空间
又聚集在一起
还是原来的形态,原来的死?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条件下,在什么样的场合
才能重现,还携带着自身的能量?
附记:能量可以转换,我深信不疑。石油被燃烧了,石油就彻底消失了吗?要是能找出来,再一次使用,石油就无穷无尽。不过,这可能吗?
六
石油里有多少死
多少死,曾经的肉体,灵魂
死了,甚至已成为死本身
遍布大地的生命
以一个纪元的生命
一起死,在同一时刻
那是近乎一个星球的死
星球崩塌,沸腾
这宇宙的悬浮物
表面的热度
呼应内里的热度
所有生命,都被挤压了一次
已死的,再死一次
和活着的,一起死
一起叠加,交织
压在石头下面,岩层下面
那个时候的时间,太阳
都归于地下
以为从此与地上失去联系
以为从此永远安宁
附记:过去,我没有把石油和死亡联系起来。不然,我会惧怕。现在,我联系起来了,却没有惧怕。石油是死去的生物转化成的。可是,没有谁见到过这些生物,他们的死,牵动不了现在的人的神经。谁会为亿万年前的生命的逝去忧伤呢?那么遥远,调动我所有的想象,我也无从抵达。
七
失去空间,空气
失去呼吸
多少死,多少毁灭
要多深的深埋
要多久远的时光
才有如今这死的形态
并呈现出来
附记:我在野外队工作了六个年头,成天和石油打交道。我的身上脸上,总是糊满石油。刚从油井里出来的石油,会冒泡,一个一个焦黄色的泡,青蛙那么大,一会儿又破碎了。我在油泡上看到的,是我的黑乎乎的脸。
八
多少黑暗的集合
才有如此的黑
多少黑暗的分解
才有如此的液体
如此的黏稠
多少死已不辨面目
形状,轮廓,和性别
和族类,和进化
和基因突变
多少死忘却了死
多少死才有如此的黑
如此黑的液体
成为石头的一部分
又区别于石头
成为地狱的一部分
又区别于地狱
沉默,成为分子结构
成为可降解物
和不可降解物,只是沉默
不存在一样,有如同没有一样
成为这么多的死
这么多的黑
是肉体,还是灵魂
已无从辨认,无从分离
附记:生命短暂,一辈子一阵风就过去了。人过留名,人忙着行动,书写。所谓的文明,也一代一代传承,而有了厚度。可是,人是脆弱的,地球震颤几下,什么都消失了。生命本身,也成了一种液体。石油如果能还原,也许会还原出当时的文化。
九
亿万年前的生命
成为石油,而不是别的
一万年前的生命
还能燃烧,还能成为火
这的确不可思议
地球让生命如花
让繁衍鲜活
也让死,以石油这种形式
保存了下来
附记:石油不经提炼,点燃后火力更强劲。我在野外队时,井口有落地油,当地农民铲回去,做饭耐烧。一马勺,可以烧开一大锅水。一次失火,烧毁了井架、通井机,井场上六个人,全被烧成焦蛋蛋。
十
如今的生命
如果经历一次大毁灭
是完全消失,还是有可能
也把死转换
也变成石油这样的物质
如果能够
那就要掠过棺木,坟墓,宗祠
掠过人伦,道德,文化
掠过典籍和所有传承
在一次巨变中
失去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物质
只变成一种流体
如今的生命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幸运?
附记:即使原始社会的墓葬被发现,也只是看到骨头的残片。生命被毁灭,要变成石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变成石油,也得具备诸多条件,也得靠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