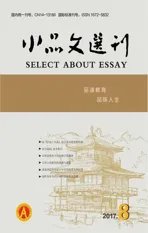论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生态小说《沙狐》的思想内涵
2017-11-25潘多
潘 多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00)
论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生态小说《沙狐》的思想内涵
潘 多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00)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我们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郭雪波生态小说《沙狐》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老人与沙狐默契互惠、和谐相处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反思,对沙漠中顽强不息的生命的赞美。本文通过维护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意识;尊重生命、平等共存的生命意识;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生存意识三个方面分析《沙狐》的思想内涵。
郭雪波;生态小说;《沙狐》
生态文学是从生态整体思想出发,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目标的来考察自然,或表现自然与人类关系,或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等问题的文学作品。
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人类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疯狂地开采矿产,毁坏森林,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与破坏。这些行为不仅打破了自然平衡,而且还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于紧张的对抗之中,面对这样的现实,人类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在中国生态文学领域独树一帜,被誉为“大漠之子”“沙漠文学”写手。他的创作多数以他的家乡科尔沁为背景,科尔沁草原的沙化、荒漠化已经无法挽回,人与自然紧张的关系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存。所以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着半农半牧沙化草原的蒙古族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环境,表达出人们面对现代文明的结果所显示出来的生存焦虑。主要作品有《大漠狼孩》、《沙狐》、《沙狼》、《大漠魂》、《青旗一嘎达梅林》、《大萨满之金羊车》等,作品曾多次获奖,并被译介到海外。
其中《沙狐》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国际优秀小说选》,是郭雪波生态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中篇小说《沙狐》主要讲述了坚守沙坨的农民老沙头,与一只沙狐默契互惠、和谐相处的故事。故事采用平铺直叙的写作手法,用质朴的语言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凄婉悲壮、荡气回肠的故事。
小说的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但是所表达的思想内涵发人深省,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人们肆意的攫取分不开,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和谐共处的,只有整个生态系统共生、共享、互惠、和谐相处,人类才有更长远、可持续的发展。
1 维护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意识
美国思想家利奥波德在写于1947年的《沙乡年鉴》中提出“大地伦理”观念,认为无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自然界中所有存在物都有其存在的权利,人类只是大地共体的普通一员。利奥波德的“大地”概念,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在他看来,大地是一个共同体,人和各种生物、自然物,同为这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的成员,所有生命物种,没有谁能单独生存。在生态学的视野中,自然界没有尊卑等级的差别,人和大地是伙伴关系,人类不该也不能成为大地的主宰者。“大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小说《沙狐》的生态思想和这一观念不谋而合。
造成草原沙化、动物数量锐减等生态问题的原因之一是人类把草原、动物等看作满足人类利益的工具、资源,这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生态领域的体现。郭雪波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同时,传达出构建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重要性。
作者站在生态立场叙述故事,批判以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立场就是站在生物圈中各物种的共同立场,即以生态中心观念代替人类中心。生态观念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即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以及各物种之间的平衡、稳定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代替以人类或生物圈中任何一个局部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人类、动物和植物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草原生态系统,它们之间是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如果人类不顾其他生物的利益,仅凭一己私欲为所欲为,这个原本完整、平衡的草原生态系统就会崩溃。
小说开头交代由于人们胡乱翻耕草地,外加自然风化,科尔沁草原变成了现在寸草不生的荒漠。人类的乱砍乱伐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是致命的,地球几千年形成的良好的生态系统,人类为了眼前的利益,几百年就消耗殆尽。不仅利益没有实现,生存都出现问题。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利己主义的结果。
作为生态正面人物的代表,《沙狐》主人公老沙头坚守在沙漠中,在沙洼地里插柳条、种沙打旺,坨坡上撒骆驼草籽、沙蒿粒,治沙封沙。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沙漠边缘的沙坨里才慢慢变得有了生机。跳兔,野鸡等顽强生存的小生命开始在沙坨里安家。
生物圈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所有的生命物种,没有谁能单独存在,只有通过自然进化过程中的分工合作,才能维护共同体的存在。生物圈中的每一个成员相互依赖,在承担着维护和谐共存的前提下,才能有自身的存在。
《沙狐》中老沙头在女儿沙柳幼年时就教育她沙漠中一草一虫都要放生,因为即使它们看起来很渺小,但是在这个生物稀缺之地却是无比珍贵的,沙漠中的任何生命都是相互依靠,紧密相连的。老沙头深深地懂得生态整体平衡、稳定的重要性。已经不仅仅是个生态实践者,而且也是生态的思想者,真正做到了与草原万物荣辱与共、生死相依。
一年沙坨子里闹鼠灾。坨子上到处是鼠洞,成群的野鼠在脚边乱窜,坨子上的好不容易培植起来的植物,都被这些可恶的泛滥的精灵啃了根,一片片地枯黄,死掉。野鼠成了沙漠的帮凶。沙狐的出现极大的减少了野鼠数量,一只沙狐一年能逮三千只野鼠,可以说是沙漠植物的小卫士。
老沙头与沙狐在这荒漠深处一起生活,之间有了一种默契,谁也不伤害谁,相安无事,在漫长的孤寂中成了互相的慰藉。
2 尊重生命、平等共存的生命意识
“大地伦理”观念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从生态层面上那个来说,人与自然中的每一个个体一样,都是生命环链关系网中的一个点,每一个个体都在各自的生物链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各种个体可以根据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享受自然的恩赐,都有在生命环链中生存、繁衍的权利。尊重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是生态意义上“平等”的精髓。
在小说《沙狐》中,老沙头从不伤害沙坨中的小动物,对一草一木都视如珍宝。沙坨中的生命与老沙头在相互依存的前提下和谐共处,尤其是老沙头与沙狐的情谊,深沉又默契。他们共同守护着沙坨脆弱的生态环境。沙狐受伤,老沙头给它在沙坨中搭窝,沙狐捕捉野鼠,维护生态平衡。老沙头一直将沙狐视为知己朋友,心系沙狐。
而反面人物大胡子领导和小秘书,为了游玩打猎来到沙坨子,骑马扛枪耀武扬威,对于沙坨子中的小动物来说是巨大的灾难。山鸡野兔无一幸免的倒在大胡子的枪口下,就连沙狐也没能幸免。他们追着沙狐进入荒无人烟,有去无回的死漠,即使是他们迷失在其中,也是因果报应。然而心地善良的老沙头还是义无反顾的去营救了大胡子主任和小秘书。在找到大胡子主任和小秘书后,他担心沙狐喝不到水,独自去寻找沙狐送水。体现了众生平等的生态理念,在沙漠中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一样高贵,生存不仅仅是人类的权利,也是沙漠中一切生灵的权利。但是就在挽救了大胡子主任后,他们还是向沙狐举起了猎枪,沙狐应声倒在了血泊中。沙漠植物的卫士就这样被射杀了,它身下护着的是三只幼小的沙狐。这是一个悲壮的结局,可能通过悲剧来展现生态整体主义所付出的代价和不可挽回的结局往往更能引起人们对生态的反思。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常常是无节制的,这种不断的索取必然引起生态系统的失衡,也会造成道德的失序,人类必须在敬畏自然和敬畏生命中不断完善自我。
大胡子主任只看到了沙狐美丽的皮毛,却看不到沙狐在生态平衡中的重要作用,没有了沙狐,就意味着野鼠的猖獗,土地沙漠化的加剧。人们总是会被眼前的利益和贪欲蒙蔽双眼,忽略了长远的、根本的生存法则。从猎杀沙狐的事情,以小见大,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为了财富利益,过度采掘开发资源,牺牲了生态环境,现在又投入百倍精力,却也换不回从前的蓝天白云,绿草如茵。
3 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生存意识
郭雪波在作品中还表达了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思想。《沙狐》中的老沙头,本来生活在沙沱子里的某个村子,在他很小的时候,土匪抢劫了他的家,把他的父母都杀死了,后来为了报仇,他当过土匪还蹲过监狱,成为被遣散到科尔沁沙地的“流放犯”。当沙沱子即将被沙漠掩埋,人们都要撤离的时候,他却主动要求留下来照看这里仅存下来的锦鸡儿、山榆丛和沙柳条子。小说谈道“也许是前半生太奔波,这儿的安宁吸引了他吧,他居然很喜欢这里”。在这里他不仅治沙封沙,而且还主动保护沙漠里的生灵。尽管后来场部想将年过半百的老沙头调回,他坚决反对,毅然留在了沙沱子里。他的女儿沙柳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好奇,向往能走出沙漠,到外面的世界生活。但是当她目睹了沙狐被猎杀,感受到了外面世界人类的残忍,心甘情愿地和父亲一起回到了沙沱子中生活。沙柳和老沙头纯朴的心灵,只有在沙漠中,才能感受到温暖和安宁,沙漠成为他们疗伤的心灵家园。虽然生活艰辛寂寞,但是沙坨里的世界纯净简单。
郭雪波的小说以生态性著称,其思想内涵多是呼吁人们关注生态问题,尊重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他的是人生经历和忧患意识分不开,生长环境对于郭雪波影响巨大。郭雪波在《哭泣的草原》中写道:“我生长在科尔沁沙地西南部库伦旗沙坨子。《蒙古游牧记》里记载这里曾是满族入关前努尔哈赤的狩猎场,有一望无际的草场和山岭。四十多年来,我是一年一年地目睹了这块绿草地是如何变成黄沙地。”由于亲眼目睹草原沙化的过程,痛惜美丽草原的逝去,感慨沙漠带给人们的灾难与贫苦,郭雪波着力于挖掘造成草原沙化的深层原因。
郭雪波在以文学的形式反映生态问题。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对神秘的大自然充满敬畏与依赖,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工业社会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通过征服和掠夺自然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物欲与奢侈安逸的生活,从而导致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们应该认真反思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尊重自然,与万物共生共享,和谐发展。
[1] 郭雪波.天出血·沙狐[M].南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2] 郭雪波.哭泣的草原[J],森林与人类,2002
[3] 郭雪波.草原的呼号[J],北京观察,2001
[4]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汪树东.看护大地:生态意识与郭雪波小说[J].北方沦从,2006
[6] 李玫.郭雪波小说中的生态意识[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5
潘多,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I206
A
1672-5832(2017)08-004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