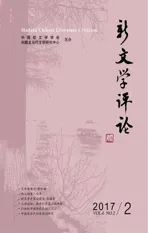上升期里的四组趋势性概念
———新世纪诗歌印象
2017-11-14◆李壮
◆ 李 壮
上升期里的四组趋势性概念———新世纪诗歌印象
◆ 李 壮
库布里克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设置了一座黑色石碑,在它的神秘辉耀之下,人类一次又一次地实现了全新的生命想象。这块历来被电影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石碑象征着一种外在的神力,同时,也不妨阐释为人类内心中永恒渴望的外化——正如库布里克将故事定位在想象中的2001年以暗示一个新的开始,当2001年真正到来之际,我们也都渴望这个特殊的数字真的能够带来一些特殊的惊喜。
这一年也确实发生了许多大事:纽约的双子塔倒下了,以恐怖袭击这种前所罕见的形式;在国内,国足冲进世界杯与申奥成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兴奋点,它们与加入世贸组织这样的经济盛事共同催生出一种繁花似锦的新时代想象。然而此后的事情渐渐偏离了我们的想象:国足一球未进地结束了世界杯之旅,北京奥运会的金牌榜第一使我们对“体育战争”的狂热兴奋趋向消退,反恐战争的世界变局与国内市场全球化步伐之间潜在的一致,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急速却平稳的上升期。如同飞机轰鸣着穿过云层之后,乘客们解开安全带,翻开手中的书:一段灿烂却略显平淡的旅程开始了。
这一切看似是大历史,实际上却同新世纪的汉语诗歌间存在着潜在的隐喻、对应关系。相比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大亢奋与大争论、大理想与大幻灭,新世纪的中国诗坛少了些大起大伏,也进入了一个稳定上升的时期。当然,这个上升的过程并不是发生在一马平川的平流层,而依然是在风景流转的对流层里;因此,气流颠簸和风云变幻依然时时发生,许多新变乃至趋势性的元素,已然呈现在我们眼前。
分裂与融合
上个世纪末的诗坛印象在1999年的盘峰论争中落幕定格:那场会议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赫然对立成两大阵营。然而进入新世纪,两大阵营森严壁垒的对立情形渐渐出现了风化崩析的趋势。这不仅仅体现在诗人个体交往的层面上,更体现在具体文本的诗歌美学层面。正如当年盘峰论争之后,许多诗评家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对深度和技术的强调,与民间写作对生命力的追求,理应相互学习、相互吸收,而不是简单的对立。这一愿景在今天正在成为事实。新世纪十五年来,上世纪诗坛二元对立式的尾音渐渐消散,变成了更加丰富的复调混响:大的阵营演化作无数条更小更具体的美学路径,并且多有交叉;争抢话筒高喊宣言的“诗歌流派黄金时代”已成回忆,更常见的是小的同仁群体,在相对平和的心态中孜孜探索着诗的技艺与真谛。
这种分裂中有融合、从分裂到融合的趋势,在沈浩波的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作为90年代后期诗坛论争中的活跃分子,沈浩波在新世纪愈发引人注意,其2000年发起的“下半身”诗歌运动更是我们回顾盘点之时无法略过的一个事件。然而倘若仅以“口语诗人”或“下半身写作”这样的标签来框定这位诗人,将会极大地损害其诗歌的丰富性、复杂性。沈浩波自己谈到“下半身”运动的时候,提到了一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来自于道德伦理和文化情感的狭隘”。对这种“狭隘”的冲破,或许才是这一看似惊世骇俗的运动的本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冲破”在诗人的写作上也并没有变成矫枉过正、一去不返的单程火车,请看诗人在2000年(发起运动的同一年)写下的这样一段诗:
而墙根的雪已经不是雪了
它是雪的癌症
它吃力地扶着墙根,它将
继续黯淡下去,直至消失
沿着墙根行走
每走几步,你就会发现这些
令人心颤的细微之物
它们看上去甚至还很新鲜
而它们到底形成于何时?
当他把因落于墙根而即将提前融化于污秽的雪比喻成“雪的癌症”、在悲悯中看到它们“吃力地扶着墙根”、为它们脆弱的白和细小感到“心颤”,并发出“它们到底形成于何时”这样近乎终极的疑问时,你很难将他与那个书写幼女乳房和倒霉强奸犯的沈浩波联系在一起(尽管在那些诗中,诗人的本意也并不在“性”)。其2013年出版的诗集《命令我沉默》,进一步显示了新世纪以来诗人写作的丰富性,其书名出自诗人下面一句:“我是人世间迷路的灰鹤/时间在秋天的密林里/命令我沉默”。诗句中丰富致密的意象、深秋般邈远的气息、沉寂而神秘的意境,已经完全不同于我们印象里那个离经叛道、“一路狂奔”的沈浩波,更不必说《文楼村纪事》这样尖锐指向社会现实的作品了。
与之相对的,是带有浓郁学院派色彩的诗人西川。在他的近作中出现了这样风格的作品:
老演员
老演员演别人,一辈子活六十辈子,可以了。
终于到了演戏完的时候,酸甜苦辣还在继续。
老演员演别人终于演到了自己的死。请安静一会儿,请关灯。
2011.4.
小演员
化了妆的准备登台的小姑娘粉衣粉裤,肩膀露在风里。
她既不快乐也不悲伤,像其他小姑娘一样。
在迈步登上那古老的露天舞台的一瞬间她提了提裤子。
2011.4.
其中的平易、近贴、坦白、诚恳,以及那种略带轻谑解构的语调,也都显示出一种流派互渗、美学交融后的神奇图景。
同文本风格的互渗互融相类似,诗歌写作、发表、传播的平台乃至整体生态,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多维并进、两栖融合的特点。新世纪诗歌分裂与交融表征的另一重要体现,便是在诗歌传播媒介上。新世纪初,网络的兴起曾经带给诗歌新的风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各种贴吧、论坛蜂拥而起,为诗歌之声的发送和传播带来了新的音色音质,一些新的诗人群体、诗歌主张也借助网络的力量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时至今日,尽管诗歌多媒体传播的PC端时代已基本走向终结,在网站论坛时代聚合起来的若干诗歌声音却一直延绵至今,并逐渐走向实体、线下,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血缘谱系。
近几年,另一种新颖而强大的媒介再一次强力推动了诗歌的发展传播,那就是移动终端,亦即手机微信平台。移动终端随时随地接收、浏览信息的强大性能,完成了诗歌文本及相关新闻对有效受众全方位的覆盖工作,而诗歌短小精悍、抽象感性的特质,也极其适合这种新的传播方式。于是大致从2010年以来,移动终端上的诗歌活动骤然活跃:诗歌微信群纷纷建立,“为你读诗”、“诗歌是一束光”、“诗人读诗”等诗歌主题公号大受欢迎,《诗刊》、《星星》等权威纸刊纷纷打造微信公号,许多著名的诗歌新闻或论争也以微信为重要平台(例如余秀华事件)。同时,新媒体与纸媒之间也并非仅仅是单向的影响输出;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许多新媒体诗歌团体开始像纸刊和传统文学机构的运作方式靠拢。例如“明天诗歌现场”微信群将传统意义上的诗歌研讨会办到了微信群里,并将讨论结果整理成正式文章;许多在新媒体平台上收获好评的诗人诗作,也登上了权威纸刊的目录,《诗刊》就曾专门为微信平台上出现的诗歌佳作开辟过发表版面。
媒介融合的大趋势,成为了近年来中国诗歌全面回暖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新媒体传播自身也存在某些致命的弱点。以当下极其活跃的微信诗歌群为例,由于数字平台空间的无限延展性和高度自由性,信息发表完全以个体意愿为根据,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筛选过滤机制,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便是信息泛滥、过分随意,少数真正有效高质的诗作和观点,极容易在汹涌的信息流中被迅速淹没。我们现在点开各型各色的诗歌微信群,最常见的不是深思熟虑、精彩透彻的作品或论述,而是无休无止的微信红包、八卦闲聊和动画表情。与之并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门槛过低——完全不入门的诗人诗作甚至有失风度的谩骂攻击充斥其间,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参与热情及对新媒体诗歌的印象,更不用说这类参与者往往是“一身多群”、“一稿群发”,导致我们的手机页面经常会被糟糕的作品刷屏。新媒体诗歌平台越来越趋向快餐化,正在追求热闹和数量的方向上滑行,而我们又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加以遏制,这形成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而据媒体从业人士透露,2015年起,微信平台的活跃度及公号浏览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这或许是微信平台盛极而衰的开始。然而,无论如何,更新的传播媒介一定会不断出现,并且在未来的几年中继续改变着中国诗歌的发表、传播甚至创作生态——我们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来。
上升与下移
汉语诗歌进入新世纪,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诗歌中枢神经与诗意动力机制的下移。不仅仅是沈浩波等人的“下半身”,所谓的“下”也远非局限在两腿之间,事实上整个文学界在21世纪初都在热闹地讨论着“身体”的话题——这里面的深层原因当然很容易推测,那就是过分发达的技术和智力元素对文学文本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遮蔽,导致它产生了思维发达、智力过剩而下盘不稳的风险。总体来说,“身体”在21世纪初(包括20世纪90年代)于文化话语系统中全面复苏并日渐流行,本质上是对修辞神话(在小说领域,亦可被置换为形式试验及宏大叙事)的一次祛魅,它试图使文学的重心下移,重新获得抓紧地面、感知温度的能力,重新唤醒个体身心的真实感觉,而不致异变成空中楼阁或是过量饮用劣质奶粉的大头婴儿。在此意义上,强调“身体”的主要目的如今大致达到了——我们今天越来越习惯讨论及物,也越来越常看到及物的诗歌,这里的及物,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下移的同义词。
下移与及物的冲动在文本与理论层面最终爆发,来自于汉语新诗自身发展与时代文化语境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上升的姿态在汉语新诗百年乃至新时期诗歌40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产生了过多的经典,在某种意义上,该抬头看的已经看完了,出色的前人封死了后来者的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样北岛式的呐喊早已被经典化,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式的悲愤,也差不多可以作为90年代精神氛围的标准画像装裱悬挂起来。另一方面,时代的变化也不再适合一个“45度角仰望星空”的姿势——我的这句引用,其实是杂糅了郭敬明与西川的标志性句子,“45度角仰望”的郭敬明属于中学生的个体生理青春期,写下“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时的西川背后则是1980年代这段历史的青春期。但凡青春期,思索的必定是永恒终极的话题,例如爱,例如死。这些事情的答案本不在世间,于是仰望便是最合适的姿态。21世纪的中国却从“少年听雨歌楼上”的青春梦幻一下跨入了“壮年听雨客舟中”的成年心态,虽然雨声依旧,心态却大不相同:务虚玄想变成了务实创业,抬头仰望变成了低头寻觅,路遥笔下的孙少安长成了《人物》杂志封面上的潘石屹。在这样的大语境下,作为拥有对现实超常敏感力的诗人,如果依然仰着头不低下,那么诗作便有架空脱水之险。
具体来说,诗意的下移,首先体现在身体感觉的复苏——不是宏大的历史身体,也不是精密的智力身体,而是那具有温度、能让体温计里汞柱上下移动的个体肉身。在这一点上,女诗人似乎具有天生的优势,例如吕约组诗《吃》里的这一首:
一个在吃的人
离开世界
离开亲人
回到自己身上
跟着食物
钻进自己的嘴巴,牙齿
穿过自己的喉咙
钻进肚子,最后的避难所
再把自己生出来
在吕约这里,“吃”成了现代人“回到自己身上”的珍贵途径,肚子则成了“最后的避难所”;而重温这一本能行为的意义,或许正隐藏在最后一句之中:“再把自己生出来”。强调身体的感觉和动作,是为了重新擦亮个体生命被现代都市烟尘雾霾遮蔽的光亮与尊严。在这点上,我们的诗歌与现代以来全球哲学界思想界的核心话题不谋而合。而此组诗歌中的另外几首,又夹杂有诸多社会性、历史性的讽喻,显示了其内在的复杂性。
除了个人身体,下移过程中的新世纪诗歌还热衷书写身体的外化之物: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尤其是与肉身生活有关的物象。譬如芦哲峰这首《对面》,简单、纯净,但“白鞋子”的意象在阳光中出现在“对面的窗台”这一特殊的空间,瞬间便具有了深长的意味——它打开了生活中无限的想象,及其背后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对面二楼的窗台上
放着一双白鞋子
每隔几天
如果天气晴朗
它就会出现在那里
静静地晒着太阳
当然,下移的力量并不意味着对高处事物的一味排斥。有时恰恰相反,正是在急速下坠的失重感中,某种反身向上的飞升幻觉会变得更加真切,甚至在亦真亦幻之中直接抵达雪线以上高海拔地带。例如封原的这首《我的女友吞下一颗摇头丸》,写的是沉沦的身体、堕落的身体、甚至违法犯罪的身体,恐怕已经没有办法更低、更下一点了;但那种令人心碎的孤独感、对爱与温暖的绝望的渴盼,又有多少纯粹高蹈的作品能够表现得出来呢:
我目击
我的女友
吞下摇头丸的样子
像吃一粒糖果
她说她又可以见到死去的父亲
我干过比这更危险的
那些日子里
我们躺在她家的床上
房间高大 噪音来自窗外
她摇头流泪
然后笑
她说:父亲来了
带来了这么多的糖果
内涌与外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诗歌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个人话语的张扬与自由精神的舒展。诗歌逐渐地从政治正确与文化使命的重轭下脱出,其文本内部的表达系统与外在的意义秩序之间在来回磕碰之间逐渐脱钩,诗歌在语言和美学意义上的自足性越发凸显出来。诗到语言为止、到个人经验为止、到个体生活为止,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个体化、充满自由精神的写作依然占据着汉语诗歌创作的主流。
总体看来,这种向内向深挖掘、捕捉内心血流涌动(这里的“内”既包括个体的内心、生活的内部,也包括词和语言的内核)的诗歌精神,符合现代诗歌的演变大趋势。但在这样的整体语境之下,不满的声音同样存在。诗坛内外的许多人都认为,诗歌的过分内倾,已经导致其难以有效回应时代生活,诗歌与时事、大众间越来越深的隔膜,应当引起注意和警惕;一种“社会性观察”的诗歌视野,理应在适当的程度上完成回归。于是,许多关注现实、甚至直接指向时事的作品诞生了。这里面寄寓着一种伸展触角、使语言洪流冲破纯诗边界向外部流溢的冲动,它在近些年被一再提及,并且已经在许多诗人的创作实绩中得到了展现。
与过往的历史不同,内涌与外溢这两种冲动,在新世纪里并没有呈现为一种相互倾轧、轮流坐庄的零和博弈模式,而是于时间上共存、于空间上并生,呼应对照以存在。它们建立起新世纪中国诗歌的混合动力机制,共同推动着写作者的笔端,也塑造着我们的诗歌印象。
在许多著名诗人那里,对生活与内心的探查、表现早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们的新世纪继续着自己的旅途,不断为我们提供着新的经典。而许多初入诗坛的年轻写作者,在向内的维度上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锋利。请看“90后”诗人玉珍笔下的孤独:
孤独太过扎实,比较难对付
我与他为敌这么多年
偶尔在失眠中握手言和
有时我甚至
爱这煎熬
或许这并不是煎熬
感谢他在粮食之外喂养我
养得我鬼神不侵
刀枪不入
如今我骨头剔透,与宇宙同色
站在屋顶像尊狂妄的大佛
这首名为《孤独这种粮食》的诗,字句间闪耀着凌厉的才华。它告诉我们,面对我们身心之内那些亘古如一的主题,优秀的诗人永远都有话可说、有诗可写,不管作者年岁几何。同时,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现代诗歌中的向内,不仅仅包括个体的内心、生活的内部,也包括词和语言的内核。树才的《心里有烟》,可谓是一套出色的“词语体操”:
心里有烟,
心里有鬼,
心里有烟鬼。
男烟鬼?女烟鬼?
心里有火,
心里有灾,
心里有火灾。
救火车!救火车!
心里有怨,
心里有气,
心里有怨气。
开门,开窗,透气!
心里有情,
心里有人,
心里有情人。
成眷属?成冤家?
心里有数,
心里没数,
心里直打鼓。
一打鼓,烟跑了。
相比于内的冲动,外的趋向由于同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因此更易形成引人注目的诗歌事件或具体潮流。在我们新世纪诗歌的语境中,外在相当程度上约等于介入,而我们印象中最醒目的两次介入,大概要数地震诗歌与底层诗歌(或称为草根诗歌)了。2008年的5·12地震似乎成了诗歌介入现实的一针催化剂。这或许同当时的整体社会气氛有关:一方面,在北京奥运之年,全国上下的集体热情、民族热情持续高涨,天灾面前,反应格外强烈;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民众的公民意识正在养成,“公民社会”等说法也颇为流行,有能力的民众介入公共事件便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就诗歌界而言,地震发生后,大批地震诗歌应运而生,一时间铺天盖地,许多地震诗歌集也纷纷出版——面对社会事件,诗歌界如此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场景,似乎很多年都没有出现过了。而底层诗歌更是近些年来持久不衰的热点:一方面是本身并不底层的知识分子书写底层题材,另一方面,许多真正来自底层的写作者也亲自加入了写诗的行列之中。前者笔下多有悲悯愤怒,后者的诗句则流淌着真实的悲哀。他们中有一些人的名字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出道最早的要数郑小琼。正如许多诗评家一再提到的,郑小琼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在我们的新诗谱系中,加入了铁的意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重塑了铁的意象:在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铁是一个火热的、燃烧的、充满正能量的意象,它同工业生产、现代化以及被许诺的幸福生活有关;而到了郑小琼这里,铁则变成了一个冰冷的、黯淡的、充满疲惫的意象,它意味着批量生产和流水线,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压榨与剥夺。还有一点耐人寻味:在前一种想象那里,铁在台前,但它不是主体,真正的主体是在背后冶炼着钢铁、充满能动性和主体性的人;而在郑小琼处,铁变成了主体甚至主人,打工妹却是实实在在的奴隶。这才是底层诗歌受到关注的真正玄机:它关乎异化、关乎人之尊严的丧失,这一问题集中体现于底层,却又绝不仅限于底层。
将郑小琼铁的意象继承书写并进一步引向深入的,是青年诗人许立志。在其最著名的一首诗里,诗人塑造了“铁做的月亮”这一惊人的意象: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现代文明和资本的秩序化作铁月亮贯穿诗人血肉的肚肠——这样的诗歌,读来真的令人心惊肉跳。而“我再也咽不下了”这样心碎而绝望的哀号,同几十年前年纪相似的北岛“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的呼喊之间,又形成了怎样痛彻心扉的对比!而事实上,现实中的许立志也真的再也咽不下了。在富士康员工自杀15连跳事件里,其中的一位逝者,便是这位年轻的诗人。
这一切当然会激动我们。借着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底层诗人走入了我们的视野,而且有关底层的诗歌确实也在不断地出现佳作。原因很简单,我们可以借用韩东当年的一句诗(尽管这句诗本身无关底层)——“这里永远怀有某种真实的悲哀”。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许多底层诗歌,在艺术技巧的层面其实是存在不足的;在此问题上更明显的则是之前提到过的地震诗歌: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回头再看当年轰轰烈烈的地震诗歌,发现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实在不多。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诗歌的介入性其实还仅仅停留在皮毛、形式的层面——有志于外的诗歌,背后若无其内的一面,则注定无法丰满。这里显示出新世纪诗歌外溢或曰介入的一道难题:如何使一种社会性、公共性的关注,真正与个体情感体验以及诗歌的艺术价值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诗歌血气充足、真诚有力、并切实地在艺术层面做到“过关”?
这或许是一种更远的期冀。但无论如何,我希望在未来看到更多像严力的《负10》以及下面朱剑《南京大屠杀》这样的诗,写大却没有写空,在介入外部的同时不丢掉切肤之痛,“永远怀有某种真实的悲哀”:
墙上
密密麻麻写满
成千上万
死难者的名字
我看了一眼
只看了一眼
就决定离开
头也不回地离开
因为我看到了
一位朋友的名字
当然我知道
只是重名
几乎可以确定
只要再看第二眼
我就会看见
自己的名字
突进与洄游
在西川新作《在南京醒来》的推荐语中,诗刊的编辑这样写道:“读者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西川。在这首诗中,他有意加入了粗糙、异质的东西,甚至‘非诗’成分,形成了一种丰富、庞杂、混沌的诗歌。”这种对异质性甚至非诗性元素的大量吸纳,显示出诗人在诗艺或曰修辞技术上的求新求变,这是新世纪诗歌继承上世纪后期先锋诗歌探索精神的一个小小缩影。即使文学史层面的狂飙突进年代已经远去,步入新世纪的诗人们依然在不断追求着诗歌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诗歌的突进并不一定要以百米冲刺或蜂拥而上的形式出现,它也可以是一场马拉松,可以是一个人漫长而执拗的朝圣之旅。
与西川类似的还有欧阳江河。在其最新出版的《大是大非》一集里,诗人试图以语言的智性打通古今中外,并包裹起现代都市生活的种种全新元素;而他的《凤凰》,也堪称现代汉语诗歌尝试长诗书写的重要成果。伊沙等人的探索依旧口语却又不止于口语,他们在数量惊人的创作之外,还不断提出、发展着自己特色鲜明的美学观点;通过编选本、推新人等方式,他们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以网络媒介上的新世纪诗典为平台,一大批构思奇崛、想象力高妙、书写事实的诗意的诗歌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当下汉语诗歌的印象与想象。
如果说朝向未知可能性的不断突进,是现代汉语诗歌自80年代延续至今的优秀传统,那么新世纪以来,一种特殊的洄游倾向,则更加值得我们关注。所谓洄游,本是一个生物学领域的概念,意指鱼类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因生理、遗传、环境等因素影响,某些鱼类会做出周期性的定向往返移动,例如鲑鱼一生在海里生活,最终却要回到自己出生的河湾里产卵繁殖。这种追根溯源、重返传统的移动方向,同样出现在新世纪的汉语诗歌写作之中。它至少在两个方向上得到显现:其一是重拾“抒情性”,其二是对本土特质与东方古典美学的强调。
有关第一点,我们或许可以将它看成是现代诗歌不断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某种自我反拨。诗歌现代性对传统抒情元素的排斥是其自我确证、自我建立的方式之一,而今天,当现代主义诗歌美学的主流地位已大致稳固,抒情元素的反弹与回归便也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号称“2014年被转发次数最多”的一首诗,便是李元胜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 ……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
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
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
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
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
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此间的精巧、浪漫、温柔,营造出一种抒情性诗歌所独具的舒适感,面对这样的诗句,人类的情感会产生一种本能般的迷恋——对抒情语言的亲近感,几乎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与此类似的,是张定浩那首流传甚广的《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琥珀里的时间,微暗的火,一生都在半途而废,一生都怀抱热望……”
而第二个方面“对传统东方美学的强调”,更是文学界近年来一直在热议的话题。中国经验、中国表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早已成为被一提再提的期待甚至焦虑,对此,我们的诗人用自己的创作给出了回应。李少君的《自然集》是一部无法跳过的作品。在这本诗集中,李少君将自然放到了诗歌美学的核心位置,并将现代主义中坚固、独立、自足的笛卡尔式主体,消融、重置于山水之间。他的诗复活了一种久违了的气息:那是大自然的气息,而非都市的气息;更接近古典性,而非现代性。与此相近的是雷平阳:他笔下的云南风物彰显着典型而精彩的诗歌地方性,《基诺山上的祷辞》一首,更是在简约、原始、近乎原生态式的语言风格中,道出了生命、希望等诸多终极性的命题。2015年末,蒋一谈出版《截句》,更是将这种美学上的洄游直接推进到了具体的形式层面:这本集子里的诗歌多数只有两行,最多时也不过四行。在形式和意味上,《截句》都如同禅偈、俳句、绝句的奇妙结合,其以寸劲形式爆发的诗意,则充满了一种截拳道式的语言魅力。但这种貌似古典的诗歌形态,却又充满了真正的现代精神;即便在那些最经典的传统诗歌意象之中,蒋一谈依然能保有一种新奇而开放的姿态,并精确地命中现代人复杂而隐秘的内心世界:
火焰慢慢熄灭
这是火焰的谦卑
月亮滑入大海
伟大的默片
雪花埋葬雪花
无人知晓它们
之间的仇意
蒋一谈的这些截句,在贴近传统的形式结构趣味中,将非传统性的现代情感书写得精彩纷呈。它是洄游,但同时更是突进。这种辩证式的逻辑也适合于前文论述过的另外三组对子:分裂之后再走向融合、极致的下移孕育着上升、外溢的动力根源于内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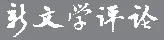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