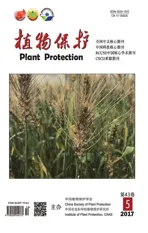植物健康概念的商榷
2017-10-09刘永强王忠跃刘崇怀
刘永强, 张 昊, 王忠跃, 刘崇怀
(1.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93;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郑州 450009)
植物健康概念的商榷
刘永强1#, 张 昊1#, 王忠跃1*, 刘崇怀2
(1.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93;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郑州 450009)
植物健康是经常在植物科学尤其是植物保护领域被使用的术语,但迄今仍然没有一个明确并普遍被认可的概念。通过梳理和总结不同哲学思想下植物健康概念的探讨和争论,试图在分析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获得植物健康概念的科学内涵,同时结合中国哲学观念提出了“特定遗传基质的植物(种或品种或生物型等)生长在适宜的环境中(土壤、水分和气候),没有受到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因子侵扰和伤害,各种生理功能平和或平衡的自然状态,植物的这种状态就是植物健康”的概念,明确了植物健康的动态性质及阐述了植物健康下的植物种群健康,并对依据这个概念从事农林生产进行了剖析,供大家商榷。
植物健康; 概念; 中国哲学观念
植物健康是一个经常使用但没有明确定义的术语,经常被滥用[1]。在国内文献中,把能够促进植物生长、保鲜、增加抗逆等多种功能的农药、肥料、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叫做植物保健,或植物保健剂[2-4];把减轻或免受有害生物的侵害或伤害而使用农药,也叫做具有植物保健作用,等同于保护植物。在国外文献中,有科学性和规范架构的植物健康一种是指对外植物检疫[5-6],比如美国农业部把通过阻止危害农业和自然资源的动物、病虫害、有害杂草的传入、定殖和传播,及支持美国农产品贸易的措施,叫做植物健康(plant health);另一种比较粗放的是把所有植物保护,都叫植物健康。尽管植物健康在农业、林业和环境保护领域非常重要和姿态鲜明,但迄今仍然没有一个明确并被普遍认可的植物健康概念,是一个发展中的不完备的概念。
1 基于西方哲学思想的植物健康观
1952年,Schimitschek最早提出了“植物健康”的概念[7],之后许多科学家对植物健康的概念进行了探索[8-9]。其中2012年Döring对西方哲学体系下的植物健康概念进行了综述[1],从自然主义与规范主义的价值取向[9-11]、还原论与整体观、功能性和恢复能力或补偿能力、唯物论和活力论、生物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等哲学层面对植物健康进行了广泛的探讨[1]。
1.1 自然主义与规范主义的价值取向
自然主义与规范主义是两种科学认识论,自然主义主张用自然原因或自然原理来解释一切现象;规范主义认为事物或现象存在着某种理性的活动规范,通过揭示这种规范能够获得或认识事物的本质和真理。自然主义认为健康源于自然,是一种自然状态,不受人类的价值观影响[12],认为自然科学足以对健康进行全面分析。健康有一定范围,通过检测各种指标就可以知道是否在这个范围内。自然主义的杰出代表布尔斯总结了健康的概念,但存在广泛的争议[13]。规范主义认为健康的概念是人定的,受人的价值观影响,人确定是否健康,认为文化价值观在植物保护及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4-17]。
1.2 还原论与整体观
还原论和整体观是哲学范畴的方法论:还原论或还原主义认为复杂的系统、事物、现象,可以将其化解为各部分的组合,对各部分的认识综合在一起,可以理解和描述整体的系统、事物、现象。整体观是指从整体上认识事物的本质,认为还原论只可用于简单事物,对于复杂事物而言,一旦被分割,将会因此丧失许多信息而失真,事物的复杂程度越高,因分割而失真的程度就越严重。两者针对植物健康存在争论[9, 18],辩论的核心是:如何对构成整体的几个部分进行调查[19]、如何理解和把握整体。
还原论认为:系统是由可分离的组分组成且各组分可以单独分析,系统(整体)可以用各组分的功能表现进行解释。其优势是:能够测量每个部分的功能;不需要逐个系统单独进行调查,就能预测所调查系统的未来行为。还原论认为从一个系统得到结论,也适用于另一个,它们都是类似的。还原论者认为影响健康的因素是可以分离的,确定健康需要的标准较少,甚至是单一的、专科学科就行[9]。最重要的是,还原主义者认为调查系统的一小部分,例如只是一种病原,一旦特定植物器官或组织没有这个特定病原,就认为这项工作已经完成。然而这一理论针对实际问题存在缺陷:病理学家早期就已经观察到,对某些病原体有抗性的植物常常更容易被其他病原侵染,例如小麦锈病,当小麦对锈病的抗性越来越好时,小麦更易被弱寄生菌如壳针孢Septoriaspp.和叶斑病侵染[20-21]。
整体论者认为物体或事情不完全能分解成各组分,除了各组分,还有各组分之间及一个组分和多个组分之间的互作关系,从一个系统得到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系统,不同系统需要单独考量[22]。整体论把每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不注重所选择组成成分的分析,而是要在一个高层次的整合层面去理解,并把重点放在系统内和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上。关于植物健康,整体论的观点体现在三个方面[23]:(1)把植物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离或隔离的部分,整体性是完整的[24];(2)把植物放在其自然环境中,需要考虑到生态系统中各个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的网络关系[25],研究植物健康需要跨学科的方法[26];(3)从整体的社会经济角度考虑,涉及人的因素[27]。同时,Balfour假设健康是可以传递的[28],可从土壤传递到植物、从植物传递到家畜和人类[29]。然而,即使多数人同意特定植物的整体性或完整性,很难想象如何构建一个(包容不同观点和潜在分歧的)整体性定义。整体论的不足或难度就是存在潜在的模糊和混乱。整体论的方法通常表现为缺乏清晰度,应用整体论的方法就好像没有知识的积累[9]。因为每一种情况都看做个体的整体,所以每一次都需要从头开始,每件事、每个点都需要研究和弄清楚。
1.3 功能性和恢复能力(或补偿能力)
对于采用人为干扰手段如对植物施用杀菌剂杀死病原菌等方法或措施,功能主义者(functionalist)的观点认为:施用农药使植物免受病害侵染;使用农药的植物能高效(或正常)发挥其功能(如光合作用、生长和繁殖等),否则植物会易被病原菌侵染从而丧失其功能;所以,喷洒了农药的植物是健康的。对应的观点认为:这种健康是短暂的,而真正的健康是长时间延续的,并不依赖于杀菌剂的使用,健康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弹性,也就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在面对胁迫时能保持其正常功能的发挥[1]。
1.4 唯物论和活力论
活力论是关于生命本质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认为生物体与非生物体的区别就在于生物体内有一种特殊的生命“活力”,它控制和规定着生物的全部生命活动和特性,而不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关于健康概念,两种观点存在着争论。
对于唯物主义者,重要的是物质,所有现象(包括活生物体、它们的健康等)可以解释为物质的相互作用,即通过原子和分子的作用来解释。在唯物主义者的观点中,健康是物质功能和在生物体内生理学的化学物质正确集中的问题,生命过程可以通过其组成成分的力学定律充分描述;因此,用唯物主义机械论方法研究植物健康,侧重于揭示植物、害虫和病原物之间关系的机制和物质基础。其研究规划通常涉及植物的防御反应、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生物化学途径。
活力论认为,生命不仅仅是物质和数学,生命与机器或其他死亡物质的区别是有一种重要的能量或生命力,在西方传统中被称为‘生命力’,印度传统中叫‘瑜伽’,中国传统医学中叫‘气’。至关重要的是,它的强度被视为生物健康的指标。一些现代活力论者用量子物理学作为支持他们观点的证据,但是,现代量子物理学家认为生命不能简化为物质[30]。
活力论受到批评和质疑的是:所谓的生命力仍然是不能解释和莫名的,而且几乎不可能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活力论对唯物主义的批评是:首先,唯物主义者在注重物质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形式[31],证据来自进化生物学,其中波动不对称已被用作应力的形态测量[32];其次,我们可以从纯物质(分子和原子)转移到物理学的其他实体,如辐射[30]。 这里就有一个进展是(重新)发现生物光子[33]:Popp[34]比较了“新鲜,健康”和“患病,枯萎”叶子的生物光子发射,新鲜叶子显示出更强的发射和更缓慢的衰变。生物光子学用于植物健康研究的潜力在于生物光子的普遍性和可测量性。因此,活力论认为应重新审视植物健康的非唯物主义概念(即使不是全部否定或代替)。
1.5 生物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生物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是伦理学范畴;人类中心主义是“要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的思想,只有人类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人类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价值评价的尺度必须掌握和始终掌握在人类的手中,任何时候说到‘价值’都是指‘对于人的意义’;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应当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生物中心主义是“生物系统的健康本身具有价值,人类对它负有直接的义务,生命个体、物种、生物过程作为生物系统的组成部分和存在形式,具有非(人类的)工具价值,主张有某种特殊的非物质因素支配生物体的活动”。
生物中心主义者声称,植物像所有生物一样有自己的利益[35-36],主张为植物的利益促进植物健康是正确的。在讨论植物健康时,无论采取何种立场,生物中心主义者都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所有生物(包括植物)有利益,那么植物病原体和害虫也有利益,因为没有理由让植物应优先于害虫或病原体。促进植物健康,必然以牺牲某些其他有机体(如害虫或病原体)为代价,这对于生物中心主义似乎是不合理的。许多哲学家的伦理观念甚至认为动物伦理优先于植物[37-38],那么这种伦理理论更难以支持杀灭害虫。
人类中心主义忽视或否认植物具有利益的可能性,并且纯粹是为了人类的益处才采取适当的行动促进植物健康(例如更高的产量或食物质量)。从纯粹的人类中心观点看,植物健康变得重要,因为它影响人类的成功和幸福。对植物健康的关注是基于植物能为人类提供食品、纤维、燃料、医药、美景等方面的重要性。因而对于没有直接保护价值的普通野生植物的态度人类中心观很少干预、也不在乎这些植物的健康改善,除非它们的不健康影响人类的利益。人类中心观的植物健康概念其核心论点是促进植物健康以服务人类,因此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植物健康时应与人类的目标和利益一致,该概念存在严重缺陷,即往往忽略人类目前认为对人类没有价值(或不直接使用)的生物的生存、进化和功能。
以上各方向的探讨,说明在西方哲学体系下,对于任何单一视角的植物健康,都能找到削弱其合理性的实例,没有一个植物健康定义是令人满意的。激进做法就是拒绝给出定义或根本不使用该术语,许多关于植物病理学的教科书就没有任何植物健康定义[39],作为一种审慎的做法,这种不给定义的做法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持[9]。Döring[1]虽然对植物健康概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综述,也提出了讨论该概念应考虑的问题及应用该概念的指导性原则,但没有给出概念。
2 中国哲学思想与植物健康
国内,尽管植物健康是一个被经常使用的术语,但没有查阅到该概念的定义和对其内涵进行讨论的文献,当然也不会有广泛接受的概念。然而,在植物科学中需要植物健康的概念,植物保护科学更需要植物健康的概念;明确了什么是植物健康,才能知道如何保护和维持植物健康。既然西方哲学体系无法给出植物健康的概念,我们试图依据中国的哲学思想,探讨植物健康的概念和范畴,并对该概念指导下的农林作物栽培进行剖析,以阐述植物健康的内涵。
古代中国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主要的哲学流派,其中尤其以儒、道、墨三家影响深远。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思维底蕴:整体关联、动态平衡和自然合理[40-43]。以下我们应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思维底蕴,分析和挖掘植物健康的概念及内涵。
2.1 整体关联与植物健康
2.1.1 整体关联与植物健康
整体关联哲学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孤立到整体之外去,更不能用它来说明整体。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里面去,才能正确认识它。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同样地,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40]。
对于一株植物,植物健康的整体关联有两个方面:第一,任何一个局部的不正常可以使一株植物的整体健康受到影响,或者一个器官的不正常可以导致其他器官也不正常,比如根系的衰败可以导致整株植物的死亡等;第二,局部的问题可以通过同一组织的其他部分或其他组织进行弥补或补偿,对整体不会产生影响,比如对葡萄根系浇水,一次只浇一半(只利用一半的根系功能),7~14 d轮换一次,不影响这个植株正常的生长、发育、产量和质量[44-48]。
对于特定植物种群,健康的整体关联与一株植物一样:一株植物的问题,可以影响整个植物种群的健康,比如一株葡萄感染了葡萄根瘤蚜,整个葡萄园就有了健康问题,就有随时被毁园的风险;另一方面,一株植物或个别植株或局部的问题,对整个特定植物群体的正常生理和生命活动没有影响,植物群体是健康的,比如病虫害危害阈值、经济阈值及其理论[49-50],个别植株或部分植株受到影响时,只要是在阈值之内(甚至远远小于阈值时),对整个群体的产量、品质没有影响。第二种状况的观点与Döring[1]讨论的弹性、补偿能力等相似,也是动态平衡理论的一部分,即植物遇到干扰时调整和维护其平衡状态。
除以上两个方面外,植物健康与生态环境的整体关联宏观上还包括:与非生物环境;与生物环境中其他植物、与以植物为寄主的有害生物、与生态功能性低等动物、与人类及畜牧类动物等整体关联。
2.1.2 植物与非生物环境的整体关联
对于特定的植物(种类或群体或个体),都需要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生存和繁衍;如果超出环境条件,其存活、生长或繁殖等就受到胁迫或挑战,甚至不能生存。所以,植物的健康与其生存的环境是整体关联的,这个适宜的条件包括气候、土壤、大气和水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是对植物健康与环境的整体关联最生动形象的描述。所以,一个物种或生物型或品种等都有一定的适生环境或适生范围,超出这个范围或环境,就非常容易产生健康问题或者难以生存。
2.1.3 植物与生态系统中其他植物物种的整体关联
植物与生态系统的各因素存在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就是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尤以化学生态关系为重要,比如化感作用。植物健康是建立在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相互有利的生态关系之上,所以不能在同一生态系统中栽种相互“敌对”植物,比如葡萄与铁皮石斛和白花车轴草混栽时,其化感作用不仅对葡萄产生影响,也对葡萄园内土壤微生物群落产生影响[51]。植物健康是生态系统整体健康的一部分,植物健康与生态系统健康是相互关联的。
现代农业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人类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甚至单一品种,形成简单的农业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的优势是有利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预,以达到标准化管理、标准化生产的目的,及非常便利地使用农业机械;但另一方面,这种简单的农业生态系统十分脆弱,易造成适应取食或危害这种作物或品种的病虫害暴发流行,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如马铃薯晚疫病的大流行造成爱尔兰饥荒等[52-55]。于是,人类又开始利用多样性形成相对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让作物更少受到病虫害的侵害,从而得到更多人类需要的资源[56-59]。这样,复合农业又开始受到关注[60]。但是,形成稳定、成熟的复合生态体系,需要大量的试验或实践经验或对自然界物种之间相互关系调查数据的积累;根据实践和试验结果,利用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相互有利的关系、摒弃或避免相互伤害或抑制的关系,形成技术模式或技术体系;我国的复种、套种、种养结合等农业生产方式,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哲学思想在我国农业文明中的体现,也是利用 “植物与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的整体关联”进行农业生产的实例。
2.1.4 植物与其有害生物的整体关联
植物与生态系统中以植物为寄主的有害生物协同进化,植物健康建立在避免有害生物危害之上;有害生物的存在既威胁植物健康又可促使植物进化。植物健康与其有害生物整体关联。
2.1.5 植物与生态系统中具有功能性的低等生物的整体关联
生态系统中与植物有关的具有功能性的低等生物包括蜜蜂等传粉昆虫、害虫的天敌、腐生性和中性节肢动物、环境中的中性微生物等。这些生物具有为植物传播花粉、控制病虫害危害、促进或帮助植物营养吸收及功能发挥等生态功能,影响着植物的健康状况;同时,植物的健康状态可影响这些生物的种群数量及生态功能发挥等。植物健康与环境中的低等生物整体关联。
2.1.6 植物与人类及畜牧类动物的整体关联
植物健康与人的健康紧密关联,植物健康是依靠植物为食物的人类和畜牧类动物生存和健康的基础。当植物受到有害生物侵扰时,有时会产生剧毒物质,比如小麦赤霉病产生的呕吐毒素、麦角病产生的麦角毒素、红薯黑斑病产生的甘薯酮等[61-63],严重威胁人类和畜牧类动物的健康和生命;动物健康受到威胁时产生多种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可以通过伴随着动物粪便以有机肥等形式进入土壤环境中,当这些有害物质残留量超标时,会影响生态系统中土壤微生物区系和功能、影响植物的健康状态;人类活动及其对植物的各种干预,是影响植物健康状态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植物健康及植物健康状态的延续,与人类及畜牧类动物整体关联。
2.2 动态平衡与植物健康
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偏差。平衡就是适度,就是恰好,既不过,也没有不及。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在失去平衡后可以通过调整达到新的平衡,即为动态平衡[45]。
动态:植物健康是动态的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植物或植物群体的健康水平是动态的,比如过去健康而现在不一定健康;另一个是生物体的生长发育也是在时刻变化,对于一株植物来讲,从种子(或其他繁殖体)萌发,形成个体,个体成长、繁衍,直至衰老、死亡,这个过程一直是动态的。
平衡:植物健康就是一种平衡状态,包括供应与消耗的平衡、吸收和利用的平衡、合成与分解的平衡等。一旦平衡状态被打破,必须建立新的平衡;平衡打破后的状态就是不健康或亚健康,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就是健康得到恢复的过程;如果打破平衡后不能建立新的平衡,植物的状态就是病态,其结果就是死亡或逐渐衰亡。
动态平衡:对于植物健康,所谓的动态平衡有五个方面的意思:(1)植物个体整个生育周期的动态平衡:植物根据不同的生长或生育阶段,调整其枝叶、根系、果实等养分吸收器官、营养合成器官(比如光合作用)、营养积累器官(果实)的数量和功能,保持其营养与消耗的动态平衡,使各种生理机能得到发挥,完成其生长和生育过程。(2)植物和非生物环境的动态平衡:植物的年生长周期或生育周期的各个阶段,其非生物环境有可能暂时或一段时间内存在或产生不利的因素。比如干旱(水分胁迫)、高温或低温等,植物会对这种胁迫压力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的协调,在分子机制、生理机能、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调整,以维持各种平衡和保证植物处于正常的状态。这就是植物和非生物环境的动态平衡。(3)植物与生物环境的动态平衡:植物的年生长周期或生育周期的各个阶段,可能受到其他生物干扰和胁迫,包括其他植物释放的化感物质、害虫的取食、病原菌的侵入等,植物会对这种胁迫产生的压力进行协调,以保证植物的正常生存。这种动态平衡能力被称为抗病性(或抗虫性、抗逆性)。(4)植物种群内部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动态平衡:物种内部存在遗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程度越高,该物种的生存力越强,反之,物种内的遗传多样性越低,该物种灭绝的风险越大。植物与其生存的环境协同进化,当植物进入新的生态区域或者环境条件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如全球变暖)时,植物物种内的种群也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化,维持其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甚至多样性更丰富)。这样,这个植物种群是有生存力的、是健康的。(5)植物个体生理机能和生存状态的动态平衡:对于一个植物个体,生理机能和生存状态也是平衡的。植物在白天不但进行光合作用也进行呼吸作用,但晚上基本只是呼吸作用,并且这种呼吸作用一般比白天弱,温度低比温度高弱;气孔的开合、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地上与地下部分的生长等,都有一个动态、调和的平衡;在肥沃土壤中生存,生理机能较活跃、生长量大,与生存状况(生物产量大、繁殖潜力发挥大等)有一个平衡;反之,在较贫瘠土壤中生存,也有相对较温和的生理机能和生存状态的平衡。这些动态平衡,是植物生存的基础,当然也是健康的必备条件。
2.3 自然合理与植物健康
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是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自然合理就是中国的哲学思想,它强调一切都要合乎事物的本性[45]。
自然合理与植物健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种植在适宜的生态区域:在合适的区域种植适宜的植物(种、品种或特定类群),才符合本性和本质。(2)生长发育规律:对于每一种植物或品种或类群,种植的季节和时间、收获的季节和时间,种植密度,生物产量(负载量)等都有特征、个性、规律,自然合理就是按照个性和规律进行种植和对各生育期进行管理。如:适时播种、适时收获等。(3)营养需求(土肥水)规律:植物的营养需求规律,是植物本性和本质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不同的植物、甚至同一种植物(或品种或类群)在不同的生育期(生理阶段)对各类营养成分需求的种类和量不同,甚至差异巨大。找到和理解植物各生育时期的营养需求规律,并参照营养需求规律对植物进行水、肥供应,满足各生长阶段营养需求,维护养分之间的平衡,让植物自然合理地生长、发育和繁衍,以保证植物健康。(4)最少的干预:人们一个惯性思路是“想到‘自然’就是不需要人为干预”。其实,这是误解,因为“自然”不等于“野生”。人类的干预是为了使植物更“自然”,因为植物的生长、发育、存活的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各种因素及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如果植物受到干扰和伤害后动态平衡被打破,植物就失去了“自然”状态。所以,在植物遭受威胁或伤害时,需要人的“帮助”,就应该采取人为干预措施。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有限度的、是渐进式的,人类的干预措施并不一定“功德圆满”,有时可能会“事与愿违”,所以人类的干预措施应该是慎重的,并且在采取干预措施时应该遵循最简单的方法、最少的措施、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等原则。
3 植物健康的概念
根据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结合西方哲学体系下对植物健康概念的讨论和争论,作者提出了如下植物健康的概念,供大家参考和商榷。
3.1 植物健康与植物种群健康
特定遗传基质的植物(种或品种或生物型等)生长在适宜的环境中(土壤、水分和气候),没有受到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因子侵扰和伤害,各种生理功能平和或平衡的自然状态。植株的这种状态,就是植物健康,或者说具有这个状态的植物是健康植物。
植物种群健康是具有特定遗传基质的种群(品种、生物型等),在适宜其生存的环境中(土壤、水分和气候)生活,当种群内所有个体都处于健康状态,或者个别个体健康受到干扰和威胁但这些干扰和威胁对种群的整体功能(景观、生态功能、生存、繁衍等)和功能平衡没有造成影响时的状态。
植物的健康状态,是实现植物生长、种群繁殖、生存机会、种群扩张潜力最大化的基础,是实现生物产量和/或质量最大化的基础。
3.2 植物健康概念的解释和内涵
3.2.1 适宜的环境
一个植物物种或品种在一定的环境条件范围内,能够正常生活、生长、繁殖,维持其物种(或品种或特定遗传群体)的生存和繁衍。这个环境(一定的气候、土壤、水和空气等条件)就是该物种(或品种或特定遗传群体)的适宜环境;具有这种环境的区域,就是该物种的适生区域。
对于一个植物物种而言,与其进化区域相比,同样或优于其进化区域的环境为适宜环境;对于人类选育的植物品种,与其选育和培育的场所相比,同样或优于该场所的环境为适宜环境。
3.2.2 特定遗传基质的种群(品种、生物型等)
可以是以“种”为单元的群体,也可以是以种以下的单元:亚种、生物型、生理型、生态型、品种等。对于人类种植的一些植物,有些是“种”水平上的物种,也有特定的遗传基质类群,比如水稻、玉米等使用杂交种,甚至有些植物品种是单倍体、三倍体的品种。
3.2.3 没有受到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因子侵扰和伤害
植物的健康状态,可以是没有受到侵扰和伤害的自然状态,也可以是受到了干扰或伤害之初,植物能够启动应急反应、功能增强、阻止伤害或避免伤害,对于轻微的伤害有能力补偿或恢复的状态。这与文献中弹性或补偿力的观念一致。
3.2.4 各种生理功能平和或平衡的自然状态
平和就是适度,就是恰好,既不过,也没有不及。不用应急反应、没有必要增强某一方面的生理功能,各生理机能有条不紊进行。平衡,就是各器官、组织及它们的功能之间配合得当、恰到好处。自然状态是植物应该具有的本然状态。植物没有受到胁迫就平和,平和中有平衡;植物受到胁迫时,一些机能(防御反应、应急反应等)不平和了,但各种机能平衡。这两种情况都是属于健康状态。
对于植物本身,维护和保持各种生理功能平衡三个最为重要的内容是:植物对营养的需求和环境营养供应能力的平衡、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平衡、植物健康水平与生长量(负载量)的平衡。对于植物之外,维护和保持的各种生理功能平衡也有三个最为重要的内容:避免有害生物的侵害、避免植物种群内部的竞争、避免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的竞争及化感作用。
3.2.5 植物健康状态有一个范围
植物健康状态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都是健康的。健康状态的范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同一个群体中的不同个体,在同一个时间序列、同一个生育阶段、同一个时间点,且在同一环境中生长,都是生理功能平和或平衡,但它们个体之间有差异,差异有一定的幅度,在这个幅度内都是健康的。这种差异是在同一‘平衡’水平下的差异,不会导致生长量或品质或产量的统计学差异。二是对于同一个群体中的不同个体,在同一个时间序列、同一个生育阶段、同一个时间点,在不同环境(比如不同肥沃水平的土壤)中生长,生理功能即平和又平衡,但平衡的水平不同(高水平、中水平、低水平的平衡),这种差异有一定的幅度,甚至这种幅度非常大,在这个幅度内也都是健康的。但这种差异是不同‘平衡’水平的差异,会导致生长量或(同一产量下的产品)品质或(同一品质下的产品)产量的统计学差异。
3.2.6 植物健康状态的时间序列
从时间上看,植物健康是一个时间点或相对短的时间间隔内的一种状态。植物有多个生育阶段,对于多年生的植物每一年还有年生育周期,植物的健康是一个随着时间可能发生变化的状态。如果说某个植物健康,是说现在健康,之后是否健康,是未知的。即种子健康、苗木健康,不能确定发芽后也健康(发芽后可能遇到病虫害危害);同样,萌芽期健康也不能确定之后就健康。
人类种植植物,是希望植物从种子(或种苗)一直到收获都健康。这个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维护和保持植物的健康。
3.2.7 植物健康状态的前后关联
对于一株植物,现在的健康状况与它之前的健康状况、之后的健康状况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关联性又有随机性。具体说,一株植物现在健康,并不能确定之前是健康的(之前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受到病虫害的侵害但后来又恢复了健康);同样现在健康也并不能确定之后就一定健康(之后有可能继续保持健康,也有可能受到病菌侵染变为不健康)。
3.2.8 植物健康的维持
植物健康的维持有两个方面:(1)种群生存稳定和种群扩张潜力的维持。从生态学上讲,种群的生存稳定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种群数量的稳定和遗传多样性丰富度的稳定。一般情况下,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种群数量在一定的水平上,就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当一个物种或种群的个体数量不足够大时,它的遗传多样性的丰富度不足,这个物种(或种群)就有灭绝的危险:大熊猫、金丝猴、白鳍豚等就是这样。所以,保持其足够的种群数量是一个种群健康的基础。此外,种群内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和充分的基因交流,是维持种群生存稳定的另一个基础。因此,延伸出来的植物健康,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植物物种自然资源的保护:保护其遗传多样性。保护其遗传多样性的基础和条件就是让它有足够的生存环境。(2)植物健康的维持。植物的健康状态,是实现植物生长、种群繁殖、生存机会、种群扩张潜力最大化的基础,是实现生物产量和/或质量最大化的基础。植物健康的实现和维持需要把植物种植在适宜的区域、各种营养元素平衡、没有病虫害等有害生物的危害、生长量与负载量平衡等。
4 植物健康和农林作物栽培
一个适宜的植物健康概念,应该能指导植物种植和栽培,为人类从事农林业生产服务。植物健康是一个相对短时间段的一种状态,是动态的;人类从事农林业生产,需要让植物在长时间(甚至整个生育周期)维持在健康状态中。在适宜区域种植适宜的植物种类、健康的植物繁殖材料、把植物种植在没有有害物质(病虫害和有害化合物)的土壤中,是植物健康的基础和条件;植物栽种后健康状况的维护(适当和及时的干预措施:栽培措施、病虫害防控等),使植物一直在健康状态下生存、生长,是实现农林业优质生产、产量和/或质量最大化、可持续发展的可靠途径。
4.1 植物健康的栽培基础
4.1.1 作物在适宜区域种植
一种作物或一个品种是否适合于在某一生态区域进行种植和栽培,首先需要对生态因子进行对比分析:生态区域的土壤、气候等,与原产地的进行比较。同样的、相近的、类似的,才有可能种植和栽培成功。如果有可能种植成功,就可以进行种植区试。
经过区试试验,能够在自然条件下生产出与原产地品质一样或优于原产地,并且产量水平在经济上可行的,就可以进行产业化种植或生产性栽培。区试试验也包括栽培措施上的优化和调整,以保证引种或种植的成功。引种也可以在缺少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试种,在试种的基础上进行区试。
对于适宜种植的区域,可以根据多年的经验和数据积累,把生态区域内的土壤类型、微气候、海拔高度等生产要素与品种或品系的对应关系进行划分,在适宜区内部形成品种或品系的区域化种植,形成地理标记产品。
4.1.2 植物繁殖材料的健康
健康的植物繁殖材料(种子或苗木)最基本的条件是没有携带病虫草害等有害生物。没有携带病毒病(脱毒种子或苗木)、繁殖材料的消毒处理、繁殖材料的检疫等,都是保证健康植物繁殖材料的措施或重要内容。从总体上,通过检疫经过消毒的脱毒繁殖材料,被认为是健康的植物繁殖材料。
4.1.3 土壤处理与消毒
土壤消毒的目的是杀灭土壤中存在的有害生物(最重要的是线虫类病原)及土壤中的有害化合物(自毒物质等化感物质),从而保证植物栽种后的健康生存和生长。土壤消毒是保证植物健康的重要基础措施之一。
4.2 栽种后植物健康的维持
4.2.1 土壤条件与栽培密度
土壤条件(团粒结构、营养水平、持水水平等)、当地的气候条件(光照、雨水)、灌溉条件等,决定了该区域一株植物根系的生长量;根系的生长量,决定了植物地上部分的大小和状态。地上和地下的平衡,是植物持续健康的基础。所以,应根据地域生态类型、植物的结构特点和特性,确定植物的栽种密度。
4.2.2 负载量与科学合理的水肥供应
根据植物的营养需求规律、土壤营养供应水平(土壤检测)、产量水平(负载能力、带走的营养元素数量),确定施肥和水分供应时期、使用肥料的种类和施肥量,实现需求与供应的平衡、负载量与营养供应水平的平衡,维持植物的健康。如果土壤营养供应在较低水平,但能实现低水平下的营养供应与需求的平衡,就可以进行(一定品质下的)较低产量的农林生产;反之,可以进行较高产量的农林生产。
4.2.3 田间管理措施
对植物在田间分布、密度、水分供应等进行管理,使植物免受生态胁迫或在受到胁迫时能保持平衡状态,维护植物的健康状态。
4.2.4 增强抗逆性
增强植物的抗逆性,是特殊区域或特殊阶段的维持植物健康的措施。比如利用抗性诱导技术或产品,在特殊的时间段或特殊区域,增强植物抗逆水平,以抵抗该时间段的某种生态胁迫,维持或维护植物健康。
4.2.5 栽培方向调整
在健康水平范围内,调整栽培方向,使作物及作物产品符合特殊用途(比如:饲料用、食品原料或复合农业生产等)。
4.2.6 有害生物的防控
对农林作物病虫害进行预防和综合治理,使植物免受伤害,维持和维护植物的健康状态。
4.2.7 葡萄产品与贸易
从植物健康概念出发,进行作物健康栽培,生产系列农产品;这些应用系列健康栽培技术措施生产出的产品,应该没有携带危险性病虫害,也应该符合质量安全标准。这也与Döring文献讨论中“植物健康的概念可以用作植物卫生和国际植物贸易有关的技术术语”的论点相符。
本文仅为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共同讨论、丰富和完善植物健康概念;随着对植物健康概念的不断讨论与完善,形成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一个被广泛接受植物健康概念的框架、内涵和哲学体系,可以引领和规范植物保护学科相关工作开展。
[1] Döring T F, Pautasso M, Finckh M R, et al. Concepts of plant healthy-reviewing and challenging the foundations of plant protection [J]. Plant Pathology, 2012,61: 1-15.
[2] 杨家书,张恩禄.麦田保健剂应用研究[J].辽宁农业科学,1996(4): 30-34.
[3] 王宗标, 王幸, 徐泽俊, 等. 植物保健剂对大豆产量及农艺性状的影响[J]. 江苏农业科学, 2013, 41(6): 85-86.
[4] 姜学玲, 董超, 于忠范, 等. 养乐多植物保健剂在苹果上的应用效果 [J]. 烟台果树, 2003(1): 35.
[5] Ebbels D L. Principles of plant health and quarantine [M]. Wallingford, UK: CAB International, 2003.
[6] MacLeod A, Pautasso M, Jeger M J, et al.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plant pests and challenges for future plant health [J]. Food Security, 2010, 2: 49-70.
[7] Schimitschek E. Zum krankheitsbegriff, disposition und vorbeugung im forstschutz [J]. Zeitschrift für Angewandte Entomologie, 1952, 33: 18-31.
[8] Tang D, Christiansen K M, Innes R W. Regulation of plant disease resistance, stress responses, cell death, and ethylene signaling in Arabidopsis by the EDR1 protein kinase [J]. Plant Physiology, 2005, 138: 1018-1026.
[9] Gimmler A, Lenk C, Aumüller G, et 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philosophical, med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M]. Münster, Germany: Lit Verlag, 2002.
[10] Schramme T. Lennart Nordenfelt’s theory of health: introduction to the theme [J]. Medicine, Health Care and Philosophy, 2007, 10: 3-4.
[11] Hamilton R P. The concept of health: beyond normativism and naturalism[J]. Journal of Evalu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2010,16: 323-329.
[12] Boorse C. Health as a theoretical concept[J].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77, 44: 542-573.
[13] Lucas J A. Plant pathology and plant pathogens [M]. Oxford, UK: Blackwell Science, 1998.
[14] Jansen S.“Schädlinge” Geschichte eines wissen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konstrukts 1840-1920[M]. Frankfurt a M, Germany: Campus-Verlag, 2003.
[15] Kroma M M, Flora C B. Greening pesticides: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rm chemical advertisements[J].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03, 20: 21-35.
[16] Abrams J, Kelly E, Shindler B, et al. Value orientation and forest management: the forest health debate [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5, 36: 495-505.
[17] McRoberts N, Hall C, Madden L V, et al. Perceptions of disease risk: from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e judgements to 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J]. Phytopathology, 2011, 101: 654-665.
[18] Wiegert R G. Holism and reductionism in ecology: hypotheses, scale and systems models [J]. Oikos, 1988, 53: 267-269.
[19] Nagel E.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problems in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M]. New York, Chicago: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1.
[20] Stakman E C. Plant diseases are shifting enemies [J]. American Scientist, 1947, 35: 321-350.
[21] Makepeace J C, Oxley S J P, Havis N D,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fungal and abiotic leaf spotting and the presence of mlo alleles in barley [J]. Plant Pathology, 2007, 56: 934-942.
[22] Smuts J C. Holism [M]//Garvin J L, Hooper F H, ed.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4th edn. London: Encyclopaedia Brittanica, 1929: 640-644.
[23] Ferretti M. Forest health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issues for consideration [J].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1997, 48: 45-72.
[24] Lammerts van Bueren E T, Struik P C, Tiemens-Hulscher M, et al. Concepts of intrinsic value and integrity of plants in organic plant breeding and propagation [J]. Crop Science, 2003, 43: 1922-1929.
[25] Cook R J. Biological control and holistic plant-health care in agriculture [J]. American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griculture, 1988, 3: 51-62.
[26] Comeau A, Langevin F, Levesque M. Root health: a world of complexity [J]. Phytoprotection, 2005, 86: 43-52.
[27] Rapport D J, Costanza R, McMichael A J. Assessing ecosystem health [J].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1998, 13: 397-402.
[28] Balfour E. The living soil [M]. London, UK: Faber and Faber, 1943.
[29] Kelly E, Bliss J. Healthy forests, healthy communities: an emerging paradigm for natural resource-dependent communities?[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09, 22: 519-537.
[30] Dürr H P, Popp F A, Schommers W. What is life? scientific approaches and philosophical positions [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2.
[31] Sheldrake A R.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M].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8.
[32] Kozlov M V, Zvereva E L, Zverev V E. Fluctuating asymmetry of woody plants [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9, 15: 197-224.
[33] Yan Y, Popp F A, Rothe G M. Correlation between germination capacity and biophoton emission of barley seeds (HordeumvulgareL.)[J]. Se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3, 31: 249-258.
[34] Popp F A. Die botschaft der nahrung [M]. Frankfurt/M, Germany: Zweitausendeins, 1999.
[35] Schweitzer A. Kultur und ethik-kulturphilosophie zweiter teil [M]. München, Germany: C.H.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23.
[36] Lockwood J A. The ethics of biological control: understanding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our most powerful ecological technology [J].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1996,13: 2-19.
[37] Hofmeister G. Ethikrelevantes Natur-und schöpfungsverständnis[M]. Frankfurt M. Germany: Peter Lang GmbH, 2000.
[38] Ingensiep H W. Geschichte der Pflanzenseele-philosophische und biologische Entwürf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M]. Stuttgart, Germany: Alfred Kröner Verlag, 2001.
[39] Holliday P. A dictionary of plant pathology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0] 楼宇烈. 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底蕴[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6-06-14(10).
[41] 张茂聪. 生态学视野中的全纳教育观[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5): 140-145.
[42] 楼宇烈. 唤醒“自然合理”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8,14(S1): 1-3.
[43] 楼宇烈. 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1): 50-56.
[44] Gu S L, Du G Q, Zoldoske D, et al. Effects of irrigation amount on water relations, vegetative growth, yield and fruit composition of Sauvignon blanc grapevines under partial rootzone drying and conventional irrigation in the San Joaquin Valley of California, USA [J]. Journal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 Biotechnology, 2004, 79: 26-33.
[45] Dry P R, Loveys B R. Grapevine shoot growth and stomatal conductance are reduced when part of the root system is dried[J]. Vitis, 1999, 38: 151-156.
[46] Dry P R, Loveys B R, During H. Partial drying of the rootzone of grape. I. Transient changes in shoot growth and gas exchange [J]. Vitis, 2000, 39: 3-7.
[47] Dry P R, Loveys B R, Düring H. Partial drying of the rootzone of grape. II.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root development[J]. Vitis, 2000, 39: 9-12.
[48] Stoll M, Loveys B R, Dry P R. Hormonal changes induced by partial rootzone drying of irrigated grapevine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2000, 51: 1627-1634.
[49] 盛承发, 宣维健. 正确理解和应用经济阈值[J]. 昆虫知识, 2003,40(1): 90-92.
[50] 缪勇, 许维谨. 经济阈值定义等的讨论[J]. 安徽农学院学报, 1990(2): 137-142.
[51] Corneo P E, Pellegrini A, Gessler C, et al. Effect of weeds on microbial community in vineyards soil [J]. IOBC/WPRS Bulletin, 2011, 71: 19-22.
[52] Goss E M, Tabima J F, Cooke D E, et al. The irish potato famine pathogenPhytophthorainfestansoriginated in central Mexico rather than the Andes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4, 111: 8791-8796.
[53] Agrois G N. 植物病理学[M]. 陈永萱等,译.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7: 13-17.
[54] 弗赖伊 W E. 植物病害管理原理[M]. 黄亦存, 张斌成,译.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8: 1-11.
[55] 黄河. 马铃薯晚疫病[M]∥方中达.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 植物病理学卷.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96: 299-300.
[56] 周幸. 太行山山地林、药复合种植模式及技术探索[J]. 中国林副特产, 2008(4): 43-45.
[57] Zhang Xiangqian, Huang Guoqin, Bian Xinmin, et al.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advantages of intercropping [J]. 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2012, 4(12): 126-132.
[58] Molnar T J, Kahn P C, Ford T M, et al. Tree crops, a permanent agriculture: concepts from the past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J]. Resources, 2013, 2: 457-488.
[59] 李新平, 黄进勇. 黄淮海平原麦玉玉三熟高效种植模式复合群体生态效应研究[J]. 植物生态学报, 2001, 25(4): 476-482.
[60] 王忠跃. 防控葡萄根瘤蚜复种植物筛选及防控机理研究[D].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4.
[61] Hofmann A. Ergot—a rich source of pharmacologically active substances [M]∥ Swain T, ed. Pla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in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236-260.
[62] Ward T J, Bielawski J P, Kistler H C, et al. Ancestral polymorphism and adaptive evolution in the trichothecene mycotoxin gene cluster of phytopathogenicFusarium[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 99: 9278-9283.
[63] Coxon D T, Curtis R F, Howard B. Ipomeamarone, a toxic furanoterpenoid in sweet potatoes (Ipomeabatatas) in the United Kingdom [J].Food and Cosmetics Toxicology,1975,13(1): 87-90.
(责任编辑: 田 喆)
Discussionontheconceptofplanthealth
Liu Yongqiang1, Zhang Hao1, Wang Zhongyue1, Liu Chonghuai2
(1.StateKeyLaboratoryforBiologyofPlantDiseasesandInsectPests,InstituteofPlantProtection,Chinese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Beijing100193,China; 2.ZhengzhouFruitResearch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Zhengzhou450009,China)
Though the term ‘plant health’ is frequently used in plant science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plant protection, however, it still has no clear substantial definition that is well accepted. In this paper, we reviewed the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on the concept of plant health. We propose the concept of the plant health based on the core thoughts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at the plant health refers to the natural states of dynamic balance of plant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a specific genetic plant when grow in prope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without perturbation by other biological invasion or extreme environmental injury and stresses. This definition emphasizes the dynamic property of plant population health. We further analyzed the potential significances of the new definition for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plant health; definition; Chinese philosophy

特约稿件InvitedPaper
S 4
: ADOI: 10.3969/j.issn.0529-1542.2017.05.001
2017-08-22
: 2017-08-31
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CARS-29-bc-5)
致谢: 本文承蒙吴孔明院士和钱旭红院士审阅并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作者据此对本文进行了删改和补充。此外,本文在三年成稿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行老师的指点,在此向所有对本文提供建议和意见的各位专家表示感谢。
* 通信作者 E-mail: wangzhy0301@sina.com
#为并列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