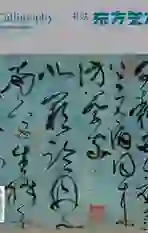海岳庵奇观:风格与中国艺术家
2017-07-20石慢
[美]石慢
北固山伫立于扬子江的南岸,坐落在江苏省南部的镇江市内,山高虽不到190英尺,但地势绝佳,在北固山上可远望山下城区的景色,领略中国境内最为宽广壮美的河流。游客们通常会取道镇江,经过宜人的林间小路,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建成的铁塔前稍作停留,随后便可到达甘露古寺。古寺往日峥嵘已不在,但是有心的游客仍可通过阅读寺内标示联想到公元六世纪、八世紀时的著名画家张僧繇及吴道子在大殿内绘制壁画的光景;亦或想象自己正如古代最德高望重的诗人才士一样,登上北固山观赏壮阔的山川美景。其中一位常登山揽胜的名士便是士大夫文人米芾(1052-1107/8)。米芾精通书法,且个性独到,其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为蓬勃兴旺的时期之一。北宋年间(960-1127)镇江又称润州,米芾移居至此,选址北固山西坡上,在寺庙和甘露铁塔的庇荫之下,筑起了自己的书庵。一个直至现在都广为流传的故事讲的就是曾有人看到米芾从一位文化底蕴深厚的藏家手中购得这片宅地,对方交易所得并非钱财而是一座形似山峦,且有三十六峰顶的研山石,而这座研山曾为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所有。【1】米芾在一块匾额上题字“天开海岳”,意为上苍掀开大海与山川,同时为自己的书斋取名“海岳庵”,即“山海间的屋舍”,以纪念眼前美景。米芾之子米友仁(1074-1151)的一幅绘画作品保留下了旧时家族书房的面貌,画中还呈现出城东圃冈上新筑书屋向外眺望之景色。【2】游客若从西南山脚下新落成的公园走进来,会先路过人称公元三世纪的“试剑石”古迹,随后在通往庙口的无名小路旁边就会找到米芾的海岳庵旧址。现在的海岳庵被船厂包围着(译者按:镇江船厂已于2002年开始实施搬迁,截止2015年,船厂已不在北固山景区内)。据镇江博物馆前馆长陆九皋先生介绍,为纪念海岳庵所建的三间展室一直都设在书屋旧址处,直到20世纪60年代其沦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初期的牺牲品。
对米芾尤为感兴趣,且颇有胆识的游人可能会穿过铁道去南边逛逛,经过化肥、水泥还有陶瓷厂的厂房,抵达城乡交界地带,紧邻着黄鹤山的鹤林寺就曾经伫立在这片土地上。1984年,我首次循沿这条线路前往镇江,通过城镇地图上的标识,寻找米芾墓的位置。很不幸的是,镇江市的地图测绘人员没能考虑到当地的人为因素作用,地图上标记的米芾墓的前方入口这几年已经被拆除,卸下来的石材则被当地人用来修建房屋和桥梁了。之后米芾墓被重新安置到黄鹤山西北坡之上,墓门口的通路已重修,三根立柱也已恢复,学者启功的书题亦为这里增色不少。百米之外真正的米芾墓地似乎并不影响这里的一切;朝圣者们终于拥有了一块向米芾致敬的圣地。
现代化发展尚未萌芽时的中国人出于敬畏之心及参与精神而向先人致敬的习俗与现代人的习惯大相径庭。尽管镇江市对米芾墓的重建工作值得称赞,但细读一下当地近百年来的地方志就能看出,这片土地上的曾经存在的古迹如今还有多少残存了下来。如今的鹤林寺由于被当地住户占用着,昔日面貌已不复存在,寺内留下诸多颂赞米芾的言辞,可知他常前往寺中探访并研习禅宗。米芾的墓志铭碑碣最早就在鹤林寺中,墓志铭文由友人蔡肇为其撰写,碑上还刻有米芾小像以及米芾之子米友仁的题识,米芾墨迹也辑刻于石碑之上。此外,米芾双亲的墓碑也安置在黄鹤山上,相传米芾还在这里修建了一处居所。在米芾去世后不久,便有人为他修建了一座祭祠,并遵其为“护伽蓝神”,不过这个说法更像是佛门佳话而并非真有其事。【3】
北固山之于米芾还远不止于此。米芾的一位忠实追随者岳珂 (生于1183年),从十三世纪初始,对米芾旧时的书庵进行了数次翻修,修葺旧所又建筑新居,每次动工俱有记载留存。岳珂四处搜寻散佚的米芾真迹时找到了曾经的研山园并住了下来,同时重新收集整理众多逸亡的米芾文稿。【4】明宣德(1426-1435)及万历年间(1573-1615)一些地方重臣重建了米芾的书斋。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又在原址处修建了藏书室。其中自然也少不了米芾和其仰慕者的书迹刻石、木制牌匾。连清帝康熙(1662-1722在位)也在一次疆域巡视时御笔亲题了“宝晋遗踪”字样,以追思米芾。【5】
镇江之外留下更多关于米芾的可寻之迹。湖北省襄阳市在米芾家族的旧产上建起了米氏祠堂。【6】米芾青年为官游历广西、广州、湖南一带时曾写下题记,追随者们记录下了这些米芾走访过的地方,并在这些题记旁留下了溢美之词。【7】江苏省北部的涟水县仍可见米芾萍踪,1725年(译者按:雍正三年),即米芾在此居住的625年后,当地知县仍在洗墨池旁缅怀先贤米芾,尽管处于当时环境下的米元章并不一定有这样的意愿。【8】现在的中国版图上,还能找到安徽无为现存的一座米公祠,这里也是米芾生平最后为官之处,此地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米芾拜奇石为兄的故事。【9】
熟悉且关注中国历史的人们或许对米芾在时间长河中留下的浓重笔墨并不感到惊讶,然而据此思考米芾身名流芳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其中出现了中国有关圣贤之标准的引述,当被问及“死而不朽”的涵义时,鲁国大夫叔孙豹回答了“三不朽”(three non-decays),即立德、立功、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0】尽管还不清楚有哪些树立德行的例证,但无论如何,人们怀念米芾的理由都与立德无关。为国效力,建功立业或是发表真知灼见亦不是米芾青史留名的原因。如果说个人价值的准绳体现在德与尽忠犬马之具体表现上,亦或是宣讲至理名言上,那么上千年来米芾为世人所熟知的原因其实是他将内在德行转而呈现在了外化的风格上面。米芾之名全部仰仗于他在书法、绘画方面的功力与艺术鉴藏水平。然而这些至多是中国传统中第二等重要的追求目标,不曾成为古人通往不朽的途径。
米芾事迹之所以值得回味,某种程度上是缘于他对不朽之名的竭力追求,不过更加引人瞩目的一点是他最终认识到不需要史训中的“三不朽”,转而通过不羁的艺术道路也可达成不朽之目标。米芾在《画史》(A History of Painting)的序言中毫不避讳争议,大胆披露自己的观点,对传统理念发表了一番戏谑之言。我们现有的资料是米芾对唐代文人画家薛稷的一幅《二鹤图》和杜甫(712-770)为薛稷所作诗句的评注:
杜甫诗谓薛少保“惜哉功名迕,但见书画传”。
甫老儒,汲汲于功名。岂不知固有时命,殆平生寂寥所慕欤?嗟乎!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之笔精墨妙摹印亦广,石泐则重刻,绢破则重补,又假以行者何可数也。然则,才子鉴士宝钿瑞锦缫袭数十,以为珍玩,回视五王之炜炜,皆糠粃埃壒,奚足道哉!虽孺子知其不逮少保远甚。【11】
米芾赞许薛稷的绘画成就高于“唐五王”的犀利评语在清代所辑录的皇室藏书中被编者隐去了,不过这个例子充分体现了米芾的狂妄,如此也证实了乖张是他被众人所熟知的标签。有人认为“尽管(这样的评论)存在,却无需讨论它。”【12】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尽管米芾的言论原本确为展现其癫狂的个性,然而无视这些评论就等于忽略了一位天赋异禀的艺术家最关切并且触及绝大多数中国艺术家本质的问题。
此问题关系到风格以及中国人最初对其价值的认知,它们是表现品性的途径,而正是这些品性构成了主体的内容或核心。主体(subject)在本文中指通过人创作出来的结果,而不是绘画或诗词中所描述的对象。人们通过呈现主体的方式来认识主体本身。也正因为如此,先贤们的著录中曾写过,宫阁之内传出的乐声可判断出当时德行基准的高低。观众通过艺术家创作的诗词来评判他的品性,写书法也是如此。米芾宣称粗浅物化、浮夸讨巧的仙鹤图竟然比唐代忠烈之仕高尚的事业更有价值,这样激烈的言辞无疑冒犯了清朝皇家的典籍编纂者们。个人的艺术创作可以表达其核心的品性,其實米芾不过是根据这种假设追寻一个结论而已,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品性比仕途成就更有可能流芳后世。不知道唐代诗人杜甫是否也怀抱这样的想法。一生忧虑如何使自己的德行、声名留世的米芾意识到能成为不朽的唯一希望就只有他的艺术造诣,所以米芾选择通过风格立德。在《画史》的序论中,米芾近乎荒诞地把这一观点发挥到了极致,说出了旷古之语:艺术是第四个“不朽”。
这是一本与风格有关的书。更确切的说,与中国艺术风格及其表现有关,它的阐述用语在译成英文时通常概括为风格(style)二字。区分这两者异同十分重要,因为分析风格者——李奥纳多·梅耶尔(Leonard Meyer)这样称呼他们,发现风格的概念在中国传统中和西方语境下所担任的角色、职能截然不同。【13】首先我们有必要引入几点关于差异的鉴别问题,如此才能建立起本书讨论的界限,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大程度上搞不清楚要区别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自1953年梅耶尔·夏皮罗(Meyer Schapiro)发表关于风格的重要文章以来,艺术史家、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还有音乐学家等都发现风格一词在英语中的运用是多样化的,他们谴责对“风格”一词的滥用,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应当还原这个词的本意。然而在实际观察之后发现,人们仿佛受了海森堡(Heisenberg)测不准原则的影响,无法拿捏风格二字的尺度。拜瑞尔·朗(Berel Lang)曾经说过:“当我们探索区别人类特质的核心地带——即探寻产生视角或思维理解(vision or understanding)功能的组织结构本身时,我们越接近它,就越难以理解其物化形式的核心组成因素到底是什么。”【14】
在拜瑞尔·朗的文章《风格作为手法,风格作为人》中,他提出风格的两种模式,从英语文法角度来讲,一种叫做“状语式”,另一种则称为“谓语式”或“及物动词式”。状语式风格认为“事物”本身与其表现形式应相互独立(通常举例说明都会用到这句话,“主体是说什么,风格是如何说。”)。依照这种分离的状态来考量,风格便可以和工具一词联系起来,且这个词(style)的词源与拉丁语 “stilus(stylus)”相符合,意思是赋予书写形式的工具。“风格作为手法”是一种可归类的模式。这样一来,它意味着艺术作品是可“处理”的,这种说法确实在艺术史的实践中被普遍采纳,为了弄清作者、创作年代、相互关系以及影响力的大小,风格一直都起着描述性的作用。艺术中包括时间、空间甚至社会语义都能用风格来说明。但是拜瑞尔·朗所认识到的风格却是人类心智与双手所创造的终极产物。他强调风格的概念是“一种典型化并自成一体的模型”。【15】这就是他认为的及物动词模式的风格,突出强调“说什么(what)”与“如何说(how)”之间并无区隔。与第一种模式相反,第二种风格带有“及物性”,表明过程即是艺术作品本身 ,而这其中存在一种形式同内容互为因果的关系。风格不是中心内容的外皮,而是整个有机统一进程的一部分,这一切根源皆来自人的传达。朗在文章中写到:“观者区分风格特性时的过程与认知创作人的过程相关联,因此观者意识到的某个特定风格既包含创作的人,又有创作人的传达媒介或审视视角,这些因素都作用于观看人时,他便可察觉到风格的存在。”【16】
我采用拜瑞尔·朗的观点是因为风格作为人的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风格的看法几乎完全相符。浏览一下中国语言中与风格有关的词汇就能发现其中的一些与拜瑞尔·朗文章中名为“由表及里的风格”的章节里所叙述的部分相似。风格一词是最常见的两个汉字组成的复合词,其中着重强调象形字“风(wind)”,类似的词还有“风格(category of wind)”,“风度(measure of wind)”,“风调(tone of wind)”。然而,最能表明“风”字的功能的词汇,是最先开始与其搭配的“骨(bone)”字。刘勰(六世纪早期)的著作《文心雕龙(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里一段常常被人们引用的段落便写到“风”是“化感之本源”:有感化力量的风可引导并影响人,使风产生作用的强大力量是骨,骨可使文辞条理清晰、融和统一。【17】严格地说,刘勰在文中所用的“骨”字其实是判断文章写作品质优劣时所用的具象比喻,并非判断人之优劣,然而通过“风”之力可将一人思想和情感传递给他人,因此这种自然延伸之喻又可以用来深度解析文章写作之人。
中国书法中关于身体的比喻随处可见,约翰·惠(John Hay)在自己的文章中已经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现象。【18】“血”、“骨”、“筋”、“脉”,全部都是衡量作者写作优良程度的关键词。再次重申,上文中列举这些的是身体某些部位的汉字写法,但若更进一步理解,就可以从某个书法家的书写形态中观察到笔墨背后所隐含的个人感情、心理甚至身体的特质。因此在中国书法相关文献中称风格为“体(body)”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拿“颜体”、“柳体”(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和柳公权的书法风格)来说,这两种书体的基本程式常为后人所使用,同时也反映出两位书法家强烈的个人风格。

对外表达的概念使风格局限于艺术家个性的层面,也许有人认为用格调、心声等词语形容艺术家内在品质会更适合。这类词同样能传达出艺术表现的不固定性,从个体角度出发,风格是最难以描述的,更不要说进一步的分析与衡量了。不过也正是基于这点,中国式的风格为艺术史学者们建立出一套迥异的基本准则。首先了解“风”的感化力和它与身体结构间的渊源,促使艺术家有意识地形成自己的风格。中国的书画论著中明确表示以上结论还远不够完美。理想化的模式应为艺术家纯粹的表达,而沟通之责全由观众承担,“知音者”即“理解音乐的人”,(艺术家创作乐曲的最佳聆听者)。【19】然而,一旦意识到(或期望)有倾听者的存在,大多数艺术家的音乐创作方式就会受到影响。言简意赅地说,就是当知道自己的诗词或书法作品将被视为本人的外延,从而为观众所审视时,艺术家会激发出操纵其作品面貌,对风格进行设计的愿望,对于拜瑞尔·朗所说的作为产生视角和思维理解功能的组织结构,也就是所谓含糊的核心地带,这样有意为之的操控设计对消除核心的含糊不定性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艺术家对风格的知觉,褪去了一层模糊无形的神秘外衣。风格成为了人类意愿的产物,而意愿是可以被描述、追溯以及分析的,这与人所做的其他有意识的决定是一样的。中国人的核心称为“德”,风格即是“德”的反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艺术家认识到并掌握這一特点后,风格反而成了由外及内的形式。对于要解答风格倾向性问题的艺术史学家,这是一种方法论式的暗示:整个过程更接近于史料分析,而非诠释演绎。不过要明确的是,这种方法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家。总体来看,只有士大夫阶层,教育程度高的菁英,也就是文人群体才对个人风格有自我意识。文人拥有最高等级的社会地位,在德行操守、治国献策、事务经纶以及最不重要的艺术领域,他们都时时进行内省且需要受他人审度。所有的这一切皆观照内在的品质和品德。在最为关心排行中位列末等领域的人看来,无论是诗歌、书法还是绘画,风格成了他用来说服外界,展示自己内在价值的重要因素。
没有人比米芾更观照艺术,也没有人比他更富于自我意识。他利用艺术来展示个人品行的想法也感染了他的儿子,米友仁,米友仁曾画下海岳庵景,取名“潇湘奇观”图,这个名字容易误导观者,以为米友仁所绘的确实是润州向南距离大约一千公里,位于湖南省的“潇湘”二河交汇之景。而且尽管米友仁在后附的跋文中明确写到画中景色即润州米氏海岳庵之景,然而将画中场景看作是主体的真实写照仍是不正确的看法。这幅画是米友仁为他远在几十公里外,于南京任职同僚仲谋所作的,彼时的润州(1137年)无可值得一画(大约7年前,由于北宋和女真部族间的激烈征战,润州城已几近成为碎石瓦砾),因而这件作品其实只是象征性的描绘而已。仲谋和其他生活在12世纪的观者一见画作,就可联想到海岳庵以及其声名远播的主人米海岳。(中国人通常都熟识书斋的名称,因为米芾别号为米海岳)米友仁在题跋中引用当时的著名学士为米芾及海岳庵所作诗文,这便充分赋予了这幅画的辨识性身份。米友仁作此画用以怀念米芾之成就,然而与其他为数众多追思米芾的后人相比,米芾之子所采用的方式不同寻常。
米友仁的画不仅仅是家族书屋面貌的记录。实际上画面中的聚焦点不是海岳庵,而是绵延至书屋所在地的景致。从右至左展开画卷,首先映入观者眼帘的是正延展开来,卷曲怪奇的云彩;随后是绵延的山丘;直到画面的最后才出现群山环抱下的海岳庵。米友仁题到:“此卷乃庵上所见,大抵山水奇观,变态万层,多在晨晴晦雨间,世人鲜复知此。余生平熟潇湘奇观,每于登临佳处,辄复写其真趣……此岂悦他人物者乎。”
“高人逸才”苏轼(1037年-1101年)早在他生活的年代就提出关于 “虽无常形,而有常理”的概念,以烟云为例,虽形态万千,但其存在的本质不变。【20】米友仁对苏轼提出的挑战毫不避讳,为实践子瞻之观点,米友仁利用手卷形式具有时间性的特点,使人在时间和空间的横轴上穿梭。然而在米友仁的绘画方式却出现了峰回路转之态,当看画人的时间之旅开始时(从右向左移动),会被弥散的怪奇云朵所困惑,不见任何常理逻辑的踪迹。这是因为云彩的浮动方向与人们观看的方向正好相反,是从左边延展至右边的。观者只有在浏览至画作的结尾处,看到米芾的海岳庵和米友仁的跋文时方能意识到,这才是看潇湘奇观图最好的视角。画家其实在期待着我们产生乍看时的困惑感(“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这实际上是米友仁有意突出观赏重点的结果,若画家将海岳庵的位置安排在手卷的最右侧,则任何人皆可展卷即尽收眼前美景。米友仁将家族书斋置于卷末,也是将他(及米芾)的视角同我们的区分开来,并且让我们了解到只有反观他的作品才可瞥见“奇观”的真意。米友仁绘画的真正主体既不是海岳庵,也不是周边景色,而是观赏的角度,一种私密的视角以及私密化的观赏行为,又或者称之为拜瑞尔·朗所提出的个人视角与传达。
朗暗指的“核心”,即“作为产生视角和思维理解功能的组织结构”。这个核心的组成因素是如此隐蔽,以至于我们越接近越难觅其踪影,而米友仁画中之云刚好象征着这个说法。云的存在暗示着常理的无常性,以米友仁从父亲那里传承下来的视角为媒介表现出来,它代表着家族的美德,但为了不消除绘画的核心特质,即无常形的表达,因而不采用描绘细节的方式处理作品。从山坡上出现的云层从左向右浮动,缓缓舒展其挛蜷拳之势,画家用云彩运动的方式传达了他的逻辑,即为了表现其中的常理所在。正如米友仁隐匿了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独到的米氏视角一样,他亦将自己的私密隐曲在画面之中。最终“德”之定义变得迷离徜恍,其内在深意只可凭人揣测。
与一般的画作不同,米友仁绝不规避作品应流露个人品行的概念,以至于这个概念成为他绘画的唯一主体,这在中国的艺术领域之中,即使是在文人当中都实属罕见。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我们会详述米友仁欲发扬光大的米氏视角及相关内容。相较于绘画,米芾所选择的表现媒介是书法,同时他磨砺自己的书写技巧,使其具备十足的表现力却又含精微神妙的独到之处,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书法自古以来就具备很强的表现力,从商代开始书法作为承载甲骨文的媒介,直到几千年后演变为纯艺术形式,其启示性意义得到众人的认可。从毛笔蘸上墨汁的一刻起,经过指肚、手掌、手腕到心和眼之间的一系列动作,最终与纸面合为一体。所有曾试着挥笔书写的人都知道,无论水平高低,一旦下笔,这些似是而非的单纯毛笔线条就变为了即成事实。毛笔下流露出的情感,在文苑儒林中人看来,便是见到了书写者本人的意象。即宋时人常说的“书为心画”。【21】
拜瑞尔·朗的及物式风格明确了作品作为过程的观点,这极适用于中国书法的语境。书法是单向性的艺术,因为其形式在时间上和图像上都是线性结构,也就是说书写的过程不可逆,最初运笔时的动势无法改变。留在宣纸或锦缎上的墨迹便是书写过程的全纪录。传统书论向我们展示了书法艺术中强调的非特意的思绪,即自然(naturalness,或直译为self-so-ness)的一面,这种非刻意的思索或许就产生了从内心深处连贯至书写表象上的线条的曲折。然而我们很有必要了解理论同实践之间存在的鸿沟,尽管自然之于书法促生了非自主状态的概念,但若认为书法只是一种生发于自然的艺术就等于否定了其展现艺术家意图的潜在作用。意识到自我的风格致使墨线出现了波磔,有趣的是,过于在意表现自然的书家也许反而会故意作态。在书家米芾的作品中就存在着自然状态与他一直加诸于书写中的意识,这两者间的博弈成为本书要阐述的核心主旨。
对于期望树立个人风格的艺术家,其目标就是制造一股持续而强力的“风”,米芾不仅在中国山水画的历史册页上留下了浓重的笔墨,更有多少后辈沿袭米芾之风,从这方面来讲,米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引言部分中最后一个要说到的,用来概括上述问题的术语实际上是一句成语:自成一家【22】,直译为“自己成为(找到)一类派别”,在实际运用中,这句成语的含义为“树立自我风格”。其中的关键字眼是“家”,上文中指思想或哲学学派。但是它词源上的象形意义却颇为质朴,(“家”字,即一头猪在屋顶之下。)这个汉字的本义与引申义十分相似。家(home),可指居所、家庭,这与米氏一族的关系十分密切,表面上看来,它就是米友仁所画的海岳庵。一个派别或一类风格的要义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古老的模式,即依靠家族和其族规的兴盛而传流下来。自成一家是艺术家个人风格的独创性和持久性的概括表达,可剖析其住所、家庭和追随者,三者关系构成的延展意义。本书厘清了此类风格从原点开始的发展路径。同时在后记中以米芾书庵为喻,阐释了米氏海岳庵何以成为中国艺术史中一块不朽的圣地。
【1】 蔡绦,《铁围山丛谈》(后文中皆简称蔡绦),卷五,96页。本书后记中有此段记述的翻译。
【2】 第二座海岳庵的修建位置尚不确定。公元1100年时甘露寺毁于火灾,此后米芾将海岳庵迁离旧址。
【3】 《鹤林寺志》,5b,6a,7a,18a-19b,20a-23b,27a,30a,32b,35a,38b-39b,41a-b,81a-b。肖像石刻推测是出自于广西桂林界伏波山上的石刻画像。
【4】 米芾文集今称《宝晋英光集》,由米氏润州宅邸的书斋中所藏晋人宝帖而得名,此集共八卷,补遗一卷,仅为米芾旧一百卷本的未十之一,原集名为《山林集》,于北宋政权倾覆之际,即12世纪20年代(译者按:靖康年间)散佚。世人将辑集《宝晋英光集》之功归于岳珂,他于公元1232年为此文集作序。然而最早开始辑佚米芾文稿的人是其嗣孙米宪,在一些版本中发现米宪于公元1201年所题的序文。北京图书馆(译者按:即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还藏有南宋刻本米宪辑《宝晋山林集》,其中收录了米芾其他的文稿,包括《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和《砚史》,见徐邦达《两种有关书画书录考辨》,63-66页。本书中所有对《宝晋英光集》的引用都源自市面可见的学生书局版本,此书中有清代抄本的翻印件,原件藏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依据公元1816年(译者按:嘉庆二十一年)阮元的题识可知,此清代抄本出自于刘克庄(1187-1269)的藏集,集内包含米宪辑录卷册(含米芾的“古赋”四篇)、岳珂《英光》本以及其他后来被认定是岳珂所录的文章。我(译者按:即本书作者石慢)校勘了年代更早的北京藏本,还有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Wu Yifeng(清代)所抄录的版本。(因此我所翻译的文献与学生书局出版版本略有差异。)岳珂增补诗文计17首并其他文类皆注“从英光堂帖册增入”,英光堂帖册指岳珂辑刻的米芾墨迹拓本。若想了解更多米芾书法相关的资料,可参见中田勇次郎《米芾》,1:167-182.
【5】 《北固山志》,卷二,10b-11a,20b-21b;卷四,8b,9a-10a,卷五,5a-6b。其中一些资料已由Gao Huiyang在《米芾家世年历考》总结。
【6】 《襄阳县志》,卷二,51ff。
【7】 翁方纲,“九曜石考”,收录于《粤东金石略》,补注,7b。方信孺,“宝晋米公画像记”,收录于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卷十一,21b-23b。《湖南通志》,卷二六九,5489;卷二七五,5605。以上参考综述可见Gao Huiyang,《米芾其人及其书法》,51-88。
【8】 《安东县志》,卷二,7a;卷十五,1b-2a。 《淮安府志》(叶长扬纂)卷二十八,16a。 《淮安府志》(陈艮山纂), 卷十四,5b。
【9】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15b。本书后记中有此段记述的翻译。米芾在无为时的其他相关材料见《无为州志》,卷4,2a-3a;卷14,3b-4a;卷28,1a-3a。
【10】 理雅各(Legge),《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5:505-7(襄公二十四年)。
【11】 米芾,《画史》,187。米芾引自杜甫《杜少陵集详注》中的《观薛稷少保书画壁》,卷十一,816-17。五王指唐人桓彦范、敬晖、崔玄暐、张柬之和袁恕己,五人与薛稷同时代,皆活跃于7世纪晚期。
【12】 《四库全书总目》,957-958页。
【13】 在与风格有关的大量文献中,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被认为最有利用价值:艾克曼(Ackerman),《風格的理论》(“Theory of Style”);贡布里希(Gombrich),《风格》(“style”);古德曼(Goodman),《风格的地位》(“Status of Style”);赫奇(Hirsch),《风格学和同义性》(“Stylistics and Synonymity”);库布勒(Kubler), 《关于视觉风格的还原理论》(“Toward a Reductive Theory of Visual Style”);朗(Lang),《风格作为手法,风格作为人》(“Style as Instrument, Style as Person”);梅耶尔(Meyer),《关于风格的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Style”);夏皮罗(Schapiro),《风格》(“style”)。
【14】 朗,《风格作为手法,风格作为人》,715。
【15】 同上,716。
【16】 同上,730。
【17】 刘勰,《文心雕龙校释》风骨第二十八,105-9。施友忠译,《文心雕龙(Literary Mind and Carving of Dragons)》,162-63。吉博斯(Gibbs),“关于风的解释(Notes on the Wind)”285-93。惠(Hay),“价值与历史Values and History”, esp. 86-87。栗山茂久,“风之想象(Imagination of Winds)”。
【18】 约翰·惠(Hay),《人体》( “Human Body” ) 。
【19】 “知音者”一词源于战国时代一位技艺精湛的琴师伯牙及其友钟子期的故事。子期死后,伯牙破琴绝弦,只因为知音子期离他而去。《列子集释》,卷五,178-79。格雷厄姆译,Book of Lieh-tzu,109-10。施友忠将“知音”译为“善解人意的评论者(An Understanding Critic)”,出现在刘勰《文心雕龙》第四十八;施友忠译《文心雕龙》,258-63。关于知音者角色的深入探讨,见欧文(Owen),《传统中国诗歌与诗学》(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54-77。
【20】 苏轼,《净因院画记》,出自《苏轼文集》,卷十一,367。布什(Bush),《中国文人绘画(Chinese Literati on Painting)》
【21】 “书为心画”出自汉代扬雄的《法言》。见《扬子法言》,卷五,十四。虽引用此说法的人数众多,然而把“书为心画”的语义从文章写作领域延伸至绘画中的自我表达之用的,则是郭若虚、米友仁二人。见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九; 亚历山大·索泊尓(Alexander Soper)《关于郭若虚的绘画见闻(Kuo Jo-hsüs Experiences in Painting)》,15页。米友仁之引用出现在《米敷文为蒋仲友画并题卷》之中,见卞永譽《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三,二十二。
【22】 “自成一家(establish the words of one school)”一说出自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其在写给友人任安的书信文章中谈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书“藏之名山”以期向后世知音发出召唤之声,从而得到他们的理解与认同。详细内容请见由博弛(Birch)编辑,海托华(Hightower)翻译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