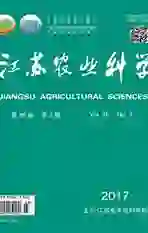个体、家庭经营特征与新品种需求的关系
2017-05-02赵峥李艳军
赵峥 李艳军



摘要:以中东部3省23镇60村500位种植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查询和实地调研,实证研究农户户主的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与新品种需求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统计特征中的性别、年龄、耕作年限、文化程度对新品种需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个体差异性中的个人兼业化和新品种创新性感知对新品种需求有极显著正向影响,持续种地意愿对新品种需求无显著影响;家庭经营特征中的耕地面积与新品种需求之间呈现“U”形关系,家庭收入对新品种需求有正向影响。
关键词:人口统计特征;个体差异性;家庭经营特征;新品种需求
中图分类号: F323.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03-0290-05
收稿日期:2015-09-2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2731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编号:2012RW004)。
作者简介:赵峥(1987—),女,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营销管理。E-mail:zhzhengjiayou@163.com。
通信作者:李艳军,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和农资品牌管理。E-mail:lyj@mail.hzau.edu.cn。
长期以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以往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出发,探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农业科技成果运行机制,以及所存在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转化周期长等问题,却缺乏在此过程中对农业科技转化成果的受众群体——农户的深入研究。农户是农业技术的最终需求方,毋庸置疑,农业科技成果只有被农户接受和消化并应用于农业生产过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1]。一般来讲,农业科技成果主要包括新品种、新农药和新肥料、病虫害防治技术、新农具和新的栽培技术等,而在对众多农业科技成果需求的排序中,农户对新品种的需求始终排在首位。随着2000年以来《种子法》的颁布与实施,整个种子产业的市场化体系已逐渐完善,这就意味着新品种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机制传送至农户手中,农户在新品种选择上将拥有更多自主权[2]。因此,从农户角度探讨新品种需求对于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品种作为一项农业科技成果,属于创新类产品。根据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新的理念或产品在诞生后,会在社会系统中通过交流的方式进行扩散和传播,而消费者根据采用新产品的时间不同,会被分为不同的采用者类型[3]。对于高新技术产品,晚期采用者会比早期采用者持更加警惕和排斥的态度,由此可见,不同特征的采用者对待新产品的态度会有差异,因此推断农户户主的个体特征会对新品种需求产生影响。此外,根据以往研究,农户的家庭收入、耕地面积等家庭经营特征也会使农户在新品种选择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目前,对新品种需求的研究大多还是将其作为技术需求的一部分,分析新品种需求的客观影响因素、农户对新品种的需求偏好等。本研究拟通过农村实地调研问卷,突出强调农户对新品种的需求是根据其本身特征而作出的决策行为,从而揭示农户户主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经营特征与新品种需求之间的关系,旨在为种子企业制定有效的新品种推广策略提供借鉴。
1文献综述与假设
1.1新品种需求
自《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各科研单位与种子企业育种积极性大幅增加,1999—2010年,我国植物新品种权申请量高达6 632项,获批2 984项,种子市场上的新品种供给十分充裕[4]。这些新品种能否产生现实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取决于农业生产者对它们的需求。根据“需求”的经济学意义和心理学意义,以及农资购销的特殊情境,本研究将“新品种需求”界定为一定价格水平下,当市场上现有种子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户的种植需要,或农户渴望尝试创新时所形成的一种愿意并且有能力购买新品种的消费欲望。
1.2个体特征对新品种需求的影响
1.2.1人口统计特征与新品种需求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农户对新技术品种的采用意愿不仅受诸如社会资本、社会结构、资源分配和公共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农户购买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以往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在获取相关信息、培训和服务等方面的機会明显较少,而在接触和使用贫困地区有限的技术信息、培训、服务的资源方面,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加边缘化。同时,常规农业技术推广方式的局限性以及技术推广人员中女性人数的占比低,都使得女性接受新技术受到一定程度影响[5]。农户年龄越大,采纳新品种的意愿越低,一方面,因为大龄农户长期的种植观念与经验使其形成习惯性种植路径依赖,不易改变;另一方面,因为农户规避风险,且采纳新品种对于大龄农户来说学习成本增加,因此年龄越大的农户对新品种越抵触[6]。耕作年限对新品种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种植年限越长,经验越丰富,农户对新品种的掌控力和认知程度就越高,对新品种的选择就会更有信心[7]。另外,农户的文化程度、个人知识等因素与农业技术扩散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3]。Snha等研究表明,在决定技术采纳者行为的个人禀赋中,受教育程度是其中最重要的1个因素[8];然而宋军等则认为,农户受教育水平与技术采纳程度之间并非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选择节约劳动技术的比例会提高,而选择高产技术的比例却降低[9]。种子新品种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产物,基于此,本研究推测农户对其需求态度应满足上述特点,故提出假设H1:人口统计特征对农户新品种需求有显著影响。
[JP2]H1.1:性别对农户新品种需求有显著影响;
H1.2:年龄对农户新品种需求有显著影响;
H1.3:耕作年限对农户新品种需求有显著影响;
H1.4:文化程度对农户新品种需求有显著影响。[JP]
1.2.2个体差异性与新品种需求
本研究中的个体差异性主要指被调查者或农户户主的个人兼业化程度、持续种地意愿和新品种创新性感知3个方面。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户兼业化现象愈加普遍,且进程不断加快。目前,关于农户兼业化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农户兼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以及兼业化对农户新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方面;有学者认为,新品种作为新技术中较特殊的成果,其采用概率与农户兼业化程度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即农户采用新品种的概率会随着兼业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但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随着兼业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10]。周未等在研究农户超级稻品种的采纳行为中指出,农民的种稻意愿表现为其种稻积极性,种稻积极性高的农民对种稻新技术的采纳会有更大可能性[11]。此外,新品种是创新类产品,农户对创新的态度应该会影响其新品种的采用意愿。尽管现有研究很少关注农民对创新性的感知对其新品种采用意愿的影响,但针对一般消费者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产品创新性的感知能正向影响其购买意愿[12]。综上,提出假设H2:个体差异性对农户新品种需求有显著影响。
H2.1:个人兼业化对农户新品种需求有显著影响;
H2.2:持续种地意愿对农户新品种需求有显著影响;
H2.3:新品种创新性感知对农户新品种需求有显著影响。
1.3家庭经营特征对新品种需求的影响
[JP2]耕地面积会对农户采用技术决策产生影响,林毅夫在不同类型技术的采纳研究中发现,经营规模越大,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大[13],但同时种植规模越大,农户更换新品种面临的风险损失也会变大。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户采纳超级稻品种技术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因为农户比较宽裕的经济条件可以使他们有能力承受采纳新技术、放弃旧技术所产生的各种风险[11];但也有学者认为,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户对新品种技术并不感兴趣。因此,提出假设H3:家庭经营特征对农户新品种需求有显著影响。[JP]
H3.1:家庭耕地面积对农户新品种需求有显著影响;
H3.2:家庭收入对农户新品种需求有显著影响。
2数据收集与变量测量
2.1变量测量
2.1.1新品种需求的测量需求的概念在经济学、营销学和心理学中均有描述和理解,它强调的是一定价格水平下,消费者能够并且愿意购买的商品数量,以及由于某种匮乏而产生的一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因此,农户对新品种的需求是新品种购买意愿的前奏。购买意愿一般从再购买可能性、搜集相关信息以及推荐他人购买等方面进行测量。本研究基于需要,并结合我国农资购销的本土情形,对新品种需求的测量主要从信息搜集和购买可能性(即是否愿意尝试种植)等方面来设计,经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了如“您希望种子品种能不断更新”“您会主动询问市场上是否有新品种出售”等5项语句。在答案设计上,采用Likert五点测量法对因变量进行测量,其中“1”表示很不同意,“5”表示很同意。
2.1.2个体特征和家庭经营特征的测量本研究的个体特征包括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耕作年限)和个体差异性(农户户主的个人兼业化、持续种地意愿、新品种创新性感知)。其中,新品种创新性感知指的是农户对新品种创新性的态度,本研究借鉴消费者感知产品创新性的测量[14],从独特性、差异性等方面来制定Likert五点量表,确定了如“您觉得种子是有创新性可言的”“您认为新品种一般比老品种技术含量高”等语句。家庭经营特征包括家庭收入和家庭耕地面积。除了“新品种创新性感知”,其余自变量均为显变量,其赋值说明见表1。
2.2样本与调查
本研究采取入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以湖北省潜江市、天门市、荆州市、仙桃市,山东省菏泽市、济宁市和安徽省阜阳市的23镇60村500位农户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面对面访谈和问卷调查,调查时间是2014年12月和2015年7月,由经过训练的华中农业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进行,保证了数据收集的质量。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10份,回收有效问卷500份,有效率为98%。样本基本信息见表2。
由表2可知,被调查者中男性占55.0%,女性占45.0%;从年龄上看,以中老年人为主,其中46~60岁的比例最大,占样本总量的55.0%;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及以[CM(25]下人群占样本总量的93.2%;从耕作年限上看,耕作年限达20年以上的被调查者占样本总量的83.8%,說明被调查者大多数具有丰富的种植经验。样本性别比例、年龄、文化程度及种植年限分布等信息基本与农村实际情况一致。从兼业化分布比例看,31.6%的被调查者在农闲时节外出务工;虽然大部分被调查者表示种植业收入较低,但在未来是否愿意继续种地的问题上,仍有95%的被调查者愿意继续种地;从耕地面积来看,种植面积≤0.33 hm2的家庭占53.6%,>0.33~0.67 hm2占30.0%,>0.67 hm2以上的家庭已算是种植大户,占16.4%;从家庭收入来看,≤5万元的家庭占大多数,比例是68.2%,>5万~10万元的家庭占25.8%,>10万元占6%(表2)。样本主体能较好地代表所研究的群体,增加了本研究的可靠性。
2.3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主要包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的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进而考察农户户主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经营特征对农户新品种需求的影响。
3实证分析与结果
3.1信度与效度分析
由于大部分自变量为显变量,因此本研究所作的信效度分析主要是对“新品种创新性感知”和“新品种需求”2个量表进行。
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来检验数据的可靠性,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7即为可靠。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信度分析,新品种创新性感知、新品种需求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分别为0.940、0.943,均大于0.9,说明这2个变量的具体测量语项之间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数据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效度是指数据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反映指标能够衡量出它所测量的理论概念程度。本研究利用SPSS 17.0对2个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进行Bartlett的球形度检测和KMO的抽样确切性衡量,因子分析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KMO值分别为0.861、0.867;Bartlett球形度检测P值均为0),说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另外,各构念下维度指标的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为0.923、0.932、0.918、0.907、0.841、0.877、0.913、0.949、0.931,均在0.8以上,表明数据具有良好的效度。
3.2相关分析
由表3可知,个体特征下面的性别、年龄、耕作年限与农户新品种需求呈极显著负相关,文化程度、个人兼业化和新品种创新性感知与农户新品种需求呈极显著正相关,持续种地意愿与农户新品种需求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家庭经营特征下面的耕地面积和家庭收入均与农户新品种需求呈显著正相关。这些数据表明,大部分农户户主的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与新品种需求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且整体来说,农户新品种需求与个体特征的相关性要强于与家庭经营特征的相关性。本研究假设得到了初步支持。
3.3方差检验
本研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了农户户主的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等变量对新品种需求的影响,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性别对新品种需求具有极显著影响,并且男性对新品种的需求程度高于女性。因此,H1.1得到验证。在≤60岁时,年龄与新品种需求呈显著呈现正相关趋势,但随着年龄继续增长,年龄与新品种需求则呈负相关(即Likert得分均值降低)。这说明农户在达到老年后,较易形成固有的品种购买习惯,不再愿意冒风险去尝试新品种。因此,H1.2得到验证。耕作年限对新品种需求有负向影响,这与年龄对新品种需求的影响类似,即农户会随着种植经验的累计增加,形成自己固有的品种购买习惯,对已有品牌产生依赖而降低了对新品种的需求,因此H1.3得到验证。文化程度与新品种需求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户较少受固有习惯影响,渴望接触新事物,对新品种有较大需求,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价值,相信新品种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种植需求。因此,H1.4得到验证。农户兼业化对新品种需求产生极显著正向影响,即有在外务工经历的农户对新品种的需求程度高于全职农户,这是因为农户在外务工使得农户增加了信息获取渠道,强化了农户在“创新—决策”过程认知阶段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外务工的收入一般会远远高于种植收入,对采用新品种可能产生的风险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因而对于新品种会抱有更加开放的接受态度。因此,H2.1得到验证。农户的持续种地意愿与新品种需求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种子作为农业生产的投入品,对农户生活的意义较大,无论农户是否愿意继续种地,出于生存购买习惯以及农户自身的乡土情结,都会对新品种产生不同程度的兴趣和关注,因此农户对新品种的需求程度不会随着本人种地意愿的改变而改变。因此,H2.2未通过验证。新产品创新性感知对新品种需求产生正向影响,新品种属于创新类产品,农户对创新的态度越肯定,就越会觉得具有创新性的新品种能增加其收成,进而对新品种的需求也就会更大。因此,H2.3通过验证。当农户的种植面积≤0.67 hm2时,种植面积与新品种需求呈极显著负相关,但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加,当和植面积>0.67 hm2时,种植面积与新品种需求之间呈现正相关趋势。这说明,当农户种植面积非常小时,更换新品种所面临的风险也较小,因此对新品种的需求程度较高,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加,更换新品种所面临的风险增加,农户越来越倾向于购买使用过的熟悉品种,对新品种的需求降低;但当种植面积越来越大,>0.67 hm2(即成為种植大户)时,他们具有较多的种植经验和品种信息,对于不同品种的种植习性有更多的了解,能够有效地控制采用新品种面临的风险;同时,对于这些农户,种植业往往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如果采用新品种成功,将会为其带来更多的收益。可见,尽管种植面积非常小的农户与种植大户对新品种的需求都高,但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因此,耕地面积与新品种需求之间呈现“U”形关系,H3.1得到验证。家庭收入对新品种需求存在正向影响,其原因与兼业化的影响类似,即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农户承担风险的能力增强,更加渴望得到新品种所能带来的正向改变,进而对新品种的需求程度较高。因此,H3.2得到验证。
4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湖北省、山东省和安徽省23镇60村的500位农户为例,初步探讨了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与新品种需求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个体特征中的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年龄、耕作年限、文化程度)与新品种需求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2)本研究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将被调查者的个人兼业化、持续种地意愿、新品种创新性感知等因素纳入到个体差异性中,丰富了农户个体特征的变量指标,同时验证了兼业化和新品种创新性感知对新品种需求的正向影响,即有在外务工经历的农户对新品种的需求程度大于全职农户,看重创新的农户对新品种需求程度大于其他农户,而持续种地意愿对新品种需求的影响尚未通过显著性检验;(3)家庭经营特征中的耕地面积与新品种需求之间呈现“U”形关系,即种植面积非常小的农户与种植大户对新品种的需求都很高,而处于种植面积中间位置的农户对新品种需求则较低,因此企业在进行新品种推广时,应该明确推广对象,有针对性地实施推广活动,进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家庭收入与新品种需求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综合上述结论,本研究认为,为了加快新品种扩散、提高农户对新品种的需求,种子企业和相关技术推广机构应该采取以下措施:(1)在严把质量关、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时,重视新品种的宣传工作,确保种子信息能及时、有效、全面地传达至农户,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新品种扩散受阻;(2)新品种在前期推广时,鼓励中年种植大户参与其中,一方面这类人群对新品种需求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他们在农户中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头作用,此外,由于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的不同,农户对新品种需求也存在差异,因此种子公司应针对不同顾客群体的特征采取差异化营销策略;(3)建立专门渠道及时解决农户种植新品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降低农户采用新品种的风险,从技术指导和售后服务等方面提升新品种使用价值,从而强化农户购买意愿并形成购买信任。此外,政府还应该从宏观上引导农资市场的健康发展,如落实良种补贴政策、加强种子市场的立法建设和执法管理等,为新品种的推广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廖西元,陈庆根,王磊,等. 农户对水稻科技需求优先序[J]. 中国农村经济,2004(11):36-43.
[2]王海军,李艳军. 社会资本对农户新技术品种采用意愿的影响[J]. 湖北农业科学,2012,51(21):4937-4943.
[3]Rogers E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M]. New York:the Free Press,2003.
[4]庄道元. 基于农户视角的粮食作物主导品种推广绩效研究——以安徽小麦为例[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1.
[5]李科. 社会性别敏感的参与式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研究[D]. 杨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学,2007.
[6]齐振宏,梁凡丽,周慧,等. 农户水稻新品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17(2):164-170.
[7]王晓蓉,宋治文,贾宝红,等. 蔬菜种植者新品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天津市的调查数据[J]. 江苏农业科学,2015,43(1):437-440.[HJ1.9mm]
[8]Saha A,Love H A,Schwart R. Adop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under output uncertainty[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4,11:836-846.
[9]宋军,胡瑞法,黄季焜. 农民的农业技术选择行为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1998(6):36-39.
[10]吴炳灿. 兼业化对农户新品种采用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德化县黄花梨为例[D]. 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3.
[11]周未,刘涵,王景旭,等. 农户超级稻品种采纳行为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北省农户种植超级稻的调查[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32-36.
[12]陈姝,刘伟,王正斌. 消费者感知创新性研究述评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36(10):3-12.
[13]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4]Goode M R,Dahl D W,Moreau C P. Innovation aesthetic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tegory cues,categorization certainty,and newness perceptions[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3,30(2):192-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