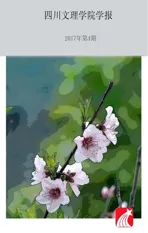发生学视野下的川陕苏区文化探析
2017-04-14蒲东恩
蒲东恩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科研部,四川达州635000)
发生学视野下的川陕苏区文化探析
蒲东恩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科研部,四川达州635000)
川陕苏区文化作为川陕边地区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其主要内容包括红军的战斗足迹、苏区建设的系列举措、红军石刻标语和方言革命歌谣;促使其生成的原因主要包括先进理论的指导、深厚的历史底蕴、革命的社会氛围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权保障;其呈现的方式是以党的宗旨路线与传统文化、传统军事谋略与游击战争、意识形态改造与社会动员、传统表现形式与革命觉悟相结合。
川陕苏区;文化建设;红军精神
川陕苏区是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战略转移到川、陕两省边界地区,与当地原有革命武装——川东游击军共同建立的一块根据地,从所辖区域和人口看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1]川陕苏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在文化方面也塑造了具有川陕边地区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我们称之为川陕苏区文化。川陕苏区文化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自红四方面军入川开始至离开这段时间内创造的,是反映川陕边地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土地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武装斗争保卫新型政权的新型区域革命文化。
一、川陕苏区文化的主要内容
川陕苏区文化是我党在巴山蜀水的战斗生活的积淀,由于当时特定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环境,保存和延续至今的文化形态主要有:
(一)红军的战斗足迹和“红军精神”
毛泽东曾说,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也是如此。时任红四方面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回忆,“红军在从进入川陕边区到撤出根据地近两年半的时间里,几乎有两年的时间都在进行战争”,可见川陕苏区战争之频繁。在这样环境下诞生的川陕苏区文化自然与战争紧密相连,很大部分都是与战争相关或围绕战争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在文化上主要体现为信念、意志、影响力等精神力量的较量。其中影响最久远的就是1934年11月1日至9日,红四方面军在赤江县(今通江县)委驻地(毛浴镇)召开了党政军工作大会,将全军各部队军训训词进行了规范,统一为“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也就是今天川陕苏区的“红军精神”。军训词通俗明快,琅琅上口,适合战士们操练时呼喊,逐渐演化成了红四方面军不朽的军魂。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和激励下,川陕苏区的面积和人口在当时都只仅次于中央苏区。红军正规部队由入川时的4个师1.4万人,发展到5个军15个师8万余人;[2]建立苏维埃地方政权23县1市,总面积达到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歼敌达10万之多,沉重打击了四川军阀的有生力量,仅反“三路围攻”的歼敌,就大致与中央红军第二、三、四次反“围剿”和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歼敌数的总和,成为我党我军早期战史上的亮点之一。正是有这种精神文化和如此不顾一切踊跃参军支前的苏区人民,才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今天留下的这些战斗的遗迹是我们寻觅川陕苏区文化极其重要的资源。
(二)为民务实的苏区建设系列举措
苏区党和政府始终以实实在在的为民务实措施,来赢得苏区人民的真心支持和拥护。一是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各层次红色学校。一种是针对适龄儿童或成人识字班的大众普及教育,如列宁学校;另一种是专门培养各种革命人才的学校,如党校、红军大学、彭杨军事学校、苏维埃学校等。正是大规模地建立了适应苏区形势发展和革命需求的学校,极大地提升了苏区各类干部及党员的文化、政治、军事等素质。二是大幅提高苏区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为了阻止苏区当时流行的烂脚病、痢疾、皮寒等疾病的蔓延,先后创办了红四军方面总医院、川陕省工农总医院等苏区医疗卫生机构,还成立了“中医学术研究会”,推动了苏区社会文明健康的进步。三是广泛开展有益身心的社会改造运动。当时川陕边成年男子百分之九十以上吸食鸦片,红军入川后制定了戒烟政策,成立戒烟机构;发布各项公告,禁种鸦片;开展多种形式的戒烟运动,采取强制措施禁绝吸食。四是不拘一格引入和使用各类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员。川陕苏区各级党委、政府为了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积极在政治上关心、经济上关怀,动用一切资源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和业务能力,尤其是在宣达战役后,建立了红军自己的兵工厂,很多技术人才都是原军阀兵工厂的人才,生活上积极帮助、协助各种人才解决婚姻和住房问题。[3]
(三)极富地方色彩的红军石刻标语
红四方面军在创建、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过程中,充分发挥川陕边地区地域文化与工农革命思想的相互融合作用,以通俗易懂、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其中在巨大的岩石上镌刻革命标语和文献,就是川陕苏区特有的宣传形式。散落在大巴山各地的红军石刻文献、标语、对联等,数量庞大,内容也很丰富,有政治宣传标语、军事纪律、土地政策等。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数量规模,在全国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极具文献和文化价值,是红色文化特殊的保存形式。这些红军石刻标语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在深山邃谷之中,在大小渡口、要隘之旧石碑、悬崖石壁、石牌坊、石匾,甚至农村房基石、石缸上刻写革命文献和标语。现在保存下来的川陕苏区红军石刻内容仍然十分丰富,有反映党和政府政治主张与法律的,有反映苏区军民拥护马列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有拥护中国工农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打倒军阀的,有工农专政、实行土地革命的,有发展苏区经济的,还有工会、年青、妇女文教工作的。这些石刻标语文字通俗,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多层次、多角度反映了川陕苏区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下,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进行以发展和建设农村为主的革命历程和文化,全面记录了川陕苏区当时所面临的历史环境、斗争历程和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也是川陕苏区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是刻在石壁上的红色史诗,具有十分重要的党史价值和丰富的革命文化内涵。[4]
(四)蕴含四川方言特色的革命歌谣
红军为了宣传革命、鼓舞劳苦大众,创作了大量的红色歌谣,是当时非常适用的战斗武器。这些红色革命歌谣的语言大多是采用川东本地方言,读起来朗朗上口、易懂易记。如“太阳出来一把火,把人晒得焉妥妥”中的“焉妥妥”就是万源地区的方言,非常形象地把那种没有精神的样子描绘出来了。红色革命歌谣的句式多变,风格多样。有七言的,如《扎在穷人心里头》“红军北上抗日走,路过村边插棵柳。柳树发芽扎深根,扎在穷人心里头”;有五言的,如《活捉这只狼》“巴山闯进狼,军阀是恶狼。喝尽穷人血,抢光穷人粮。霸占穷人妻,烧毁穷人房。打到成都去,活捉这只狼”;有十言的,如“我刘湘坐重庆,神魂不定。想从前思今后,珠泪长倾。悔不该我当年,整治穷人”;也有八言的,如《打的刘湘钻土巴》;有的歌谣在一首之中就有多重句式的运用,句式多变,运用灵活。而且一般情况下,这些革命歌谣都是按照律诗的韵律来用韵的。如《见红军》:“太阳出来照石岩(读:áī),唱起山歌上山来。一眼看见红军哥,乐得心头山花开。”这些革命歌谣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5]
二、川陕苏区文化的生成动因
(一)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指引
20世纪30年代,在封闭、贫困的川东北秦岭巴山地区,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文盲,普通群众仍然对传统封建宗族伦理思想深信不疑,根本谈不上信仰什么主义,了解和渴求救国救民的道理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川陕苏区开辟之后,经过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治理,苏区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普遍有很大提高,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引导下逐渐开始接受阶级、政党、国家的词汇和政治概念,渐渐明白了为何要反对帝国主义才能实现民族独立的道理,树立起实现社会平等、工农民主的执着追求,进而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也正是由于有坚定的信仰作支撑,苏区群众才以极大的牺牲精神鼎力支持,才使革命运动得以持续。川陕苏区鼎盛时辖区4.2万平方公里,人口600万,有23个县和1个特别市苏维埃政权,有8万多人参加红军,10余万人参加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川陕苏区人民如此拥护中国共产党,为了赢得新生活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这些凝聚着血与火的苏区文化无不是因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觉悟,因此说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是川陕苏区文化生成的理论渊源。
(二)巴人遗风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底蕴
巴人是一个神奇的民族,在春秋战国受邻国的挤压,逐步沿长江向西迁徙,最终落脚在长江中上游地区,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铸就了这个单纯而又具有丰富性格的民族。首先,巴人具有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性格,表现在对自己所处的恶劣环境不屈不挠的改造。由于巴人所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不得不与野兽抢夺生存的空间与资源,不利的自然条件导致了巴人不得不勇敢地面对大自然,不得不勇敢地与大自然做搏斗,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生存下去,这从一个侧面也激发了巴人潜在的拼搏精神,在世世代代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当中,练就了勇敢顽强、坚如磐石的民族性格。其次,“尚武精神”也是巴人的一大性格特征。巴人在长期的征战中,表现出了勇猛顽强、坚韧不拔的精神。关于这点从巴人传说中就能证明,巴国君廪君就是凭投剑能中石穴的高强武艺才当上国君的。现在考古发掘出的早期巴人使用的剑,不但样式多种多样,其风格也与其它地方不同,因而被人们命名为“巴式剑”。由此可见,巴人尚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慷慨悲歌的文化因子就是巴山风骨,正是这些文化渊源构成了川陕苏区文化生成的历史底蕴。
(三)革命运动提供了革命实践的土壤
川东北地区建立党组织后,我党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和斗争,沉重打击了四川的反动势力。其中影响较深、规模较大的有:一是遂宁大石桥起义。1929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28军第7混成旅,在代旅长地下党员旷继勋等领导下树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大旗,攻占蓬溪县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二是广汉起义。1930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28军第2混成旅,接受共产党员的策反宣布起义,但由于受“立三路线”的影响,未得到广大农村的响应。三是升(钟)保(城)暴动。升保暴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在川北南部的一次农民武装起义。1930年,升保地区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抗捐抗粮的斗争不断爆发。四是通南巴地区的抗捐斗争。受革命大环境的影响,通南巴地区的抗捐、抗粮活动的声势浩大,到1932年下半年,已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这些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虽然影响的范围有限,但从客观上打乱了军阀统治的根基,激发了人民的革命激情,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实践土壤,也为红军入川和川陕苏区文化的形成提供前期实践的机会。[6]
(四)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2年12月红军从巴中通江县两河口入川,以迅疾之势推翻当地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以现在的巴中市为中心的23个县和1个特别市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始终秉持把人民的政治、经济解放摆在首位,积极推进苏区各项建设工作,大力普及文化知识,使苏区人民在精神上获得洗礼。苏区政府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让人民群众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翻身得解放,更在于在文化上得到解放,让广大青壮年、妇女儿童从此摆脱了封建文化的禁锢。为实现这一目标,苏区政府大力开展文化建设,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并培养革命的后代和接班人。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文教工作在整个苏维埃运动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苏区各县各地创办了各类文化教育设施阵地,如党校、苏维埃学校、红军大学、彭杨军事学校、童子团学校、院坝课、夜校识字班等,给苏区人民群众提供了参与文化教育活动的广阔舞台。
三、川陕苏区文化的衍生方式
川陕苏区文化是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熏陶,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下,发展产生起来的文化形态,其产生和发展都其特定的生成方式。
(一)传统文化与党的宗旨路线的结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可谓博大精深,但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崇德”“尚礼”,且特别强调个人的修养与境界,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和建设川陕苏区的过程中,非常注重思想文化的作用,要求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加强党性修养,崇尚节俭的风气,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传统儒家思想强调国家大一统,视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易经》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关注现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的集中体现。传统文化中也有“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思想,要求人们不要怨天尤人,要去克服困难勇于实践,有知难而上的精神。苏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发动一切力量,捍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异常艰苦的环境和无私奉献的情怀造就了苏区党员干部的良好作风,这也是构成川陕苏区文化的民族基础。党的思想路线之所以在能在苏区扎根,这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追求紧密相联,为川陕苏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营养和启发,是川陕苏区文化的重要渊源。
(二)传统军事谋略与游击战争的结合
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千里转战到川东北,这里山高林密路险,且资源相对富足,非常适合建立作为战略后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周旋,先后取得了川陕苏区一些列进攻和反围攻作战的胜利。尤其是反“六路围攻”中战略战术运用最为娴熟。在强敌进攻时,依托有力地形收缩阵地,避其锋芒;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利用有利的地形,对孤军深入之敌集中优势兵力以歼之,消耗其有生力量。总之,在整个反“六路围攻”中,很好坚持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运动中阻击和消耗敌人,积蓄自己的力量,最后反攻。具体战术方面:一是选充分有利地形进行积极防御。占据有利地形阻击敌人进攻,大量消灭敌人于阵地前,根据具体情况实施阵地反击。如在万源保卫战的一线的坚守防御中,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大规模进攻,并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实施反击歼灭了大量敌人。二是寻找各路进攻之敌的空隙,大胆穿插向敌人侧翼和后方出击,调动和歼灭敌人。如1934年1月1日的西线反攻,西线红军乘敌不意,穿插到敌人的侧后方仪陇城南五里墩,向敌反击歼敌六百余人,取得西线反攻的胜利。三是充分发挥我军擅长夜战、近战的优势。在整个反“六路围攻”作战中,夜战、近战发挥了重要作用,除几次主动出击外,几乎都是由夜袭开始的,并都取得胜利。如1934年1月23日夜袭庆云场,8月9日夜袭青龙观等。[7]
(三)意识形态改造与社会动员相结合
川陕苏区文化是川陕苏区人民在在党和红军领导下,反映川陕苏区党和红军、苏维埃和人民群众的文化,既有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因素,也有川陕地域文化的社会动员因子,是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党、红军和苏维埃的政策主张、社会影响、价值观念。正因为很好地结合苏区群众易于接受传统文化因素,加上一些反映群众需求的政策主张,在川陕大地的影响甚为广泛,也因此吸引了大批有识之士加入到革命之中。川陕苏区文化作为一种带有区域性的革命文化,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宣传党的主张,推动党和红军的社会影响力,展示苏区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动员和激励党员干部群众,同时也是打破专政文化禁锢的重要武器。因为川陕苏区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川陕苏区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文化反映,是反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这种文化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其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把松散的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到党的周围,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去参加革命和苏区建设工作。这种文化还能激励和动员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也能促使群众树立革命意志、共产主义信仰,造就不畏艰难困苦、敢于牺牲奋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在具体实践中激发无限的创造能力。
(四)传统表现形式与革命觉悟的结合
为了打击敌人,苏区干部群众利用戏曲、歌谣、教材、标语等传统表现形式加上一些自我创作的的内容,达到歌颂共产党的领导和打击敌人的目的。川陕省委、省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共产党》《川北穷人》《战场日报》等机关报,除了揭露敌人的阴谋和屠杀人民的罪行,更多的是组织广大军民起来反击敌人的消息、通讯、言论等,也有反映川陕苏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的社论和文章等内容,同时刊登苏区新面貌、打胜仗等内容。少共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为适应青少年读者特点,图文并茂,除了短小精悍的文章、报道,还有吸引人的绘画和歌曲,以及宣传青少年加紧识字学习、老人送子参军和消灭刘湘的报告。川陕省委宣传部和剧团编辑通俗易懂的歌谣几千首,不定期出版《工农小曲》歌曲小册子。剧团编演的《送郎当红军》《十劝夫》《扩红谣》等深受军民欢迎,流传广泛。特别是以“送郎当红军”为主题的歌谣、剧曲最多,诸如《巴山重逢再结婚》《妹愿等哥九十九》《送郎当红军》。《刘湘自叹歌》通俗易懂、诙谐幽默,深受群众欢迎。[8]
[1] 尹家福.川陕苏区何以成为第二大苏区[J].中国老区建设,2003(2):33.
[2] 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33.
[3] 毕瑛涛.为民务实:川陕苏区根据地治理的重要特点[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4(1):9.
[4] 谯长卫.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石刻概述[J].四川档案,2011(3):33.
[5] 蒲仁胜.万源红军歌谣的艺术特色及传承利用初探[C]//孟兆怀.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63.
[6] 蒲东恩.红四方面军入川时环境的社会生态学分析[J].达州新论,2012(3):47.
[7] 盛学仁.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兼谈徐向前的指挥艺术[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2):43-47.
[8] 王发祯.浅谈川陕苏区红色文化与苏区精神[C]//孟兆怀.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72.
[责任编辑 范 藻]
Culture Study of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in Embryology
PU Dongen
(Research Section of Party School of CPC's Dazhou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The culture in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was a unique New Democratism culture, whose contents include the Red Army's fighting events, numbers of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slogans on stones and songs for revolution in dialect. The culture was formed by the advanced theory, long history, revolutionary society circumstance and stable regime. It shew itself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Party's principl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and guerrilla wars, the idiology reform and society mobiliz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forms and revolutional awareness.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culture construction; Red Army spirit
2017-04-15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在川陕苏区的法制实践研究”(SLQ2016B-17)
蒲东恩(1984—),男,湖北利川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D231
A
1674-5248(2017)04-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