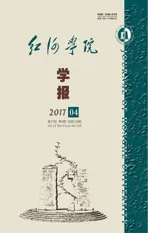怒族民间传说中女性形象解读
2017-03-09刘薇
刘 薇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昆明 650031)
怒族民间传说中女性形象解读
刘 薇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昆明 650031)
怒族民间传说中女神、女仙社会角色感强,形象丰富多彩,贴近民众生活,传说中女性角色正是怒族社会女性的生活写照。文章通过分析怒族民间传说中女神和女仙形象特征及其相关情节单元,解读怒族社会中的女性崇拜。
怒族;民间传说;女性文化;探讨
怒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有民族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民族文化传承主要通过口传心授。千百年来,怒族先民们创造了内涵丰富的民间传说,这些作品不仅凝聚了民众的智慧和心血,还体现了怒族人民的审美观念,是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怒族信仰原始宗教,多神信仰崇拜,因此,民间传说中大量出现始祖神、自然神和具有神奇法力的精灵,其中女性神灵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传说中绝对的主角。本文选取的神话主要来自于《怒族民间故事》[1]《怒族文学简史》[2]《怒族独龙族民间故事选》[3]《七彩贡山——贡山民间故事集》[4]《福贡县民间故事集》(上、下)①等著作中。通过梳理怒族传说中的女性形象,对传说中丰富多彩的女性群体进行解读,阐释怒族女性形象形成的文化成因和社会体现。
一 丰富多彩的怒族女性世界
(一)女始祖形象
怒族社会中,几乎每个村寨都流传着自己始祖的传说,这就很好地解释怒族氏族名称多如繁星,数不胜数的原因。在《女人出嫁和生育的来由》中,[1]7女始祖茂充掌管着世间一切大权,茂英允与花蛇、马鹿、蜜蜂、老虎交配后,才有了怒族的后代。起先是由男人嫁给女人,但男人出嫁时舍不得家产,放声大哭,女人看后觉得可怜,就答应由女人嫁到男人家。起先由男人生孩子,坐月子要杀一头牛,还日日夜夜呻吟不止,女人看到后可怜男人说:“以后你们男人不要生孩子了,由我们女人生好了”,从那时起,就由女人来生孩子了。从这则神话中看,早期怒族社会女强男弱的现象,同时也表现出了怒族女人吃苦耐劳,敢于担当的精神,至到今天,在怒江地区还有老人的记忆中保留着过去男子出嫁的史话。“茂英允”在怒语中为“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在怒族社会中茂英充被公认为各氏族共同的女始祖,但各氏族仍然有各自代代相传的始祖神话。如聚居于福贡县匹河乡老姆登村人的传说,认为其祖先为鸟;福贡县果科、普乐等地传说,他们是虎氏族的后代。在《腊普和亚妞》中,[1]10-13天神派下未成年的腊普和亚妞兄妹俩来到人间,兄妹为了繁衍人类而结合,生育下七个子女,有的兄妹结为夫妻,有的与会说话的蛇、蜂、鱼、虎结姻繁育下一代。这则传说讲到人与动物结合后,与蛇所生的为蛇氏族,与蜂所生的为蜂氏族,与鱼所生为鱼氏族,与虎所生为虎氏族。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前,怒族主要以狩猎为生,人与动物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怒族传说中人与动物成亲的故事特别多,始祖传说中的动物被认为是本族人的图腾,成为了民族的姓氏,有的成为民间信仰的崇拜物。《那麻与亚尼公主》[1]29-34讲述了亚尼公主即怒族传说中的四脚蛇公主授天神的旨意下凡来到人间,在大蟒蛇的口中救了勤劳勇敢而又善良的那麻,并与他结为夫妻,亚尼传授给他们的子孙烤洒和织布等生活技能。在怒族村寨里,认为四脚蛇是亚尼公主的妹妹,是为了来看望和保护他们的了孙,永远留在人间的。在怒族的洪水再生神话《小白蛇的恩惠》,[4]7-11则认为女始祖是龙女。远古时期,洪水过后只剩下一个善良的男青年,他在寻找同伴的途中,遇到白蛇和黑蛇在打架,他帮助了处于弱势的白蛇打败了黑蛇,原来白蛇是龙女所变,龙王看到男青年在世上孤苦伶仃,就让龙女与男青年一同来到人间繁衍人类。在贡山一带的怒族认为他们是龙的后代,对龙非常崇敬。始祖形象是祖先崇拜和母权崇拜的结合,另外图腾崇拜文化的体现,成为寻找氏族血缘的纽带。
(二)女猎神形象
怒族居住在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的山腰地带,边峰际天,峭壁千仞。特殊的生活环境和习俗,在怒族传说中塑造了非凡的恩赐女性形象,被神化了的猎神总会来到人间,教会猎人捕猎的办法,让狩猎者获得丰厚的回报,甚至还来到人间教授驯养家畜家禽,纺线织布。《猎人与女猎神》这个传说就是其中的代表,传说讲述了一个猎神化身的姑娘,在森林中遇到了一个善良、勇敢的狩猎人,并结为夫妻,与猎人来到村子,一起建房、种地、砍柴、饲养家畜,教授猎人捕获猎物的技巧,共同生活几年后女猎神不得不离开猎人和他们的儿子。女猎神虽然离开了,但怒族后代在女猎神的庇护下丰衣足食。在怒族的民间信仰中,森林中的一切飞禽走兽都是由猎神来掌管的,猎神是一位女性,不仅在传说中有所体现,在怒族著名的《猎神歌》中所歌颂的同样也是一位女猎神,“猎神姐姐啊!尊敬的猎神母;你是管辖大山的神灵,你是管辖大箐的神灵;那天,我去山上住一夜,梦见犄头上戴着珠珠帽;身上挎着漂亮的彩串珠,管辖大山神灵的儿女。”[5]138生活在怒江和澜沧江两岸的怒族,背靠山,面对水,几乎没有平地,人与自然,猎人与猎物,在这片领土上和平相处,怒族的成年男子左肩背弩及箭包,用以狩猎或防御敌人,获得猎物认为是猎神相送。现在的怒族社会虽已是以农业为主,但狩猎在怒族人民的生活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仍然保留下了一些特殊的仪式习俗。如,猎人在野外猎得猎物后,在他背着猎物进门前,需用门压死一只鸡来祭猎神,作为回敬猎神的礼物,猎物是雄的,压的就是母鸡,猎物是雌的,必定是公鸡。有关猎神的传说,并没有用很多华丽的言语,而是用很朴实的语言,塑造了一个个结实而勤劳的女性形象。
(三)女山神形象
怒族是一个以大山大江来命名的民族,它巍然屹立在西南边陲,有着雄伟怒山的豪迈气概。怒族人民的生产劳动都与大山息息相关,人们对山神有一种共同意识,认为每一座山峰都是神祇和精灵所在。怒族神话中,除了山神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之外,更多表现出的是世俗的一面。在《灵芝姑娘》[4]107-108一文中,故事讲述了很早以前高黎贡山上光秃秃一片,没有生机,山洞里住着山神姐妹,姐姐叫灵芝。离高黎贡山不离的卡哇嘎布村寨有一个妖精王,心狠手辣、无恶不作、强夺民女,当地人们深受其害,不久山神妹妹也被妖精捉走,姐姐在花仙老人的帮助下除掉这个害人精,同时也身负重伤,腿上的血流了一地,那些血流到的地方,光秃秃的山变成了绿幽幽的山岗。当地都说,高黎贡山上的奇花异草是山神灵芝的血变的。传说中有不少是神仙下凡来到人间,而下面这则山神的神话,却是人为神后,对家乡父老的馈赠。相传福贡县匹河乡一带流传着《山神娶妻》的故事,[3]3凡间女子义梅被腊马王直岩山神看中后娶为妻,被封为女山神,后来义梅的舅舅和叔叔上山打猎,受义梅恩赐收获颇丰,当地的人们为了也得到女山神的恩惠,每年都要带着家畜和家禽到山神所居之地腊马王直岩处祭祀,祈求山神多赐猎物,迄今,居住在果科格甲登村的怒苏自称是山神氏族,又称为拉甲要。凡间女子已化身为女山神来庇护她的乡亲,拥有神奇的法力,体现出神灵的神圣色彩。福贡县匹河乡怒族的传统节日“如密期”的一个重要仪式是对山神的祭祀,怒族生活的环境山高谷深,地势险峻,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人们自然需要去寻求山神的护庇,在“如密期”祭词中,“先祭深谷的岩神,岩神保佑怒村安宁;岩神保佑庄稼丰收”。②怒族人砍大树之前,要带上公鸡和酒祭山神,大树砍倒后,都会在树桩上放一块石,认为树是石头砍的,希望山神不要怪罪。正是人们对山神的这份敬畏之心和感激之情,才使得当地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
二 神幻奇境中的仙女形象
(一)圣母仙姑形象
这类女性形象是怒族百姓的救世主,为了人民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鲜花节的传说》[4]4塑造的就是一个为民谋利的女性形象,阿茸姑娘为给乡亲们找水源,不辞辛苦,手提砍刀、肩扛石锤,在高黎贡山的悬崖峭壁上苦熬了九十九个昼夜,终于在半腰凿了一个洞找到了泉水,使怒江两岸变成了绿洲,人们都说机智聪明的阿茸是仙女下凡,但阿茸为民造福的行为却招来了土司的陷害,土司认为阿茸在半腰凿洞破坏了风水,要抓阿茸问罪。阿茸逃到了自己开凿的洞里,土司用火烧洞口也没有把她逼出来,据说她变成了一座石像,甘甜的泉水就是从她身上流出的。阿茸遇害这一天,正是农历三月十五日,怒江两岸的村寨都沉浸在一片悲愤中,人们想念为民造福的阿茸姑娘,人人都采了一把把鲜花送进溶洞,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怒族的传统节日——鲜花节,也叫仙女节。贡山的怒族在节日这天,全体村民穿上节日盛装,带着祭品,牲礼从四周村寨会聚到仙女洞前祭拜,以求人们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免去病灾,怒族信奉“仙女”是母系氏族尊崇女性的一种体现。仙姑与孤儿的婚恋在怒族社会传为佳话,天上的飞禽、林中的走兽,水中的鱼儿均可化为美丽善良的仙姑,仙姑被勤劳善良的孤儿打动,他们结为夫妻相亲相爱生活在一起,但其中还要经历许多难题考验,如《蝴蝶姑娘》《仙草与公主》《梦中的仙姑》[1]78-90,在这些故事中,丈夫遇到迫害一筹莫展时,仙姑却表现出有胆有识勇于反抗的精神,在同邪恶势力抗争中,又被塑造成有胆有识,机智过人的“女强人”形象。这类女性形象的共有特征是机智勇敢,关心百姓的疾苦,有强烈的奉献精神,体现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至今仍然深受当地民众喜爱富于活力。
(二)龙女形象
在怒族社会中龙女形象尤为活跃广为流传,她们聪明善良,有恩必报。龙女与凡人的恋情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主题,故事类型大多是孤儿因为善良或救助了龙女变身的动物,得到了龙女的青睐,带着他来到龙宫,在龙王的许可下,龙女以身相许报恩,此后,男青年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都在龙女的神奇魔法下化险为夷,最终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在《腊塞与龙女》中,[1]36-44怒江东岸的孤儿腊塞救下了受恶龙欺负的龙女,龙女报恩与腊塞结为夫妻,但恶龙不肯就此罢休,使用种种计谋来陷害龙女,后在龙王和龙女的智慧下制服了恶龙。《孤儿的奇遇》、《金花和银花》和《变小狗的姑娘》都表现了龙女的有情有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1]56-77《孤儿的奇遇》中的孤儿救了龙王,龙女为了报答救父之恩,以身相许,并带来了可以变出任何东西的宝葫芦。当地的头人看到宝葫芦后,用尽各种办法想占为已有,但都被龙女所制服。《雪峰洞》[1]51-55塑造是则一个违抗父命、敢爱敢恨的龙女形象。怒江龙王的小女儿被许配给凶恶残暴的开江龙子,龙女逃婚来到人间与孤儿结合,正当他们用双手创造美好未来之时,龙王强行掳走了龙女,孤儿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救回龙女,得以团聚。怒族生活在江河之畔,靠怒江丰富的水资源生存繁衍。怒族认为龙神是水源之头,被人们奉为司云雨和掌管江河水源之神,对水资源的依赖导致对江河的敬畏,如果说对龙王的崇拜是为风调雨顺的话,那么龙女故事体现出的则是人类自身的繁衍,龙女与孤儿的婚恋,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孤男青年的意愿,也是怒族民众向龙神祈求生殖力量,获取繁衍后代能力的诉求。
三 怒族女神崇拜的文化内涵
综观怒族民间传说,不难发现典型的女神、女仙都以怒族社会中特定女性角色为原型。虽然女性至上已经成为怒族社会中的历史,但从当代怒族社会中仍然能窥视到女性崇拜的踪影。怒族主房的中柱、横梁或中柱与横梁间的衬垫上还可以看到用玉米面画的日、月及星星图案,他们认为,太阳是母亲、月亮是父亲,这与中国汉人社会中太阳为阳,月亮为阴是相反。在怒族社会中,没有父亲的孩子可怜但不被称为孤儿,但没有母亲,人就会成为孤儿,很可怜。怒族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从宗教信仰、人生仪礼、节日习俗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性。
(一)传统社会女性角色的原型折射
在怒族很多人神婚恋故事中,强调恋爱自由的同时,也需征得家长的认可。《龙女种瓜》中就讲述了龙女大胆直白的求爱方式,如龙女见到男青年后,直表心意地说:“我要跟你走,请带我去吧!”男青年再三回绝,但龙女用魔法使他只得答应。怒族青年恋爱大多不受父母的干预,但恋爱不等同于婚姻,婚姻最终还是由父母来决定和安排。在婚俗中以“母”为大,一切活动都听从女方家人的意见和安排,从订婚起,女方家的地位总是比男方家高,姑爷以及他的父母在女方亲属面前都要毕恭毕敬。在婚礼中,新娘的父母及亲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开席前,要先由新娘家的人对菜品进行品尝,在得到肯定后婚礼才可以正常进行。怒族的婚姻制度中,还留存着母权制的残余,如姑舅表的优先婚,据50年代对怒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反映,“在达拉(三村)、秀楞、茶腊村和彭登四村的调查,在68对婚姻中,14对是姑表婚,12对是舅表婚,3对是姨表婚,10对是三代以上的氏族内婚。有27对同藏、白、傈僳和汉等民族通婚。”[5]77舅权的习俗反映了现代的父系家庭结构,在社会控制上却很大程度依靠母系血缘延伸出的舅权制度。
怒族民间故事中,女神或女仙在与凡间贫贱男子的生活中,她们没有因为自己的高贵出生而高高在上,相反在大多故事情节中她们只在幕后出谋划策。这些都是怒族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化身,如《龙女种瓜》[4]75-79中的龙女与一个怒族穷小子结为夫妻,龙女在家织布,丈夫去外犁地。当财主看到美貌的龙女后心存妒忌,有意为难她的丈夫,他只好回家求助龙女,这些难题都被龙女一一破解。房屋的主房是怒族家庭活动中心区域,房中的中柱是神圣的象征,中柱里一定会放置钱币和七彩线,他们认为钱币代表的是父亲,负责全家的生计,七彩线代表的是母亲,她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给全家带来温暖,故事中体现的正是现实生活中贤妻良母的形象。从龙女传说我们发现,她们热爱劳动,不嫌贫爱富,富有反抗精神等性格特点,使得她们成为了无懈可击的完美女性。
(二)原始宗教信仰的反映
宗教信仰与社会发展、生产生活有必然联系,在民间故事里也会得到相应的反映。人们无偿地从大自然中获得食物,从而对大自然产生强烈的依赖感,但狂风暴雨、野兽侵袭,也会把人们辛勤劳动的成果毁于一旦,甚至危及人命,又产生恐惧感。人们为了化解矛盾产生了自然崇拜。怒族的山神、崖神、猎神多数被认为是凡人变的,《女子崖》[5]中的凡间女子被猎神看中,被封为崖神。贡山怒族“望夫崖”的传说讲的是,有个叫吉娜木忍的妇女为等待打猎不归的丈夫化为崖神。这些凡间女子成为保护神后,当地人把她们看作猎神、山神、生育神等诸神职能于一身的神祇。人们每逢建房需要砍伐树木,或是开荒种地等生产活动时都要祭山神,目的是劳作中万一触犯了山神,也会得到山神的宽恕。要开垦一块山地,要先行由巫师主持祭祀山神,巫师是本民族的智者,知道一块地是否可耕种,哪些树木需要保护,祭山神反映了怒族的对环境依赖以及对大自然恩赐的感激,同时也反映出无意识的生态环境保护。
(三)审美追求的体现
《猎人与女猎神》[1]20中年轻的猎人追着女猎神到树洞里,女猎神居住的树洞里堆着麻皮和麻线,她穿的裙子是麻线织成的,那麻布织得又匀细又漂亮。姑娘的头上戴着品飘(头饰),身上挂着红红绿绿的珠子,那头发辫子长长的、黑亮黑亮的;姑娘的脸庞儿端端正正的,皮肤红润红润的;牙齿排的很整齐,雪白雪白的;姑娘的身材又匀称又结实,结实的手臂,结实的脚板,结实饱满的胸脯。人格化的女猎神,正是怒族先民对女性审美标准的反映。女猎神心灵手巧的形象,也正是怒族社会对女孩子编织技艺水平的评判标准,织布技艺在怒族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女性本分职责和身份的象征。怒族女孩子一般在12岁左右开始勤学纺线织布,代表传统织技的怒毯,主要通过看线条是否笔直,宽度是否对称,来评价姑娘手工艺水平,在对福贡怒族的一些村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四十岁以上的妇女都能娴熟地掌握织布技艺。另外,女性健壮的身躯、乌黑的头发,是怒族男青年择偶的标准。
(四)节日仪礼中折射出的社会表现
贡山怒族一年一度的“仙女节”是以女性为主的重要节日活动,源自纪念阿茸姑娘,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这天,当地民众手捧火红的杜娟花或其他艳丽的山花,带上牲礼酒器,聚集于各自村落附近的“仙女洞”同祭“仙女”,以求来年得到仙女的保佑,保佑人们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免去病灾。这个节日是母系氏族崇拜的遗存,早已在2006年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物质文化遗产。“仙女节”以祭祀女神阿茸为主题,同时也把生殖崇拜、性器官崇拜的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石灰岩溶洞中的水滴,传说是阿茸化作身为神后流出的“仙乳”,据说喝了“仙乳”后不仅能强身健体、消灾避难,还能让久婚不育的妇女受孕、产乳,使婴幼儿健康成长。因此,仙女节这天主祭人率领所有朝拜者在仙女洞前跪拜后,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去接“仙女乳汁”。“仙女节”作为怒族社会的集体记忆,在建构的过程中维系了怒族女性的地位,也折射出了母系社会的女性崇拜。
综上所述,透过分析怒族民间故事里女性群体的共有特征,看到故事中的女性何尝不是生活中鲜活的女人们生活原型。怒族民间传说中的女性形象折射出了怒族人民对女神、女仙的崇拜,进一步反映出怒族远古时期的生殖崇拜和母权意识。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从民间信仰、家庭婚姻、节日习俗等方面仍然可以看出怒族女性具有较高的地位。
注释:
①福贡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福贡县民间故事集(上、下),2008年。
②叶世富,李卫才,普利颜,罗自群.怒族神歌,2009年,第13页。
[1]叶世富,郭鸿才.怒族民间故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2]攸延春.怒族文学简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3]左玉堂, 叶世富,陈荣祥.怒族独龙族民间故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4]泽米,王新宇.七彩贡山——贡山民间故事集[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
[5]“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怒族社会历史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龙倮贵]
Nu nationality Folklore in Female Image Interpretation
LIU W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 China)
The goddess of clan in the folklore, nymph,strong sense of social roles,colorful image,close to people’s lives,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is just the life portrayal of clan society women. In this paper,by analyzing the clan folklore of the goddess and the Sprite imag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related plot,reading the female worship of the clan society.
Nu Nationality; Folklore; Female culture; Discuss
C953
A
:1008-9128(2017)04-0049-04
10.13963/j.cnki.hhuxb.2017.04.014
2017-01-14
刘薇(198 0-),女,四川会东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民间文学、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