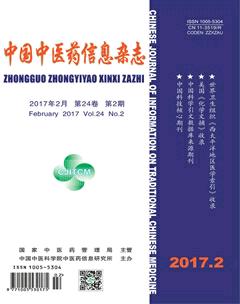从中医“木旺侮金”与肠源性内毒素血症探讨肝肺二脏病理传变
2017-03-04毛娅男赵国荣袁振仪何宜荣艾碧琛肖碧跃陈研焰
毛娅男 赵国荣 袁振仪 何宜荣 艾碧琛 肖碧跃 陈研焰
摘要:“木旺侮金”是中医对肝肺二脏病理联系的解释,肝木升发太过或肝火上炎、肝阳上亢均可传变至肺,致肺失肃降、肺阴亏虚。西医学的肠源性内毒素血症致肝肺损伤同样存在肝病传肺的病理机制。本文通过比较中西医学对肝肺二脏关系的不同理解,阐述“木旺侮金”科学内涵,为临床肝肺综合征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木旺侮金;肠源性内毒素血症;肝肺综合征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7.02.030
中图分类号:R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7)02-0112-03
木旺侮金是中医将五行学说与藏象学说结合而对肝肺二脏病理联系进行的阐述。生理状态下,肝木受肺金所克,故肝木是肺金之所胜。当肝木有病,传及肺金,出現反侮现象,称为木旺侮金。迄今学术界对肝肺二脏病理关系仅限于中医理论解释。兹从中西医两方面论述肝病传肺的病理机制,以揭示木旺侮金与西医学肠源性内毒素血症(intestinal endotoxemia,IETM)致肝肺损伤的相关性。
1 木旺与肠源性内毒素血症致肝损伤
木属五行之一,木曰曲直,条达舒畅,具生发之性,在五行生克乘侮规律中表现为木生火克土、乘土侮金等方面。中医将藏象与五行结合,将具升散、舒畅之性的肝脏类同于木,称肝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
酸生肝,肝生筋……”叶天士根据肝的特性,将其功能高度概括为“体阴用阳”,“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体阴,是指肝主藏血,并通过调节血量而制约肝阳,濡养形体官窍;用阳,则指肝主疏泄,疏即疏通,泄即发泄、升发。肝性喜条达,内寄相火而主升、主动,故为主疏泄。主要体现在调节情志,促进脾胃运化,调节胆汁的化生和排泄,以及促进血和津液运行与输布、调节女子月经和男子排精等方面,故其用属阳[1]。生理上,肝体用相互调和,肝疏泄正常,气血畅通,有利于肝之藏血,肝血充足可制约肝阳,使肝气不致过亢;病理上,体用失调,肝木过旺,是肝病的基本病机,表现为肝火上炎、肝阳上亢、肝郁化火等。西医认为,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腺体,具有分泌、排泄、合成、生物转化及免疫等功能。近年来,IETM与肝病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表明肝病多伴有IETM[2]。
正常机体肠道内寄生的多种革兰氏阴性菌分泌内毒素(LPS),肠黏膜作为机体保护屏障将LPS限制在肠腔内,避免入血。当肠道菌群稳态失衡,肠黏膜受损致通透性增加时,大量LPS被吸收入门静脉,超过肝巨噬细胞(KC)吞噬、清除能力,即进入体循环而形成内毒素血症。由于LPS来自肠道,故称为IETM。过量LPS可激活KC而产生大量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如促炎因子、趋化因子、一氧化氮、内皮素、自由基及活性氧等活性物质,造成肝脏炎性损伤。研究表明,信号转导通路活化是LPS激活KC的关键,LPS与KC上的相关复合受体CD14/TLR受体4结合,导致TLR4寡聚化,随即通过髓样细胞分化因子88(MyD88)依赖和非MyD88依赖两条途径触发一系列的信号级联反应,诱导核因子κB(NF-κB)、核转录因子激活蛋白-1(AP-1)和干扰素调节因子-3(IRF-3)等转录因子磷酸化和核转位,上调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IL)-1、IL-6、IL-8及干扰素-γ(IFN-γ)等细胞因子表达,启动炎症反应,导致肝脏损伤[3]。可见,中医肝火上炎、肝阳上亢等木旺病理与IETM致肝损伤具有可比性。
2 侮金与肠源性内毒素血症致肺损伤
金为五行之一,曰从革,指金具有刚柔相济之性,引申为凡具有沉降、肃杀、收敛等性质或作用的事物和现象均可归属于金。在中医藏象学中,肺的特性以肃降为主,故归属金,称肺金。中医将肺的基本功能概括为主治节,《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曰:“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肺主治节体现为两方面:①对肺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主要体现在肺主气,司呼吸,肺主行水,肺朝百脉。肺气宣发与肃降,不断吐故纳新,实现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气体交换。同时肺有节律的呼吸可促进全身之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气行则血行,肺气在调节全身气机时推动血液运行,助心行血;气行则津行,肺气宣发肃降可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和排泄。②作为相傅之官,肺对其他脏腑有辅助、协调作用。肺气贯心脉,辅助心行血;肺气右降,助肝气左升;肺气宣降辅脾化生水谷精气、输布津液;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为水之上源,肾为主水之脏,肺可辅肾蒸化、升降水液,纳气,藏精。肺气宣降是发挥主治节功能的关键,若肺失宣降,则气机紊乱,呼吸不利,血运不畅,津液输布困难;影响其他脏腑功能,则心血瘀阻、肝失疏泄、脾不运津、肾不纳气等。西医认为,肺除具有呼吸功能外,还包括防御屏障及免疫功能、内分泌及代谢功能各方面。研究表明,促炎因子与抑炎因子失调,炎性介质如TNF-α、IL-1、IL-8、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及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等大量分泌是IETM致肺炎性损伤的关键,当IETM形成后,大量释放的细胞因子主要通过2种途径使肺脏受损,即IL-1/ICAM-1途径通过诱导血管内皮细胞与中性粒细胞间的相互作用,造成肺脏炎性损伤,以及INF-γ/TNF-α途径诱导肺细胞大量凋亡,导致肺脏功能衰竭[4]。总之,肺金受侮,失于宣降的病理与IETM致肺损伤也具有可比性。
3 木旺侮金与肠源性内毒素血症致肝肺损伤
五行相侮,是指五行中一行对其所不胜的反向制约和克制。木旺侮金,即木气过于亢盛,其所不胜行金不仅不能克木,反而受木的欺侮,正如《素问·五运行大论篇》说:“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木旺侮金是中医用五行乘侮解释肝肺二脏的病理传变,指肝木太过对所不胜的肺金反向制约。生理上,肝肺二脏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气机调节及阴阳互相制约方面。《素问·刺禁论篇》云:“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后世医家将“左肝右肺”逐步发展成为概述肝肺气机升降,调节全身气机的理论,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咳嗽》指出:“但人身气机,合乎天地自然,肺气从右而降,肝气由左而升,肺病主降曰迟,肝横司升曰速。”肝主升主发,肺主降主收,如此一升一降,一发一收,共同维持气机升降协调,使全身气血上下内外环绕周运不休。同时,肺之阴津可协助肾阴制约肝阳,以免使其过亢。病理上,肝气亢旺,不受金制,反而侮金,肝气上逆于肺,致肺失肃降之能;或肝火过旺、肝阳上亢,均可灼烁肺金,耗伤肺阴,致肺阴亏虚。在IETM致肝肺损伤发生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肝病传肺的病理机制。肠道来源的LPS首先损伤肝脏而激活KC,活化的KC通过MyD88依赖和非MyD88依赖的2条信号通路,将大量炎性介质如TNF-α、IL-1、MCP-1等释放入血,炎性因子随血流至肺脏,导致肺脏炎症损伤[5]。同时,由于肝解毒能力下降,被激活的肺内巨噬细胞代偿性清除LPS,分泌大量活性物质如一氧化氮、TNF-α、IL-1、IL-8及其他炎性介质,加重肺脏损伤。
4 小结
中医通过结合五行、藏象学说,将肝肺二脏的生理联系、病理传变概括为金克木及木侮金。金克木表现在气机调节与阴阳互制两方面:一方面肺主肃降,肝主升发,肝肺二者升降相宜,则全身气机其分为痰饮、悬饮、溢饮及支饮,又从饮停时间长短、部位深浅及轻重的角度命名“留饮”及“伏饮”。因此,该篇虽名“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但实则重点论饮。此后从汉代到宋代,虽有论及“痰”,并试图将二者分开论述,但并未能将“痰”与“饮”完全区分,饮病学说仍占据主导地位[4]。直至宋代杨仁斋《仁斋直指方论》将“痰饮”分而论之,指出“痰之与饮,其由自别,其状亦殊,痰质稠粘,饮为清水”,此外,还对痰和饮从病因病机及治法方面作了鉴别。后世多宗其说,定义稠浊者为痰,清稀者为饮。
2 对“饮病”的认识
自杨仁斋将“痰”与“饮”明确分开后,众医家把目光更多投放到痰病的探究中,而对饮病则无更多阐发。此后痰病学说日渐丰富,而饮病学说的发展则停滞不前。因此,对饮病病因病机的探讨更多集中在唐代以前。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云:“人之有痰饮病者……外有六淫侵冒,玄府不通,当汗不泄,蓄而为饮,为外所因”;《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有“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太阴在泉,湿淫所胜,民病积饮”;《素问·五常政大论篇》曰:“……湿气变物,水饮内积,中满不食。”可见,六淫之邪可致饮,尤以寒邪和湿邪影响机体气化,易致水液停聚而成饮病。《素问·经脉别论篇》对人体水液的运行描述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由此可见,人体水液的正常运行,有赖于多脏腑的协同作用,包括脾的运化与输布、肺的通调水道、肾的蒸腾气化等。因此,除了寒、湿等外邪客体,七情内伤、饮食不节、劳欲过度等所致脏腑功能失调,尤其是肺、脾、肾三脏的虚损,亦会导致机体气血运行不畅,水液输布障碍,停聚壅塞而成饮病[5]。
3 病因病机
对于鼻鼽病因病机的认识,古今医家多从外邪侵袭、内脏虚损的角度论述,外邪以寒邪为最,亦有热邪致病说,而内因则多责之于肺、脾、肾三脏虚损,其主要病机为肺气虚致宣发肃降失司,脾气虚致传输运化无力,肾阳虚致蒸腾气化不能,导致水液代谢障碍,津液流溢,外渗鼻腔,发为鼻鼽[6]。由此可见,鼻鼽与饮病有相似的病因病机。就临床表现而言,鼻鼽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性疾病,常因寒冷或某些特殊物质刺激而发作或加重,与饮为阴邪,伏而难化,遇感引觸而为病的特点相符;此外,鼻鼽最显著的症状就是清水样涕,符合“饮为清水”的性质。 饮,是机体水液输布障碍、停聚壅塞于某一部位或某些部位的病理性水液,是病理产物,亦是致病因素。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饮邪停聚壅塞于机体偏虚之处,引发相应的病证,则形成饮病。而鼻鼽正是饮邪停积于鼻腔所形成的一种饮病。
4 针灸治疗思路
4.1 温阳化饮,治病求本
从饮邪特点而言,饮为阴邪,遇寒则凝,遇阳则行,得温则化,故饮邪为患,当温而化之。从病因病机而言,《临证指南医案·痰饮》提出“阴盛阳虚,则水气溢而为饮”,鼻鼽作为饮病的一种,其病机总属阳虚阴盛,本虚标实,治当补虚泻实,温补虚损之阳,温化停聚之饮。因此,在针灸方式的选择上,当重视灸法以温促通、通调气血、开发窍道、扶正祛邪的作用。《针灸资生经》有“风门,治鼻鼽衄时痒痒,便灸足大指节横理三毛中十壮,剧者百壮”,《备急千金要方》言“涕出不止,灸鼻两孔与柱齐七壮”等。现代医家采用多种灸法治疗鼻鼽,如天灸、艾条灸、艾炷灸、雷火灸等,均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7]。在腧穴选取上,有学者统计发现,古今文献中鼻鼽的选穴均以迎香为最多[8]。一方面,迎香位于鼻旁,属局部取穴,同时位于头面部,“头为诸阳之会”,针刺头面部腧穴有温阳之功效;另一方面,迎香为手足阳明经交会穴,阳明经多气多血,针刺可调和鼻部气血。此外,督脉为一身“阳脉之海”“诸阳之会”,具有调节一身阳气的作用,故除局部取穴外,可配伍督脉之百会、大椎、上星等穴,以调动一身之阳,同时激发诸阳经之经气,从而振奋阳气以疏散外邪。足太阳膀胱经循行于人体背部,背部属阳,故针刺膀胱经腧穴,亦有通调一身阳气之功,尤以背俞穴为脏腑经络气血输注之处,取之更能温补虚损之脏,调整脏腑虚实,扶正固本以利邪出。
4.2 辨证论治,调和诸脏
“温药和之”除了强调“温”法,亦不可忽视“和之”。“和”有平和、调和之义。古今医家对“和”一字也各有见解,主要言“温”不可太过,当防燥烈太过而伤阴,另有言“和”当包含“行、消、开、导”之义,使温而不燥不腻,令邪有出路[9]。鼻鼽其病本为肺、脾、肾三脏虚损,故针灸选穴当在温阳化饮同时,根据脏腑辨证随证加减,如肺气虚者常配伍肺俞、风门补肺固表、祛邪外出,脾气虚者加用脾俞、足三里、阴陵泉、三阴交健脾利湿、益气行水,肾阳虚者多伍肾俞、命门等温肾固本、助阳化气。此外,饮乃有形阴邪,易阻滞人体气机,气行则水行,气滞则水停聚而为饮;又肝主疏泄,调畅气机,故有学者提出从肝论治鼻鼽,临证配伍合谷、太冲、肝俞等穴以疏肝调气,使气行则水行[10-11]。因此,“和”字亦包含调和五脏六腑气血阴阳之义,只有脏腑功能正常,气血津液方能正常输布与代谢,人体阴阳方能得以协调。
5 典型病例
患者,女,35岁,公司职员,2015年10月21日就诊。8年前春季,患者出差时突发鼻痒、喷嚏、流清涕,在外院行过敏原测试示“屋尘螨++++,粉尘螨+++,柳树花粉+++”,确诊为变应性鼻炎,予西药抗过敏治疗后症状缓解。后每因季节变换出现鼻痒喷嚏、流清水样涕,秋冬季发作更频繁,西药治疗后可缓解,但停药后又复发。刻下:患者鼻塞鼻痒,喷嚏连作,流清涕,眼痒,晨起尤甚,余无明显不适,形体偏胖,平素恶风怕冷,纳谷不香,食生冷则便溏,舌淡红,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苔白滑,脉濡滑。查:鼻中隔右偏,左下甲肥大明显,鼻黏膜水肿,鼻道见少许黏性分泌物。中医诊断:鼻鼽(肺脾两虚证)。治当健脾益肺、温阳化饮。针灸处方:迎香(双),印堂,上星,合谷(双),足三里(双),阴陵泉(双),丰隆(双),大椎,肺俞(双),脾俞(双),其中足三里、大椎、肺俞、脾俞施以补法,行针得气后施以温针灸,余穴均平补平泻,留针30 min,隔日1次,6次为1个疗程。治疗1次后患者感鼻塞明显缓解。1个疗程后,患者鼻塞不显,鼻痒、喷嚏、流涕亦有减轻。守方继续治疗1个疗程后,诸症消除。巩固治疗1个疗程,随访半年,未再复发。
6 小结
本文从治饮的角度简述了鼻鼽的针灸治疗思路,宗仲景“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旨意,首先在针灸方式选择上,临床可适当配合灸法以加强温通之功,包括艾条灸、艾炷灸、雷火灸、温针灸等。其次,在穴位的选取上,一方面从“温阳化饮”角度,可在局部取穴的基础上,配合督脉、足太阳膀胱经穴,以振奋机体阳气,使饮邪得化;另一方面,当重视“调和诸脏”,辨证取穴以调整脏腑虚实,同时重视调畅气血,可选取合谷、太冲,配合多气多血之阳明经穴如迎香、禾髎、足三里等,使气血和调,邪自难生。
参考文献:
[1] 李杰,赵翡翠,王明礼,等.《内经》鼻鼽刍议[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1):33-34.
[2] 杨清华,黄建军.鼻鼽的古文献研究[J].中医药信息,2005,22(1):6-7.
[3] 杨尊求.饮病学术源流考略[D].昆明:云南中医学院,2015.
[4] 柳亚平.《金匮要略》饮病学说的理论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5.
[5] 周新颖.从中医古代文献比较痰饮成因、部位及其常见病证的范围[D].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07.
[6] 王任霞,张春晖,宁云红.从脏腑虚损论治鼻鼽[J].山东中医杂志, 2009,28(2):80-81.
[7] 刘群,杨佳,赵百孝.不同灸法治疗过敏性鼻炎研究概况[J].世界中医药,2014,9(7):923-926.
[8] 胡引,吕凯露.古今针灸治疗变应性鼻炎取穴思路分析[J].甘肃中医, 2011,24(6):51-52.
[9] 潘俊杰.《金匮要略》痰饮病因机证治辨析[D].杭州:浙江中医药大学,2015.
[10] 石志红,陈晟,付钰,等.“疏肝调神法”在治疗过敏性鼻炎中的作用[J].内蒙古中医药,2013,32(7):130-131.
[11] 谭程,王燕平,王朋,等.从情志变化试论过敏性鼻炎的针灸取穴思路[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28(3):317-319.
(收稿日期:2016-08-29)
(修回日期:2016-10-20;编辑:梅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