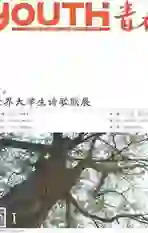爱情诗
2017-02-09黑凝
黑凝,本名张俊,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发表过中、短篇小说、散文百万余字。出版中篇小说集《蝴蝶谷之泪》,小说《证据》获中国小说学会奖,另有多篇小说、散文获奖。
今年六月初六。一早起床,我看太阳很好,是一片耀眼的灿烂。我们这里的坊间兴六月六晒“龙袍”(其实是日常穿戴的衣帽而已)。我在晒自己“龙袍”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存放乡间老宅阁楼的那一捆书来。它们寂寞地呆在黑暗的阁楼三十多年,应该已经落满了灰尘。
——题记
有一次学校图书馆搬迁,我是农村来的孩子,块头大,力气足,老师就叫我帮忙从一个屋子往另一个屋子搬运图书。我本来不想偷那本书,要怪那个脑袋尖尖,个子矮矮的图书管理员老头,他帮我码了没过脑袋的一摞书,我走路时眼睛都看不清前方。走到一个花坛边时,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堆在最上方的一本书滑进花坛月季丛中。我没有第三只手去捡起那本书,我本来想回来的时候再从月季花丛中捡起后交给管理员。可是,我当时不知忙了哪件事,忘记了花坛里的书。第二天想起来后,我又担心个说话唠唠叨叨的图书管理员老头会怀疑我故意为之。放学后,我悄悄溜到花坛边,把它取在了自己书包里,占为己有。
从此我有了一本普希金的爱情诗。
一直认为,我的诗歌启蒙老师是那个叫普希金的情种和疯子,他见到漂亮女人就写诗赠诗,他写的《给娜塔利亚》《致克恩》《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哥萨克》……每一首诗都让我读得泪流满面。有一段时间,我常常一个人步履沉重、满腹心思地徜徉在学校通往村子的家乡濑水河滩大堤上,我抓着自己的头发在濑水滩涂天空自由飞翔,我不知自己在梦里,还是现实中,但是,只有这样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濑水河上古老的石拱桥,濑水滩涂两岸的杉林,天空中飘浮的白云,校园里高耸的蓄水白塔,阿爹手中牵着的水牛,甚至穿梭在村野之间三婶母家那条调皮的黄狗,我都认真地给它们写过诗,激情飞扬地赞美过它们。我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和我分享激情,分享快乐,我曾经将诗稿投寄过南京一家叫《青春》的杂志社,石沉大海后,我再也没有将诗稿投寄过任何一家杂志社。因此,我们学校的师生,我们村上的社员,他们都认为我热爱劳动,尊敬长辈,不偷不抢不赖不懒不邪不恶,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孩子,他们又怎么会知道他们身边有一个天才少年诗人。
只有三婶母家的那条黄狗例外,有一回,我在濑水滩涂割青草的时候,看见它在河边闲溜跶,我把它哄到一片荒地上,从裤兜里掏出新写的诗,专门为它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那次,我读得泪水滂沱,它听得摇头摆尾,甚至眯着眼睛,用鼻尖来回磨蹭我的膝盖,舌根发着“呜呜”的声息,像是表达共鸣,又像是催我早点回家。后来,三婶母家的黄狗见到我总是扭头便跑,怎哄也不回头。
读初三时,我们班换了一位年轻姓杨的英语老师,她披垂着大卷波浪发,看学生的两眼波光潋滟,长相特像电影《白莲花》中一号女主角吴海燕。她是全校少数几个化着淡妆,敢穿紧身衣,敢袒露胳膊和大腿的女教师。那个年龄,那种时代,我还不懂得性感,但已经知道见了漂亮女人心痒。长辈们曾十分严肃地教导过我,见到漂亮女人就随便心痒的男人不是正派男人,换句话说是下流胚子。我们家族中从未出过下流胚子,所以,我努力克制自己心莫痒。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只要杨老师一走进教室,我就会情不自禁心痒。我对自己很失望。莫非我生下来就是下流胚子。
我想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一首接着一首地给杨老师写诗,从她眼角眉目写到举手投足,从一笑一颦写到星星月亮……那段日子,我的想像力疯狂滋长,它奔放、热烈,色彩炫丽。我发现自己比天才普希金更有天才,我的灵感像村子后面的濑江水,遭遇丰沛的黄梅雨,泛滥了,一浪高过一浪,汹涌不息,绵延不断。有时灵感突然来袭时,半夜我都会溜出宿舍,匆匆跑到学校最偏的厕所,伏在那盏老祖父眼睛一样浑浊无力的灯光下,贴着群蝇飞舞的厕所墙面写诗。或者,蒙在浓烈脚臭味的被窝里,打着手电光写……尔后,我会将写在小纸片上的诗句,工工整整地抄在我表姐送我的那本浅浅蓝色的日记本了,再在每首诗标题下用破折号隔开,标注献给女神MISS杨,再配上拙劣的插图。当然,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世界,我把那本日记本藏匿在最保密的枕头套内缝里,宿舍里没人时才掏出来翻翻。休息天,还将日记本带到濑水滩,站在密密的杉木林中,充满激情地朗诵几首。
是一节课外活动,我和同学在操场上愉快地抢着篮球,我刚好将手中抢到的篮球抱在手里,向球框迈着优美的三步投篮,我的班主任盛老师把我叫住了。
我赶到他面前时,发现他脸色是褚褐色的,像被陌生人大街上抽了耳光,十分难看。盛老师是教语文的,因为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平日里,同学们都看得出他对我有些偏爱。
盛老师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随着。走出十来步,他贴在我耳边嘱咐我,到教导处要主动认错,态度要诚恳,认识错误要深刻。我木讷讷地随着班主任后面,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导主任正襟危坐在进门第一张办公桌边,目光像审判长一样犀利地盯着门外每个过往的行人。一路随我而来的一只绿头苍蝇突然加速飞到余主任那绺油腻腻的发上。余主任是个秃顶,他的头发属于地方包围中央型,他总喜欢自作主张地占用有限的地方资源掩盖头顶的荒凉。可能地方也贫瘠,长出的毛发干燥、枯竭,因此余主任常常不得不到食堂揩些菜油抹上,以便凝聚。苍蝇正好喜欢油腻、腥膻。我双脚跨进教导处时,余主任正夸张地挥舞着双手,驱赶着那只可恶的苍蝇。我也想上前帮余主任一把,可是班主任盛老师悄悄地拉住了我。这时,我才发现坐在余主任侧边的杨老师深埋着头,在嘤嘤哭泣着。
我不知道漂亮的杨老师为什么要哭,而且哭得如此伤心,几乎一口气接不上一口气。我挪了挪脚,想上前劝慰杨老师几句,我不愿她如此伤心。但是,盛老师迅速用目光阻止了我。我好奇地环顾着教导处办公室内的空间,那只绿头大苍蝇还在余主任头顶低低地盘旋。盛老师轻轻拉了下我的衣角,像一个犯错的孩子,讨好地叫了余主任,又威严地对我说,还不快向杨老师作深刻检讨?
这时手忙脚乱的余主任才又恢复我们进门时的正襟危坐。他捋了一下搭到眉毛凌乱的地方资源,将它盘回中央,右手扶着眼镜,从眼镜后面跳出眼珠子来,子弹一样射了我一梭子。你叫童小兵?没等我回答,余主任又说,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我听得清清楚楚,他用的是犯罪两字。我们村上有一个小伙子,曾经恋爱不成,就杀死了那个他追求的姑娘,结果被以故意杀人罪吃了铁花生米。我做梦都没有做过杀人、放火这样的事,怎么就犯罪了?
盛老师抢先我一步说,余主任,童小兵同学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他这回就是来向杨老师作深刻检查的。又拉着我的衣角,示意着我。
我好奇地看着三位老师和那只低低盘旋的苍蝇,脑袋嗡嗡作响,一片空白。
余主任突然从办公桌抽屉里掏出一本浅浅蓝色日记本——没错,是誊写着献给女神杨老师诗歌的那个日记本。没等我反应过来,余主任“啪”地将日记本拍在办公桌上,又用左手五指在日记本上弹着,以一个掌握确凿证据的检察官的口吻说,童小兵同学,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杨老师哭泣节奏明显加快了,由于过分激动,或者说受到了当面侮辱,哭泣时呼吸不畅,哭后的泣声拖泥带水,很有点乡下吊丧的味道。
我吓呆了,像被掏走了五脏六腑,空空的傻傻的站着,不知所措。余主任显然被杨老师的哭声感染了,他嗖地站了起来,愤怒地拍着桌子吼,童小兵,你这是对杨老师的侮辱,你这是流氓行为,你这是犯罪。杨老师是我校优秀青年女教师,冰清玉洁,又怎能容你乡下胚子流氓诗句的侮辱?
由于说话语速过快,唾沫星飞溅在离他不到两米的盛老师脸上,盛老师抹脸时,用愤怒的眼神瞪着我,说看看你这事弄成啥了?看把杨老师气得。还犟着干啥?还不向杨老师道歉?
我不能理解,那些干净、美丽、纯洁的语言竟成了诅咒,成了侮辱,成了流氓、犯罪的把柄。我犯了什么罪?我瞪了一眼仍在嘤嘤泣泣的杨老师,心里莫名产生了厌恶。突然,不知哪来的勇气,我快速上前,一把抢过被余主任捂着的日记本,飞也似地逃离了教导处。
扑面而来的阳光照在我满脸泪水的脸上,光怪陆离。第二天,做完课间操,全校两千多名师生都齐刷刷地站在操场上,巴巴地盼着一声解散的口令,等来的却是高音喇叭“扑、扑、扑”刺耳的调音声。余主任通过高音喇叭庄严宣布了对流氓学生童小兵的处理意见,给予童小兵同学行政记大过处分,留校察看。
因为行政记大过处分,留校察看处理的污点,决定了十六岁的我上不了县上的任何一所高中。
那阵子急坏了我爹,他老人家尽管也因他的下三烂儿子而蒙受耻辱,但他不像我娘只知道整天唉声唉气。我爹就我一个儿子,他对我的忧虑再正常不过了。
我爹想到了他在一所山区农村中学担任校长的战友,他和我娘提了两只生蛋的母鸡,忐忑地敲开了老战友家门。那位头发花白,腰板直挺的校长是个爽快人,他听了我爹向他吐出的一肚子苦水后,竟满口应诺了。
我进高中学校的第一天,校长把我单独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了他和我爹的战友之情,说了他们在部队艰苦岁月,说了人生的不易和人间正道的走法。后来说的话跟我爹教育我的论点差不多。最后他说,你一个农村娃娃写个狗屁诗干嘛,那分明是文人骚客做的事嘛。有那时间,不如帮你爹放牛割草呢!你爹把你交给我了,我就得对你负责,读高中期间,一律不准再写什么狗屁爱情诗。
他说话时,我基本上保持沉默,我听人讲过沉默是金的道理。不过,校长让我有了再次读书的机会,有点再生父母的感觉。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和礼貌,我始终拿眼睛注视着他,不时还点下头,让他认为我在认真听他说话,我其实是个可以教育好的乖孩子。而实际上,我却在心里默默数着他的眉毛,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校长的眉毛长得很粗壮,白白的一撮,匙子一样坚硬地往上翘着,因为他说话老喜欢挥舞手臂,摆动脑袋,我数了好多遍,才数清他左边眉毛352根,眉心毛21根,右边眉毛403根。
看得出校长对我认真谦虚的态度很是满意,我走出校长室时,他甚至像待老朋友一样拍了拍我的肩膀。
学校静卧在苏、浙、皖三省交界的天目山余脉的繁枝密林和变幻云雾中,神秘而潮湿。一条溧水河从学校一侧潺湲而过,溧水河上接锦云水库,下连太湖。锦云水库由天目山脉崇山峻岭间千万条涧溪水汇集而成,湖面水光潋滟,干净而调皮。
我很喜欢这种环境怡人的学校,它让我神清气爽,一时忘记了初中时的不愉快经历。
我是寄读生,吃过晚饭,如果不用洗衣服,有一段空闲时间,我常常一个人溜到学校背后狮子山的密林里转悠。山上有很多墓碑,一簇簇像一个小村庄,多的地方简直就是一个小县城。我有时会挑上一块光洁的墓碑坐到天黑。不过,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是锦云水库,它像密林丛中的一面镜子,光洁、明亮。有一次,我在水库边呆久了,回到学校,第一节晚自修已结束。值班老师说我目无纪律,罚我在黑板前站了两节晚自修。站着的时候,我的上下眼皮老打架,我竟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与普希金同志在狮子山的密林里散步。我们不用翻译,走着说着,谈笑风生,好好的,他突然从他的拐杖里掏出一支枪来,向我连射多枪,我躺倒在一块墓碑边,身上流满了血,我睁着眼睛无助地看着渐渐黑暗的森林,而普希金这个疯子却狰狞地笑着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高二秋季开学时,从城里重点中学转来一位叫小霞的女学生。瘦小个子,习惯将长发垂在前额,遮住一张脸,看人时拨开一条缝,发现有人与之对视时,目光中流露着紧张、惊恐。一时,同学间的猜测、传言很多,有说小霞高一时跟男老师恋爱,还堕过胎;又说小霞读过一年高二,转到这里留一级,巩固基础,准备考大学;还说小霞有忧郁症,请过一年病假。反正不这样说,同学们都很难理解一个女生在县城重点中学读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转到穷乡僻壤的农村中学来。
我不打听别人的隐私,也从不向人透露自己的经历。
一个周六,我没有回家。我多备了一周的口粮,对爹娘谎称要留校补习功课。我爹娘自然喜上眉梢,我爹还往我裤兜里多塞了2块钱,我娘也开心地为我多煮了5个鸡蛋。
吃过晚饭,因为没有值班老师管着,我一个人在山里转到很晚才返回教室。我当时多想像梦中一样,能在黑森森的山林中碰到那个疯子普希金同志,哪怕真的被疯子掏枪打死也心甘。可是,我除了碰见一个守山的老鳏夫外,连一只野鸡也没有碰上。
返回教室时,我很奇怪这么晚教室里还亮着烛光。那个年代,电还是件奢侈品,平日里断电是常有的事,节假日,学校是绝对不可能送电的。所以,每个学生都备有蜡烛。我从后门绕进教室,我发现小霞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双手托着下巴,她前面摆着的一台黑色的小收音机,她正在专注地听着收音机里播的由孙道临朗诵的配乐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没有惊动小霞,站在教室最后一排,屏住气,静静听着: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
校园的四周一片黑暗,偶有从狮子山豁口吹来的夜风,一记一记小心地扑打着烛光。烛光在调皮着,左右前后,手舞足蹈,样子有点像大年初一邻家的五岁顽童,欢欢的、傻傻的,跑前跑后。突然听到如此动情的诗朗诵,我沉寂了一年多的心,被点燃了,激活了,随着烛光跳动着、燃烧着……
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冲出了教室,一口气跑到了锦云水库大坝上,面对深邃黑暗的苍穹,双膝下跪,嚎啕大哭……
第二天,我睡到晌午才起床。到教室时,只有小霞一个人在看书。我悄悄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从课桌抽屉里取出作业做时,却发现里面多了几本书,有一个叫惠特曼的美国老人的诗选,有新月派诗选,还有一本叫《瓦尔登湖》的散文。我当时又惊又喜,没顾上翻下书,贼贼地看了一眼教室四周,四周空荡荡,秋日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窗户玻璃上,一只黑鸟飞来撞击玻璃后,呜呜地鸣叫着飞走了。
鼓足勇气,我向小霞发问,这……书是你放我抽屉里的?
小霞的座位在我前三张课桌,她抬起头,慢慢扭过身,拨开遮在脸上的发,冲我莞尔一笑。我第一次看到不遮脸的小霞的那双略显忧郁的眼睛竟清澈如泉,只一个回眸,尽显了少女的妩媚,吓得我都不敢再看第二眼。我一个濑水滩涂农民的儿子,一个被余主任和杨老师称作下三烂胚子的贱民,自卑的虫子一直在我身体里蠕动着,啮噬着,我怕自己猥琐的目光会玷污了眼前如蝶少女,我怕多看一眼会弄脏她的衣裙。
她说,是的,我知道你喜欢诗歌。
我正在犯疑。她笑道,我是从你的眼神中发现你喜欢诗歌的。她的笑得很干净,很自信。
你的眼神迷离,飘游,你目空一切,却又分明很不自信。你从不与人对视,但却看着很遥远的一个地方。我说的不对吗?小霞有点调皮地看着我,三月桃花,满面笑靥。
你和平常不是一个人。我说。疑惑地看着她。
小霞咯咯笑了,笑毕又用手捂着嘴,恢复略显忧郁的眼神,轻描淡写地看着教室外,像自言自语,却分明是说给我听。她说,我当然还是那个我,只是没有找到与这个世界对话的窗口而已,与自己之外的人交流是一件痛苦而尴尬的事。难道你不是这样?
我愕然地看着离我不足五米的小霞。我正想说些什么,班里的寄读生已经陆续返回学校。
通过小纸条的交流(她把想说的写在小纸条上,乘没人注意时,夹在我的书本里;我也投桃报李,如法炮制),我了解到,小霞的父亲是一名将军,母亲是著名的诗人。她的父母相差近20岁,他们的婚姻缘于母亲对父亲的崇拜。然而,文革中,红卫兵指责她母亲有一首诗涉嫌反动,被揪着了,先是戴着写有反动派高帽四处游街,又被剃了阴阳头拉到礼堂批斗。忍受屈辱和折磨的母亲原指望将军丈夫会救她于地狱,会像他带兵打仗时一样,不顾一切地拎枪冲进礼堂保护她。没想到她父亲为与反动妻子划清界限,竟向组织提出与她的母亲离婚。离婚后,她母亲把小霞托付给县城的外公外婆,自己投河自尽了。她送我的书就是她母亲留下的。
小霞的境遇令我唏嘘,难怪她会隔着发帘看人,见到生人的目光会紧张、惊恐、躲闪。更难怪她会说与自己之外的人交流是一件痛苦而尴尬的事。
与小霞交流多了,我也会挑选一些自己写的诗,通过小纸条传她看。只是对我写的诗,她从不评论,偶尔趁同学不注意时,会从一帘发缝间给我传递一个微笑。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小霞相约到锦云水库去走走。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和一个女同学约会,心里不免紧张。小霞在前面,我和她保持着约500米的距离。走到校门口时,水老师从传达室走出来。水老师老婆没工作,他就在传达室开了个代销店,兼顾门卫。水老师平时只有两大爱好,一是为他老婆向学生兜售代销店里的日杂用品;二是好管闲事,若有同学夜出校门,他一准会悄悄地跟踪到底,第二天再向校长汇报。所以,有男女同学夜间出来,大都从厕所一侧的围墙翻出去。我和小霞是大白天出去,光明正大,我们干嘛要翻围墙?
水老师问我出校门干啥去?说着还看了看前面慌慌走去的小霞。我没跟他答话,只是瞟了他一眼,昂着头走了过去。
我和小霞在水库走累后,找了一堆干净的石子坐下。她跟说得最多的是她的母亲和她母亲的诗。我给她读了我写的几首新诗,也跟她谈了对诗的看法,我没有说我初中时的那件丑事。我们聊天的时候,已近黄昏,湖面吹来的风已经凉得浸洇肌肤。我见小霞打了个哆嗦,便脱掉自己的外套,想给小霞披上,小霞推却着。就在这时,水老师带着两名公安已经立在了我们身后。等我发现时,一名公安已经扭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了一边。
我和小霞分别关在了派出所的两个房间。我不知道他们怎样提审她,很担心她的安危。
提审我的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年轻公安,但火气不小。他问了一些基本信息后,开门见山地又问我和小霞什么关系?我答同学关系。他说同学关系你就可以把她引诱到水库边调戏了?我说没有,我话还没说完,他“啪”一个大耳光子就上来了。
我捂着发烫的脸,又说没有。他“啪”又一个大耳光子。很不耐烦地嚷道,老子可没那闲功夫跟你干耗,我们的眼线已经跟踪了你多次,你也在你的作案现场多次踩点,你把人家女学生的约到偏僻的水库边就是图谋不轨,你想调戏人家,幸亏我们的人及时赶到了。
我捂着发烫的脸,争辩道,没有就是没有。公安干脆不审了,他一脚踩上用于提审我的桌子,蹭地越了过来,劈头盖脑给我一顿拳脚。要不是那个从水库边抓我来的高个子公安赶到,我非死在他的拳脚下不可。
当天晚上他们把我扔在滞留室,没再审我。
第二天,我听到外面走廊里吵吵嚷嚷,好像校长和我爹在跟谁交涉着,争论着,场面有点混乱。有一个干部口气的可能认识校长,他向校长解释着什么。我还听到了我娘绝望的哀叹声,我当时对我娘有点生气,她一辈子遇事只会唉声叹气。后来,不知是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弱,还是昨天晚上我的耳朵被那个公安打坏了,我一点都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再次审讯我是第五天上午。其实,那次不叫审讯,应该叫指认。仍然那个帅公安和高个子公安,他带来了余主任,杨老师,我初中时写的那些“流氓诗”的书面证明,并从我家时取来了那本我没舍得扔掉的浅浅蓝日记本,以及我给小霞披的那件秋衣。他们叫我一一指认并签字。
签完字后,他们便把我扔进了拘留所。
半个月后,我被以流氓罪宣判劳动改造八年。
1991年秋天,我被刑满释放后,没有直接回家。我先去了锦云水库。那天,天空一忽儿晴空万里,一忽儿乌云密布,一忽儿又电闪雷鸣。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水库边,狂风吹起的浪花四下飞溅,打湿了我的衣裤,我的脸。一片泪光中,我看到小霞正张开双臂,笑着向我飞奔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