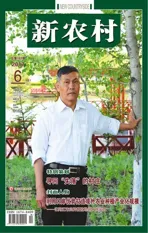古村保护难在哪儿?
2017-01-31
古村保护难在哪儿?
村中道路已大量使用现代建材,与老房墙体不甚和谐。
桑峪村,位于门头沟区潭拓寺镇,属清水河流域。村落四面环山,静谧而优美,为清水河流域形成最早的古村落之一。
元代初,桑峪地区就生活着50多户居民。明代前,桑峪曾叫“三遇”,这是因村中有三条沟壑相连,三沟之水相汇为一而得名。明朝后期,村中桑树茂密成林,久而久之,“三遇村”演变成为“桑峪村”。
然而,随着一条水泥路进村,人们目光所到之处,除一些破败的四合院,都是结构简单而现代的民居平房,虽然有的房子房顶还是用瓦片盖的,但是几乎所有房子的围墙都是用砖头和水泥建成,有的房子已经废弃无人居住。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说:“现在看到的房子都是新修的,那些文革时修的房子有的都破得不成样了,那些老房基本都被拆掉了,没有拆的老房里面也不住人了。”
这么一个700多年前就伫立在京郊的古村,却为何一点也不古老,历史踪影在这里几乎荡然无存。
清华大学建筑系研究乡土建筑的教授楼庆西感叹:“古村落的保护,比保护故宫更难。”之所以这样感叹,是因为故宫的时间是定格的,它从1911年起就被定格成为一座博物馆而没有人居住。而古村从古到今,都是村民居住的地方。这样一种与村民共生的关系,让古村随着居住的村民而改变。随着社会与科技的进步,古村的居住形态和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
与人的互动性是古村繁衍的气息所在,但这也正是古村保护的难点所在。古村的保护,不仅仅应该保护它的建筑,使之不因天气、时间等外部因素而损毁,更应该保护其与人的互动性,在人与古村的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籍教授罗杰对比了国外与中国古村的保护情况,认为中国对古村的保护应该更注重人与建筑的共生关系。他强调,世界上的游客认为庞贝古城是保存完好的古建筑,但它已经失去了让人居住的能力,成为一座博物馆之城,而不能再称之为一座真正的城邦了。他认为,古村落的保护是一种人与村中建筑和谐共生的状态。
欧洲的小镇历史悠久,漫步其中令人享受到安逸和悠闲。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小村镇,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450年,但是它的木头房子、湖边栈道都未经过改变。“这些地方与中国古村镇最大的不同在于人。”罗杰表示,欧洲小镇,村民不愿离开自己世代生存的地方。政府也想通过保护措施与投资,将居民更好地留在那片土地上。而中国的古村镇,由于大部分地处偏远与欠发达地区,居民为了生计而离开,同时,古村镇往往因为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而衰败。
中国古镇保护发展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很多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初始阶段不重视保护古村镇,反而为了追求快速城镇化急于求成,破坏了古村建筑。一段时间之后又想到文化的重要性,就开始造假,后来就又建起一个新的古城。
虽然,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有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但古村镇的保护问题更复杂,需要因地、因村制宜。在这些口号与标准之下,古村镇作为人的历史的见证与承载者,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其保护过程中的灵魂。
沿着桑峪古道继续往山上走,就是广惠寺。“广惠”在佛语当中是大智大慧、消除烦恼之意。庭院里挂有许多藏族的经幡,还有一对矗立了1300多年的雌雄银杏树,仿佛这座寺庙的守护神,庄严地审视着每一个村民。然而,这位守护神尚且不知,它庇护下的这个古村正面临着现代化的巨大考验。
(京郊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