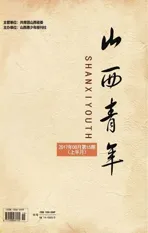“买卖型担保”之法律性质探析
2017-01-30伏海璇
伏海璇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买卖型担保”之法律性质探析
伏海璇*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当事人针对同一笔款项先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借款合同》,并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借贷合同提供担保,该种交易方式名为买卖,实为“担保”。“买卖型担保”不能被认定为让与担保,因担保物的权利并未实际移转,亦不能实现优先受偿的担保效力。“买卖型担保”合同系属诺成性约定,实质上为附条件的债的变更,不应将其混淆为代物清偿合意或代物清偿预约。
买卖型担保;让与担保;代物清偿;债的变更
债务人为获得融资,与债权人就同一笔款项先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借款合同》,并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债务人如到期不能偿还债务,则须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交付房屋以抵顶借款,此类交易系“买卖型担保”。对“买卖型担保”之法律性质,学界众说纷纭,司法实践中的判决亦呈现出不同的解释路径。为明确“买卖型担保”的法律性质,厘清其所产生的各项法律关系,确有必要从法教义学的角度,考察学界和实务中既存观点的理论基础,并对各种观点进行辨析和探讨。
一、“让与担保”定性之辨析
在“朱俊芳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借款协议》涉及同一笔款项,《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借款协议》提供担保。但具体到案件事实,当事人并未就标的物设立抵押权,而仅约定,债务人在届期不清偿债务时,负有以标的物抵顶债务之义务,故此类担保并不属于法定的典型担保。对此,杨立新教授求助于“让与担保”之定性,并提出“后让与担保”之概念。笔者认为,若承认“后让与担保”这一概念,那么所有权在先转移的担保也可以被称为“先让与担保”。据此,“让与担保”实为“后让与担保”的上位概念。换言之,“后让与担保”法律关系之本质仍为“让与担保”。
笔者认为,“让与担保”这一界定值得商榷。首先,从概念出发,德国法仅以强调要点的方式概括让与担保的特征。我国台湾地区则接受了德国关于信托的让与担保理论,将让与担保界定为所有权的转让、返还和就担保标的物受清偿的一种非典型担保制度。我国大陆地区对于让与担保之界定,总体而言是对台湾地区及德日之引用或改造而来。对于让与担保概念之界定虽各不相同,但都强调了让与担保的关键要件——担保物权利之移转。具体到买卖型担保,当事人之间仅成立了一个以设立让与担保的合同,而标的物的权利却并未移转于债权人。担保物权之设立须遵循“区分原则”,在设立担保物权的合意之外尚需存在一个独立的担保物权设定行为。而买卖型担保仅包含设立让与担保之合意,担保物的权利却并未移转于债权人,不符合让与担保的构成要件。
其次,从效力层面出发,对内而言,让与担保的中心效力在于,让与担保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可以行使让与担保权以获得优先受偿;在担保人陷入破产程序时,债权人对担保物享有别除权;对外而言,在担保人的一般债权人强制执行担保物的场合,基于让与担保的“保护机能”和“经营维持机能”,根据具体的责任状况,应当肯定债权人享有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的权利,或保障债权人就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
然而,基于买卖型担保当事人所设立的让与担保的约定,在债务未到期之前,担保物权利仍归属于债务人,即使债务人擅自处分担保物,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主张违约责任,并无力干涉其处分。同时,买卖型担保欠缺公示手段,设立担保系当事人间的内部约定,无权对抗第三人。一旦债务人陷入破产程序,债权人仅具有普通债权人的地位,对担保物并无优先受偿权。在债务人的其他一般债权人强制执行担保物的情况下,债权人无权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或主张优先受偿。据此,买卖型担保并不具有让与担保的一般效力。综之,将买卖型担保认定为“让与担保”值得商榷。
二、代物清偿界定之反思
(一)“代物清偿合意”效力之争
买卖型担保合同又被称为以物抵债协议,其约定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须向债权人为他种给付以代原定给付,与代物清偿发生相同的法律效果。“代物清偿契约之成立仅当事人之合意尚有未足,必须现实为他种给付。”代物清偿为要物契约已为台湾地区学说和判例所一致认可,在德国和日本亦为通说。我国大陆地区学界也延续了“要物合同说”的观点。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210号民事判决书裁判理由指出“代物清偿是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清偿,以债权人等有受领权的人现实地受领给付为生效条件”,明确将代物清偿定性为要物合同。
具体到以物抵债协议,当事人只是约定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而该他种给付并未被现实履行。倘若借助代物清偿合意来认定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问题即在于,单纯的代物清偿合意是否有效。
《德国民法典》第364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受领所负担的给付以外的给付以替代履行的,债务关系消灭。”该规定未提及代物清偿合意强调。通说未否定代物清偿合意的效力,认为受领给付的过程当中同时发生代物清偿合意,由此使代物清偿合意与清偿效果重叠。当今德国多数学说则不再将代物清偿合意视为要物性合同,而认为,代物清偿合意使债务人获得以履行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替代权。若债务人不行使该替代权,其仍负有履行原给付的义务;若其行使替代权,在其履行他种给付之后,债务才得以清偿。以上两种观点一致认为,即便达成代物清偿合意,原有的债权债务内容也并未发生变更,只有在债务人实际履行他种给付之后,代物清偿合意才能对债务人发生拘束力。
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则恪守代物清偿之要物性,认为单纯代物清偿合意并未现实为他种给付,不发生效力。对此,陈自强认为,在契约自由原则下,只要成立契约之意思表示健全且契约内容不违法,就不应否定单纯代物清偿合意的效力。
笔者认为,基于鼓励交易和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现实需要,同时为了实现意思自治原则的功效,只要单纯的代物清偿合意不违背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公平等基本原则,就应遵循契约自由之精神,肯定其效力。但因代物清偿之本旨在于消灭原债权债务关系,故无论是基于代物清偿要物性之理论建构,还是依“债务人单方替代权说”将代物清偿合意从要物合同的范畴内抽离,只有在债务人实际履行他种给付后,代物清偿合意才对债务人发生拘束力。
而依据以物抵债协议,他种给付虽未实际发生,但当事人已约定了他种给付的条件,并承诺在条件发生后实际履行。据此,以物抵债协议应属诺成性约定,其对债务人之拘束力的发生时点应为约定达成之时,而不是在物之所有权转移之后,这显然与代物清偿合意对债务人之拘束力的发生时点不符。鉴于此,不应将以物抵债协议混淆为代物清偿合意。
(二)代物清偿预约之审视
在代物清偿协议达成之后履行之前,台湾学者借鉴日本之判例,谓之为“代物清偿预约”,并就其效力产生分歧。孙森焱认为应依据代物清偿权之归属判定代物清偿预约之效力。陈自强教授则认为,无论代物清偿权之归属,代物清偿预约均有拘束力,但特定情形下债权人负有清算义务。司法实务中亦有观点将以物抵债约定界定为代物清偿预约。
笔者认为,“代物清偿预约”这一界定并不妥当。其一,“代物清偿预约”产生的法律效果与以物抵债协议之本旨相违背。预约之效力主要体现在对当事人不履行预约在法律上可能发生的效果,权利人得诉请法院命契约人为订立本约的意思表示。基于代物清偿之要物性,订立代物清偿本约即意味着强制执行标的物以清偿债务。而以物抵债协议约定债务人仅在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才负有以标的物抵顶债务之义务。据此,代物清偿预约之法律效果显然有违以物抵债协议之本旨。其二,“代物清偿预约”中双重合意之叠加将简单的法律关系复杂化,亦悖于实践中的交易惯例。预约是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若采“代物清偿预约”之定性,基于代物清偿之要物性,法律关系可抽象为:代物清偿预约—代物清偿协议—给付的履行—债权债务关系消灭这一递进链条。由此可见,“代物清偿预约”蕴含着双重合意,“代物清偿合意”被包裹于预约合意之中,“预约”之引入为实现债务清偿之法律效果增加了一步环节,这实则是对简单问题的复杂化。具体到以物抵债之实践,当事人通常也不会约定将来订立以物抵债协议,而是先订立以物抵债协议,再在以物抵债协议中具体约定履行他种给付的条件。由此可见,不宜将以物抵债协议界定为代物清偿预约。
三、债的变更认定之探讨
买卖型担保合同系属诺成性的约定,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权利义务关系:①债务人如期履行还款义务(以下简称“义务A”),债权债务关系消灭;②债务人到期不履行义务A,义务A消灭;债务人须将物之所有权转移给债权人(以下简称“义务B”),物之所有权转移后,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换言之,在债务人违约的条件成就时,义务A变为义务B。据此,笔者认为,可将买卖型担保认定为附条件的债的变更,且该债的变更系属处分行为。
首先,契约变更自由为契约自由原则之应有之意。债权契约自由之内涵囊括缔约自由、相对人选择自由、方式自由、内容自由和结束自由。因此,在合同成立之后,结束之前,当事人有权自行调整或变更合同标的、给付方式等事项。
其次,台湾地区早有判例指出,仅约定将来应为某他种给付以代原定给付时,属债之标的之变更,而非代物清偿。台湾地区民法学界对债的变更和债的更改做出明确区分,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究为债的变更,还是债的更改?对此,陈自强教授指出,债务变更契约系指债权人和债务人变更原有债之关系之内容的契约。区别于债之更改,达成债务变更契约后,原有债之关系并不因此而废止,而是仍然保持其同一性。债的更改,系成立新债务而消灭旧债务之契约,经济上,新成立债之关系为原有债之关系之延续。由此可见,区分债的变更与债的更改的关键标准在于,原债务是否消灭或废止。就买卖型担保而言,探寻当事人间“义务A变为义务B”之约定的真意可得出,在债务人违约的条件成就后,义务A直接消失,义务B产生,义务B之关系为义务A之关系的延续。故买卖型担保之构造,更接近于债的更改,而非债的变更。
但回归至我国现行法,并无必要区分债的更改和债的变更,因债之标的之变化通常以变更协议的方式实现。我国《合同法》将合同界定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明确了变更协议的合同效力,且合同的变更在我国法上被限定为合同内容的变更。以双方行为协议变更合同乃意思自治的体现,此时的变更协议属于另外一个新的合同,适用合同成立和生效的规定。
依买卖型担保当事人之真意,若债务人违约,义务A消灭,义务B产生。据此,买卖型担保并不宜被认定为负担行为范畴内的债务变更契约或变更协议。一来,债务变更契约或变更协议之认定不符合当事人之真意,因当事人约定原债务在条件成就后直接消灭,而并未约定须履行免除或废止原债务的行为;二来,从学理角度出发,如上文所言,其在构造上应被认定为债的更改,而非债的变更。考虑到在我国现行法上并无必要区分债的变更和债的更改,故在此处可将买卖型担保视为处分行为意义上的“债的变更”。换言之,一旦债务人违约的条件成就,义务A即变更为义务B,而非约定义务A变更为义务B。因债的变更以债务人违约为生效条件,故可将买卖型担保视为处分行为意义上的附条件的债的变更。
四、结语
当事人采取“买卖型担保”之法律构造,旨在以不动产所有权之移转构建担保效力。但从法教义学角度考察让与担保和代物清偿的构成要件和效力,并不能对“买卖型担保”的性质做出妥当界定。此时,基于清简思维,分解其法律关系,将其认定为债的变更,既符合法教义学上的概念要件,亦能使事实上担保效力的构建正当化。
[1]杨立新.后让与担保:一个正在形成的习惯法担保物权[J].中国法学,2013(3).
[2]董学立.也论“后让与担保”[J].中国法学,2014(3).
[3]向迎春.让与担保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4.12.
[4]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896.
[5]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20.
[6]崔建远.合同法[M].法律出版社,2010:132.
[7]陈自强.无因债权契约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30-331.
[8]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2011.58.
[9]崔建远.以物抵债的理论与实践[J].河北法学,2012(3).
伏海璇(1996-),女,江苏淮安人,华东政法大学,2016级民商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D
A
1006-0049-(2017)15-007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