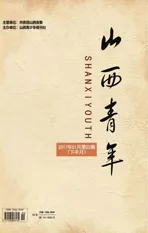对农村城镇化中失地农民政治权利行使状况的思考*
2017-01-30朱亚南
朱亚南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对农村城镇化中失地农民政治权利行使状况的思考*
朱亚南*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随着农村城镇化建设的纵深发展,许多原有依靠土地种植生存的农民在国家的征地建设中失去土地变为失地农民。失地农民在变为市民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表现在政治权利行使方面则是功利性和被动性的特征。本文通过对失地农民在农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参与政治的表现进行研究,总结出失地农民政治权利行使的现状,并结合笔者对大量文献的阅读和实地调研的走访探究这种现状存在的原因。希冀通过文章的表述可以引起各界对失地农民政治权利的关注,进而为失地农民未来的发展增添新的保障力量。
农村城镇化;失地农民;政治权利;现状和原因
一、农村城镇化中的失地农民
农村城镇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对于什么是农村城镇化,虽然众说纷纭,但基本的内涵仍然是农村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是农村各个方面向现代化靠拢的必经阶段。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改善,对于衡量农村城镇化发展状况的标准,许多学者曾指出,农村城镇化不仅是城镇数量和规模的增加,也不仅是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是农村各方面的发展,因此,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状况如何应全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水平,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使得那些原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变为失地农民群体。
失地农民并不是在农村城镇化中才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类群体就存在,但多是一些城市在扩建过程中征收土地,使得征收土地地区的农民失去土地,当时的农民是获得较多利益的,再加之离城市中心较近,后续的生产生活有较多保障,所以未引发出较大的问题。农村城镇化中的失地农民是在国家大规模的征地建设新农村中失去土地,群体的规模较大,且集中连片的存在。有学者曾经归纳过失地农民的失地途径。马丽琴 在归纳孔祥林、王君萍和李志建的观点后总结出,农民失地的路径有三条:第一条路径是利益集团(包括某些违规批地的地方政府、名目繁多的开发区以及各类娱乐项目投资商)非对称性的强占乱建失地;第二条路径是政府政策诱致的组织性失地,为了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政府政策诱致的组织性失地是允许的;第三条路径是农业比较经济效益的自愿性失地。由于土地耕作的生产经营成本较高,种田的收益低甚至赔本,农民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主动离开土地,造成土地搁荒,实际上是一种自愿性失地。[1]本人所研究的失地农民主要是指那些在政府拆迁或者招商引资征收农民土地使原先靠土地生存的农民,居住在政府统一规定的地区内,并在户籍上变为市民的失地农民。
总结看来,失地农民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第一,年龄都比较大,“4050”群体尤为居多。失地农民过去是依靠土地种植为生,多是响应国家号召分田自干的农民,在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失去土地;第二,文化水平较低。因长期居住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许多失地农民的教育水平都停留在初中水平以下,有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小学水平或未接受过文化教育,许多失地农民只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识字能力有限;第三,经济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过去,失地农民依靠土地耕作获益,但收益较少,现如今失去土地后,虽然国家给予相应补贴,但因缺乏其他劳动技能,许多失地农民缺乏谋生渠道,收入很低;第四,对城市生活适应能力较差。失地农民搬入社区后,人上楼心却未上楼,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节奏,仍然保留着农村的生活作息,日出而活动日入而休息,没有了土地,他们很空虚,尤其是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在发展能力方面表现出较弱的倾向,许多失地农民养成了好吃懒做爱打麻将的陋习。
二、失地农民政治权利行使的现状
厦门大学的学者李琦将政治权利定义为:“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从而得以在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实现人的内在需求的权利。”[2]李琦学者定义的政治权利有两方面的侧重点,一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是有前提的,即满足公民的内在需求,二是这种需求是公民不可或缺的权利,他人不可剥夺。北京大学的王浦劬教授在《政治学原理》一书也为政治权利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政治权利,就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关系及其体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由政治权力确认和保障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的主张其共同利益的法定资格。政治权利的内容是对于共同利益的主张,形式是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法定资格,行为上表现为政治权利法定范围内的自主性。”[3]王浦劬教授所定义的政治权利更多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角度出发,强调国家赋予人民政治权利,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自愿参与政治生活。《宪法》[4]在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作了详尽的规定,其中关于政治权利和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等。失地农民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政治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笔者发现失地农民在政治权利行使方面存在着一些与法律和现实的偏颇。政治权利的行使具有极大的功利性。这个功利性不能片面的等同于李琦学者所说的那种公民内在的需求,而是一种异化的需求,即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顾他人权益的追求。失地农民在获取国家补贴方面与当地政府是存在诸多矛盾的,他们希望自己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因此,在政治参与方面,他们只参与对自己有利可图的决策或者选举,对认为与自己无关的政治活动,他们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功利化的政治参与表现的非常明显。虽然从理性经纪人角度看失地农民的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但若仔细分析,这实际上体现了失地农民对自己所居住的地区没有归属感,只将其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工具或容器,以前的村落还是熟人社会,农民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是熟人调节,中国人又比较爱惜面子,有内在的自律意识,将村落视为自己归属地,在参与政治方面也是表现的较为积极和容易被鼓动参与政治活动,而在面临一个新构建的农村社区,失地农民总有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又不熟”等心理围绕着失地农民。
由此进一步发展的现状是,失地农民在行使政治权利时也表现出了被动性,对绝大部分认为与自己不相干的政治活动要么不参与,要么极为不情愿,除了利益方面的考虑之外,失地农民对许多年轻的大学生村官也抱着一种轻视态度,农村人自古以老为尊,在村落居住时期,村庄中说话较有分量的人往往是村中年龄较大的有能力者,失地农民在面对年轻的大学生村官时,总是有轻视心理,不愿配合其工作,对待自己的政治权利,有利者则誓不罢休,无利者则极不情愿。当然,农民群体对政治权利的意识是非常不足的,失地农民也是如此,他们中大部分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不明白何为政治权利,只是通过经验和与自己相熟且拥有相关知识的人交流来判断自己所能享受到的政治方面的权益。在政治权利的行使方面有极大的被动性。
三、出现失地农民政治权利行使异化的原因
农村城镇化是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施行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效果尤为明显,但这些成果,实际上是使农民成了利益成本的支付者。农村打破了原有的生产结构和布局,许多农民变为失地农民,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许多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只能依靠国家的帮扶和当地资源的开发生存,由于无法适应城镇生活的方式,许多农民在生产生活上表现得较为消极,更不用说去关心自己生活的社区事务了。政治权利是每个人在一个国家中赖以生存的权利,但失地农民这一群体对待政治权利的行使已表现出消极的一面。对待失地农民政治权利行使异化的原因,笔者将其归纳如下。
传统观念的影响。失地农民原先居住在自然村中,深受影响的是自然村的传统文化,对待政治这一方面,许多农民仍然是过去落后的官本位思想,存在“清官判案”思想,认为与“官”打交道是不好的。其次,失地农民在参与政治活动方面有着自卑心理,许多失地农民表示,自己做不到像城市人那样有文化,经常将“城市人”和“农村人”这两个词语挂在嘴边,用标签去衡定行为,究其原因是自卑心理在作祟。再次,上文中也提到了关于部分失地农民轻视年轻基层工作者的问题,农村传统文化中的“尊老”思想使得部分失地农民对年轻的基层工作者组织动员群众参与政治活动表现的很不配合,认为自己的资历比那些年轻人高,与其共事或受其“指使”有失面子。
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跟不上经济的发展。“硬件设施”是指失地农民可以享受到的与市民享有权利相等的诸如经济保障权、医疗卫生保障权和劳动保障权等权利,以及失地农民生活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设备。“软件设施”则是指让失地农民接受教育使得其与市民的文化素质达到同等高度的措施。可以发现,在失地农民生活的区域,“软件”未跟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就造成了农民虽然住上了楼,但是内心却没有进楼,依然停留在村落居住的政治心理层面。
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建设在大规模的开展,失地农民能否顺利解决失地后面临的经济难题,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权利的关注是在人们获得基本的温饱并有闲暇时才会有机会浮出水面。“政治权利的理念化和制度化,必须立足在一定的社会的现实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成熟。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是这种理念在制度上能否得到或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体现的决定性条件。”[5]因此,当地经济的发展,关乎着失地农民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许多地区因缺乏优质资源,虽然建了很大规模的城镇建筑或工业厂房,但经济效益却不是很好,这对失地农民的政治权利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
国家政策的不到位。失地农民成为大规模城镇建设的利益成本支付者后,国家拿出了补贴政策,但却未做好失地农民未来发展方面的政策。失地农民没有经济生活的保障,更谈不上对政治生活的关注。亨廷顿就曾说过,“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参与扩大的主要转折点是农村民众可以介入国家政治。……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是能否动员农村民众在承认现存政治体系而并非反对它的条件下参与政治。”国家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不能仅仅限于一次性付清的经济补贴,而应该考虑是一种长效发展的策略,为失地农民未来的发展方向做一个恰当的引导,不能放任自流。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政策关注的焦点是城镇建设,而不是城镇中人的建设,从国家公共财政的投入方向,就可以清晰看出国家政策在对失地农民增强政治权利意识这一方面的缺位。
四、结束语
农村城镇化中的失地农民在政治权利形式方面表现出的异化还有很方面笔者未有涉及,如如何来针对这些异化的表现作出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增强失地农民的政治权利观念,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仍然是一大难题。农村城镇化发展至今,一方面它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改善是不容忽视的,但另一方面造成的失地农民群体产生的问题也是不能够被抹去的,失地农民的政治权利行使异化是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衍生的问题,也是可以慢慢通过各种方式改善的问题。解决这种政治权利行使异化的关键是在国家的引导上和国家的行动上,引导失地农民积极就业,给与失地农民一定的就业指导和便利条件,这才是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常态,也是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手段,建设一个富强、民主和文明的国家,既要有罗尔斯所倡导的正义理论中的公平原则,也要有全面发展的总体布局战略。因此,失地农民的政治权利行使异化问题必须受到各界的重视,关注这类问题,为更好地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扫除障碍,健康发展。
[1]马丽琴.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权益问题研究——基于政府行为的分析[D].南京农业大学,4.
[2]李琦.公民政治权利研究[D].厦门大学.
[3]王浦劬.政治学原理[M].96.
[4]1982年宪法.
[5]吴铭.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权利缺失及对策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2007.
*安徽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编号:J18520254)”经费资助。
F323.6;F
A
**作者简介:朱亚南(1994-),女,安徽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本科生,现已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录取为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政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