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视域下艾芜《南行记》的美学风格
2016-12-23麻三山
余 玲 麻三山
生态批评视域下艾芜《南行记》的美学风格
余 玲 麻三山
生态批评通过对作品文本及其结构深层次的解读,向读者宣扬作者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帮助读者打开获取作品中生态信息的通道。此外,生态批评还担负着繁荣生态文学的重任,通过分析作品中生态内蕴被呈现出来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帮助生态文学作家总结创作的优劣得失,促进其提高创作水平,加强作品的感染功效,更广泛深刻地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为解决生态危机创造条件。
艾芜并非准生态文学作家,《南行记》也并非“准生态文学”,就以上意义而言,用现代生态批评对文本做生态式解读,来观照其基于生态理念上的艺术化表现手法,多少有些苛求。但是,单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用生态批评理论的视角仍能对艾芜作品进行解释,也可看出其作品的前瞻性和历史性。而且,虽然不是典型的生态文学,《南行记》的某些“生态内蕴”如“天人合一”,却也是疗救人类“生态意识缺乏症”的精神良药。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南行记》的美学风格,就会发现其独特的美学价值。
意味深长的生态意象
宣扬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思想,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是生态话语承担的责任,为了避免直白说教,生态文学会借用意象将“生态内涵”蕴蓄起来,分析生态意象是把握小说生态内蕴的关键。
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往往包含着隐喻、象征等深层意蕴。《南行记》中充斥着大量意味深长的生态意象,艾芜艺术功力的深厚与绵长,其质朴无华的生态智慧在这些意象之中熠熠生辉。
首先,“森林”“山川”“河流”等自然意象反复出现。
整天遇见的,全是望不尽的古老松林。朝山顶上望,是松林,朝山壕里瞧,也是松林。这在近处看起来,松针映着阳光,还显得通明翠绿,令人怡悦。如向四周远眺呢,却又有些怕人,处处黑压压的,气象十分蛮野。(《荒山上》)[1]
山风卷着松涛,像海洋的狂澜似的,带着吓人的声浪,从远处荷荷地滚来,一阵阵地刮着崖头刮着树,打着板壁打着门,发出怖人的巨响。有时且扬起尖锐的悲鸣,像是山中的妖怪在外巡游一般。(《松岭上》)[1]
史怀泽说:“我们越是观察自然,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自然中充满了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秘密,我们与自然中的生命密切相关。”[2]艾芜笔下,“森林”“山川”“河流”在“土地”的怀抱中,一股来源于大自然的原始生命力与和谐美让读者感慨万千,内心深处也涌动着对“大地”母体的敬畏与尊重。
其次,鸦片作为颇具代表性的意象被多次提及,它与自然有关,耐人寻味。
《三峡中》强盗魏老头子无事时就吸烟,《松林上》挑担卖货的老头把烟枪比作自己的大女儿,无比宝贝,《我诅咒你那么一笑》中,“我”的老板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抽烟,《洋官与鸡》中的寸师爷也是很自觉地享受着店主们打上福的鸦片,《我的旅伴》滑竿夫老朱冒着生命危险私运鸦片,歇脚客店的老板娘也是终日伺候烟客,而这烟客中竟然不乏普度众生的缅甸和尚。
鸦片来源于罂粟,但是罂粟本身不是鸦片,最初被作为药品被大面积种植,是人类对金钱、对快感的贪婪,向自然过度榨取,加工成鸦片,违背其自然本性,才最终走向精神的消解和生命的终结。作品中的烟贩和烟民,生活因为鸦片而虚度,生命因为鸦片而衰竭,人生也因为对鸦片的狂热嗜好而失去价值,这是自然对人类的警示和惩罚。艾芜借鸦片这一意象,引发读者对生命意义、生存方式的思考,艺术化地表达了自己的生态哲思,却了无痕迹,不愧是文学大师。
画龙点睛的背景材料
背景材料,是指与所叙述事件相关的历史和环境材料,用来衬托作品的主题。艾芜借用背景材料来反映生态环境的变迁,通过对比性的差异来传达自己的生态思想。
《月夜》中,吴大林以“读书人”身份敲开回族少女的院落大门后,关于屋内的陈设和装饰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们随着女主人走进一间屋子,里面点起油灯,看摆设的桌椅板凳,漆得黑油油的,只是一处屋角落单,木架子上重重叠叠放了十几个簸箕。屋子正中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很大的画像,有二尺来高,腰间佩一把长刀,宛如一个将军一般。纸色旧而且黄了,但画中的人物样子,却极有神采,威风凛凛地望着我们,仿佛就要开口吃人一样。画像顶上横起两行字,不是中文,却是一点一弯的像是回教徒的文字。屋子里有股浓烈的气味,闻着有些闷人。(《月夜》)[1]
从画像纸质的黄、旧,可以判断其年代的久远,画中人物样子凶狠,且画上没有汉字,鉴于之前少女再三拒绝,不难推测,确实如少女所说,这里的回族村落仇恨汉人,对于过去的历史仍然耿耿于怀,既反衬出历史背景的真实(清朝咸丰年间的云南回民起义),又足以说明这段杀戮的灭绝人性。
“我”的“爱人”,是从沙拉瓦底县(Tharawaddy District)捉来的“强盗婆”,她看起来面目狰狞,似乎对谁都不友善,然而却并不妨碍“我”对她的同情。
谁不知道沙拉瓦底县是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缅甸农民暴动的发源地呢。
在我被捕之前,曾看见英政府从农民那里夺回来的旗子,是一幅三角形的白布,绘着一条遍身鳞甲的大蛇,被一位威风凛凛的神人踏在地上,不断挣扎。那神人有着一副雷公嘴,头上顶着小尖塔,手肘上长着一对翅子;左手捏着蛇尾,右手的刀作着快要砍下的姿势——这显然是一幅英缅斗争的剪影,巨蛇不正是象征着毒害全缅的帝国主义吗?(《我的爱人》)[1]
以上背景材料合理解释了回族姑娘“恨得没道理”及“我”默认了“强盗婆”是爱人。从表面上看,是历史上的种族杀戮和帝国主义造成了回汉不容和“强盗婆”的悲惨命运,而从生态的角度去把握其深层的含义就不难发现,无论是种族灭绝还是帝国主义的肆虐,都源于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资源的掠取,对生存空间的争夺,进而引发了有关生存的哲学思考——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人究竟应该怎样生存、人应该怎样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由此,《南行记》的思想价值在小说的背景材料中彰显无遗,守卫自然家园的环境伦理意识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想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深深的鞭挞。
“多声部”的对话元素
前苏联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曾经说道:“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3]
由此可见,在对话的概念中,各种声音的相互联系和作用被突出强调,这一点在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麦克杜威尔的论述中也得到了印证,“假如一种生态批评以此为出发点:处于伟大自然之网中的一切实体都应得到承认并拥有发言权,那么这种生态批评就有可能探索作者如何再现自然中人类和非人类声音的相互作用。”[4]
艾芜在《南行记》中多次运用了“对话”理论,通过制造截然不同的声音来引出和升华主题。尤其是涉及人与自然的冲突、人对自然的依存、不同人物不同的自然观念等问题时,作家通过这种“多声部回响艺术结构”的展示引发读者的思考,体验不同观点的相互碰撞,潜意识里参与“对话”,由此慢慢贴近作家的创作意图,去探寻其生态理念,往往令读者印象深刻。
《三峡中》老头子、鬼冬哥和“我”就“书”的价值进行的对话,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这里涉及自然和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我们的有友人》中老江与众人的对话,看似幽默的调侃却道出了“理智”总被“欲望”征服的观念,这是人性异化后的后果。《快活的人》中“我”和胡三爸就“生命的意义”“生存的方式”进行了交谈。最耐人寻味的当属《月夜》中,回族少女就吴大林和“我”再三请求留宿时的争论,因为“你们汉教的兵,先前在这里杀过我们的人,妇人小孩,都没有饶过,还烧过房子”,“我们从小就习惯了,一提起你们汉教的人,就想起杀人放火,连妇人,连小孩……”[1](《月夜》)。无论吴大林如何申明自己“好人”“平民”“穷人”的身份,都不能动摇回族女子因为他们是“汉人”而拒绝他们的决心,直到听说他们是“读书人”才勉强给他们食物,容他们歇息了片刻。这里回族女子对“读书人”的认可,体现了“回族人民尽管经受了清朝时期的劫难,但尊重知识文化的传统依然是整个民族传统的一部分”[5],此处,折射出作家关于人与人如何维系和谐关系、人与人的内在联系的哲思。
宣教的非叙述性话语
非叙事性话语指叙述者自身在陈述故事的过程中,或者叙述者通过事件、人物或环境,表达或传达对故事的理解和评论。非叙事性话语主要体现为叙述者的观念和声音,它表达的是叙述者的意识和倾向,但是它也可以通过对事件、人物的描述渗透到叙事或人物话语中,用以凸显叙述者的存在。
《南行记》中的“我”承担了叙述者的角色,“我”是故事材料的提供者、组织者、表达者和担保人,“我”对故事加以安排、分析、修辞乃至制造反讽。“我”或者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或者隐蔽自己,去观察、听闻、记述别人的存在和发生的事实。很多时候,“我”是公开存在着的,正如布斯所说,“纵使作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他的伪装,他绝不可能使自己消失。”[6]大量非叙事性话语,正是保证“我”不消失的重要叙事手段。
《南行记》到处可以听见“我”的声音,第一篇《人生哲学的一课》中有大量集中的描写,可以说是作家艾芜关于生存、生命、人生思考的集中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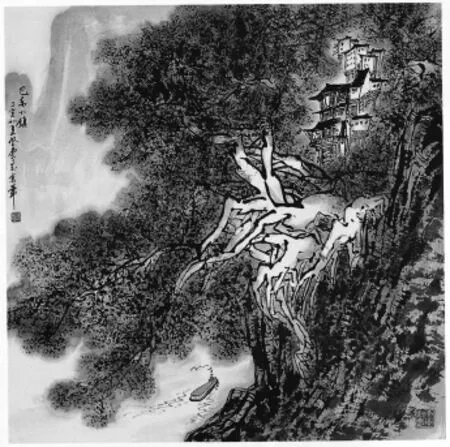
张登堂 巴东小镇
真的,为了必须生存下去的事情,连贼也要做的,如果是逼得非饿死不可的时候。[1]
饥饿的威胁,逼我一直勇敢下去。[1]
只要有炭来添,我这个火车头是不怕一天到晚都跑的。找百回事,总要碰着一件吧,我是抱着这样不灰颓的心情罢了。[1]
花去两个铜板,买点东西马马虎虎地吃了之后,觉得这两次小小的挫折,也算不得怎么一回事。我的肌肉,还没有倒在尘埃里给野狗拖扯、蚂蚁嘬食的时候,我总得挣扎下去,奋斗下去的。
我心里没有悲哀,眼中也没有泪。只是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颗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念头:我要活下去!就是有时饥饿把人弄到头昏脑胀浑身发出虚汗的那一刻,昏黑的眼前,恍惚间看见了自己的生命,仿佛檐头一根软弱的蛛丝,快要给向晚的秋风吹断了的光景,我也这样强烈地想着:至少我得坚持到明天,看见鲜明的太阳,晴美的秋空的。
工作找不到手,食物找不到口,就值得让饥饿侵蚀自己的肌肉,让饥饿吮吸自己的血液了,不过这究竟还能够把生命支持到某些时候的。(《人生哲学的一课》)[1]
艾芜通过“我”主观地间隔原本连贯的情节,意在强调叙述者的权威,从而使读者不仅从“我”的叙述,也从“我”的这些非叙事性话语中全方位地理解事件的表层与深层因素,王晖在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中说,“受众最希望了解的是叙述者对人所共知的事件、人物和问题的真知灼见,而不仅仅是事件、人物和问题本身。”[7]这里,“我”便是用自己的声音述说对人生的看法,直接指出“生存”是人的基本需要,生存在受到威胁时,人会被激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公开的评论”显示出“我”的自我意识,具有控制读者的力量,引导读者去评判故事中的是是非非。
显然,这些非叙事性话语集中表达了艾芜关于生命和生存的思考。满足饥饿的需要是人生最根本的需求,然而,饥饿到何种程度才算生命即将耗尽,人应该通过怎样的手段来满足饥饿的需求,这也是作家启发读者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立足于当今严重的生存危机、精神危机,便不难发现这是由生态危机引发的,继而用生态思维去观照,就会回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来,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便是一切问题的本源。从这个本源再去把握作品,就不难领悟到作家生态平等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智慧了,而这也正是《南行记》文体魅力之所在。
生态伦理的叙事视角
叙述视角是指作品中叙述者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叙述的特定角度。叙述的魅力不仅在于讲述了什么事件,还在于是什么人、从什么视角观察和讲述这些事件。叙述视角的特征通常由叙述人称决定[8],叙述视角的选定至关重要。
生态小说作家比较看重“内聚焦”型视角,在“内聚焦”型视角中,每件事都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主人公或见证人)的感观去看、去听,以展示故事材料。《南行记》中“我”在众多事件中承担旁观的角色,一方面站在“我”的角度能够拉近读者和作品的距离,另一方面,读者也是“我”的旁观者,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脱离“我”所受到作家当时创作动机的影响,去挖掘作品更丰富的内蕴。“我”作为内聚焦型的叙述视角比较容易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认同。
艾芜在《南行记》中还采用了生态伦理叙事的视角,表现出一种独有的人生态度和体悟生命的方式。“伦理叙事”通过文学的手段探寻属于个体生命的感受和体验。现代的伦理叙事则试图发掘日常生活中斑驳的道德力量和道德价值。
在《南行记》中,艾芜“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勾画南国迷人的风光和生活情境,唱出了作家对下层人民在反动统治的裂缝中挣扎求生的内心沉痛。”通过丰富的小说意象衍射出作家内心的真情实感。因此《南行记》被誉为“‘真’的文学”,“已融合和升华作家的经历和体验,他的痛苦和欢欣,他的留恋和憎恨,他的人生思考和理想追求。”[9]然而,挖掘人性扭曲的社会根源并不是艾芜的最终目的,他更执着于人性在未来的健康发展。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感染读者,使人们知道在他们的生活圈子以外,还有一个更具活力,色调明亮的世界。”[10]他的艺术风格独特而自然,引领读者欣赏边陲风光和品味异国情调的同时,使他们获得一种诗画交融的审美趣味,体会到中下层人民身上纯良的品性。
此外,正是采用了生态伦理视角这一艺术化的故事讲述形式,作家在作品中巧妙地穿插了一些非情节性的生态知识,既提高了作品生态知识的含量,又了无痕迹地达到了作家生态宣教的目的。《南行记》所写的都是远离现代文明的滇缅边地。它们带我们进入了一个与现代文明相距遥远又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自然景观雄奇、奇崛、奇丽、迷人。无论是松岭、山峡,还是茅草地,都是风景优美独特。《南行记》中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有许多对异国异乡风光情调生动细致的描绘,这些生动的描述除了具有生态学的价值和意义外,还向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蓬勃生机,读者便可以把握作家敬畏自然、崇尚自然的生态哲思。
结 语
《南行记》折射的生态哲思,是艾芜作品能够穿越时代、永葆魅力的重要原因。然而,作者采用意味深长的生态意象、画龙点睛的背景材料、“多声部”的对话元素、宣教的非叙事性话语以及生态伦理的叙事视角使得生态文学所担负的说教使命悄无声息地蕴含在字里行间,其匠心独运的艺术手法为以后的生态文学创作带来了启发。
[1]艾芜.南行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Michael J.McDowell.The Bakhtinian Road to Ecological Insight[J].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 in Literary Ecology.Cheryll Glot felty&Harold Fromn,ed.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
[5]白草.论艾芜小说《月夜》中的回族女子形象[J].回族研究,2005(1).
[6][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付礼军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7]王晖.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3(2).
[8]童庆炳.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9]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0]吴进.论沈从文与艾芜的边地作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1).
余 玲,女,湖北汉川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北海校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和英语教学法。
麻三山,苗族,湖南花垣人,博士,广西北海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保护与规划、文化遗产景观设计、文化遗产和人力资源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