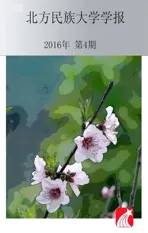回族聚居区的文化特征及其对汉语方言变体的影响
2016-12-17李生信
李生信
(北方民族大学北方语言研究院,宁夏银川750021)
回族聚居区的文化特征及其对汉语方言变体的影响
李生信
(北方民族大学北方语言研究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回族的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回族聚居区在地域观念、文化认同、民族意识、宗教影响等方面体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以回族文化为内核,特殊的语音变体、宗教色彩深厚的借词、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专有词等汉语方言变体类型逐渐形成。
关键词:回族;汉语方言;语言变体
汉语是方言众多且分歧较大的语言。促使汉语方言发生变化的因素是多元的,有历史文化因素,有方言地理因素,也有社会环境因素。这些因素既有产生于语言自身的,也有来源于语言外部的。内在因素体现了语言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外在因素则比较复杂,是语言、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各种因素的综合。汉语方言的差别虽然没有形成不同的语言,却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变体。从各个方言变体的形成过程不难看出,方言变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
严格地说,回族话是一种汉语方言变体。在以往的回族话研究中,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化差异对汉语方言形成的影响,但关于地域文化差异对汉语方言形成的影响却研究较少。其实,方言变体既是地域文化的外化形式,又是地域文化的底层遗存。方言是居住在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观察事物、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有效方式,承载着这一语言群体的文化特性、风俗习惯、礼仪往来等人文要素,也折射着方言群体的社会心态、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回族话作为一种汉语方言变体,既有民族性,又有地域性。
居住方式是地域性最突出的表现。回族作为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居住方式分为回族聚居、回族和汉族杂居、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等形式,其中回族聚居、回汉杂居的地域特征对区域汉语方言变体的形成影响较大。在回族聚居区,民族文化特征更加外显,是该区域汉语方言变体形成的重要因素。
一
回族以民族聚居、民族杂居的居住方式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在宁夏银川、吴忠、同心、泾源、西吉、海原,甘肃张家川、临夏,新疆昌吉,青海门源、大通、民和、化隆以及河北孟村、大厂等许多地方都形成了回族聚居区。由于民族聚居的因素,回族聚居区表现出以下一些文化特征。
1.地域观念。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形成,一般都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有些民族聚居区本来就是民族发祥地或先民居住地,有些民族聚居区虽然是迁徙而来所形成的,但也经历了长久的居住历史。悠久的居住历史陶冶了浓厚的地域情结,这无疑是乡音方言形成的人文基础。一个民族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民族发展进程,以相同的地域、相同的文化、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心理特质为纽带,形成了牢固的共同体。每个民族大都形成了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共同居住区域,但民族居住区域并不是绝对不变的,由于各种因素,会出现民族迁徙。在民族迁徙中,会出现失去以往的共同地域、在新地域形成新民族聚居区的情况[1]。语言会随着聚居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形式使回族聚居区的汉语方言出现了一些变化,区域汉语方言既保留了回族话中共有的民族语言特征,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等方面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又由于聚居区域不同而形成了新的地域方言变体。不同聚居区的回族话融入了所在地域的汉语方言,打上了地域文化符号的烙印。
2.文化认同。民族聚居区是民族文化形成的丰厚土壤,由于民族长期聚居,民族文化氛围比较浓厚,民族文化特征比较外显。民族聚居区基本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习惯、民族艺术、民族礼仪、民族服饰、民族节庆等文化特征。民族聚居区的民族经济特点、民族生产方式也伴随着民族文化而传承,这些具有传承性的民族文化几乎融入民族生活的各个层面。语言是记录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基本手段之一,回族聚居区的汉语方言必然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语言现象,在民族语言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融入民族文化成分。
3.民族意识。民族聚居区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性,长期居住在这里的民族成员耳濡目染,从小就接受民族文化的陶冶,民族意识比较强。回族和其他民族交往时使用汉语,在民族内部交往时也使用汉语。在语言交际中,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在所使用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在回族聚居区的汉语方言中,由于长期的语用“别同”心理,有意无意间形成了汉语的方言变体,这种变体是旨在形成回族内部民族文化意识的共同语言特征。这种共同语言特征正是民族意识在语用方面的外显,也是回族聚居区汉语方言变体形成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4.宗教影响。我国55个少数民族大都保留着本民族的宗教观念,无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信仰喇嘛教的藏族、蒙古族,信仰佛教的傣族,还是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原始宗教的一些少数民族[2],都把语言作为传播宗教观念的主要工具。不同民族的宗教理念必然会以各种语言形式进入本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中,影响民族语言的各种特质。宗教的这种影响力在回族聚居区的汉语方言变体形成过程中同样产生作用。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在宗教生活中,汉语的一般词汇已经不足以完全表达伊斯兰教理念,于是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转化为汉语借词进入回族使用的汉语方言,形成了回族聚居区汉语方言变体的特殊类型。
二
语言不仅具有交际功能,还具有文化传承功能。方言在使用者的交际过程中,往往承载着情感认同、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使用者对方言的选择,折射出对语言的态度。从前文对回族聚居区文化特征的分析不难看出,虽然方言变异有其内在因素,但真正促使方言变异的还是社会文化因素。在回族聚居区,回族文化的地域观念、文化认同、民族意识、宗教影响等特征,促使回族聚居区汉语方言形成了以下一些变体类型。
1.特殊的语音变体。这种变体是回族文化地域观念在语言中的表现,回族话作为汉语的方言变体,因为聚居区域不同而在语音上有明显差别。宁夏回族说的是宁夏汉语方言,青海回族说的是青海汉语方言,新疆回族说的是新疆汉语方言,陕西、甘肃、云南等地的回族话都融入了所在区域的方言之中,形成了各自的语音差别。回族话在汉语民族变体中又因聚居区域不同而形成了地域变体,表现出回族汉语方言地异音殊的语音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回族话在融入聚居地汉语方言的同时,在声、韵、调等方面又表现出与该方言区汉族话的不同,形成了回族聚居区汉语方言的语音“别同”现象。如宁夏平罗回族话中有卷舌韵母ar,古日母止摄开口三等字“儿尔而耳饵”都读ar,而汉族则长读a;另外,除a组外,其余后鼻尾韵母均并入前鼻尾韵母[3]。宁夏银川纳家户方言更能体现回族聚居区的语言特点。纳家户地处宁夏银川近郊,方言和银川话相近,属于兰银官话银吴片。纳家户回族方言和周围汉族方言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同时,在民族内部,由于使用者的年龄和身份差异又分化出老派方言和新派方言。老派方言把普通话中的后鼻尾音韵母大都归并到前鼻尾音韵母中,新派方言则把普通话中的前鼻尾音韵母大都归并到后鼻尾音韵母中[4]。老派方言和新派方言的形成,表面上是年龄差别的结果,实际上是聚居程度差别的结果。老派方言使用者多为年长者,受聚居区的影响较大;新派方言使用者多为年轻人,受聚居区的影响相对较小。地域化的程度成为纳家户回族方言变体形成的一大要素,这是符合方言变体形成规律的,也恰好证明了回族聚居区汉语方言语音变体形成中的地域文化因素。
2.宗教色彩深厚的借词。回族话中的借词主要指那些用汉语音译或音意合译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汇。这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汇,由于宗教表达的需要,融入回族使用的汉语方言中,形成了回族聚居区汉语方言的特殊类型。这些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在拼读时,在声韵方面已经汉语化了,回族人在读“安拉”“胡达”这些借词时,按照汉语的拼读原理,在声母、韵母上保持着汉语的拼读组合规则,在声调上却形成了自身的特征。单从语言本体的角度来分析,声调是回族使用的汉语方言变体中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特殊身份的标记。这些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融入回族聚居区的汉语方言,在语法上符合汉语语法的一般规则,在语调上却表现出特殊性。回族聚居区汉语方言中这些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大多为宗教用语,语用范围主要在宗教生活、宗教礼仪等环境中。汉语中的借词大多是因新事物、新概念的引入而进入汉语的新名词,这些新名词或者以音译的形式,或者以意译的形式,或者以半音半意的形式进入汉语词汇中,成为汉语中的外来词。回族聚居区汉语方言中的借词来源比较特殊,语用者在使用时带有民族情感因素,成为回族话中的一种特殊借词。这些借词的出现源于宗教需求。在回族聚居区使用这些借词的频率要高于回族散居区和回汉杂居区,在语用时也形成了特定的对象和场合,回族在族群内部交流时会经常使用这些借词,回族和汉族及其他民族交际时并不常用。回族聚居区的穆斯林使用这些借词的频率高于一般居住地的穆斯林,回族宗教礼俗、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环境中这些借词的使用频率高于普通生活环境。
3.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专有词。回族聚居区内的生活以伊斯兰宗教信仰和伊斯兰文化习俗为内核,聚居区内的汉语方言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专有词。这些专有词只出现在回族使用的语言中,在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交际时并不使用,这是回族使用的汉语方言的一种特殊类型,也可以视为一种方言变体。这些民族专有词,有表示礼仪的,如“开学”“穿衣”“点香”“冲洗”等;有表示教派的,如“教坊”“教门”“新教”“老教”等;有表现器物的,如“汤瓶”“吊罐”“吊桶”“拜毯”等;有表现婚姻生育的,如“踩生”“卸担子”“守限子”等。这些民族专有词是回族生活的真实写照,如回族服饰名称中的“号帽”“盖头”等词,既突出了名物文化,又突出了宗教文化。“号帽”“盖头”这些服饰名称颇具形象色彩,这只是名物的表象,其内涵是回族宗教文化在名物中的体现。“穿衣”是回族话中一个特殊用词,指称为在清真寺念书毕业的满拉举行的宗教仪式,和汉语“穿衣”的一般用法完全不同。“汤瓶”“吊罐”也是回族生活中最常见的专有词。由于宗教理念,回族人对用水特别讲究,跟水相关的专有词在回族话中并不鲜见,除常用的“汤瓶”“吊罐”,还有“带水”“换水”“着水”等以“水”为词根构成的系列专有词,这些词伴随着回族人的一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族专有词在回族聚居区使用得更加广泛[5]。
三
当居住形式不同而导致方言产生变异时,在方言变异的初始阶段,使用者的语言态度无疑发生着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方言变体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外部因素,包括社会环境、民族文化、语言态度等;二是内部因素,包括语言生成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自我调适等[6]。回族聚居区的汉语方言变体在形成过程中,这两个因素都发生着作用,但外部因素往往大于内部因素。
作为社会现象的表现之一,语言的基本功能就是反映社会形态。语言的社会功能使语言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会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语言无法成为一个封闭系统,民族社会生活中的自然语言是在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社会的基本形态会在语言运用过程中留下自己的印迹。和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聚居区域相比,回族以“大分散、小聚居”为分布基本形式,回族聚居区在民族习俗、民族礼仪、民族文化甚至民族经济类型等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汉族聚居区的不同,这正是回族聚居区汉语方言变体形成的因素之一。
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中国化的结晶,回族以汉语为民族共同语,这本身就是伊斯兰文化本土化、中国化的突出表征之一。如果仅从语言结构系统来分析,回族聚居区的方言和所在区域的汉语方言在语言本质上是没有区分的,回族聚居区的汉语方言变体只是汉语方言的一个特殊类型;如果从汉语方言变体生成的种种要素来分析,回族聚居区的汉语方言变体十分特殊,民族文化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金炳镐.中国民族聚居地区民族问题特点和发展趋向[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2).
[2]赵升奎.西部民族杂居区的语言使用特点[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3]李树俨.平罗回族使用汉语方言的一些特点[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4).
[4]林涛,许钟宁.纳家户方言的语音系统[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5]李生信.回族话形成的民族语言基础[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6]孟万春.语言接触与汉语方言的变化[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责任编辑李小凤】
收稿日期:2016-04-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宁夏生态移民方言变化跟踪调查及语料库建设”(14BYY049);宁夏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回族聚居区、回汉杂居区汉语方言变体类型研究”(14NXBYY01)
作者简介:李生信(1960-),男,宁夏海原人,北方民族大学北方语言研究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回族语言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6)04-013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