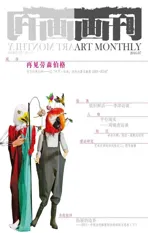拓展的边界
——2015·中国当代雕塑创作的回顾与思考(下)
2016-12-01何桂彦
何桂彦
拓展的边界
——2015·中国当代雕塑创作的回顾与思考(下)
何桂彦

《紫色》展览现场 刘韡 2015年
三
(接上期)
如果回顾中国当代雕塑的发展,主导性的力量仍来源于雕塑界内部的变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几个重要的节点,如1992年的“青年雕塑家邀请展”、1994年在中央美院举办的“雕塑五人展”等。整个90年代,也是雕塑界构建“当代性”,力图完成语言学建构的重要时期。但一个不能忽略的现象是:雕塑界的发展曾受到当代艺术界的影响。简要地追溯,90年代末期,中国在海外的艺术家如徐冰、黄永砯、蔡国强、陈箴等形成了一种新的倾向——立足于全球化的语境,秉承多元文化的立场,用一种国际化的当代语言,转译、重构自身的“中国经验”。所谓国际化的当代语言,在当时主要是装置。虽然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初期,装置与雕塑有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但到了60年代,随着极少主义与“新达达”的崛起,二者在语言的表达层面殊途同归。从某种意义上讲,海外中国艺术家的成功,不仅在于他们的作品强化了本土的文化经验与中国的文化身份,而且,在语言、修辞、媒介表达上保持了与西方的同步。虽然他们创作的作品大多是装置,却具有雕塑化的视角特征。2000年以来,雕塑与装置的既有边界更是日趋模糊。事实上,我们已经很难用单一的标准去判断张大力的《种族》(2003年)、王鲁炎《被锯的锯?》(2007年)、宋冬《穷人的智慧》(2005-2011年)、徐冰的《凤凰》(2010年)等作品到底是一件装置,还是一件雕塑?
2015年,以刘韡、艾未未、徐震等艺术家先后举办的个展为代表,同样为当代雕塑的发展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参考维度。2015年2月,刘韡在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了名为“颜色”的大型个展。展览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以现成品为媒介。当然,刘韡对现成品的使用不局限于媒介自身的“物性”,而是会注意它们的社会学来源,譬如与建筑、时尚、废弃物等发生联系。不过,艺术家的目的是希望将这些原本熟悉的材料重新“编码”,使其脱离作为日常性材料的意义指涉,并将其纳入到一个独特、奇幻、抽象化的形式结构中。对材料的拆解与重组,自然会消解媒介的日常属性,而新的视觉与形式结构,则摆脱了观众的审美期待,使其在“陌生化”的氛围中,让人产生一种惊诧的视觉体验。同时,作品与展览空间所形成的“剧场”效应,也进而让观众的观看成为作品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创作方法论与形式语汇构成的特点考虑,刘韡的装置与西方晚期现代主义的雕塑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2015年3月,徐震在龙美术馆举办了个展,其中出现了几组大型的雕塑作品。由于不是学雕塑出身,并且其作品很少参与雕塑界举办的展览,那么,这类作品应该以装置去看待,还是直接就可以看作是当代雕塑呢?或许,与雕塑界的创作比较,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徐震仅仅只是将雕塑作为一种媒介、一种表现手段,其目的仍在于强调作品背后隐藏的观念。譬如在《永生》中,一类形象来源于希腊古典时期的雕像,而另一类形象则是东方化的佛像。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造型原则,有着两种不同的文化来源,代表两种不同的审美趣味,但最终超越了时空,被艺术家“并置”到一起。在《永生- 马拉松的士兵宣布胜利, 受伤的迦拉太人》中,拼接组合在一起的雕像制造了一种荒诞而奇妙的视觉效果。很显然,徐震不是一个迷恋雕塑技巧、追求形式风格化的艺术家,相反强调的是创作的方法论意识,这在对挪用、并置、重组、解构、戏拟等后现代语言方式的使用中可见一斑。同时,艺术家对戏剧性的强调、对叙事性的偏爱,使作品在时空与文化错位的背景下流露出强烈的荒诞感。
2015年6月,艾未未在唐人画廊与常青画廊举办了名为“艾未未”的个展。展览的主体是一座名叫“汪家祠”的古建筑。这座建于明代的祠堂位于江西婺源的晓起村,是汪氏家族祭祖、举行庆典、商议重要事务、惩戒违反族规行为的场所。艾未未与他的展览团队将这座古建筑进行拆解,分成1500多个构件,然后将它们在两个画廊之间进行重新的吊装,尽管穿墙而过,但艺术家仍尽可能地保留了“汪家祠”的原貌。由于“汪家祠”离开了它原有的环境,因此,自身所负载的在宗法社会具有的象征意味完全消失。相反,因为置身于画廊之中,于是,它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艺术品。同时,因为观众的介入,“汪家祠”与画廊的空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场域。表面看,“汪家祠”还是物质意义上的“汪家祠”,然而,随着时间、空间,以及作为艺术家的艾未未以“拆解”的方式的介入,其意义早已发生变异。按照既有的雕塑思维,这件作品也很难看作是一件雕塑,然而,如果从作品一系列的劳作,例如各种部件的安装、组合来看,这和一位结构主义雕塑家的工作方式又有本质的区别吗?如果从行动——社会性介入,以及赋予作品一个新的阐释语境的角度理解,艾未未的“汪家祠”是否具有“社会雕塑”的意味?
立足于当代艺术的语境,倘若仅仅只是从形态学的角度对雕塑与装置予以区分,已经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相反,如何为既有的雕塑范式注入新的可能性,如何形成新的创作方法论,如何让雕塑创作与中国当下的文化现场发生关系,才应是雕塑界更为关注的问题。

《永生——马拉松的士兵宣布胜利, 受伤的迦拉太人》 徐震 玻璃纤维混凝土、大理石粉 157cm×96cm×250 cm 2014年 没顶公司出品
四
如果就2015年雕塑领域总体呈现出的特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120瓦的凸起》 王恩来 2015年

2. 《消磨》(局部) 杨牧石 雕塑、木、漆 800cm×400cm 2013-2016年

3.《无题·断肠》 杨心广

4.《看》 刘韡 装置 尺寸可变 2015年
1.普遍反映出形式上的自觉,许多作品都有较强的制作感。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雕塑所掀起的第一波现代主义的浪潮,就源于艺术本体的回归与形式上的自觉。从形式变革的路径上看,当时主要有四种类型:①从学院写实雕塑出发,将创作的重点逐渐从内容、题材转到作品的形式与风格表达上。②从民间文化、地域文化中寻求形式的现代转换。③有意识地模仿、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语汇,赋予作品个人化的风格。④从本土的视觉文化资源中汲取养料,积极寻求形式语言的现代建构。不过,就近几年雕塑领域的形式表达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即重视自身的造型与风格化的特征,强调作品的结构与空间所形成的张力;另一种是“观念化的形式”,所谓“观念化的形式”就是雕塑家在作品形式表达的过程中重新予以观念化,如对形式表达的日常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的强调,或者改变既有的物质或材料的形状,以解构的方式完成作品形式的重构。当然,“形式自觉”的雕塑创作的背后,一部分艺术家考虑得更多的仍是作品的商业性,并且,这一脉络的雕塑也契合了当代艺术总体上追求“去政治化”的倾向。
2.从传统的“雕”与“塑”转向对媒介“物性”的研究,强调“物”所负载的物理与文化属性。在西方现当代的艺术史情景中,我们可以看到“物”所具有的两个来源,一个是极少主义,一个是波普雕塑。极少主义中的“物”实质可以追溯到早期现代主义绘画中的媒介,即格林伯格所说的二维平面上的媒介物性。而波普雕塑的来源之一则是杜尚对现成品的使用。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极少主义与波普在对待“物”的方式上殊途同归。今天中国的雕塑家不仅对“物”和现成品的使用驾轻就熟,而且,十分重视挖掘“物”所负载的社会、政治、性别等文化属性。由于大量的使用现成品,所以,当代雕塑领域呈现出“去雕塑化”的趋势。
3.在展示作品时,重视“剧场化”的表达。“剧场”这个概念来自极少主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早期的极少主义艺术家逐渐从对“物”、“场地”、“空间”的强调转向观念表达时,一个更新的美学观念“剧场”或者“剧场化”(theartical)开始凸显出来。所谓的“剧场”,最基本的诉求是讨论观众、物、展览空间形成的关系。在极少主义艺术家的理解中,雕塑并不是单纯的客体,也不仅仅只追求形式的自律。相反,它需要与空间、与环境,而且一定要与观众的观看发生关系,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审美体验。换言之,在由人、物、场所形成的“剧场”中,不仅解放了观众的观看,而且,将展示的现场、展示空间作为作品的一部分。一旦“剧场性”形成,“观看”就有可能被意识形态化,或者让观看具有某种仪式性。同时,也有可能让大型的雕塑展具有超级景观的特征。
4.观念雕塑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多元局面。观念雕塑并不同于重视逻辑和概念表述的观念艺术,因为观念雕塑虽然也强调观念,但作品仍具有雕塑的某些形态与视觉特征。事实上,观念雕塑的重要一脉,是从质疑雕塑的本质入手的。譬如,许多雕塑家从时间、过程、偶然性,甚至通过大量“无意义的劳作”来创作雕塑。然而,有一种后果是我们需要预计的,那就是,最前卫的观念雕塑有可能最后是“反雕塑”的。这无疑是一个悖论。就像杜尚在追问“什么是艺术的本质”的时候,最终却走向了“反艺术”。事实上,当时间、过程、观念替代了雕塑家成为意义的生产者,这一切似乎也预示着,雕塑会走向终结,至少它的形态边界会日趋模糊。于是,一个急迫的问题需要回答:在观念的介入下,雕塑艺术是否会消亡?或许在保守的雕塑家看来,或者站在学院雕塑的立场,一定会有人说:是时候保卫雕塑了。倘若以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却会发现,在既有的范式的坍塌中,在观念化的推动下,当代雕塑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更加充满了活力。
5.当代雕塑涉及到多个主题,如对身体、性别、观看、景观等的讨论。譬如有的雕塑家直接将身体作为媒介,或者借助身体讨论与性别、文化身份相关的话题。有的雕塑家希望将“观看”纳入作品意义的表达中。由于侧重点不同,在“观看”的范畴中,有的重视“凝视”,有的强化“偷窥”,有的赋予“观看”以仪式性,有的则讨论“观看”方式背后隐藏的话语权力。同样,有的雕塑善于利用“场域性”的表达,使作品具有“景观化”的特征。就形态与媒介表达而言,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装置的、建筑的、3D打印的、影像艺术的手法融入到雕塑创作中。2015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曾举办了“天行意动——国际动态雕塑展”,力图将科技与雕塑创作进行有机的融汇。显然,跨学科、跨媒介的方式一定会为未来雕塑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
如果立足于当代雕塑“当代性”的显现方式,或者基于雕塑内在的文化诉求而言,虽然中国雕塑界呈现出蔚为壮观的多元创作局面,但其内在的路径仍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方向:①在文化现代性的变革中,强调中国当代雕塑本土化的发展轨迹,尤其在审美与文化身份上,倡导向传统回归,以此构建自身的“中国性”;②立足西方当代雕塑形成的谱系,重新审视中国当代雕塑语言学的发展路径;③从学院的角度观察雕塑既有的内部系统发生的激变,从而寻找新的切入点;④从当代艺术的整体氛围去考量当代雕塑的发展。实际上,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都会发现,中国当代雕塑的“当代性”一直处于不断的建构与流变的状态,而且,从一开始就多少呈现出混杂的特点。甚至有的时候,在同一件作品的内部也可能同时会有前现代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的因子。但是,它的发展方向却十分明确,一方面是不断地打破既有的形态边界;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地融入当下的文化情景之中。
2016年4月于四川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