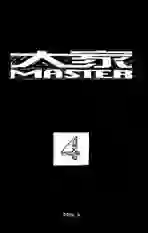墨迹
2016-11-02胡竹峰
胡竹峰,1984年生于安徽岳西,现居合肥。曾获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已出版《空杯集》《墨团花册:胡竹峰散文自选集》《衣饭书》《豆绿与美人霁》《旧味:中国古代饮食小札》《不知味集》《民国的腔调》《闲饮茶》等散文随笔集,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日语。
平日偶得闲情,我会看看碑帖里笔墨的旧影心迹。古琴素手纸窗瓦屋灯火青荧天与地合,意与神会,情通自然。意与神兮如痴如醉,情通自然兮惠风和畅。惠风和畅,如痴如醉,我觉得中国书法里有酒气药气茶气,有些书法里也有烟火气脂粉气青铜气,它们是旁门左道。
中国书法的笔墨之间有酒气——如痴如醉,对笔痴,对墨醉。所谓书法,不过笔墨同醉耳。所谓书法,不过人书同醉耳。所谓书法,不过天地同醉耳。
中国书法的笔墨之间有茶气——吃茶去,超然物外。吃茶去,烟火人间。吃茶去,逍遥乐事。吃茶去,饮水解渴。吃茶去,谈佛论道。吃茶去,家长里短。
中国书法的笔墨之间有药气——悲天悯人,针石心肠。书法是一味药,是清凉剂、醒酒汤,安神、疗伤、治病,是对无可奈何的排遣,是对百无聊赖的打发。
中国书法讲究笔法、墨法、章法,还得有想法。笔法墨法章法者也,没有想法,都是作法,做作的作,做作得很。艺术只有在艺术家那里才能散发个性的光芒,艺术在匠人那里只能是工艺品。书法家还应该有烂漫之心,烂漫之心生出一团团元气。
中国书法有中国文章所没有的一种旁若无人:字从心出,人就是这样。心借字形,法就是这样。读书法,我常常看见性情,有人诚恳恭敬、天真烂漫,有人特立独行、不拘一格,有人仰天大笑出门去,有人战战兢兢进屋来,有人桀骜不驯,有人规规矩矩,有人放肆泼辣,有人内敛斯文……
很久以前,我家壁橱上有一张怀素的狂草挂历,走笔枯若秋风,斑斑驳驳,让我觉得简洁通灵。当时一个字也认不出,但能感受到怀素笔势的有力,俨然是舞动了极高明的剑术,使转如环,奔放流畅。
搜索那时的记忆,脑海中常常有这样的镜头:一个少年仰着脸,阳光从背后老屋的木窗上泼过来,透过尼龙窗纱,洒在东墙,浓淡交错,像毛边纸上暗黄的淡墨。
壁橱的墨迹与墙脚的光影对应着,墨迹断断续续,光影若即若离,光影疏朗有静气,墨迹带精蛇之美。古人是很会比喻的,记得萧衍在《草书状》中说:“疾若惊蛇之失道。”真是内行话,非精于此道者不能言也。
书法的奇妙在于,每个字的点画构成以及字与字连绵动感产生的墨迹之美。我对书法的兴趣,严格说来是对墨迹的沉迷。
《六祖坛经》云:自古传法,气若悬丝。
宣纸上,中国文脉轻流徐淌。
墨迹间,前人气息缕缕不绝。
北冥鱼
本来文章的名字叫“扶老携幼”。扶老携幼是套话。前人见王羲之《兰亭序》的字体有大有小,疏密俯仰,多好以扶老携幼、顾盼生情喻之。
近来疲了,对写作疲了,笔墨荒废久矣,只好说说套话。幸亏疲而不乏,每天还能读点书。昨夜读一本关于王羲之的册子,买来两个月,没拆开包装,还是新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不亦乐乎的并非文字,而是书内所录王羲之的墨迹照片,读得人神清气爽,凌晨时分方有睡意。
去年秋天,开始写点字,每天临临帖,读读和书法有关的文章,给自己放松。写了六七年,说不麻木是假的,所以我就放下。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放下,而是“放下写作站着临帖”的放下。既然不能顿悟,索性将它搁置一旁。就像和妻子柴米油盐过日子,相处久了,难免疲惫。若疏淡些时日,再相会,倒能小别胜新婚。
写作以横行的姿态左右逢源,书法以竖立的方式寻幽取静。
既是谈书法,先从王羲之说起。王羲之是天才中的天才——神才。所以天才的王献之“磨尽三缸水”还只能“惟有一点似羲之”,终与其父差了一个层次。神才与天才的差别是对人生的理解: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能说这样的话的人,王羲之前有老庄,后只有曹雪芹。
公认王羲之的代表作为《兰亭序》,可惜我辈所见,皆是后人摹本。绍兴兰亭里的王右军祠中放置有多种《兰亭序》的摹本碑刻,有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欧阳询、文徵明诸贤手笔,大有可观,每个人落墨的效果、风格有别。本本有异,越发显得王羲之神龙见首不见尾。王羲之是北冥之鱼,褚虞冯欧好不容易织就渔网,刚扔进海里,羲之这条大鱼却化为大鹏展翅千里。一帮人湿淋淋地空着手,站在岸边目瞪口呆。正是:
羲之已化大鹏去,褚虞冯欧眉上愁。
大鹏一去不复返,细浪拍沙荡悠悠。
我猜想,《兰亭序》的真迹里包含了所有临本摹本的精华。我猜想,临本摹本不及真迹处大概是温文尔雅的喜悦之情。时过境迁,王羲之也写不出永和九年暮春那场醉后的笔墨。笔墨间的微妙,强求不得。
中国书法,轻者不重,重者少轻。讷者不敏,敏者缺讷。刚者不柔,柔者欠刚。唯王羲之的笔墨轻重缓急,刚柔共济。《兰亭序》是太极鱼,阴阳互参。
有一年,我把《兰亭序》的印刷品挂在家里。窗外春暖花开,柳风袭人,王羲之风神俊秀。窗外烈日高悬,暑气弥漫,王羲之风神俊秀。窗外秋意萧瑟,落叶飘零,王羲之风神俊秀。窗外晨霜匝地,雪片抖索,王羲之风神俊秀。我突然觉得,《兰亭序》不能临摹,看看就好了,四时佳兴对其凝眸沉思,想想王羲之的生平,或许可得书法一二。
我对王羲之的认识是“不修边幅,天生丽质”。胡竹峰习字仿佛学仙,书之道终究渺茫,到底作文自在。
墨迹让我与王羲之共醉,淡掉人生的悲欣,抹去世间的无奈,把玩着法帖,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补记:
除了《兰亭序》,我最喜欢《丧乱帖》。《丧乱帖》由行入草,随着情绪的变化,草字愈来愈多。“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此两行已不见行书踪影,全是草字。《丧乱帖》有大悲愤。
本文又名《北冥之鱼》,羲之面前不写“之”字。再记。
梧桐叶
突然想起二〇一三年夏天看见的《立马铭》碑刻。
在四川南充开会,看见张飞的书法碑刻《立马铭》,感觉大美:
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溕立马勒石
二十二个字,丰满遒劲,刚健凝重,结体浑朴敦实,“蚕头”暗藏,“燕尾”明显,刚柔并济。张飞不仅书法作品甚佳,还喜欢画画,尤工美人图。卓尔昌的《画髓元诠》载:“张飞……喜画美人,善草书。”
张飞书法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陶弘景的《刀剑录》:
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赤朱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后被范疆杀之,将此刀入于吴。
后人解释说,刀铭便是张飞所写。原物不传,查无对证。
明人的《丹铅总录》载:“涪陵有张飞刁斗铭,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
读来的印象,张飞生得粗粗大大,貌如梧桐叶。梧桐叶像张飞,粗粗大大中有细腻。
梧桐叶是敏感的,古人说“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王勃也在《风送滕王阁》中写出了“梧桐叶落秋将暮,行客归程去似云”的句子。
独坐窗前听风雨,雨打梧桐声声慢。夏天雨中,我在楼头等候友人,友人迟迟不来,雨水打在梧桐上,声声慢,时间过得也慢。梧桐雨是词牌名,声声慢也是词牌名。
前几天在植物园,捡起一片梧桐叶,比我手掌还大,叶脉像一只大手的纹络。
梧桐的名字大抵以地域分,中国梧桐、海南梧桐、云南梧桐、法国梧桐。有人称法国梧桐为悬铃木。悬铃木三个字我看了,心里觉得真悬。
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喜欢的人物是张飞,觉得他身上有真气有勇气。看到《立马铭》,越发增添了对张飞的喜爱,真气勇气之外还有文气,难得。
岣嵝碑
重游绍兴大禹陵,感觉还是好的。好在松柏,苍滋滋绿着,存几分野逸。好在石阶,一侧蔓生有青苔,古意上来了。
古意总归是好的,哪怕是故意的古意,也比翻新好。翻新让人烦心,修旧如旧,婉婉动人,修旧成新,看了烦心。
在绍兴大禹陵见到岣嵝碑,心一沉。沉入历史,像钻入故纸堆里的书蠹。车辚辚,马萧萧,只是行人无弓箭,行人皆儒士。儒士著文章,这文章是岣嵝碑碑文。
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堙。郁塞昏徙。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岣嵝碑的文章我不喜欢,因为不懂。但我喜欢岣嵝碑的字形,因为不懂。
岣嵝碑之字,形如蝌蚪,又不同于籀文蝌蚪,也不同于甲骨文、钟鼎文。一方面有蝌蚪的烂漫,一方面有蟾蜍的沧桑。入眼只觉得烂漫沧桑。烂漫让人心气浮动,沧桑又使我心气沉郁。浮动与沉郁之间,味道上来了。味道不仅上来了,而且味道膏腴肥厚得很,像绍兴的陈年花雕。
这几天在绍兴喝了很多花雕。
我过去是滴酒不沾的。
绍兴温热的花雕,肥厚甘醇,装在锡壶里,暖暖地汪起一泓春意。其色如老琥珀,酒味有旧味,仿佛上古的青铜器。或者用小盅浅酌,或者用浅而大的陶碗慢饮。如对美人、如观薄雪、如视晚霞、如坐松下、如嗅兰桂、如会名士。将进酒,如果这酒是绍兴黄酒,我愿意一樽复一樽,坐喝至微醺。此间有真意,不能与外人道也。
有人猜测岣嵝碑上的文字可能是道家的一种符录,有人索性认为是道士的伪作。我以为岣嵝碑之好,正是好在仿佛符录上。线条是厚的,字形是厚的,章法也是厚的。
汉以前的书法,声乐比之,古琴与缶声也。琴声如水,绵延徐逝,缶声似珠,激浪奔雷。
籀文、篆文、甲骨文、钟鼎文,文文不同,混沌毁灭,天地重开之感是一样的。一个字一个字写得像残节老根——虫蛀的竹节,斑驳的老根,也就是一片洪荒。洪荒过后,是怎样的山水风物,无从知晓,也正是好在无人知道。
汉晋唐宋的书法当然好,清高隽永,章法飘逸,走笔森然,下笔又不缺烟火意味。此前的书法不是这样,戈壁荒漠,一片深林一片沼泽,一笔一画与木石交,与鹿豕游,与天地老。
可能远古人在体力上要好些,周游列国,合纵连横。在青铜器旁敲钟击缶鼓琴舞剑,声遏行云,一腔心血尽在其中。
桃花流水斜风细雨,后来的事情。
蛙鸣阵阵乌云密布,先前的风气。
岣嵝碑的文字真好,似图腾、似缪篆、似虫书、似象形,春秋笔法里波谲云诡,四野苍然,斜月如钩。
上次来大禹陵,没发现岣嵝碑。一回有一回的机缘吧。
如豆
晋唐以前的书风高深莫测,不必说甲骨文与篆书,某些隶书也高深莫测。
好的艺术,往往高深也常常莫测。也有高深不莫测的,譬如庄子的文章,王羲之的行书,颜真卿的大楷。也有莫测并不高深的,譬如竟陵派、桐城派,康有为的书法。还有不高深也不莫测的,譬如李白的诗歌,唐宋的传奇,李煜的填词,陆游的笔记,明清的话本,张岱的小品,八大山人的花鸟,曹雪芹的小说,鲁迅的序跋,家常中遥不可及。钟繇的书法也差不多如此。家常的遥不可及,比高深莫测的遥不可及更难。
钟繇的字是青菜豆腐家常菜,元明后的书法越来越像满汉全席了。晋唐五代与宋人的书法,吃素的,绝了荤腥,面目兀自丰腴,实在是天资,也实在是天赐,何止文章天成。
钟繇为艺有痴气。艺之道从来离不开痴,痴是先天之元。钟繇习书精思三十年,坐与人语,用指头在地上写字,躺着则在寝具上写字,天长日久,寝具被写穿了。
我是苦路子上走过的,从来信奉敏而好学,敏是题外话,好学才是读书人的根本、读书人的底色。赵孟頫苦练小楷经年,运笔如飞,一天可写万言。文徵明起床先写一遍千字文才进早餐,八十多岁,一笔蝇头小楷写得炉火纯青。邓石如习书,不分昼夜,始有大成。
钟繇为人贪心,贪是一份执着。有小说家言,钟繇求韦诞所藏蔡邕《书说》不得,捶胸吐血,被曹操以五灵丹救下。韦诞死后,发其冢而得《书说》。虽纯属虚构,但见人精神。
钟繇的真迹早佚,只有《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墓田丙舍帖》《荐季直表》等几本刻帖存世。
钟繇烹饪得一手好豆宴。《宣示表》浑圆如土豆,《贺捷表》内敛如豌豆,《力命表》清秀如黄豆,《墓田丙舍帖》奇崛如扁豆,《荐季直表》高古如蚕豆。钟繇的小楷尤其如豆,一个字一个字写得像土豆、豌豆、黄豆、扁豆、蚕豆,更像一灯如豆。
晚饭前,翻钟繇书帖,随手取了红豆与薏米熬粥。粥好菜香,掀开锅盖,红豆与薏米分不清了,在沸水中滚动,真像钟繇的小楷。
瘗鹤铭
闲来理书,书箱里翻出《红楼梦》来。一翻就翻到“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一节。曹雪芹的笔墨至此快到尽头了,大观园的故事露出残景。曹雪芹写残景,犹带明朗气,像盛夏的西天晚霞。高鹗的续书,狗尾都称不上,顶多是条井绳。六七岁的光景,被蛇咬过,至今看不完《红楼梦》后四十回。
《红楼梦》的续书,见过不下十种,只有张之的《红楼梦新补》读完了。张先生的新补,新颖别致,清香扑鼻,读得人禁不住击节称赏。张之了不起的地方是推翻前人续作,融会贯通,另起炉灶,写元妃赐婚、黛玉泪尽而逝、贾府抄没一败涂地、荣宁子孙树倒猢狲散、贾兰贾菌中举、宝玉宝钗家计艰难、王熙凤被休弃含恨自尽、宝玉躲避穆侯举荐而悬崖撒手、史湘云怜产妇沿街乞讨、宝玉遣婢、生计所迫卖画打更等情事,叙来洋洋洒洒,又惊心动魄、满腹辛酸。张之遣词描红,多得曹公笔法,可谓续书翘楚。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今人未必不如古人。
前几天和诸荣会闲聊,谈起《瘗鹤铭》,他说古今那么多人学《瘗鹤铭》,无人得其宏旨,只有徐悲鸿入神了。见过不少徐悲鸿的书法,人云亦云“受益于康有为”。荣会老兄法眼,一语道破天机,让我受用。
《瘗鹤铭》的瘗字,才认识不久。有个阶段把瘗字读成糜字,有个阶段把瘗字读成病字。病鹤成汤,瘗鹤成铭,想当然耳。当年乡下物资紧俏,鸡鸭鹅之类的家禽病了,舍不得扔掉,赶紧杀了炖汤。
“瘗鹤铭”三字组合,视觉上有压迫的意味。但《瘗鹤铭》的书法却舒朗,像中年儒士着家居服散步,况味几近李斯当年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
《瘗鹤铭》残石,字体松散夸张,横竖画向四周开张。黄庭坚认为“其胜乃不可貌”,誉为大字之祖。曹士冕则推崇其“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东洲草堂金石跋》说它:“自来书律,意合篆分,派兼南北。”我不以为然。某人家养的鹤死了,埋了它并写了铭文,是有些玩笑成分的,一个煞有介事的玩笑而已。《瘗鹤铭》文辞戏谑不乏豁达,可贵处在于游戏,在于家常,内容有机趣,也就是心情。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夺余仙鹤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巾,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晦之志,我等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
相此胎禽,浮丘之真,山阴降迹,华表留声。西竹法理,幸丹岁辰。真唯仿佛,事亦微冥。鸣语化解,仙鹤去莘,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后荡洪流,前固重局,余欲无言,尔也何明?宜直示之,惟将进宁,爰集真侣,瘗尔作铭。
鹤是珍禽,浮丘公曾著《相鹤经》。雷门大鼓,白鹤飞去不再声闻千里。丁令威成仙后化成仙鹤,在华表上停留显形。这些事幽微迷茫,难以分辨。而你化解身形,将往何方?在焦山西侧筑起你的坟茔,这里是安宁之地。坟后有鼓荡的长江洪流,坟前的焦山就是重重墓门。左方是遥远的曹国,右方是险峻的荆门。茅山北面是凉爽干燥之地,地势胜过华亭的风水。于是我邀集了几位朋友,在此埋葬你,并写下这篇铭文。
《瘗鹤铭》作者不传,有人说是陶弘景,还有说是王瓒,有人说是顾况……还有人说是王羲之。如果是王羲之的话,我倾向青年王羲之,时间在坦腹东床之前,《瘗鹤铭》里有青年人的烂漫之心。
说到王羲之,索性绕远一点。
王羲之书法有一个遵古时期和创新阶段,《姨母帖》之类几乎是古法用笔,《瘗鹤铭》也是古法用笔。到《丧乱帖》以及《兰亭序》,则用了新法。
不少古人喜欢鹤,梅妻鹤子是美谈。近日读《瘗鹤铭》,想起今年春天结伴和朋友一家去孔雀园玩,见到几只长腿白鹤,并不见佳,如呆鸟。
不热
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得让人忘了具体年份,只知道那天是七月十一日。太子少师杨凝式午睡醒来,肚子有点饿,友人送来韭花,正中下怀,为答谢美意,信手在麻纸上写了封短笺,文不长,六行六十三字:
昼寝乍兴,朝饥正甚,忽蒙简翰,猥赐盘飧。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羜,实谓珍馐。充腹之余,铭肌载切。谨修状陈谢,伏维鉴察,谨状。七月十一日状。
文章和魏晋时人相比,稍弱一层。但轻松愉悦、萧散闲适的心境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自有一份旖旎。
帖中“助其肥羜”的“羜”是指嫩羊羔。生于南方的缘故,韭菜花与羊肉放一起吃,还没尝过。汪曾祺先生著文说:“以韭菜花蘸羊肉吃,盖始于中国西部诸省。北京人吃涮羊肉,缺不了韭菜花,或以为这办法来自内蒙古或西域,原来中国五代时已经有了。”汪先生所论有误,以韭菜花蘸羊肉的吃法先秦已有记载。《诗·豳风·七月》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孔颖达疏:“四之日其早,朝献黑羔于神,祭用韭菜。”
斗转星移,送韭花者是谁,已不可考,这顿韭花可真没白送。当收到杨凝式的手书回信,我想他肯定高兴了一阵子。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箱子里,然后选一个吉日,请裱师装好挂上。在久雨未晴落木萧萧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对墙而立,以手书空,细细品味。
《韭花帖》介于行楷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董其昌曾说:“少师《韭花帖》,略带行体,萧散有致,比少师他书欹侧取态者有殊,然欹侧取态,故是少师佳处。”(杨凝式官至太子少师)何止“少师”,董其昌分明“老学”——到老还在学习杨凝式。
韭菜我不喜欢,韭花爱吃。韭花,韭菜苔上生出的白色花簇,多在欲开未开时采摘。韭花炒鸡蛋,夹在碗头,我可以多吃半碗米饭。韭花炒肉丝,清炒或加豆瓣,滋味甚妙,我可以多吃一碗大米饭。我家习惯,韭花多腌来吃。祖母这样,母亲也这样,腌韭花吃在嘴里,有淡淡的香甜。
据说杨凝式喜欢涂墙,尤好佛寺道观之壁,洛阳两百多寺院皆有其书。搞得那些没有杨凝式墨迹的寺院很没面子,特意将墙壁粉饰得干干净净,备足酒肴,摆好笔墨,以待其字。杨凝式倒也配合得很,过几天跑去了,新墙光洁可爱,越发引得他如痴如醉,行笔挥洒,且吟且书,直把墙壁写满方休。
时人以杨凝式性情纵诞,赠其“风子”之号。车前子说有回杨凝式题壁正在兴头上,一位白衣胖妇人正好以背对他,一路题上四个大字:“肉食者鄙。”不知道是老车戏言还是真有其事,下次问他。
除《韭花帖》外,杨凝式还有《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神仙起居法》《步虚词》《夏热帖》数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楼台烟雨中倒也罢了,只可惜那一壁壁杨凝式书法。
清末梁鼎芬致杨守敬小简曰:炖羊头已烂,不携小真书手卷来,不得吃也。杨凝式没有梁鼎芬这样的朋友,不然少不得多存几件传世真迹。这是我的俗念。传世真迹不需要多,王羲之没有传世真迹,书圣非他莫属。吴道子没有传世真迹,画圣非他莫属。仙人逸士,神龙见首不见尾,方有意趣。
《夏热帖》,我读过,丝毫不热。杨凝式的法帖透风,入眼清凉。
霜天帖
史浩的《霜天帖》,名字真好,好在有霜意,又迎面不寒。《霜天帖》的书法也好,文墨舒朗,把玩间,仿佛远望徽州老宅鱼鳞瓦屋顶的秋霜。我去过很多地方,看到过很多次霜,徽州老宅的瓦上霜最让人难忘。
霜让凡物皆美,落在菜园清白相间,落在枫叶红白互映,落在瓦片雪白分明霜色如银,银色纯净,霜色也纯净,只是多了几分清寒。读张继的《枫桥夜泊》,至“月落乌啼霜满天”,脑际一惊。霜满天,霜漫天,眼前倏地呈现出一片清寒,静夜阒然,天地冷了下来,山孤零零的,一钩残月挂在村口,地面上铺了薄薄的一层霜。大概就是所谓通感吧,跟着就想起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乡下的板桥不少,开门即有,凝神远望,冷风中,霜色遮住了板桥,人迹却无,越发感觉清寒扑面。霜在板桥上泛着潮白,铜钱厚。早起的老汉,拉水牛饮水,过桥时,牛蹄叩下去,干而脆地响。霜色极淡,落在青黑色的瓦片上,像洒了层薄薄的盐末。
有一年大清早,去菜园里拔萝卜,只见青菜的叶子上裹着一层厚霜,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霜刮下来,捧在手心,手心一凉,舌头一舔,舌尖冰凉,然后又贴在眼睛上,眼睛也冰凉。
念书时,每天总要路过一条小河,冬日的清晨,河堤泛黄的草上有淡淡霜色。人走在上面,脚板传来扑簌簌的声音。山水之间,风起霜生。风霜在山水之间弥漫,虽冷,心向往之。
《霜天帖》气息凛冽、干净,差不多书如其人。史浩其人,《宋史》有传,读来的印象,官至丞相,做过宋孝宗的老师,位高权重。位高权重,又难得一身正骨。故下笔有贵气有清气有福气。王羲之的书法有贵气无福气,孙过庭的书法有福气无贵气,董其昌的书法有清气有福气无贵气。文人书法多清气,王侯书法多贵气,福气只可意会。
福气要修,清气要养,才气是上天给的,趁早挥霍干净,尤其是写作,越来越不耐烦才气文章了。
福气要修,来之不易,要分外惜福。肉身脆弱,福气护佑着才好。
《霜天帖》是史浩写给皇帝的辞官信札。功名富贵,不过秋草瓦上霜,史浩看得清楚。
霜降之后,草苦石寒,松苍竹老,天地冷白萧瑟,一年过得差不多了。
富贵湮灭,终是惆怅。闲翻《霜天帖》,竟生出惆怅。
佛首与孩儿面以及无上清凉
近来每日读苏轼手书小楷《金刚经》,无上清凉,极受用。《寒食帖》高歌悲凉,看久了,颇不耐烦,先放一放。
苏轼手书《金刚经》,一颗颗汉字如佛首如孩儿面,抱团取暖,庄严又烂漫。庄严又烂漫是异数。有人烂漫不庄严,有人庄严不浪漫。孤陋寡闻,庄严又烂漫的书法,所见唯东坡一人。
大前年深秋,书家朋友持赠《苏轼书〈金刚经〉》。他不喜欢苏东坡小楷,觉得太肥了。我喜欢苏东坡小楷,觉得肥得漂亮。都说东坡字肥,实则表象,骨子里味厚意足。味厚容易,意足太难。白居易的《咏怀》诗云:“白发满头归得也,诗情酒兴渐阑珊。”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即便兴渐阑珊也不脱大袖挥挥的意气。习苏字正是难在这里。写得出苏东坡的笔画,写不出他的意思,好不容易写出点意思了,气息上又相差太远,气息上接近了,精神上还是隔了肚皮,一肚子不合时宜。
学苏之初,如在眼前,越写越觉渺茫。王羲之是天师,苏东坡是隐士,“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有人懂苏东坡的文章,书法上隔了一层。有人懂苏东坡的书法,文章上隔了一层。
苏轼的书法,好在字纸背后站着一个写《赤壁赋》的人。学苏字,不妨先学学苏家文章。从《东坡志林》入手,继而诗词,存一分文章意思,或可得三分字墨法度。
《苏轼书〈金刚经〉》笔缓轻转,菩萨低眉,玉竹临峰。玉树临风用得烂俗了,改为玉竹临峰如何?玉竹为何竹?当然不是玉雕之竹。玉竹属草本,耐寒性喜阴。《本草经集注》云:“茎干强直,似竹箭杆,有节。”苏东坡下笔耐寒,端正大气,小品文也写得欣欣向荣: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