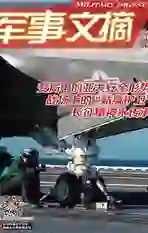原版“李云龙”:开国中将王近山的传奇人生
2016-10-21祝小茗
祝小茗
看过电视剧《亮剑》的人,一定会为李云龙打仗和追求爱情的那股“疯”劲而动容,尤其是他和女护士田雨那惊涛骇浪般的爱情,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殊不知,作为“李云龙”原型的开国中将王近山的经历,其实比电视剧更精彩、更传奇。
王近山,原名王文善,1915年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高桥许家田村。15岁从军,16岁任连长,号称“小连长”。先后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第10师副师长、八路军129师386旅769团团长、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无论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淮海战役的战场上,还是在抗美援朝的上甘岭前线,王近山以善打硬仗、恶仗而勇冠三军,独树一帜,屡建奇功,所向披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2年3月,军事科学院出版回忆王近山将军的文集,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书名——“一代战将”。江泽民同志题词——“杰出的战将,人民的功臣”。杨尚昆同志题词——“王近山同志英勇善战,战功卓著”。李先念同志题词——“人民的战将王近山”。至此,历史终于为戎马一生、骁勇善战、功勋卓著但却命运多舛的一代名将王近山作出了公正、客观的评价。
智勇双谋,歼灭日军观战团
和共和国的许多将军一样,王近山也是从大别山的红安县走进红四方面军、并逐渐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的。他中等身材,面孔白晰,浓浓的眉毛下有一双极为和善的眼睛,嘴角常常挂着微笑,讲起话来慢条斯理,一句一顿,口齿清晰。就是这样一位白面书生似的将军,却有一个与他的外表极不相称的外号——“王疯子”。他喜欢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在枪林弹雨中谈笑自若,视若无物。打起仗来拼命往前冲,有时要派六七个警卫员跟着他,以便当他往前冲时拉住他。他不听劝说,就几个人压在他身上,有时他气得又急又火,又踢又咬。在血火交织的战场上,“王疯子”之名勇冠三军,闻名遐迩。
1943年10月,时任太岳二分区司令员的王近山奉129师刘邓首长之命,率386旅之16团从太行山回师陕北,保卫延安。全团2千多官兵在王近山的率领下,晓行夜宿,一路西行,很快就来到了太岳根据地边缘的临汾县韩略村一带。前方侦察员报告韩略村村旁的公路上常有日军经过,且地势险要,非常适合打伏击。王近山司令员当机立断,决定来它个顺手牵羊,利用韩略村的有利地形和敌人的松懈麻痹,以速战速决的手段,打一个干脆利落的伏击战。
10月24日凌晨,担任伏击作战任务的6个连队借着浓浓的夜色,隐蔽进入了韩略村公路两旁的庄稼地里,迅速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上午8时,由临汾方向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紧接着,编有3辆小汽车和13辆卡车的日军车队,满载着日军官兵进入了我伏击圈。王近山一声令下,担任截尾任务的6连首先打响了第一枪,随后,前面的日军汽车也在接二连三的地雷爆炸声中被掀翻在路旁。突遭袭击的日军官兵慌忙下车应战,而我军布置在公路两旁的轻重火力,居高临下,泼水般地射向敌人。顿时,整个韩略村公路上杀声震天,弹雨横飞。许多日军还没明白子弹来自何方,就糊里糊涂地送了命。王近山司令员见突遭袭击的日军惊慌失措,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和反击,遂命令司号吹响了冲锋号。我军官兵当即向敌人发起勇猛的冲锋,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开始了。只见公路上刀光闪闪,喊杀声、惨嚎声不绝于耳。战士们的刺刀和大刀与日军指挥官们的军刀相互格击,闪闪的刀光下不时传来日寇军官们狼嚎般的惨叫声。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血战,180余名日军全部被我军歼灭。
战后,我军从打扫战场时缴获的文件中得知,被歼的这支日军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组织的所谓“皇军军官观战团”。原来,身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为了推行他在扫荡我太岳根据地时所采用的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不仅到处大吹大擂,扩大影响,还特意组织日军“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的5、6中队和其他一些军官,组成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战场参观团,共180余人,赴太岳战区观战学习。万万没想到,观战团一到太岳区,就迎头碰上了八路军著名战将王近山和英勇善战的太岳16团。包括一名少将旅团长、一名联队长在内的120余名日军军官和60多名士兵悉数被歼,不可一世的“皇军军官观战团”在英勇的抗日军民面前灰飞烟灭。
勇挑重担,喋血激战大杨湖
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在刘邓麾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任第6纵队司令员。虽然身居要职,但他秉性依然。往往只要他在战士们面前一出现,便会引起一场不小的轰动,随后大家就会明白,一场大战、硬战、恶战就要开始了。
1946年8月,蒋介石一下出动了14个整编师共38万余人的强大兵力,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进攻。当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刚刚打完陇海战役,人困马乏,粮弹两缺。全军仅有4个纵队约5万多人,许多建制团甚至连2个营的兵力都不足。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刘邓首长决心集中现有兵力,首先歼敌孤军冒进的整编第3师。该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参加过远征缅甸的对日作战,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然而,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区区5万疲惫之师,要想吃掉兵力与自己相差无几、但装备远远强于自己的整3师,谈何容易。在野战军召开的作战会议上,第6纵司令员王近山拍案而起,当着刘邓首长和各纵队司令的面,他慷慨激昂,言出如山:“我和政委(杜义德)商量过了,我们纵队打。我——王近山立下军令状,我们纵队和整3师干!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了,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太行山的父老乡亲!”
关键时刻,英雄虎胆的王近山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让一向感情内敛的邓小平激动万分,他指着王近山大声说:“好样的!我支持你!”刘伯承也顺势站了起来,对王近山说:“你打!你大胆打!”
40年以后,邓小平对王近山勇立军令状一事还记忆犹新。他说:“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
王近山慷慨领命,率部一个猛虎掏心,直扑整3师师部所在地——大杨湖。
大杨湖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四周地形开阔,村外有一道壕沟,深约3米,村南有一个大水塘,芦苇茂密,形成天然屏障。为了保护师部的安全,赵锡田把整3师战斗力最强的20旅59团放在了大杨湖。该团进入阵地之后,立即构筑完备的防御工事。在村内主要道口,筑有暗堡工事,结合穿墙破壁的枪眼,构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为了扫清射界,赵锡田命令飞机扔下汽油弹,将村外的民房、柴禾堆全部打燃,使得大杨湖上空火光冲天,烈焰滚滚,一片通红。
1946年9月5日夜,第6纵总攻大杨湖。打响前,刘伯承亲临第6纵指挥所,对王近山及在场人员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今天来给你们看管行李。”素来持重的刘伯承亲临前线,足见大杨湖之战至关重要。王近山一声令下,第6纵18旅旅长肖永银亲自上阵,率部向大杨湖发起了波浪式的冲锋。战至次日拂晓,第6纵共有6个团的兵力攻进了村落,并把敌59团团部及残敌压缩在了一片还算坚固的院落当中。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是刺刀见红的时刻了。我第6纵虽然攻入了6个团,但每个团的兵力都还不满500人,有的团甚至还不足百人。敌人虽已穷途末路,但仍在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经过苦战,我军也伤亡惨重,攻击锐势已是强驽之末。
紧要关头,王近山果断投入为数不多的预备队,并组织起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全力投入了拼死决战。短兵相接的战斗空前惨烈,代价高昂,就像两个负伤恶斗的人在做最后一搏,双方的血都快流尽了,但谁都不肯放手,仍旧拼死搏斗,就看谁先倒下。战至最后,敌人终究没能顶住第6纵的最后一击。血泊中的大杨湖,终于被王近山踩在了脚下。大杨湖一失,整3师的防御体系顷刻间土崩瓦解。刘邓大军其余各部乘势进击,迅速对残敌进行分割围歼。一番恶战,骄横跋扈的整3师全军覆没,师长赵锡田束手就擒。
强渡汝河,狭路相逢勇者胜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经过艰苦的跋涉,十万大军越过黄泛区,渡过涡河、沙河、颖河、洪河,随后一路冲杀来到了汝河。为这支南下大军中跃马挺枪的开路先锋,依然是一代猛将王近山和他那能征善战的第第6纵。
率先到达汝河的先头部队是肖永银的18旅,尤太忠的16旅和李德生的17旅。肖永银刚刚率部来到汝河岸边,就见汝河南岸烟尘大起,马达轰鸣。敌人的堵截部队已先我一步到达对岸,并摆开了一副随时应战的架式。而经过长途奔袭的刘邓大军可谓后有追兵,前有强敌,中间还隔着一条性命攸关的汝河。
说到汝河,其实它并不宽大,只有60米宽,水流也不太急。但经过长年的冲刷,河漕深陷,河堤陡峭,水深丈余,根本无法徒涉。千军万马,要想渡过汝河,必须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架设浮桥。机敏干练的肖永银大手一挥,马上派一个营的兵力在敌人未展开兵力之前强渡汝河,争取在南岸建立一个牢固的桥头堡,以掩护部队架设浮桥。利用惟一的一叶小船和几个木筏,先头营开始在敌人的猛烈火力之下强渡汝河。一些性急的战士干脆往河里跳,拼命向对岸游去。经过浴血奋战,先头营终于登上了汝河南岸,并牢牢地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此时,我后卫部队已与追兵交火,而在汝河南岸,敌人的一个整编师也拉开了架式,准备全力阻止过河。生死关头,刘伯承、邓小平来到了第6纵,走到血战中的18旅。望着王近山和肖永银那坚毅的面庞,邓小平一字一顿地说:“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刘伯承也环顾众将,豪迈地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从现在开始,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动用多少飞机大炮,我们都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历史决不能逆转,大军南下的战略决策不能改变!”
刘邓首长的坚定信心,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第6纵的将士。王近山虎吼一声:“传令全纵队,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血路,突过汝河!”肖永银亲自下到营,代替营长指挥;团长下到连,营长下到班。全军上下每一支步枪都装上了寒光闪闪的刺刀,每一颗手榴弹都掀开了盖子。曳光弹、信号弹一道道划过,似金线银弧在夜空中穿梭。
踏过浮桥的队伍狂飚一般冲向敌阵,气吞万里如虎。火光中,无数战士的身影一掠而过,奋勇向前。团长、营长、连长和他们一样,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与敌人拼杀。打下一个村庄,又扑向另一个村庄,碰上敌人就扑上去拼杀,消灭了就再往前冲。冲锋的队伍像龙卷风一般向前滚动,所向披靡。直到天色微明,第6纵终于为全军在汝河南岸打开了一条长10千米、宽4千米的通路,并在这条通路两侧一字排开,抗击敌人的反扑,像两条坚固的堤坝,护卫着通道的安全。在第6纵的猛烈攻击之下,汝河南岸的阻截之敌终于溃不成军。刘邓大军的后续力量日夜兼程,快速渡河,终于越过千里跃进之路上最为困难、也最为险恶的这道屏障。
遭遇婚变,大起大落过一生
全国解放以后,王近山出任了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l2军军长,并率部来到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和举世闻名的上甘岭大战。回国之后,他先后出任公安部副部长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硝烟散尽,和平年代的生活是安逸宁静的。但对于戎马一生、身经百战的王近山来说,这种宁静却蕴藏着另一种危险,这种危险来自于他的情感世界。一个在战场上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的一代名将,在陌生的情场上却手足无措、进退失据。更令人可叹的是,无论是在战场或者是在情场上,将军都本色不改,保持着那种勇猛顽强和毫不畏惧的品质。这种可贵的品质,可以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为他创造辉煌,但在情场上,却给他造成了令人扼腕的悲剧。
闯入王近山的情感生活并且不顾一切地爱上他的人,恰恰是他那结发妻子韩岫岩的嫡亲二妹韩秀荣。面对这畸形的爱恋,王近山不知所措了。耿直、坦诚的王近山未能躲避这斜刺里射来的丘比特之箭,他欲罢不能,欲弃不忍。
其实,王近山一开始并没有离婚的打算,毕竟是结发夫妻,又有了那么多的儿女,谁家没有点磕磕碰碰?可是韩岫岩也不顾及王近山的感受,身为海军医院副院长,她使用了当时最典型的做法:发动亲友声讨、找组织、去妇联。逐渐延伸到北京军区直至中央。最后还是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又亲自指定刘少奇出面处理。此时,作为北京军区副司令,王近山的个人生活已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了。老战友以及很多中央领导人找王近山谈话,希望王近山不要离婚,有人甚至暗示说,离婚的话会受到严厉的处分,只要不离婚哪怕是维持现状也行!但王近山却斩钉截铁地说:“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离婚我铁定了,组织爱咋办就咋办!”1964年初,王近山和韩岫岩离婚了。
王近山的离婚案,一时间引起了全军乃至全国的一片哗然。当时,有不少高级干部厌倦了原配夫人,离婚现象比较严重。中央为严厉打击这种不正之风,对很多干部进行了严厉处分,人们称之为“铡美案”。王近山也很快被推上风口浪尖,竟成了“铡美案”典型。王近山为他的执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开除党籍,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级,调往河南某农场任副场长。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就在被撤职、降级以后,韩秀荣也放弃爱情,选择了离家出走。剩下的,就只有一位身心疲惫、遍体鳞伤的王近山。
就在王近山在心中默默地咀嚼着自己的痛苦、孤零零地收拾离京的行装时,识字不多但却深明大义的勤务员黄慎荣站了出来。她诚恳地对将军说:“首长,你这样的身体,到那么苦的地方去,没个人照顾怎么行呢?我没有文化,只要您不嫌弃我,就带上我吧,我照顾您一辈子!”1964年10月,黄慎荣和王近山结婚,与王近山一起到河南西华县黄泛区农场,育有一女一男。
时光如水,转眼间到了1969年春。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已在农场劳动了近十年的王近山写了三封信。一封给自己的老部下、时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的肖永银,另两封请他转交给许世友,其中一封信请许世友转交给毛泽东。
在北京开会期间,许世友面见毛泽东,一向耿直的老将军为了王近山的命运,向共和国领袖仗义执言:“主席,战争年代有两个人很能打仗,但他们俩现在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刘志坚,恳请主席过问一下。”在许世友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王近山终于重回军界,到许世友任司令员的南京军区任副参谋长。
1969年7月,火炉南京烈日炎炎,酷热袭人。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站着三位专门来迎接王近山的高级将领,他们是:老部下肖永银,尤太忠与吴仕宏。当历经磨难的王近山一手拎着一口旧皮箱,一手拎着三只老母鸡从硬座车厢上下来时,三位昔日的部将热泪盈眶,感叹万分。
1974年,时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王近山渐感身体不适。11月份,因大吐血,他不得不住进医院,经诊断是胃癌。在弥留之际,老将军还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敌人打到哪里了?我们谁在那里?”他的小儿子回答说:“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听着专门为他播放的军号声,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在南京逝世,享年63岁。
责任编辑:彭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