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襄乡浮图考
2016-08-08张鹏飞
张鹏飞
东汉襄乡浮图考
张鹏飞
摘要:郦道元在为《水经》作注的过程中,地合南北,遍寻古迹,广辑碑文,收录诸多汉魏时期汉地佛教寺庙佛塔及碑刻,如《北魏永宁寺碑》、《洛阳瑶光寺碑》、《北魏祇洹碑》等,而《水经注》卷二十三《汳水注》还记载了我国传世文献所见最早汉地佛塔“襄乡浮图”。“襄乡浮图”及汉末笮融所起“浮图祠”是传统“仙人好楼居”汉式重楼向兼具汉印特色“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楼阁式佛塔的过渡性建筑,标志着汉地佛塔的真正产生,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而襄阳市樊城区出土“菜越墓陶楼”则是汉末重楼式浮图祠的一件出土文物标准器。“襄乡浮图”早于笮融所起“浮图祠”十余年,故“襄乡浮图”不仅是传世文献所见最早之墓塔,亦为我国传世文献所见最早之佛塔,而笮融于广陵所起“浮图祠”则为传世文献所见最早之寺塔。
关键词:襄乡浮图;浮图祠;《水经注》;熹平某君碑
郦道元在为《水经》作注的过程中,地合南北,遍寻古迹,广辑碑文,于注中就行旅所知记载了汉魏时期各种金石文献,其中收录诸多汉魏时期汉地佛教寺庙佛塔及碑刻,如《北魏永宁寺碑》、《洛阳瑶光寺碑》、《北魏祇洹碑》等,而《水经注》卷二十三《汳水注》“汳水出阴沟于浚仪县北”条还记载了我国传世文献所见最早汉地佛塔“襄乡浮图”,对于研究汉地佛教早期发展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本文试以《水经注》著录文献为本,并结合相关传世文献及新出土文献,通过对佛教初传阶段汉地早期“浮图”及汉末“浮图祠”之分析,以厘清汉地佛塔之源起,从而明确“襄乡浮图”为我国传世文献所载最早之佛塔,并对“襄乡浮图”之侧“熹平某君碑”*施蛰存:《水经注碑录》卷六《汉某君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6页。然施氏考论简略,本文姑妄补其缺漏。予以考辨。
一、汉地早期“浮图”考
“浮图”,梵文Stupa,汉译“窣堵坡”、“嘿堵波”、“塔婆”、“休屠”、“佛图”等,原为印度吠舍时代以窣堵坡埋葬逝者之用,婆罗门教、佛教皆有以浮图埋葬僧侣舍利、骨灰,用以顶礼膜拜供养之俗,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以佛教为国教,推行佛法,于印度各地及域外造八万四千塔以供养佛舍利,如《水经注》卷一《河水注》“屈从其东南流,入于渤海”条记载了古印度“阿育王大塔石柱”及“泥犁城石柱”*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一《河水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页。,即为其例。在佛像未创以前,窣堵坡,即佛塔是佛教主要的礼敬供养对象。汉地佛教所谓“浮图”者,初与“浮屠”同,又译为“佛陀”*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浮屠正号曰佛陀,佛陀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6页)“浮屠”者即为“佛陀”之义。,后专指“佛塔”之意。关于汉地佛塔之起源,学界历来有以汉明帝时洛阳“白马寺浮图”、楚王刘英所尚“浮屠仁祠”为汉地佛塔源起之两说。
(一)白马寺浮图说

考《魏书·释老志》:“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3029页。其中所称“浮图”者,即汉地楼阁式佛塔,有一级至三、五、七、九级多重,为四方式,其形制仿天竺覆钵窣堵坡旧状,并结合汉地重楼高阁而重构形成,至西晋时,洛阳城中有浮图塔者达四十二所,可见佛教自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洛阳建白马寺后,至晋世发展之盛况。然《魏书》未明言永平构建白马寺时即有汉地佛塔建造,一些学者遂误以为永平时白马寺建有浮图为汉地佛塔之最早者。如孙福剑认为:“我国第一座楼阁式塔是东汉永平十一年在河南洛阳所建的白马寺浮图。”*孙福剑:《浅谈中国古塔的演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吴庆洲、李玉珉亦认同此说*吴庆洲:《佛塔的源流及中国塔刹形制研究》,《华中建筑》2000年第1期;李玉珉:《中国早期佛塔溯源》,《故宫学术季刊》1989年第3期。。然《魏书》所言者,实为永平求法之后,至北魏之世,汉地渐有兴建“浮图”之说,并未明确指出永平十一年白马寺即建有“浮图”。又考《洛阳伽蓝记》卷四:“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浮屠前柰林、蒲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杨衒之著,周振甫译注:《〈洛阳伽蓝记〉译注》卷四,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杨衒之所言白马寺之“浮屠”者,实为佛寺,而非佛塔之“浮图”。《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名寺众多,言其寺中有“浮图”者,皆言其层数,如卷一永宁寺“九层浮图”、长秋寺“三层浮图”、瑶光寺“五层浮图”;卷二灵应寺“三层浮图”、秦太上君寺“五层浮图”;卷三景明寺“七层浮图”,双女寺各有“五层浮图一所”;卷四宝光寺“三层浮图”,冲觉寺、融觉寺皆有“五层浮图”等。唯言及白马寺者,未有几级浮图之说,可见洛阳白马寺,汉魏之世并未立有佛塔,而关于汉明帝时洛阳白马寺为中国最早佛寺之说,学术界亦存有争议,故以汉明帝时洛阳“白马寺浮图”为汉地佛塔之源,实乃学者之误判。
(二)楚王刘英尚“浮屠仁祠”说
楚王刘英,汉光武帝刘秀第十一子,许美人生,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刘英于建武十五年(39)封为楚公,建武十七年(41)进爵为王,建武二十八年(52)就国,永平十四年(71)以谋反罪国除自杀。刘英于建武二十八年就国后,于“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明帝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28页。其中所言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者及“尚浮屠之仁祠”,似乎刘英为汉地最早之佛教徒,其所“尚浮屠之仁祠”,一些学者以为是汉地最早之佛寺塔庙,如陈亚萍认为楚王刘英是中国最早的佛教信徒,其建造的浮屠仁祠为“中国最早的一座佛寺”*陈亚萍:《中国最早的佛寺是东汉楚国的“浮屠仁祠”》,《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依此说,则汉地最早之佛寺当为刘英之“浮屠仁祠”,建于明帝永平八年(65),早于白马寺(永平十年)二年。
然楚王刘英晚年所好者实为黄老神仙之说,所称“浮屠”者为佛陀、佛教之义。刘英学习佛教斋戒祭祀之仪,仅仅是将佛教作为一种普通的神仙方术之说以求长生久视。日人镰田茂雄认为:“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英,以黄老与浮图并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充分显示佛教与后汉时代流行的神仙术和黄老信仰同时被容纳,与其说后汉的佛教,勿宁说是道教的佛教。”*[日]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一卷,关世谦译,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年,第32页。此说甚是。楚王刘英所信奉之浮屠,实际上是将佛教作为道教之一种求仙之说看待,即道教的佛教,故楚王刘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
楚王刘英所尚“浮屠仁祠”亦非佛寺塔庙,实为两汉之世贵族求仙常用之“仙人好楼居”式重楼。考《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公孙卿曰:‘仙人可见……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茎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仙神人之属。”*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0页。此公孙卿者为武帝时齐地之方士,可知西汉时,中原即有建重阁高楼并置祠楼下,以招仙神之风俗,刘英所尚“浮屠仁祠”,亦当为“仙人好楼居”汉式重楼,用于登高求仙,而与佛寺塔庙无关。除楚王刘英外,汉末桓帝亦于宫中立“浮屠祠”,《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2932页。,又卷三十下《襄楷传》:“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第1082页。,桓帝所立“黄老、浮屠之祠”者,与楚王刘英所尚“浮屠仁祠”相类,皆为黄老之汉式重楼神祠,非佛寺塔庙也。故以楚王刘英“浮图祠”为汉地最早之佛寺塔庙者,亦为误也。
由此可见,“白马寺浮图”及“楚王刘英所尚浮屠仁祠”两说皆有误,皆非最初的汉地佛塔。东汉明帝时,虽然永平求法,使佛教初传中土,并于皇室贵族中流传,然于民间影响甚微,中原地区尚未有大量的佛寺及佛教徒产生,而作为佛寺建筑之核心的佛塔一直没有真正出现。直至汉末桓灵之世重楼式“浮图祠”的产生,作为传统汉地“仙人好楼居”式重楼向楼阁式佛塔的过渡性建筑,才真正形成中原地区特有的楼阁式佛塔,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二、汉末浮图祠考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2922页。佛教自汉明帝时,作为一种神仙之说于帝胄之中流行,楚王刘英、汉桓帝皆信其术,然皆以黄老之附说为求仙,直至东汉末年,佛教逐渐从贵胄帝室传入普通士人民众,洛阳至徐州一带逐渐产生早期的汉地佛寺塔庙。学术界关于汉地佛塔最初造型起源主要有重楼式(或称楼阁式)佛塔和密檐式佛塔两说,其中“重楼式”占主流。汉地佛塔之主要形制——楼阁式佛塔,亦在汉末三国时出现,故黄文昆认为:“塔寺之举起于东汉灵帝时,以洛阳周围至徐州一带较早。”*黄文昆:《佛教初传与早期中国佛教艺术》,《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而汉末洛阳至徐州一带,民众所起重楼式浮图祠正是汉地楼阁式佛塔之渊源。
(一)“笮融大起浮图祠”——传世文献所见汉末浮图祠
“浮图祠”者,最初见于东汉初楚王刘英所尚“浮屠仁祠”,然刘英所尚“浮屠仁祠”是两汉之世贵族常用之“仙人好楼居”重楼,用于道教之致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浮图祠”。迄至桓灵之世,随着佛教在民间流传,洛阳至徐州一带逐渐有兴建“浮图祠”之风,而传世文献所见汉末丹阳人笮融于广陵大起“浮图祠”,即为此典范者。
笮融,汉末丹阳(今安徽宣城)人,《后汉书》无传,为汉末建安年间徐州牧陶谦之僚佐,为下邳相,并督广陵、彭城、下邳三郡漕运,曾于任内擅断三郡钱粮,用于广陵起“浮图祠”,后为扬州刺史刘繇所破,走入山中,为人所杀,其生平事迹散见于《后汉书·陶谦传》、《三国志·吴书·刘繇传》及《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后汉书·陶谦传》所载简略,而《三国志·吴书·刘繇传》则详细地记载了笮融于广陵大起“浮图祠”之事:
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刘繇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8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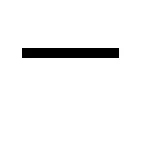
笮融所起“浮图祠”,《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记载:“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刘繇传》,第1185页。《后汉书·陶谦传》则记载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三《陶谦传》,第2368页。依此两文献记载,此“浮图祠”其下有重楼阁道,规模之大可容三千多人,其上有九重铜盘(相轮、宝刹),为古印度覆钵式浮图形制。由此可见,笮融所起“浮图祠”已不同于汉初刘英所尚汉地传统之“仙人好楼居”式“浮屠仁祠”,而是在传承汉地高阁重楼之形制外,又具备印度原始佛教窣堵坡式建筑特色,这种兼具汉印特色的重楼式“浮图祠”,可谓汉地楼阁式佛塔之渊源。对此,梁思成在《中国的佛教建筑》一文中明确指出笮融所起“浮图祠”:“这是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中比较具体地叙述一个佛寺的最早的文献……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所谓‘上累金盘’,就是用金属做的刹;它本身就是印度窣堵波(塔)的缩影或模型。所谓‘重楼’,就是……汉武帝建造来迎接神仙的,那种多层的木构高楼。在原来中国的一种宗教用的高楼之上,根据当时从概念上对于印度窣堵波的理解,加上一个刹,最早的中国式的佛塔就这样诞生了。”*梁思成:《中国的佛教建筑》,《清华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
(二)襄阳“菜越墓陶楼”——出土文献所见汉末浮图祠
汉末之“浮图祠”,除正史记载笮融所起广陵“浮图祠”外,近年来在一些楚地出土的汉墓陶楼及江南吴晋墓葬出土堆塑佛像重楼的魂瓶中皆有体现,其中尤其是襄阳出土的“菜越墓陶楼”,可以说是汉末重楼式“浮图祠”的出土文物典范。
2008年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菜越墓地M1出土一陪葬品“菜越墓陶楼”(M1:128)*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9期。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认为此墓为东汉至三国时一将军夫妇合葬墓。,为一黄褐釉重楼式陶楼,由门楼、长方形院落和二层重楼阁组成,其顶部装饰一印度式立柱覆钵七层宝刹(相轮),带有印度覆钵式窣堵坡建筑特色,陶楼位于院落中央,体现了早期佛寺以佛塔为中心的建筑格局特点。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人员认为此墓为东汉至三国时一董姓将军夫妇合葬墓,然发掘出土一铜盘(M1:137)底部铭刻“永初二年八月八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9期。,即汉顺帝永初二年(108)秋,则此墓葬年代当上推至东汉中晚期,此陶楼也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汉地佛塔模型,年代早于笮融所起“浮图祠”,其建造结构(重楼、相轮铜盘等)与传统汉墓出土“仙人好楼居”式陶楼形制有较大差别,与笮融所起“浮图祠”极为相似,可以说是汉末重楼式浮图祠的一件出土文物标准器。
“襄阳菜越墓陶楼”虽是一件陪葬明器,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罗世平、何志国皆认为其形制与笮融所起“浮图祠”略同*罗世平:《仙人好楼居: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4期。,基本代表了东汉重楼式浮图祠之特色,是一件难得的重楼式浮图祠出土文物。
从以上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双重证据可以证明,我国早期汉地佛塔,是从“仙人好楼居”汉式重楼渐变为带有印度相轮塔刹建筑特点的“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楼阁式汉地佛塔,即汉末重楼式“浮图祠”,亦即何志国所言“中国最早的佛塔形制是中国楼阁式建筑与印度相轮塔刹的结合体”*何志国:《从襄樊出土东汉佛塔模型谈中国楼阁式佛塔起源》,《民族艺术》2012年第2期。,浮图祠是其初期的标志,而后世汉地寺庙的建造亦如“浮图祠”,多以重楼即佛塔为中心,这在杨衒之《洛阳珈蓝记》所记载洛阳永宁寺、白马寺、瑶光寺等佛寺塔庙中得以体现。
三、“襄乡浮图”及熹平某君碑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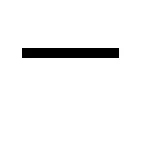
(一)汉地佛塔之祖:“襄乡浮图”
《水经注》卷二十三《汳水注》“汳水出阴沟于浚仪县北”条:
(汳水)又东迳夏侯长坞。《续述征记》曰:夏侯坞至周坞,各相距五里。汳水又东迳梁国睢阳县故城北,而东历襄乡坞南。《续述征记》曰:西去夏侯坞二十里,东一里,即襄乡浮图也。汳水迳其南,汉熹平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树碑,以旌厥德。隧前有狮子、天鹿,累砖作百达柱八所,荒芜颓毁,彫落略尽矣。*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十三《汳水注》,第5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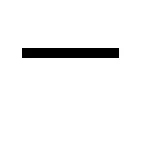
“某君”姓氏不可考,或为当地信佛之乡吏,“襄乡浮图”为某君于生前所立,故言“死因葬之”,浮图立于墓上。依《续述征记》记载,熹平某君墓及“襄乡浮图”于东晋尚存遗迹,然已“荒芜颓毁,彫落略尽”,唯墓上浮图及墓隧前狮子、天鹿尚存。“隧”为墓之神道,其前立有狮子、天鹿等石兽(“天鹿”疑为“天禄”之讹,这是我国传世文献所见最早石雕狮子记载),而言“累砖作百达柱八所”者当为“襄乡浮图”之形状,文或有脱字,“百达”当为“达百口”,内有“柱八”,则塔身或达百尺,塔内以八柱架构,其建造形制当与同时代笮融所起“浮图祠”相似,亦为重楼式佛塔,塔顶亦当有佛教相轮(宝刹)。惜《水经注》传抄日久,其文或遗漏对“襄乡浮图”具体建造情况之记载。
“襄乡浮图”为佛教信徒熹平某君仿天竺佛教之俗,生前为己修墓所,以浮图为往生之径,造佛塔于其墓上,此为汉末民间葬俗受佛教影响之表现。浮图于古印度本为埋葬僧人之窣堵坡,一般建于墓上,故在汉地佛教初传时期,受印度佛教葬俗影响,汉地佛塔会遵从墓上建造之旧制,一般建于陵墓,以为纪念奉祀亡者之用。《洛阳伽蓝记》卷四“白马寺”条言:“(汉)明帝崩,起祇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杨衒之著,周振甫译注:《〈洛阳伽蓝记〉译注》卷四,第146页。“祇洹”,亦称“祇洹精舍”(Jetavana)、“祇园精舍”,为“祇树给孤独园”之简称,位于古印度佛教圣地王舍城,与王舍城外“竹林精舍”为印度早期佛教最重要的二座寺庙。《洛阳伽蓝记》卷一“景林寺”条亦言:“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祇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杨衒之著,周振甫译注:《〈洛阳伽蓝记〉译注》卷一,第41页。范祥雍先生注曰:“祇洹,梵名,亦译作祇陀,即祇树给孤独园……指禅房内修法处所。”*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3页。此“祇洹”即佛教寺庙之义,此为传世文献所载建佛寺于陵上最早者,然未言有浮图。“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依此推之,则明帝以后,东汉中原民众逐渐有立浮图于冢上,《水经注》所载“襄乡浮图”则为传世文献所见最早立浮图于冢墓上者。
汉末既有立浮图于冢墓上者,亦有将浮图微缩成明器用于墓葬陪葬品者,如“襄阳菜越墓陶楼”,这些反映了汉末三国之世,受佛教传播的影响,中原地区汉族葬俗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一些佛教因素,如佛像、浮图出现在墓葬之中。这种影响,至魏晋时期,进而从中原地域传播到江南地区。近世江苏、安徽、浙江等地一些孙吴至西晋时期墓葬出土大量佛饰魂瓶(谷仓罐),如江苏金坛孙吴墓出土青瓷堆塑罐(1973年3月江苏省金坛县白塔乡三国吴墓出土),其罐口顶盖为六重高楼,楼阁鸱尾为佛教菩提叶之形态,这种重楼菩提鸱尾形态,为佛教在江南地区传播之产物。
对于“襄乡浮图”在中国早期佛教发展史上之重要地位,历代以来亦有学者明确评价,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三《浮图之始》按曰:“熹平为汉灵帝年号,中国之有浮图当始见于此。惜‘某君’不传其姓名,所云‘累砖作百达柱八所’,岂即浮图之古制乎?”*俞樾撰,贞凡等点校:《茶香室丛钞》卷十三《浮图之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一册,第289页。俞荫甫明确肯定“襄乡浮图”为中国之有浮图始见于此。施蛰存以为“兴建浮图,魏晋以后,始盛行之。汉末所建,仅见于此”*施蛰存:《水经注碑录》卷六《汉某君碑》,第226页。,施先生以为“襄乡浮图”为传世文献所知汉末浮图之仅见者,或有误,《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笮融于广陵所起“浮图祠”,亦为汉末之世,然其年代略晚于“襄乡浮图”。对此,当代著名郦学家陈桥驿《古建塔史与〈水经注〉的记载》一文进一步明确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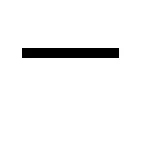
(二)“熹平某君碑”
“襄乡浮图”之侧另立有“熹平某君碑”,为东汉熹平年间某君卒后,其弟所立,以旌某君之德。“襄乡浮图”立于熹平中,故此碑所立年代当在汉末熹平至中平之时。碑文当述某君之家世生平仕宦及建造浮图之事,并作铭辞以赞其德,惜《水经注》未载此碑文。此碑除《水经注》以外,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后世诸家金石文献皆未载,唯洪适《隶释》卷二十、顾蔼吉《隶辨》卷八依《水经注》皆载有《熹平君碑》,其文同,可知碑早已亡佚。
四、结论

襄阳汉“菜越墓陶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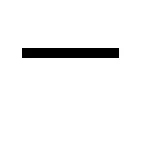
[责任编辑渭卿]
作者简介:张鹏飞,广东警官学院公共课部副教授(广东广州 510230)、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学院访问学者。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水经注》金石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15BZW058)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