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的“硝烟”
2016-05-26马晓彬
马晓彬
那年是六岁还是七岁?已记不太清楚了。适开蒙识字之初,就被大点儿的孩子指着楼角一块白色长方形木牌上三个隶书黑字,逐字教读:“西-四-楼”。甫交换齿之龄,门牙洞开,说话岔风漏气,语焉不详,怎么用心去念,都是“西-西-楼”,因此饱受大孩子们的奚落和恶意模仿,并当作笑柄在一同的玩伴中广为传扬。心下惭且忿,暗自苦练矫正,终因难逾当时的生理条件,几次尝试相继失败,乃灰心作罢。
而西四楼从此成为童年的记忆铭刻。在爬满苔藓的砖墙上,纽扣般排列着一行鹌鹑蛋大小的神秘洞孔。阅历丰富的大孩子曾遥指给我看,语调低沉地说,那是“文革”初期军方在弹压两派武斗的红卫兵时留下的弹孔,当时那血啊……
在铅灰色和血红色相互交染的色彩震憾中,我一下子对自己的诞生地肃然起敬。这座粗糙得像掺了土的煤砖一样的三层青砖大屋顶架构的宿舍楼,灰扑扑呆立在七十年代末学校大院燥热而懒散的阳光下,开始了西四楼孩子们最初的战争启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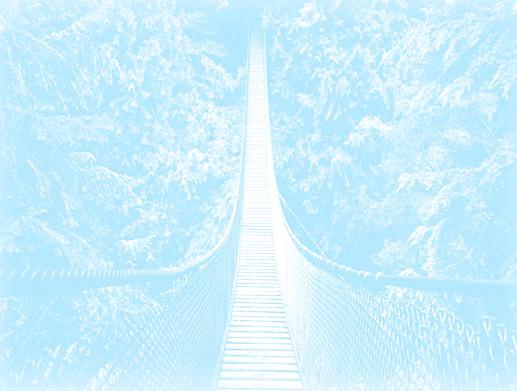
七十年代是个英雄主义泛滥的激情岁月。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国内气候云诡波谲,让战争随时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老百姓们在政府屡次发出的战争警报下,几乎都已具备了预备役战士良好的临战心态。敌人都分散在世界各地,但主要是苏修和美帝,还有盘踞在台湾岛的蒋匪残势。防空洞的大规模修筑,远比今天暴富的土豪们盖小洋楼的气派还要壮观。战争影片频频放映,让大人和小孩经常是撂下饭碗,抹抹嘴,赶集似地扶老携幼聚集到灯光球场。各家的地段和位置,早已被抢先的孩子们分片“割据”。
露天的夜晚,从未有过和平的气氛。机关枪、迫击炮密集的攒射声,战斗机被击落的呼啸声,坦克履带沉闷的碾压声,此起彼伏,相互交织,最后必定是嘹亮的冲锋号伴以同志们震天动地的“冲啊!”掀起整晚的高潮。敌人溃不成军,纷纷偃旗倒戈,激昂的背景音乐和旁白解说的兴奋声音在夜空中回荡:“这是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战争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在焰火般刺亮的硝烟炮火里,西四楼的孩子们屏息凝神,眸光闪烁不定,兴奋的小脸因异常激动而变得通红,就像是一块块烧窑时烧红的土坷垃。
但在普遍和平的年代里,错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等不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孩子们,演习战争便成了最令人心醉的游戏,孩子们管这叫“玩打仗”。每次战事拉开,敌我的角色提前都有严密分派,大体以“好人、坏蛋”作粗略划分,具体到军种角色,好人可能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或者是解放军、志愿军;坏蛋无外乎国民党匪兵、日本鬼子、告密的地主、穿便装戴军帽的伪军汉奸。
这种选角工作常常让“高层首脑”大为头痛。因为西四楼的孩子们戏路都不宽,全都是本色演出,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让自己饰演凶残、狡诈、卑鄙的反派,几乎可以被认为是对自尊心的污辱和践踏,不像现在许多演腻了正角的戏骨大腕们纷纷反串奸角,以显摆自己纯熟的演技。哪怕坏蛋们都穿着考究的毛料或质地柔滑的绸缎,装备也比较精良,也无法左右孩子们对正邪的取舍。
邪恶的暴力并不是那个时代崇尚的精神,这一点和如今的小屁孩们在电玩中单纯膜拜极致暴力的模糊是非观有质的区别,虽然形式和原态都能归结到战争。
经过一番带有威胁性质的硬性命令,再辅以轮流坐庄的灵活机制,一小部分人的情绪滋扰一般不会影响整个战局。家家户户的炉子生起来了,一只只雪花铁皮的烟筒像黑色的炮筒整齐伸出窗外,冒起一股股白色浓烟。开饭前的喧闹潜伏着开战前的寂静,屋后楼角、树丛田埂、墙头路边,甚至一些废弃的工地沙堆上,弥漫着一种大战将至的迫人氛围,使得游戏策划者无需太多说戏,就能让孩子们瞬间进入最佳状态,因为所有游戏环节的设置,几乎超不出对经典电影片断的克隆和模仿。
矮小狭窄的西四楼门洞,是整个战区唯一戒备森严的关卡,“司令部”就设在里面。一盏油腻的40W电灯炮被风吹得晃来晃去,四周的物事鬼影一般忽长忽短。下面就笔直挺立着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哨兵,手里端着一把漆黑锃亮的“卡宾枪”,那是从对过儿红星染织厂废弃的织布机上卸下的半截铁管配件。腰里扎着一条用书包带改制的帆布军带,头上顶着杨树枝条编成的伪装帽,树叶缝隙里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机警盘查着每一个进进出出的可疑人员。
“口令!哪部分的?”哨兵一声断喝,对方一定得回答“酸菜粉条”或“洋芋炒肉”,接着自报家门:“美八军五师”,要么“李向阳的部队”。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无从考证, 当时的高层军事首脑将这些算得上一级军事机密的口令以菜入名,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和决策?似乎多少有损作为正规军应有的神采威仪,倒有点像历史上某一支由菜农领导起事的义军。许多年以后,偶然碰到一个儿时玩伴,说到小时候的事,突然提起这茬儿,他哈哈大笑。原来他当时曾任过一届“司令”。因为打小爱吃这两样菜,老妈也常给做,情急之下憋不出好词,严肃的军事会议桌上便出笼了一张家常菜谱。他现在在市内某家颇有名气的酒楼做事,而且是一川菜厨子。
凭借这种极富创意的“菜谱口令”,有几回还真逮着了几个敌方细作,被五花大绑拴在司令部楼梯口栏杆上严加看管。直到敌方司令以兵力不够为由罢战相挟,才遣送回营。然而就有一次几个郊区农民装束、背着藤条背斗的大人要过关卡,因为答不出口令,再加上形迹可疑,被警惕性极高却又捂着鼻子的哨兵堵在门外。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考虑到是大人,“战争,让大人走开!”才勉强予以通行。后来得知,那是几个近郊菜农来偷挖学校宿舍楼厕所的大粪,因为白天不方便,只好夜里行动,不料误闯战区,让双方一场虚惊。这时候,孩子们才觉出那晚的紧张气氛中,确实还散发着一股异味,但谁也没留意停在路边的一辆粪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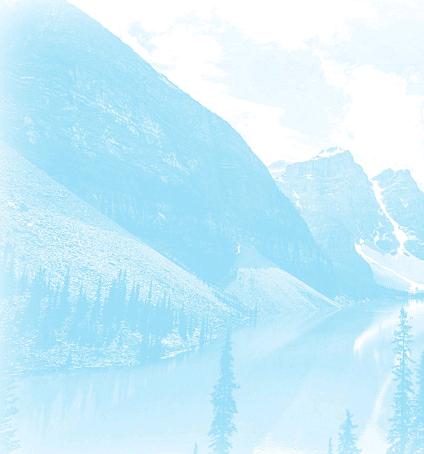
信号弹在夜空中清脆炸响,是一支过年时都舍不得燃放的“月里行”。大战前的寂静顿时被密集的枪炮声打破了。各种仿真的混响,全都发自孩子们造型不一的小嘴里,并助以手榴弹的投掷,其实都是战前精心挑选出来的松软土坷垃。有时因为激战正酣,不留神就把一块铁疙瘩一样的鹅卵石毫不犹豫投向敌方阵营。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很快传来孩子的哭声。一个拖着鼻涕的小男孩头破血流爬出战壕,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妈呀……”;脾气躁些的,捂着血丝乎拉的脑袋直冲对方,嘴里喊的不是“投降”,而是“赖皮”,认准了扔石头的冒失鬼后,好一顿撕扯扭打。战争变成了殴斗,往往是孩子们的游戏流程,反之,则是成人世界的战争规律。
这时候,战斗自然暂告一段,“国共”再度精诚合作。双方司令乘势整顿军容军纪,调整战场规则,检查装备部署。敌方司令在一伙奇装异服的高级将领前呼后拥下,亲临前线督视。司令扮相极酷:披着一块千疮百孔的麻袋片,当然这得叫“斗篷”或“披风”,光头上顶着一款用竹圈绷圆的大檐帽,套着一双白色棉线劳保手套,左手的马鞭不停地朝右手掌心轮番拍打。然后在半截烧得黑乎乎的烟筒前停下来,非常倨傲地伸出两指轻轻一拭,目光冷峻地环视属下:“炮弹离炮位太远了,太麻痹了,太麻痹了!” 这是每次开战时,敌方作为饰演反派的重要条件而被强烈要求保留沿用的一个经典桥段。
未几,战事重开,硝烟又起。几个回合后,敌人按规定弹尽粮绝,还得负隅顽抗一阵儿。我方阵地适时吹起嘹亮的冲锋号,孩子们像小老虎一样跳出战壕,“冲啊!缴枪不杀!”的喊杀声响彻夜空。追剿穷寇的过程是孩子们最爽的时候,但有回一位司令发出总攻令时过于冲动,手中权当马刀的半截铁片一挥之下幅度过大,竟砍伤到自己脚面。当时是夏天,又不穿袜子,翻卷的伤口像非洲人民性感的嘴唇,从战场到家再到卫生所的路上,不用狗鼻子也能显而易见一路洋洋洒洒的血迹,让人怵目惊心。
孩子们被闻讯赶来的父母纷纷呵斥回家,偌大的部队被瓦解在各自家里,每个孩子打开窗户左顾右盼,忐忑不安地担心着司令的伤势。据说司令在卫生所缝合伤口时,还不断偷偷嘱咐随同副官,要他把丢弃在水沟里的半块西瓜壳捡回来,生怕下次战役时没得“钢盔”带。这使得孩子们钦佩不已,也对战争的血腥本质开始有了模糊认识。
战斗总是在孩子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和喧叫声中偃旗息鼓。倘若一旦发生挂彩事件,迫于舆论压力,照例要休战一段时间。硝烟散尽,和平的麻雀在战场上空飞翔。歌舞升平的背景里,女孩子们出现了。扔沙包、蹦房房、掷骨节、跳皮筋、丢手绢、藏猫猫、过家家等一应充满温馨祥和、活泼明丽的女性游戏,开始占据了整个和平年代。
战争狂们在一旁冷眼观望,开始是抵触捣乱甚至故意寻衅滋事,随着一些热爱和平的小男孩不断加盟,孩子们相继马放南山,改刀为犁,十分不情愿地同女孩子们组建起临时家庭,个个充当起不苟言笑的爸爸或者爷爷。但动辄又挑动干戈,大搞邻里纠纷,频频破坏游戏规则。战争是雄性生命的情绪化发泄,而脆弱的和平却常常需要充满妻性和母性的女孩子们柔情呵护。当我不再是孩子的时候,终于懂得了人性的暴虐和关爱,都缘于孩提时代的启蒙。
许多年后,西四楼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四处颠沛流离。当年那支历经百战的雄师劲旅,开始混迹于物欲纷争的成人世界,在各自生存的战壕里流汗打拼。司令还是士兵,已没有任何分别。当我从酬酢周旋的世务中疲惫归来,听说西四楼已被拆除,要改建为学生公寓。
血色的夕阳在黄昏的暮霭中划出一抹致命伤痕,把西四楼的残垣断壁映衬得沧桑而深刻。我像一位凭吊古战场的幸存战士,轻轻拿起半块残砖,深情地摩挲抚摸。遥远的天际突然间炮火隆隆,杀声震耳,一种神秘的声音铺天盖地,响绝四野……
孩子们的“硝烟”,毕竟是一种美好的童年回忆,而狼烟四起的世界,硝烟里的孩子们又在开始每一天噩梦般的逃亡。
(本文系西宁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少年向前冲》节目特约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