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本的艺术宽度及诸多可能
2016-05-26李新勇
李新勇
从《风声霞影》谈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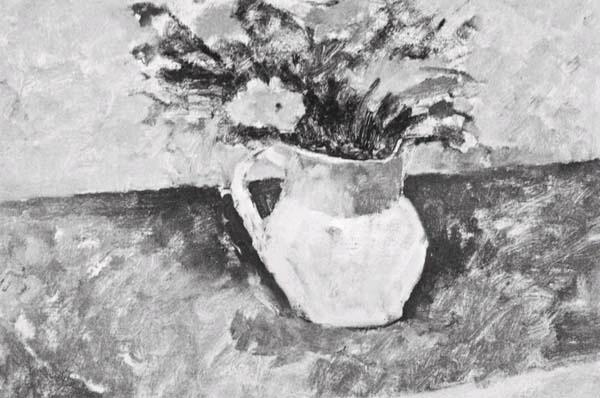
2013年中秋前后,收到柳小霞的散文随笔集《风声霞影》,顿时为一位极富实力和潜力的文学新秀的出场感到说不出的兴奋。《风声霞影》全书十六万字,分五卷将发表在各地报刊上的散文随笔“捆扎”在一起。之所以用“捆扎”,是因为我觉得,几乎所有的散文随笔集都可用“捆扎”二字。写作时间有前有后,所表现的内容和思想各个不同,使得每一篇文章都如旷野上的花朵,各有各的颜色和姿态。面对缤纷多彩的鲜花,“捆扎”得好就是插画工艺,“捆扎”得不好就是一堆乱草。柳小霞不愧是编辑出身,深谙此道,在“捆扎”时以少取胜,十篇左右为一卷,不贪多求全,使每一卷的重点和亮点都能突出出来,重点和亮点互不倾轧、互不重复。第一卷写河湟风物与作者的感悟;第二卷写故乡的人和事,表现作者最朴实纯粹的感情;第三卷则从时间和历史的角度来考量山川风物;第四、第五卷则是文艺随笔,观点清晰,新颖独到。好的散文就该这样,不以数量,而以质量取胜。
《风声霞影》中的散文语言特别,文字闪耀着真诚的光芒,富有生活气息,别有韵味。《河湟记事》通过青海河湟地区老百姓的两个口头禅——“泼烦”和“哈怂”——表现河湟人透亮本真的性格。有了这个基础,作家顺势进入对河湟人家的叙写。这样铺陈充足,蓄势正好,让我这位长期生活在东部城市的喧嚣中的人,一下进入到某种沉静和安详中,心里顿时向往:要是能到那样的干净雅致、充满阳光的村落住上十天半月,那才是人间至真至纯的享受。作家对河湟有着天生的热爱,因为她出生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每天清晨,阳光透过红瓦铺下来,整个院落都恍如处在一片黄澄澄的光芒世界里。那时刻,鸟鸣声会停下来,时光会在静谧中滑过几分钟,柔和的空气在微微流动。”她的文字承载了那片土地的温情和笑语。
《风声霞影》出版后,柳小霞没有停歇,马不停蹄于她文学的追梦之旅,我又读到柳小霞一批新创作的散文。这批散文以全新的的面目出现——读柳小霞的文章,你能感受到某种生长的力量。《河湟之秋》是一篇刊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此文大气滂沱,语言精致,带着阳光的温度和干草的醇香,特别喜欢。“因为有了夏末的雨水滋养,空气倍显朗润,到处都能闻到太阳散发出的干爽成熟的气息。很多人家都开始晾晒衣物,阳台上整日缤纷一片。棉被在秋日艳阳下一经曝晒,似乎能将秋天辉煌的气息融化进每一根丝絮里,好几天后,这种气息依然会在房间里弥漫。秋天用其强大的能量将天地之间的成熟之脉打进了万物的深处,重新唤醒了万物的生长欲望。”作家所解读的河湟的秋天充满生命力、充满阳光和想象。
柳小霞的散文语言是精致的,更是细致的,充满诗意和真诚,充满超然物外、俯照众生的力量和敞亮热情的激情。散文《一笑泯千愁》写青海人爱笑,不动声色写了许多令人发笑的语言、动作和情景,诙谐幽默,不疾不徐。
十八年前,我二十刚刚出头,到县团委上班。单位上有几个男同事,比我年长不了几岁,但都已成家立业。大家因为同样年轻的缘故,普遍都爱笑。他们说话喜欢带机锋,我初入社会,整天昏头昏脑,总是听不明白真正的含义,只觉得每句话都足以让人捧腹大笑。我常常会在第一时间笑将起来,笑得他们更加欢欣鼓舞,很快一个个全都“笑脱靶”了。最后书记干脆大笑一声说:都整工作,整完了再笑。我只好接着再笑。
我们常常读到一些文字死板、叙述僵化的散文,好似一堆死面,问题就出在作者不懂得幽默,语言没有弹性和光泽。而柳小霞的文字,自由,灵动,充满人间烟火而又让幽默无处不在。这里所说的“幽默”,是一种更接近于“情趣”的气质。它充斥于行文和叙写对象中,它无形地灌注到作品的思想内核深处,它是作品中的盐,是山川大地上干净的阳光,能驱散读者心头的阴霾,能给予读者无限宽阔的温暖、启发和情感体验。散文创作上取得的成功,为柳小霞未来的创作铺设了一条厚实而宽阔的道路。
跨文本的艺术宽度及诸多可能
在谈柳小霞的散文的时候,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一个是其散文的“细致”,一个是其散文的“情趣”。
《风声霞影》中有一篇《故乡影事》,其中有一个“河滩地”片段。作者像一个优秀的取景师,单单取了一个年纪并不大的老汉听见河滩妇女吟唱思念远在他乡的丈夫的花儿时的情绪和表现,有伤感,有失落,感叹青春不再,为年岁不饶人而怅然……各种复杂的情绪都落到他吃了一点点儿媳妇替他做的手擀面、深切地感受到腿酸腿痛、躺到檐下矮榻上之后的最后一句话:这当儿,他的牛不停地在草房门口反刍。这哪是牛在反刍呢,分明是一位力不从心的老者对隐藏在岁月深处的故事的回味。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读了这篇文章,我对柳小霞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你一定要坚持自己对生活特别的感悟和表现能力,这是许多散文家终其一生都没有培养出来的东西,你也许天生就有,好好呵护,用心培养。这是什么?这是文字的趣味和温度,这是文学的含蓄和魅力,这就是柳小霞之所以叫柳小霞的原因。第二句话是,柳小霞有写小说的潜质和能力。你看,为表现一个老者对生活的热爱,他通过老者力不从心时的怅然和不甘来展现,心痛是令人心痛的,但小说的勃勃的生机却在这个作品枝叶婆娑。
同在这一本书中有一篇叫《最后的时光》的散文,写母亲临终前如何指导别人替自己做老衣这一节,细致而特别,这是绝望的人间烟火,是温馨的临终关照,是庄重的登场。无处不在的细节和故事式的叙写,既是盘旋也是飞升,使散文变得灵动起来,让读者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正因为如许“跨文本”的气质,柳小霞的文字是有情趣的、有情态的。读者能够毫无障碍地进入作家所描述的场景。
最近又读到她的散文《莲花晤》,里面有一个特别“小说”的镜头:作家年轻时候贸然进入一座虚掩着门的寺庙,看见一出家人在画唐卡,僧人将她视若不存在,而作家的心却在天界和凡间奔波,当她轻轻推门出了古寺之后,僧人轻轻把门关上。作家特别有趣的文字就来了:“我迈过门槛走了大约十几米后,门在我身后‘吱哑一声关上了,但关得很谨慎。门依然没有关严实,而是就像我来时一样,仅仅是虚掩着。噢,他明明看见了我,而且他不喜欢被贸然打搅。可是,他为什么不闩门。”紧接着作者写到“夕阳西下时,余晖变得辉煌明亮。这时候,光芒铺过大金瓦殿,塔尔寺笼在一片金色里。虚掩的门是红色的木门,而门两旁是青砖砌的墙。金色的光芒从虚掩的门扉间反照过来,仿佛一面柔软的光墙在我的眼前浮动。这一时刻宁静,而又激荡。我望着那束辉煌的光芒,惊呆了。忽然间,我的心灵有所触动,心中持久的忧伤被一种更为坚实的感动击垮。”这段文字我读了三遍,特别有趣,可算入骨了。柳小霞的行文就这样,所转达的意境和情趣看不到细碎与小气,只有开放的格局和开阔的气象。
“细致”和“情趣”是跨文本创作的两个重要特征。“跨文本”兼具散文和小说的许多特质和表现手法,拓展了艺术空间,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它比传统散文更多一些细节和情趣,又比传统小说更多一些现场感和真实感。在柳小霞的作品中,许多作品都具有“跨文本”的影子。文学作品当然不能为“跨文本”而跨文本,文学作品应直指艺术、思想和内心。从柳小霞的这类作品可看得出,她早就做好了在小说创作领域纵横驰骋的准备了。
柳小霞身为女性,她了解女性,2014年陆续读到她一批小说,《那槐花飘香的时节》《风儿轻轻吹》《归妹》《苏苏》《蓝钥匙》《北方有佳人》《桃花坞》等短篇小说,均以婚姻家庭为主。这些小说里面,作家着意想要表现的就是女性在困惑面前的秉持,和对情感的渴望,对尊严的维护。小说里面的每个女性都在坚定地说着“不”,她们都不想要凑和的东西,都渴望着真挚和高尚的情感,都是有所选择,有所反抗的。哪怕社会再复杂,诱惑多强大,人声多喧嚣,她们的心中始终都有一盏灯。
因有散文创作做底子,柳小霞的小说很意思。《归妹》语言有筋道,干净而富有弹性,叙事有张力。《风儿轻轻地吹》是写“接访”的,有很沉重的现实感,表现作家的责任担当。《桃花坞》语带双关,故事无可挑剔,发人深思。《桃花坞》一看标题,便知道取源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名字如此诗情画意的地方原本应该是人们返璞归真时的一方净土;青少年时代的同学相聚自身带有现代人返璞归真的一种情感需求。然而桃花坞里的这场重逢,在简单的几句寒暄后,马上升腾出现代社会的喧嚣和锐利气息,连过门都来不及打,久别重逢的同学们马上进入戏谑状态,最后演变成一场闹剧。而且这场闹剧的背后作者用酒后吐真言的方法,带出一个几近于残忍的家庭故事。桃花坞在现代文明的冲撞下最终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
柳小霞的小说除了故事讲得好,更重要的是有筋道,有嚼头。短篇小说《苏苏》,写“我”与一个叫苏苏的重庆女孩在北京培训结束后去山海关,女孩发短信给旧时男友,女孩曾经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女孩陷入深沉的回忆中,她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在说与不说间、也在见与不见间,她的爱情还与山海关这个特殊的故事背景有关。女孩若即若离的叙述一定触碰到“我”的某根神经、某段往事。作者先后两次写“我”流泪,直到文本的最后也未写“我”为何伤感。这就是作家的高明之处,苏苏其实是“我”的镜子,青春年少时的故事是多么相似。不说比说更令人回味。这就是艺术含蓄的魅力。
凭个人的创作经验,我感觉,柳小霞的散文创作是为她的小说创作做准备的,柳小霞“跨文本”的本事,为她创作优秀小说做好了铺垫。柳小霞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散文家,因为她坦率真诚、敞亮细致,充满阳光而富有幽默情趣。柳小霞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因为她的小说充满人间烟火却又贴着地面飞翔,在俯视众生中远眺文学理想。不管是哪一种,都让我们一起对柳小霞未来的创作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