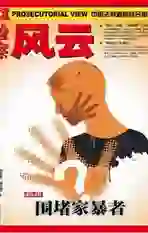韩天衡:老去犹当学
2016-05-14
本期客座总编辑
韩天衡先生,现任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院长、上海中国画院顾问(原副院长),中国石雕博物馆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等。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检察风云》:尊敬的韩天衡老师,很高兴今天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的“学艺七十年书画印展”从杭州去到了武汉,继而从武汉回到上海,在上海又经历了上海中国画院的专场,到韩天衡美术馆的开幕,作品数量之多,风格之盛,内涵之佳,可否请您谈谈在办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刻感受?
韩天衡:首先我要感谢上海文联、上海书协,和中国书协、西泠印社、中国篆刻院、上海文史馆等单位的关心,促成了展览的成功举办。我有很多年没有办过这样大型的展览了,这次的展览大家如此关心和支持,所以我尽我所能,希望将展览办得好一些,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原本定的是“从艺”,但我将这“从”字改为了“学”,因为我从小开始学,到现在仍然在学,“从”字与“学”字,两者之间是不能有隔墙的,既然有志于这门艺术,就必须学到老,事实上学到老也是学不尽的。
现在有那么一点点成绩,但骨子里还是靠一个“学”字,比如说现在的风格,想要有所改变、有所突破,这便是一个学的过程。用“学艺七十年”作为展览的标题,有人说我谦虚,其实不然,这是一句很实在的话。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自己处于一个学的过程,在学的过程中搞创作,用创作促进进一步的学习,创作和学始终存在着因果关系,两者不可分割。因为是学艺七十年,于是我选用了70件书法、70件(套)的中国画、70件篆刻作品,三个70件,上海人有句玩笑话,说“不管三七二十一,丑婆娘总要见公婆吧”,所以作品总的是210件。从三十多岁时的作品,到现在的作品,另外有学术著作和书画印的著作,大概110种左右,表现的面相对宽广一些。
《检察风云》:据了解,浙江美术馆有一个统计,您在杭州的展览参观人数超越了两万人,他们认为这是创了一个纪录。
韩天衡:在杭州展览反响不错,确实超乎了我的想象。另外在武汉的展览,也得到了大家的欢迎,应武汉方面的要求,展览结束后又延长了25天。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即展览在杭州、在武汉,为什么有比较好的反响?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艺术成就问题。作为海派艺术的传人,或者从时段上来说,20世纪辉煌的、在书画印艺术领域占全国半壁江山的海派艺术,尽管后来我们宣传少了,对外的展览少了,但海派艺术的影响仍然存在,艺术爱好者们总有那么一种欣赏海派艺术的情结在。
我们海上的书画篆刻艺术家,确实应该更多的走出去,不要让我们老一辈开创的辉煌的海派艺术在我们这里走向下坡。我想海派的书画印,如果我们有关方面组织的好、策划的好,定能产生更好的影响。通过目前几次的展示,我深深觉得,作为海派艺术的传人,有这样一份责任,要弘扬我们的海派艺术,不能让它成为过去式,它应该是充满活力的,向更新的方式发展,这是我从展览中得到的重要启示。至于我个人来说,我尊重传统,但又认为传统必须要发展,一定要推陈出新,否则有了古人还要你做什么?要向前走,正如我过去说的,“传统万岁,出新是万岁加一岁”、“推陈出新的本质是推陈出新”。所以艺术工作者,作为海派的传人,我们有责任不断地前进,才能使海派生生不息,具有无穷的活力和崭新的氛围,无愧于先贤、无愧于后人。
《检察风云》:您的“七十年学艺展”不知接下来是否还有巡展的安排?可能会在哪些地方?什么时间?
韩天衡:刚才说到展览在杭州和武汉、上海三地展出后反响不错,又接到了一些地区的邀请,我也乐意接受了。今年已经定下有三个地区,四月份在云南的昆明,六月份在澳门,九月底在山东的济南。昆明和济南的展览,基本与前几次“学艺七十年”的展览同一内容。澳门作为特区,主办方提出与内地的展出要有所区别,所以展出中会有百分之五十的新作品。
《检察风云》:您最近又在吴昌硕纪念馆举办了“追踪缶翁”的艺术展。大家都知道吴昌硕是海派的书画篆刻大师,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吴昌硕的?吴昌硕的艺术所带给您的启发有哪些?
韩天衡:我仍然从海派艺术说起。为什么作为后来人都要高举海派艺术的大旗,这是我们不能推却的历史责任。吴昌硕是海派艺术重要的开拓者,一位泰斗级的领军人物,如今在海内外还有着重大的影响。我们敬仰吴昌硕先生,所以我的展览的主题词定为“追踪缶翁”。我们要高举前辈的大旗前行,追踪缶翁,不是从保守的意义上来说,重复他的观念,重复他的技巧,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便是接过他创新的理念、创新的技法,让海派艺术得到更好的新生。
吴昌硕先生的艺术,要从深层次去领悟。晚清时期,国弱民穷,饱受苦难,民族危亡之际,吴昌硕先生雄强的画风,无疑在那个时代的精神上是振奋的。所以,我将吴昌硕先生的这种精神,用他刻过的一枚印总结为“强其骨”,“强其骨”的精神是向上的、阳光的、奋斗的正能量。
吴昌硕先生最早成名的是篆刻,他对篆刻有一个揭示创新的理念,即“道在瓦甓”。在吴昌硕之前,所有的篆刻家都没有福分见到晚清出土的、大量的封泥、瓦甓等。前人未见,时人未悟,吴昌硕则从中发现、发掘,并提炼精华,从而使他的篆刻艺术充满了新奇、雄浑、强悍、空灵的韵致。他从“道在瓦甓”中悟出了道,这便是吴昌硕先生给我的两点最深感触,一是他的“强其骨”,二是他在借鉴传统时的方向把握,由瓦甓入手,吸取养料,结合自己的努力和天分,形成了他完全独立的风格。
我们今天敬重他、纪念他、学习他,不是照抄他的理念、他的技巧,而是要学习、继承他最本质的创新精神,继而创作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新的艺术,那么我们海派艺术的振兴完全指日可待。
《检察风云》:现在方介堪、方去疾昆仲美术馆在温州落成了,您为该馆题写了馆名。我们都知道您曾受教于两位老先生,可否请您谈谈您从这两位先生处分别学到的?
韩天衡:我年轻时运气非常好,有很多有成就的大师给了我许多的教诲和帮助,我至今感恩他们。比如谢稚柳先生、陆维钊先生、陆俨少先生、程十发先生、沙孟海先生等,每位老师都有非常重要的某一点,能够让我在艺术的道路上循序渐进。
谈到篆刻艺术,确实这两位老师给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他们俩的差别在哪里呢?我觉得介堪先生教会了我如何进入传统,古玺印、秦汉印、宋元印,它们的妙处在哪里,如何正确的学习传统,这便是“进入”。方去疾先生教会了我如何走出传统。走入了传统,那么一辈子守传统吗?我二十三岁时,方去疾先生看过我的印章,他说“你可以变了”。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尽管去疾先生与我没有太多技法上的交流,但他的这一“变”字,让我懂得学习传统的目的,不是恪守传统。深入了传统,是要再走出传统的,是要推陈出新的,更让我努力的跳出了传统,这个“跳”不是舍弃,是带着深刻的传统感悟和理解去出新。
《检察风云》:您虽然已经七十六岁,但平时仍然勤奋的创作着,我们也经常欣赏到您的新作。请您谈谈您现在对治印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考?另外,是什么动力让您笔耕不辍?
韩天衡:通过七十年的学艺,我觉得关键是“打通”二字。不单单是治印,我还对绘画如何融入书法,绘画书法中的元素,如何融入篆刻,印章的元素,又如何融入书画进行思考。
我注重传统,但不保守。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心态,我始终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与时代同步,探索着区别于过往、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我自小有着一个艺术梦,但梦想和现实之间毕竟路途遥远。由于各种原因,使许多有志于艺术创作的朋友半途而终了,理想便成了空想。我的运气不错,从小学艺术,走了不少曲折的道路,最后进入了专业艺术团体。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即爱好、追求,与工作相互合一,老天给了我恩惠,让我如鱼得水,成为了专业艺术工作者。
不过我深深觉得,人生短暂,切莫虚度,在有生之年,我唯愿继续淡定的探索。我们这门艺术是个手艺活,除了思考,更多的是实践,思考需要时间,思考可以产生灵感,但只有思考和灵感而欠实践,那依然是一场幻梦。不做一生勤奋的人,没有殉道者的精神去对待这份事业,要取得任何成绩,都是一句空话。
采写:唐吉慧
编辑:沈海晨 haichen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