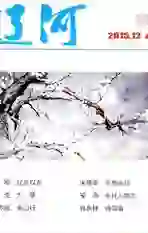远去的辘轳声
2016-04-20张立国
张立国
吱——吱——吱——哗……
吱——吱——吱——哗……
……
那时断时续、不紧不慢的辘轳声传来,带着一股悠远的韵律,于是,辘轳声便也像井沿的藓苔般古老了。
不紧不慢且有着悠远韵律的辘轳声,就像村头那棵古槐树上的钟声,让村里人闻声起床。日出日落间,村里人总是摇着它迎接每一天的黎明,摇着它目送每一天的落霞。
辘轳声一直陪我长大。小时候看村子里大人们用辘轳绞水,总是充满了好奇与羡慕。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站在井沿上都是一种姿势:一手叉腰,用另一只长满茧子的手掌摁住辘轳控制速度,“扭扭、扭扭……啪”,水斗坠到井底,接下来晃动着井绳,水斗子盛满水,然后再用手握住辘轳把,“吱扭、吱扭”一圈圈地绞上来。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辘轳艰难地支撑着岁月的日子,给村民输送甘甜。
我始终认为,辘轳与早、中、晚间的炊烟一样,是村里人生活的一部分,吃的水、洗衣水、洗菜水都要靠它绞上来,就连谁家的菜园子渴了,也要靠它把清凉的水一斗一斗地绞上来,浇灌各种菜蔬。乡下井水的好坏,大约是与地下的水脉有关联的,所以有的井里的水是甜的,而有的井里的水却略带苦涩,煮出饭来味道就很是不同。在我的记忆中,村子里大小井有很多眼,但是要数刘家、马家、陆家的三眼大井最出名,水充足,清澈,带一丝丝甜味,用它的水煮饭泡茶,清香四溢,味甘可口。马家和陆家座井的时间短,最长也不过五十年。只有刘家的那眼井,时间久远了。到底什么年代就有,不知道。几个娃娃去问村子里寿数最高的老爷爷,老人抚着雪一样洁白的胡子开口了,声音也像那辘轳声、不紧不慢:“我还是孩子时,刘家的老辈子就摇那辘轳了。呶,就这样——”老人用颤微微的手向村子边上的刘家菜园一指。
正在摇着辘轳浇园的,是刘家现在的当家人,身材高大,有着一张古铜色脸庞的老头。掌畦的,是他的还没有锹把高的小孙子,活脱脱就是他爷爷的影儿。
在我的印象中,刘家是村子里有钱的大户。早年间,为了自家用着方便,他们的祖上在菜园里打了这眼井。井口约有磨盘大小,整个井从下面到井口都是用石头砌成的。井口的上边架着木制的辘轳,平时井绳缠绕在上面,水斗子悠闲地空悬在辘轳下,或是放在井沿旁。辘轳本身在井绳经年累月的勒磨下,已印上了一圈圈的沟痕,把柄也经过长年与人手的摩擦,已经变得光滑锃亮了。可以说,这是刘家人代代生活留下来的历史印记。
刘家老人穿一件老式的肥裆裤,上面隐隐约约挂有汗渍,一双大大的光脚踩在青石漫就的井台上。台沿上,被刘家十几代人踩过来,竟留下了两个深深的脚窝。
刘家的菜园南边跟村头的麦地衔接在一起。小葱一片碧绿,菜花一片金黄,黄瓜正上架,蚕豆角正成熟。一群群小蜜蜂在这儿嗡嗡地飞舞,一双双燕子在这儿喃喃地掠过。这个小菜园给整个村落增加了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菜园的北边靠着个果树林,这林里有梨,有柳,有白杨,有香椿,有桃、李、杏,有蜂,有蝴蝶。这些树种中,唯有梨树多。梨树都长着低矮的树干,矮树干上长起一蓬枝条。每年梨子的重压,又使那些树枝弯回地上,形成一个大伞盖。春暖花开的时节,方圆几十里远,尽是白花花的海洋。如今梨树的叶子,都是翠绿翠绿的,风一吹起来,树顶上翻着深绿色的波浪。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要有吃有穿,脸皮是白皙的,皮肤是细腻的,头发是乌黑的。
老人光着脊背,脊背也是古铜色的,松弛的皮肤皱成一道道纹路,汗水顺着纹路流下来,流到裤腰,往下湿去。
光着屁股的小孙子蹲在地头,浑身上下黝黑透亮。他看一眼菜畦,看一眼爷爷,一会儿那细嫩的嗓音响起来:“爷爷,满了!改畦啰——”拖一声长长的尾音。
老人直起腰,稍稍停顿一下,喘口气,接着便小跑着过来改畦。改完畦,拍拍小孙子的脑瓜笑一笑。小孙子呢,咧开小嘴,露出两颗豁牙,也回敬爷爷一个甜甜的笑……爷爷满足了,劳累也被这笑驱走了,重又回到井边摇起辘轳来。在老人的眼里,刘家又多了个接辘轳把的人,甚至比自己的儿子们更靠得住……他摇得比先前更起劲了。但见他双手握住辘轳把,身体一起一伏地用力,背部的、胳膊上的肌肉也在松弛的皮肤下颤抖地动起来。每提上一斗水,老人一手扶住辘轳光滑的轴辊,一手背在身后,身子侧开来,水斗子自己向井下坠去,辘轳便“扭扭”地响起来。老人便眯上眼,听着“扭扭”声。这声音、尖得刺人耳朵,可在他听来,比戏园子里那曲调悠扬的老调梆子还动听得多……
老人是个勤劳的人,村里人都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总是迈着稳实的脚步,走在前头,自家女人在后头跟着,他们顺着垄沟边上的一条光明小道走进去。在井上架起辘轳,泡上斗子。然后捡一颗梨树荫里歇下脚。歇足了精神,就开始甩开膀子浇园。那时候,他和自家女人在菜园里活干得很惬意,浇完了黄瓜,又浇韭菜、青菜,又拔完菜畦里的草。菜在干旱的畦里,就萎靡不振。用水浇过的菜畦,不多一会,就绿沉沉起来。他想:“也许,这就是生机!”
刘家的大儿子从自家的地里忙完活回来,路过菜园,便折进来。伏天的日头,火辣辣地照在人身上。他见父亲的裤子已被汗水浸湿了半截,心疼地说:“爹,这活太累了。”
“不累”老人摇着辘轳不抬头。
“爹!”
“嗯!”老人还是不抬头。
“你看人家浇园都用水泵,咱家还用这个辘轳把提水浇园,这也太落后了吧?爹,一台水泵才三百来块钱,咱家也买一台吧,我们一早一晚就能把园给浇了,你也该歇歇了。”
老人慢慢地回过头,瞟了儿子一眼,说:“庄稼人,生就了干活的命,省着力气干嘛?哼!”
大儿子慑于父亲的威严,便不再做声了。他默默地过去,替老人摇起辘轳来。他和父亲一样,依旧摇出那不紧不慢的韵律。
二儿子从城里卖东西回来,也折进菜园,他对蹲在地上吸烟的父亲说:“爹,说您老是不听,非要费这个傻力气。这儿离机井又不远,修个垄沟过来,交不了几块钱的电费,一会儿就浇完了,你……”
“混账!”老人火了,他最不爱听这话。二儿子嘴唇蠕动着,还想说什么,大儿子用目光把弟弟制止了。在他的眼里,自己的兄长像父亲一样讷于言辞,目光便也像父亲那般的威严。二儿子无可奈何,气哼哼地离开菜园。
大儿子理解自己的父亲,老人不折不扣地恪守着祖上留下来的训示。就这小菜园,他从不允许上化肥,每年农闲时,他总是粪筐不离肩,较之化肥,他更信服大粪。
在村人眼里,刘家的这个小菜园是相当出色的。老人是个种菜的把式,巧于调度,也善于利用。畦里种的是越冬的菠菜、韭菜、羊角葱;还有开春种下的水萝卜、莴苣菜。每年都是这期春菜下来,老人就赶紧种黄瓜、豆角、西红柿。这期夏菜过后,他又紧接着就种上了一水的大白菜。这园子常常是一年收四季。这还不算,老人是见缝就插针,没有一个地方不被利用,比方,畦埂种的是蚕豆角,墙根栽着老窝瓜,占天不占地,白得收成。
老人呢,还在生二儿子的气。自己的爷爷都是这么摇过来的。这眼井,老辈人传说正好打在一条龙的嘴上,任你怎么着,水线降到一定位置就再也不动了。这两年旱得厉害,这眼井也没见过干,只是水浑浊了点,但他认定,只有这水才能养菜。当年,他从父亲手里接过辘轳把时,父亲就是这样关照的。老辈人的嘱托,就像那沉甸甸的水斗子,他接过了辘轳把,也就接过了一条规矩,做晚辈的,怎么好随意更改呢?
是啊!手中的辘轳虽给刘家人带来世代的艰辛,但这井水毕竟养育了他刘家数代人。在老人的思想里,规矩就是铁律,由不得更改。岁岁年年,转动不已的辘轳显示着他刘家人的意志和力量。虽然古井青苔,辘轳转悠,星转斗移,寒来暑往,日经风吹雨打,辘轳早已消磨了它的棱角,一身被井绳勒出圈圈凹痕。但他看在眼里心里十分舒坦,这分明是他刘家人在生活中勤快的见证。他觉得人越是勤快,老井越是不会干涸,反而愈淘愈旺,恰似人的生命,有志者愈勤奋、愈努力,愈是探测不到自身蕴有何等厚重的能量、何种雄浑的潜力。他打心眼里感谢辘轳给他刘家日子里带来的恩惠。
暑假期间,老人在京城上大学的三儿子带着对象回来了。他虽然没按照父亲的初愿,成为一个上好的庄稼人,但上大学,毕竟是争了庄稼人的面子。
三儿子知道这个时辰父亲一定在菜园里忙活,就没有领着对象径直回家,便直接一头折进菜园。果然不出所料,父亲正不紧不慢地摇着辘轳,小孙子照例还像从前那样掌畦,照例还是用那细嫩的嗓音喊起来:“爷爷,满了!改畦啰——”。他从父亲的手中接过辘轳把,一边与父亲说着贴己的话,一边拧着辘轳浇园。三儿子身子骨茁壮,一只手拧得辘轳咯啦啦地响。他一斗斗浇着,清凉的井水从井池流到垄沟里。水面上顶着一层白色的泡沫,从干燥的土地上流过,激得土地嗤嗤地响着。对象是城里的姑娘,自然没干过农村里的活,看水流过来,张着手不知怎样下铁锹、怎样改畦口。这儿铲铲,那儿铲铲,把铁锹粘成泥榔头一样。水冲破了垄沟,流了满世界。她手忙脚乱,累得出了一身汗。三儿子在一边看着,心里真想笑出来,说:“真是!小姐身子丫环命,离开咱庄稼人,还要饿死呢!”说着,两步迈过去,从对象手里抓过铁锹,说:“看我的!”他的两只手强壮得像老虎钳,钳起锹柄伸在水里涮去泥土,放在垄沟口上,轻轻掘入,掘起泥土放在垄沟里,把水流挡入菜畦,又轻轻一拍,说:“得!”
老人在一旁看着自家三儿子娴熟的动作,并像教小孩子学走路样教自己未来的媳妇干活,打心里觉得高兴。自小他就喜欢这个宝贝儿子,觉得他头脑灵活,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比他两个哥哥强上好几倍。老人本打算叫他接过家里的辘轳把,只可惜,三儿子考上了京城里学校,朝着更出息的方向去了,虽然没有成为一个上好的庄稼人,但老人还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老三和两个哥哥在一起时,他们谈起了辘轳的事。老三并没去劝父亲,却叫老人到城里去逛逛,说如今城里大变了,到处是时兴景儿。
老人答应了。第二天,由大儿子用自行车带着他进城,刚出了村又折了回来,嘱咐三儿子别忘了浇园,摇辘轳时悠着点劲儿。
傍晚回来,老人便急着去了菜园。往常,他大老远就能望到园子里那架辘轳,于是,来了精神,紧走几步。今天,菜园里的井沿上却空空荡荡,不见了辘轳架的影子。三儿子和未来的媳妇还有小孙子在掌畦,一条新修的小垄沟从不远处的机井哪儿伸向菜园子,清凌凌的水流进菜畦,一会儿就到了头。
老人长叹了一口气,蹲在了地上……
三儿子呢?望着老人嘻嘻地笑。未来媳妇的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小孙子瞧着三叔甜甜地笑。比对爷爷的笑还要甜许多呢……
……
三儿子扶上自己的父亲回家了。一路上,他对老人说了许多可心的道理。三儿子知道,父亲的思想陈腐,对老人这种对过去事情总有那怅然若失的情感应该抚慰,老辈子留下来的艰苦、朴实的遗风虽是宝贵的财产,但那“吱吱扭扭”的辘轳声,在与“嗡嗡”欢叫的机井马达声相比,毕竟是太古老了。
村里寿数最高的老人,抚摸着雪一样洁白的胡子,对又围在身边的几个村里的娃娃说:“这辘轳按于什么年代不知道了。记住,是今天拆的。刘家的老三,到底是没有白喝几年墨水啊!”
老人眼里流露出赞许的目光。是啊,辘轳像炊烟一样,作为乡村的标志性象征,虽然在刻有一个时代鲜明特性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使用辘轳的日子,还是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