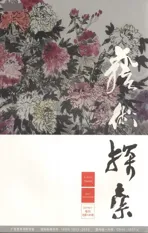古代漆器髹饰工艺经典著作《髹饰录》
2016-04-08长北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18
长北(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8)
古代漆器髹饰工艺经典著作《髹饰录》
长北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18)
[摘要]《髹饰录》作为中国古代唯一传世的漆器髹饰工艺著作具有经典意义,又因此而难以避免时代局限。漆器髹饰工艺传承的关键在于走出“文化虚热症”,走出把化工涂料机器工艺当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误区,将髹饰工艺还原为天然材料手工工艺,还原为生活的漆艺、民间的漆艺、民用的漆艺、诗意的漆艺。
[关键词]《髹饰录》;漆器;髹饰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
“漆器”之名出现于中国汉代,《汉书·贡禹传》下如淳曰:“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后来,人们把用天然漆髹涂,通过绘、刻、填、罩、磨、钩、贴、雕、镶、嵌等艺术手段装饰的器具,统称为漆器。也就是说,只有富于美感的髹漆之器,才能够称得上是漆器。今人有托袁枚之口赞清代扬州漆器名工卢映之漆器:“阴花细缬珊瑚明,赧霞隐隐东方生”①今人诗托名古人,见王世襄《扬州名漆工卢葵生和他的一些作品》,《文物参考数据》1957年第7期。,这两句诗,将漆器独特的材料美、工艺美,甚至将漆下朝霞般的光彩都形象地描绘出来了。中国传统的朱红、石青、石绿、金、银等入漆颜料,成就了天然漆漆器深沉典丽、含蓄蕴藉的色彩风范。天然漆精制厚髹于器物,红推光漆层红如珊瑚,黑推光漆层黑如乌玉,褐髹紫髹,莫不美感含蓄,光色柔和,退光则见古朴,推光则见莹亮,泽漆揩光则见细腻。透明漆下的图画,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是那样地神奇瑰丽,又是那样地深远无限,带给人无穷的遐想,因而更有韵外之致,更适宜表现虚灵化、情致化、若有若无、似与不似的诗的境界。中国漆器装饰万千,集中了古代工匠的智慧,曾经与丝绸、瓷器并列,享有极高的世界声誉。
古代漆器用天然漆或大漆加干性油髹饰。天然漆指从漆树割取的树汁,《本草纲目》引《说文》释漆:“木汁,可以髹物,其字象水滴而下之形也”,中国民间称其“国漆”“大漆”“土漆”“树漆”,日本称其“うるし”。华夏先民发现漆树汁液有高度的粘结性,涂刷于各种质材之上,便留下一层坚固、耐水、耐热、耐磨的保护膜。天然漆被用在宫殿、器具等的髹饰美化上,出土漆器埋藏地下几千年,即使木胎朽烂甚至无存,漆膜依然光泽如新。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华夏先民进一步发现了天然漆与颜料、干性油的亲和性,发现了它成膜前后,分别具有软质材料的可塑性和硬质材料的可雕刻性,发现了它无穷无尽的装饰潜能,发现了它厚髹之后独特的美。几千年来,髹饰工艺花样翻新,不断精进。借助引起料在漆胎引起不平,填漆磨显,可以出现苍苔、繁星、团花、松鳞等各种自然纹饰;反复髹漆到一定厚度,又可以雕刻山水花卉、楼台人物;漆面嵌贴金、银、螺钿、蛋壳,则成为更加华美的装饰;精制漆兑入金、银粉和颜料拍打成膜,则出现含金蕴银、浅红轻绿的靓丽颜色;利用精制漆快干起皱、稀释流动的性能,有画笔达不到的妙趣……大漆髹涂的艺术品,美感谦冲而温厚,含蓄而神秘,接近诗的意境和诗教传统,大漆艺术品的气质,正是中国人温柔敦厚气质的折射。农业社会以诗教为传统的中国古人,从精神内涵上穷究深研这一静观的、精微的、富有情感的艺术,顺应天时地气,利用天然美材,运之以巧手匠心,将漆器的装饰潜能发挥到了极致,使大漆髹饰工艺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表现力。中国漆器深沉典重的色彩基调和优雅静穆的审美趣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工艺美术,形成庄重、沉郁、含蓄的色彩基调和重咀嚼、重把玩的审美品味,影响了东方乃至西方的视觉艺术。
明代中国诞生了专门记录漆器制造工艺的著作《髹饰录》。“髹”指拿刷子蘸漆髹涂于器物,“饰”指装饰。①髹饰初见于《周礼·春官·駹车》。髹,出自《汉书·外戚传·第六十七下·颜师古注》:“以漆漆物谓之髹”,饰,指装饰。中国髹饰工艺传到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等东亚国家,经过东亚各族人民的创造,成为驰名世界的东亚特色工艺。《髹饰录》作为古代唯一传世的漆器工艺专著,对于中国乃至东亚大漆髹饰工艺传承的意义,如《圣经》之于基督教徒,《论语》之于儒门子弟,不待言说,东北亚艺术院校的漆艺专业都以读解《髹饰录》为必修课程。
一、《髹饰录》的经典意义
《髹饰录》作者系明代隆庆年间(1566~1572年)安徽新安名漆工黄成。书分乾、坤二集,计十八章、220条。半个世纪以后的天启年间(1620~1627年),浙江嘉兴名漆工扬明为之笺注。就是这样一本原文加笺注不足万言的专著,成为中国、东亚乃至世界髹饰工艺史上永远的经典。
《乾集》与《坤集》集首,作者以百余言概括说明全集要旨。《乾集》凡两章,《利用第一》记录制造漆器的材料、工具、设备,《楷法第二》强调髹饰工则并列举各类工艺可能产生的过失。《坤集》凡十六章,《质色第三》至《单素第十六》把漆器装饰工艺分为十四大类,逐类予以记录:《质色》章记录胎上做灰漆、糙漆以后素髹一色的髹饰工艺,《纹》章记录漆面以细阳纹为饰的髹饰工艺;《罩明》章记录在漆地或是装饰上罩透明漆的髹饰工艺;《描饰》章记录在漆面描写纹饰的髹饰工艺;《填嵌》章记录在彩漆、金银、螺钿纹饰上髹漆再磨显出纹饰,文质齐平的髹饰工艺;《阳识》章记录堆写出高于漆面线纹的髹饰工艺;《堆起》章记录堆起图画并加以雕刻的髹饰工艺;《雕镂》章记录以雕刻为手段表现浮雕图画的髹饰工艺;《戗划》章记录在漆面轻镂浅划出阴纹,阴纹内填入金银彩色的髹饰工艺;《斒斓》章记录将两种或三种装饰工艺谐调地并施于一件漆器的髹饰工艺;《复饰》章记录漆地已经装饰了纹样,其上再以另一门工艺制成花纹装饰的髹饰工艺;《纹间》章记录文质齐平的填漆、嵌螺钿、嵌金银工艺,与文质不平的戗划工艺、款彩工艺互为主次装饰;《裹衣》章记录胎上不做灰漆,而糊裹皮、罗或纸为“衣”的装饰工艺;《单素》章记录胎上不做灰漆的单漆、单油、黄明单漆、罩朱单漆工艺。除记录文法的十四章之外,《质法第十七》记录漆器制胎工艺,《尚古第十八》记录漆器的仿古、仿时与修复。《乾集》以天象设喻,《坤集》谈效法古人。作者以“乾”“坤”二字为上、下两集命名,当受《周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易·系辞上传》)的启示。论从哲学高度论述造物而又自成体系,中国古代考工著作除《考工记》外,《髹饰录》堪列第二。笔者试析《髹饰录》经典意义如下。
(一)系统确立了髹饰工艺的完整体系
《髹饰录》诞生在中国漆器髹饰工艺集大成的时期。它全面梳理和系统确立了中国漆器高峰时期的工艺体系,完整记录了明后期千文万华的漆器装饰,提出了较为合理的髹饰工艺分类法则。对漆器髹饰工艺的逐条记录,蔚成大观又体系完整、纲目清晰,使后世漆工既可以追宗溯源技有所本,又能据此生发不断创新;为各类漆器装饰定名并且分类,使后世文物工作者为古代漆器定名分类有所凭据;品鉴髹漆工艺良窳,切中肯綮,成为后世漆艺研究者、收藏者的重要参照;以阴、阳变化作为漆器装饰工艺分类的标准,尤为极富中国特色的创造。
《髹饰录》问世之后,大漆髹饰工艺不断成长衍变精进,大体是在《髹饰录》记录的工艺体系基础上变通、更新并且超越。有《髹饰录》这样一本经典在,人们就可以按照它所记录的髹饰工艺体系,全面恢复失传、失制的大漆髹饰工艺,重振中华漆文化的光荣传统;就可以在它记录的髹饰工艺体系基础上创新,并且按照其工艺体系归类记录新创髹饰工艺,使髹饰工艺生生不灭,光景常新。当代中国各地的漆艺家们,逐条仿效《髹饰录》记录的漆器髹饰工艺,创作出许多反映时代精神的新艺术品;日本、韩国漆艺家对《髹饰录》和髹饰工艺传统的尊重与敬畏,有过于中华子民。《髹饰录》将与中华历史、东亚历史同在,流淌在东亚文化、人类文化的长河之中。
(二)集中反映了天人合一的造物思想
《髹饰录》集中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的造物思想,天人合一是贯穿全书的思想主线。
《乾集》卷首提领语:“凡工人之作为器物,犹天地之造化……利器如四时,美材如五行。四时行、五行全而百物生焉。四善合、五采备而工巧成焉。今命名附赞而示于此,以为乾集。乾所以始生万物,而髤具、工则,乃工巧之元气也。乾德至哉!”中国古代,人们视天为最高信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辞上传》),工匠制造器物,正是对天地自然的模仿,工具、材料好比四时、五行,四时、五行化生万物,天时、地气、材美、工巧相合,再巧用五色,便造成器物。《乾集》开首,便凸显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造物观。
此集中,以天、地、日、月、星、风、雷、电、云、虹、霞、雨、露、霜、雪、霰、雹等天文景象,春、夏、秋、冬、暑、寒、昼、夜等时令交替,山、水、海、潮、河、洛、泉等山川景象比附制造漆器的材料与工具。如黄成以“天运”比附旋床,因为旋床像天一样圜形运转;以“日辉”比附金,因为金光好比阳光;以“月照”比附银,因为银光恰如月光;以“电掣”比附锉刀,因为用锉刀如风驰电掣;以“云彩”比附颜料,因为漆调颜料如五色彩云;以“水积”比附湿漆,因为漆是漆树的汁液;以“露清”比附桐油,因为桐油如露之清;等等。黄成说:“土厚,即灰……大化之元,不耗之质”,扬明注:“黄者,厚也,土色也。灰漆以厚为佳。凡物烧之,则皆归土。土能生百物而永不灭。灰漆之体,总如率土然矣”。土是鸿蒙初开时造物主赋予人类的物质,在五行之中居于首位,不管什么物质,焚烧以后都归于泥土,土能化生百物而永远不灭,做漆器用的灰,大抵像随处可见的黄土。用隐语指代制造漆器的材料工具,读者很难贸然理解,而一俟联想到“名”与“实”诸方面的关联,又不能不为其中微妙的联想叫绝。
《坤集》卷首提领语:“凡髤器,质为阴,文为阳。文亦有阴阳,描饰为阳。描写以漆。漆,木汁也。木所生者火,而其象凸,故为阳。雕饰为阴。雕镂以刀。刀,黑金也。金,所生者水,而其象凹,故为阴。此以各饰众文皆然矣。今分类举事而列于此,以为《坤集》。坤所以化生万物,而质体文饰,乃工巧之育长也。坤德至哉!”中国古人认为,万物都由地所化生,“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易·辞上传》)。《坤集》以阴阳五行为纲,为纷纭错综的漆器装饰工艺定位并且分类:凡是造漆器,地子是阴,纹饰是阳;漆器用漆来描写花纹,漆是木,木生火,描写的花纹凸起于漆面,所以是阳;雕镂的刀是黑金,金生水,雕镂的花纹凹陷于漆面,所以是阴。据此,不管什么漆器装饰都可以区分阴阳,阴阳相调才能化生万物,阴阳相调,漆器装饰才能臻于完善。
中国古代造物,讲求“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考工记》)。《髹饰录》上、下集提领语和每条内容,莫不强调工人制造器物当取法天地造化。作者以乾、坤大道阐述髹漆工则;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附会漆器工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人应该尊重自然,师法自然,利用自然材料造物,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造物思想。反思近百年来,人类对自然近乎疯狂地毁坏掠夺,人类遭到了自然的报复。今天,人类终于重新发现了中华先民的生存智慧——天人合一,觉悟到只有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才会给人健康的生命、轻松的生活和无尽的收获。天人合一成为疗救工业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
(三)严格树起了敬业敏求的工匠规范
黄成将工匠品德作为漆工入门之前必须知晓的工则,置于《髹饰录》第二章并予以高度强调。《楷法第二》涵盖两方面内容:《三法》《二戒》《四失》《三病》,从理论上树起了一个合格漆工的品德规范;《六十四过》则靠实论述髹饰工艺中可能产生的过失。《三法》中,“巧法造化”指师法自然,“质则人身”指漆器的胎、灰、布、漆当取法人体的骨、肉、筋、皮,“文象阴阳”指漆器纹饰依据阴、阳设定。作者一次次地提出取法天地造化的造物法则,甚至将它列入工则。《二戒》忌“淫巧荡心”,忌“行滥夺目”,也就是反对装饰过度,反对粗制滥造。扬明注“淫巧荡心”:“过奇擅艳,失真亡实”,注“行滥夺目”:“共百工之通戒,而漆匠须尤严矣”。作者以全书大半的篇幅记录林林总总的漆器装饰,同时反对过于奇巧、华而不实的时风,反对舍本逐末、虚有其表而实质偷工减料的制品,这在明中叶以来业已泛滥的造物奇巧之风气中,难能可贵。《四失》是“制度不中”“工过不改”“器成不省”“倦懒不力”,黄成要求工匠自始至终都要具备勤勉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制器前,要了解髹漆工则;制器中,要知过即改;制器后,要严格省察。第四失“倦懒不力”扬明注“不可雕”,语出《论语》“朽木不可雕”,则明显指向工匠的品行。作者认为,工匠品行最为重要,如果一个漆工连敬业精神都不具备,和他奢谈工则,又有什么用?由于学成手艺的不易和制造手工艺品给人带来的精神愉悦,古代工匠总是以虔诚的心态沉浸于造物,所谓“不问千日工,只问谁人做”,练好手艺成为工匠的精神需求。《楷法》章强调的,正是这种近乎宗教虔诚般的敬业精神。《三病》是“独巧不传”“巧趣不贯”“文彩不适”,扬明注“独巧不传”:“国工守累世,俗匠擅一时”,不仅反对技艺不肯传人的保守观念,更对工匠提出了要当国之名工、不当俗匠的期愿;“巧趣不贯”要求漆工注意艺术作品整体趣味的连贯;“文彩不适”要求漆工注意花纹色彩的适度。一件漆器,如果整体不和谐,装饰不适当,愈奇巧,愈与美感背道而驰。“贯”与“适”,正是艺术作品传达美感的关键。
除《楷法》章外,敬业、敏求的工匠精神贯穿全书。如黄成对洗盆和手巾的解释是“作事不移,日新去垢”(《利用第一》),语出《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扬明注为:“宜日日动作,勉其事不移异物,而去懒惰之垢,是工人之德也”,显然不仅在解释洗盆,更要求工人像每天盥洗一样,日日自省。书末讲仿效古漆器,仿效的目的是“以其不易得,为好古之士备玩赏耳,非为卖骨董者之欺人贪价者作也”,仿效他人之作,“有款者模之,则当款旁复加一款曰:某姓名仿造”(《尚古第十八》扬明注)。对比今天人心的浮躁与假货的泛滥,黄成、扬明严肃不欺世的态度,堪为工匠百世师、万世法。
(四)通篇体现了温古知新的创新精神
《髹饰录》诞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中晚明,西方思想随传教士来华进入中土,中日文化交流也进入民间频繁交往的崭新阶段,日本髹饰工艺前所未有地进入了中国。黄成与扬明一次次赞扬“傅金屑者”以“倭制殊妙”,“倭纸薄滑者好”,体现出开放的视野和开放的胸怀。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基于开放形势下的开放胸怀、开放视野、重振传统、锐意创新便成为全书主旨。中外艺术史上,不乏借“复古”创新的实例,如唐代古文运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等。鉴于明代漆器审美倒退、唐宋古法湮灭的现状,黄成于书末专设《尚古》一章,扬明更高张起了“温古知新”的大旗,“一篇之大尾名尚古者,盖黄氏之意在于斯。故此书总论成饰而不载造法,所以温古知新也”(《尚古第十八》扬明注)。黄成论剔红:“唐制多如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复有陷地黄锦者。宋元之制,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精致”(《雕镂第十》),推崇的是唐代剔红的古拙和宋元剔红的藏锋含蓄;扬明注洒金:“近有用金银薄飞片者甚多,谓之假洒金。又有用锡屑者,又有色糙者,共下卑也”(《罩明第五》),眼见洒金工艺比唐宋倒退,扬明褒贬指向明显。黄成反复夸赞“宋元之制”,提出“模拟历代古器及宋、元名匠所造,或诸夷、倭制等者”,目的是“为好古之士备玩赏”,亦即适应明中期以降收藏市场的需要,“不必要形似,唯得古人之巧趣与土风之所以然为主”(《尚古第十八·仿效》)一句最堪人们深思:学习古人,不要徒学形骸,而要琢磨古人的审美及其审美观形成的时代精神。为激励工匠创新,《髤饰录》除《质法》章记录制胎程序以外,各章确实“总论成饰而不载造法”,“不载造法”可以使工匠不为成法所拘,温习“成饰”,再创新法。温古知新的创新精神,是黄成、扬明与庸匠夜郎自大不思进取“一招吃遍天”的根本区别。面对今天大漆髹饰工艺传统的大范围丢失,《髹饰录》“温古知新”的创新法则,不正为丢弃传统的“创新”敲响警钟么?
二、《髹饰录》的时代局限
作为古人著作,《髹饰录》不可能不打上时代印记。
(一)思想局限
《髹饰录》思想局限举其首者,在于对民间诉求的忽视。髹饰工艺是一项广泛服务于民众生活的手工技艺,不仅用于髹饰漆器,还长期被运用于琴瑟、民具、家具、建筑构架等的髹饰。《髹饰录》却把髹饰工艺的功能定位在迎合江南“好古之士”玩赏之上,明确声明意在尚古。因此,全书倾力于各种装饰漆器工艺的记录,不记民间最为常见的油光漆髹涂等家具髹饰工艺,将民具髹饰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单素”工艺放在《坤集》末尾略笔带过。而恰恰是在民间,髹饰工艺才有着健康质朴、生生不灭的活力。唤起群体的推力,使大漆髹饰工艺回归民间、回归生活,这是笔者在系统梳理漆器髹饰工艺的同时,整理古琴、民具、家具、建筑构架等髹饰工艺的苦心所在。
《髹饰录》全书中,黄成过多地套用经史名句等与工艺无关的文字,也使叙述蒙上了层层面纱。如黄成对旋床的解释是“有余不足,损之补之”,语出《老子·七十七章》“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对湿漆的解释是“其质兮坎,其力负舟”,语出《易·卦传》“坎为水”、《庄子·逍遥游》“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黄成将曝漆盘并煎漆锅命名为“海大”,解释为“其为器也,众水归焉”,语出《庄子·秋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至于“模凿、斜头刀、剉刀”像河图上的天数与地数有五十五之多,便托其名为“河出”;“笔觇、笔觇”像洛书对角的数字相加都得十,中央的数字是五,便托其名为“洛现”,则简直是牵强附会了。套用经史名句是宋《营造法式》以来形成的中国古代造物著作传统。明中晚期,匠而能雅、匠而能士成为时髦风气。黄成身为工匠,淹通经史,自是一件儒雅之事。遗憾的是,工匠多不通经史而学者多不通工艺,如此用典,给双向传播设置了阻隔和障碍。
《髹饰录》中,黄成过多地以天文山川时令交替附会制造漆器的材料、工具与设备,使不明就里者不知所云。如《乾集·利用第一》写装饰漆器的材料“金”,黄成托名为“日照”,解释为“人君有和,魑魅无犯”。这些文字,与髹饰工艺毫无关系,冲淡了文字的主旨,幸有扬明作注,才将漆器用金的作用点出。《利用第一》写装饰漆器的材料“银”,黄成托名为“月辉”,解释其为“宝臣惟佐,如烛精光”,也与髹饰工艺毫无关系,幸有扬明作注,才把漆器用银的作用点出。《髹饰录》不往简单务实去说,偏偏往虚处说,绕远了说,绕到君臣伦理大道上去说,绕了很大的圈子才说到工艺,却偏偏寥寥数语点到即止。后世漆工视《髹饰录》为天书,后世学者长期远离工艺引经论典去解释《髹饰录》,其由头在于原著文本的艰深。
(二)材料局限
《髹饰录》原作者黄成与最早笺注者扬明,生当交通不便、信息相对闭塞的古代。其时考古学还没有诞生,传世文物有限,加上作者视野受限,因未闻、未见而产生的错误与缺点也就在所难免。如《髹饰录》扬明序“漆之为用也,始于书竹简”,其实,早在文字发明以前的新石器时期,先民已经在木器上涂漆。《髹饰录》扬明序“盖古无漆工,令百工各随其用。别有漆工,汉代其时也”,显然因为《考工记》没有记载髹漆之工而汉代典籍中有了关于漆工的记载。而现代考古成果证明,湖南长沙战国墓出土的漆器上已经刻写有工匠名款。王国维《古史新证》提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进一步发挥说:“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考古学诞生之前,明代人是没有办法掌握“二重证据”的,更是没有办法取异族故书、外来观念进行释证、补证和参证的。今人不能苛求古人。
20世纪以来,中国湖北、湖南、贵州、四川、江苏、浙江、安徽、山东、陕西、河北、广东、甘肃、新疆乃至境外蒙古、朝鲜等地出土了大量战国秦汉漆器,其中立雕与透雕胎榡,针刻、铜扣等工艺,均为黄、扬二氏未曾闻见而未见载于《髹饰录》。《髹饰录》问世以后,许多漆器髹饰工艺如福州薄料漆工艺、台花工艺、仿青铜工艺、仿窑变工艺,扬州雕漆嵌玉工艺、漆皮雕工艺,重庆平地研磨彩绘、高漆研磨彩绘工艺以及现代箔粉研绘、罩明研绘、嵌蛋壳工艺,等等,更为《髹饰录》无法加载。
(三)文本局限
作为记录视觉艺术的著作,《髹饰录》没有插图,文字过于简略。笔者逐字记数,黄成原文加标点仅5 597字,扬明笺注加标点6 510字,原文加笺注加标点共计12 107字。减去笔者所加的标点,原著加原笺共约万字。以如此简约的文字记录千文万华的漆器装饰工艺,只能点到即止,无法言述具体。这可能因为,书是写给业内工匠看的。古代信息闭塞,工匠们很难知道历朝历代曾经流行过、外地市面正在流行着哪些漆器装饰。他们需要见多识广的人帮助他们学习传统,翻为新样。至于具体工艺,千变万化,因人、因地而异,得道与否,全靠工匠自己在实践中体悟,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今天,谙熟漆艺、无须讲解具体工艺的专职漆工少了,爱好漆艺、希望了解大漆文化的业外学子多了,数千言没有插图“不载造法”的经典,便见出文化传承的不足。
《髹饰录》章节顺序尚可推敲。漆器不管如何装饰,都要先制造胎骨,黄成将记录制胎工艺的《质法》章置于记录装饰工艺的各章之后,与漆器工艺流程不合。《楷法·六十四过》专门记录制造漆器过程中的过失,列于论述制作之理的《楷法》章,与章题不合,且在尚未展开对漆器制造过程的论述之前,先论述漆器制造过程中的过失,为时过早,读者很难凭空理解过失形态。《描饰》章工艺共同的特点是:描饰之后不再罩漆研磨推光“于文为阳者”,黄成将“于文为阴者”的“描金罩漆”条列于《描饰》章,与自己确定的分类标准不合。百宝嵌虽然五彩斑斓,究其工艺,与《雕镂》章“镌蜔”工艺都属于雕刻镶嵌,黄成将《百宝嵌》置于“二饰、三饰可相适者而错施为一饰”的《斒斓》章,又与自己确定的分类标准不合。
《髹饰录》条目次序比较混乱,一些条目内容重出。如《利用》章记录过于散乱,理应将材料、工具、设备各自归类,以助读者总体把握。黄成记“山生,即捎盘并髹几”,把作为工具的捎盘与作为设备的髹几合为一条,更属眉毛胡子一把抓。《质色》章黄成于《合缝》条谈“捎当”工艺,有承接下文之意;《捎当》条又谈合缝工艺,条目内容交混。“衬色”本是螺钿漆器制作的一道工序,不是“二饰、三饰可相适者而错施为一饰”,黄成于《填嵌》章单列“衬色蜔嵌”条,已属牵强,于《斒斓》门又列“衬色螺钿”条,既属重出,也造成分章概念的混乱。
《髹饰录》一些概念未尽清晰。如黄成先已言“黄髹,一名金漆”,后又言“罩金髹,一名金漆,即金底漆也”。“罩金髹”“金漆”“金底漆”其实各有所指,尽管漆器业内“金漆”称谓混乱,同一本书里,作者理应注意区别。黄成又说“描金,一名泥金画漆”,其实,描金的手段有贴金、上金、泥金、清钩描金等,不主要是也并不限于泥金画漆。“识文”本是《阳识》章中识文描金、识文描漆、揸花漆的前期工艺,黄成于此章另立“识文”条,将“识文”界定为“有通黑,有通朱”,扬明补注为“以灰堆起”“花、地纯色”。也就是说,黄、扬二人都以同一名词指向不同内涵的属、种概念,使此章各条概念交叉含混。
扬明笺注大大丰富了《髹饰录》的内容,升华了《髹饰录》的工艺价值,但也无庸讳言,有误注或注窄、注宽之处。如“揩磨之五过·毛孔”条下扬明注“漆有水气及浮沤不拂之过”,所注不属于“揩磨”过失而属于上涂漆过失,也就是说,注文与原文不合。《描饰》章扬明注“稠漆写起,于文为阳者,列在于此”,而《描饰》章包括“描金、描漆、漆画、描油”数条,并不都是“稠漆写起”,也就是说,注文较原文外延偏窄。《阳识》章扬明注为“其文漆堆,挺出为阳中阳者,列在于此”,而从黄成下文看,《阳识》章不仅包括用漆堆写出花纹的工艺,还包括用漆灰堆起线纹的工艺,堆写的花纹上,有加之以描金、描漆等阳纹,也有加之以戗金、刺花等阴纹,并不都是“其文漆堆,挺出为阳中阳者”,注文外延又较原文外延偏窄,扬明于此章“识文”条注“以灰堆起”,自己将章首注文推翻。《雕镂》章“堆红”条下,扬明于黄成“灰漆堆起”“木胎雕刻”两种工艺之外,增补“漆冻脱印”。《堆起》章“隐起描金”条下已注“漆冻模脱者”,《雕镂》章“堆红”条下又注“漆冻脱印者”,同类工艺注于两章,见分章概念的交叉与含混。如果“漆冻脱印”归于《雕镂》章能够成立,“漆冻模脱”何以又注于《堆起》章“隐起描金”条下?依笔者拙见,在木胎上浮雕以后罩以朱漆宜归于《雕镂》章,用灰漆堆起或用漆冻脱印浮雕图像宜归于《堆起》章,用漆冻脱印线型锦纹,则宜归于《阳识》章。《斒斓》章“金理钩描漆加蜔”的特点是有金线而无金象,扬明却将“为金象之处,多黑理”注于此条,是为误注。《复饰》章黄成所举,有二饰重施,也有三饰、四饰重施,扬明注为“二饰重施”,偏窄。黄成于《裹衣》章已列“皮衣”一条,《质法》章“布漆”条下,扬明却注“古有用革、韦衣”,将作为装饰的“衣”注于制胎工艺中的“筋”即“布漆”之下,混淆了“衣”与“质”的根本区别。白璧微瑕,扬明笺注对于后人理解《髹饰录》,对于髹饰工艺的传承功莫大焉。它将与《髹饰录》永远共存于髹饰工艺史册。
古代信息闭塞,漆工各操方言而识字者少,造成漆器业中大量地方性术语和一词多义、多词一义现象的存在,《髹饰录》作者著书之时,正面临这样的困境。概念含混,是中国漆器制造业长期存在的通病。面对髹饰工艺的大量专门词语、地方词语,业外人士如堕五里雾中,业内人士想了解髹饰工艺体系的枝经肯綮,非花十年八年绝难有成。有感于此,笔者早就呼吁:有必要建立漆艺“共同语”,按照《髹饰录》已经创立的工艺体系梳理髹饰工艺,以适应新人学习和文化交流的需要,[2]切不可各人生造工艺名词,使本已复杂的工艺概念愈趋复杂混乱。
三、《髹饰录》诞生的时代背景
明初,太祖向全国征集十余万工匠聚居于南京城南,由此带来商贾的云集和人口的猛增,也带来城南密集的商市。南京钟山下建有漆园,南京龙江建有规模庞大的宝船厂,成为永、宣年间郑和七下西洋的物质储备,也成为髹饰工艺在江南空前兴盛的物质储备与技术铺垫。朱棣迁都之后,江南手工业和商业更为迅猛地发展起来。北迁的王朝经济积累日渐丰厚,工艺造物竭尽装饰。宫廷玩好之风流播民间,京城“至内造如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坊之珐琅,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内市(在今北京景山正门与神武门间)重价购之”(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江南文人和富豪之家也竞相收藏时玩,“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之大贾。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沈德符《敝帚斋余谈》)。宫廷以华为美的审美导向与江南收藏之风,使明代中晚期工艺品装饰愈来愈奇巧,工艺愈来愈繁琐,“今吾吴中,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其势尚未已也”(王世贞《觚不觚录》)。漆器、瓷器、金属工艺品、织绣工艺品中数量可观的一部分,背离了它作为生活用品的根本用途,装饰化、陈设化、纯艺术化了,以至西方人认为“装饰艺术才是明朝艺术最大的特长”[3]。时风所向,漆器造型奇巧,工艺翻新,到了“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识”(《髹饰录》扬明注)的地步,一些漆器脱离生活实用,走向了装饰的极端。黄成以《斒斓》《复饰》《纹间》三章,记录以多种工艺装饰漆器的时风,正反映出明中叶以降装饰风的弥漫和漆器审美的倒退。
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带来了西方文化。面对西方务实的思想和实用的器具,晚明士子开始反思儒家空言心性的弊端,掀起了一股实学思潮。思想的活跃带来学说的活跃,晚明学说著作蜂起,中国古代最务实、最富于创造精神的工艺论著,集中出现在晚明。如果说明代以前有限的造物典籍与哲学接近而离科学较远,明后期著书走向了调查实证;如果说六朝开创了中国艺术理论的形而上性格,明后期至清代,中国艺术论著从形而上走向了形而下,从坐而论道走向了对材料技法等的靠实记录。
徽州古称新安。在明代,徽州人就以经商名扬天下,晚明“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谢肇淛《五杂俎》卷四)。美丽的山川、悠久的历史、丰厚的人文积淀以及徽商的财力支撑,孕育出了包括新安理学、新安画派、徽州版画、徽州建筑、徽州园林、徽州盆景、徽剧、徽墨、歙砚在内的一整套徽州文化,也孕育出了以剔红、软螺钿为代表的新安漆器。《新安志·卷一》记:“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苏州府志·卷二十》记:“漆作,有退光、明光,又剔红、剔黑、彩漆皆精,皆旌德人为之”。清代徽州人大量进入江南和周边各省,明后期以来江南乃至江右漆器生产的高潮,与徽州人的推动有直接关系。黄成号大成,生当文化高潮之中的徽州,生前作品售价便“一盒三千文”(吴骞《尖阳丛笔》),晚明人记:“新安黄平沙造剔红,可比园厂,花果人物之妙,刀法圆滑清朗”(高濂《燕闲清赏笺上·论剔红倭漆雕刻镶嵌器皿》)。受徽风濡染,黄成能通经史,见闻广博,于是以自身经验加之以耳闻目见,写成泽被千古的《髹饰录》。
浙江嘉兴西塘,水路四通八达,农、工贸易兴旺,元后期便以制造漆器名闻遐迩。西塘人彭君宝(明人笔记又记作“彭均宝”“老君宝”)“戗山水、人物、亭观、花木、鸟兽,种种臻妙”(曹昭《格古要论》)。永乐时,西塘漆工名达禁中,宫廷作坊果园厂剔红上承元后期嘉兴剔红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的风格,成就了中国剔红漆器的巅峰。扬明号清仲,生当天启间的嘉兴西塘,或为西塘扬茂后裔。受漆器之乡氛围的濡染加之以家学渊源,方能为《髹饰录》笺注并且作序。
《髹饰录》诞生在明后期这样一个时代动荡变化的关捩,所以,其《乾集》立意、造句、遣词带有浓重的哲学色彩,《坤集》落脚在分门别类的装饰工艺,从形而上走向了形而下。《髹饰录》的诞生,是明后期文化氛围使然,是明后期漆器装饰工艺集大成使然。《髹饰录》之前,北宋李诫《营造法式》卷第十四、卷第二十五、卷第二十七记录了大木作髹饰工艺中的描油与油饰;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全面记录了制琴之法;程大昌《演繁露》、邢凯《坦斋通编》、元代佚名《画塑记》有关于髹饰工艺的片言只句。宋以后,明代袁均哲辑《太音大全集》、张大命辑《太古正音·琴经》、蒋克谦辑《琴书大全》等琴书记录了制琴工艺和制漆工艺,内容有抄袭宋人、有相互抄袭,其中制漆、退光、推光工艺等,可补《髹饰录》之未备;清代祝凤喈《与古斋琴谱》真正面向漆工调查记录,工具图例尤见珍贵;清代匠作则例在开列油作工料或佛作工料等的同时,提到相关的髹饰工艺程序。笔记类著作如元末陶宗仪《辍耕录》,明代沈周《石田杂记》与高濂《遵生八笺》,曹昭《格古要论》,王佐增补《新增格古要论》,朗瑛《七修类稿》,李东阳《怀麓堂集》,陈继儒《妮古录》,张岱《陶庵梦忆》,张应文《清秘藏》,屠隆《考盘余事》,都穆《听雨纪谈》,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以及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清代高士其《金鳌退食笔记》,阮葵生《茶余客话》,吴骞《尖阳丛笔》,钱咏《履园丛话》,谢堃《金玉琐碎》及20世纪邓之诚《骨董琐记》等,各有关于髹饰工艺的零星记录,《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漆工部》《太平御览·卷七六六·杂物部一》等类书各汇集有千字左右历代关于漆、漆器、漆工的文字记录。论所记髹饰工艺的专业性、系统性、体系完整性,以上都无法与《髹饰录》相比。再往上溯,纵使五代的《漆经》①《漆经》,五代朱遵度著,久佚,仅存书名,见载于《宋史·艺文志》。没有失传,也不可能成为髹饰工艺史上首屈一指的经典著作。因为五代髹饰工艺尚欠丰富,作者朱遵度无法预见明后期千文万华的髹饰工艺。是时代把《髹饰录》推向了古代漆器髹饰工艺经典著作的位置。
结语:漆器髹饰工艺向何处去
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艺术品市场迅速崛起并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古代漆器成为拍卖市场上的新宠。2009年11月,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卖乾隆皇帝所用的剔红漆盏托,以高达近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2010年12月,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康熙款百宝嵌漆盒,起价达600万;2011年6月,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清代宫廷用描金屏风一堂,审美极其陈腐平庸,起价高达650万。旧富新贵们纷纷注目古代漆器,注目未为化工涂料染指的手工剔红,仿古造假成为时风,手工剔红作为时玩,价格百倍上窜,产品供不应求,原产地木雕工人纷纷改业剔红,销售市场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与此同时,手工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热捧,大漆髹饰工艺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漆器髹饰技艺、北京金漆镶嵌髹饰技艺、北京雕漆髹饰技艺、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厦门漆线雕髹饰技艺、成都漆器髹饰技艺、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宁波朱金木雕技艺泥金彩漆技艺与硬木挖嵌擦漆技艺、天台山干漆夹纻技艺与造像髹饰技艺、徽州菠萝漆髹饰技艺、绛州剔犀髹饰技艺、波阳脱胎漆器髹饰技艺、楚式漆器髹饰技艺、潍坊嵌银髹漆技艺、阳江漆器髹饰技艺、重庆漆器髹饰技艺、天水漆器髹饰技艺、屯溪漆器髹饰技艺、彝族漆器髹饰技艺等,先后三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遗憾并令人心痛的是,大批化工涂料工业产品造成了对大漆髹饰工艺的毁灭性杀伤。一方面,作为商品的漆器大失传统格法;一方面,商业的、功利性的“漆画”失去了“漆”自身的独立品格,沦落为不见传统由头的化工涂料展板。各地漆器工艺与风格迅速靠拢,轻浅的浮光、靓丽的颜色、省工换料急火赶制的作品代替了大漆漆器谦冲温厚、静穆优雅、含蓄神秘的东方气质,漆器失去了原本的良家面目,一窝蜂追求浮华庸俗。当代中国漆器的总体状况是外华内贫,商业氛围的轰炸和不适度的炒作,妨害了手工艺人沉潜静心钻研技术、传承技术。
近百年来,人类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人们不得不反思化工涂料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对工人身体造成的极大伤害,渴望传统漆器的复归。大漆髹饰工艺才被世界人士承认为漆艺,化工涂料工艺则被世界人士嘲笑为伪漆艺。有鉴于此,笔者曾经提出“绿色漆艺”的观点[4],呼吁国人从保护环境、珍爱生命出发,禁止生产化工涂料餐具,限制生产污染环境的化工涂料艺术品,有意识地、哪怕是局部地、点滴地回归天然材料,不仅是对东亚髹饰工艺传统的尊重、对自然的尊重,更是对人类自身生命的尊重。绿色漆艺也就是大漆髹饰工艺才是真正的漆艺。回归绿色漆艺不是复古,而是人类从工业文明回归生态文明新形势下髹饰工艺的新生。笔者切望国人走出“文化虚热症”,走出把化工涂料机器工艺当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误区,当前急需要保护、扶持与抢救的,是原产地天然材料的手工工艺,不是化工材料机器工艺。享受国家津贴的大漆髹饰工艺传人,理应坚守一线传承,坚守天然材料,坚守大漆髹饰工艺。工艺传人的任务不是创新,而恰恰是“守旧”。非传人也应该以传统为源头活水去守正创新,而不是省工换料、偷工减料,挂着羊头去销售狗肉,把传统当污水随意泼弃。
漆器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漆器髹饰工艺体系积淀着中华民族农耕生活八千年的文化精髓,其中贮满了中华民族的光荣记忆。大漆漆器与人亲和的、耐得品味的美,是粗糙的、雷同的、没有情感的、快买快弃的化工涂料工业产品所永远无法替代的。在大漆髹饰工艺日趋粗陋单调的急迫形势之下,按照《髹饰录》已经确立的工艺体系,全面完整地抢救、复原、传承大漆髹饰工艺,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工艺自身。大漆髹饰工艺的丰厚积淀,是依托于漆器而存在的。漆器髹饰工艺又主要是依托于木胎漆器皿与夹纻胎漆器皿而存在的。传承大漆髹饰工艺,首先要从难度最高的木胎质法漆器皿与夹纻胎漆器皿做起。作为东亚文化的原生地,中国理应肩负起完整梳理大漆髹饰工艺体系、完整传承大漆髹饰工艺体系的重任。
笔者相信,国人会从错把化工涂料伪漆器当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迷障中走出来,从珍惜生命、珍爱环境出发,重视并且保护大漆资源,重视并且开发大漆文化,努力使高污染机器工业向着绿色手工艺渐次回归,将髹饰工艺还原为天然材料手工工艺,还原为生活的漆艺、民间的漆艺、民用的漆艺、诗意的漆艺,还原到器皿和民具、家具、古琴、建筑构架、室内装饰与陈设等的髹饰。当国人重新认识大漆髹饰工艺庞大体系无与伦比的价值、自觉远离化工材料工业“漆器”之日,人们会反转身来审视有着八千年深厚积淀的大漆文化,大漆髹饰工艺体系会在涅槃之后获得全面新生。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47.
[2]长北.概念混乱,漆艺专业术语亟待确定[J].中国工艺美术,1989(4):7.
[3]苏立文.中国艺术史[M].曾堉,等,编译,台北:南天书局,1985:246.
[4]长北.“绿色漆艺”——中国漆艺的守望[J].美术观察,2008(11):23.
(责任编辑、校对:徐珊珊)
Review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XiuShiLu
Chang Bei
[Abstract]As the only classical literature on lacquer techniques in ancient China, Xiushilu occupies a unique place of its kind though not without era localization. The key to inheritance of lacquer ware techniques lies in shedding the "False Culture Conservation Mentality" which takes chemical paint and machining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restoring natural materials and handicraft to lacquer ware.
[Key Words]XiuShiLu; Lacquer Wa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作者简介]长北,本名张燕(1944~),女,江苏扬州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漆艺、工艺美术史、艺术史。
[收稿时间]2015- 10- 28
[文章编号]1003- 3653(2016)01- 0073- 09
DOI:10.13574/j.cnki.artsexp.2016.01.011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