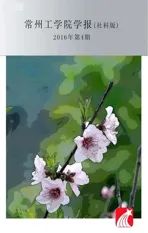略论《诗薮》之诗体流变观——以七言体为例
2016-03-28赵鹏程
赵鹏程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略论《诗薮》之诗体流变观
——以七言体为例
赵鹏程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诗薮》一书体现了胡应麟的诗歌流变观,是明代晚期一部重要诗歌理论著作。文章以七言体为例,兼及古体七言歌行及其所影响的七言律诗,分析胡应麟《诗薮》之诗体流变观。分别考察“辨体”与“体变”、古体七言之变、近体古体七言之变,分析《诗薮》诗体流变观之复杂性与宏观性,运动性与规律性。
七言体;胡应麟;《诗薮》;诗体流变观
《诗薮》是明代晚期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该书“本着格调说的观点对历代诗歌的流变与发展及其艺术成就作了详尽的评述”[1]24,体现了胡应麟的诗歌流变观。关于诗歌流变的观点,《诗薮》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夫诗,心声也。无古今一也。顾体由代异……”[2]序言可见,关于诗歌体式的讨论,是胡应麟诗歌流变观的一个重要方面。《诗薮》在内编中即以诗歌体式为纲,分述古体、近体,该编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体以代降”“格以代兴”的观点。在此,笔者以七言体为例,略及古体七言歌行及七言律诗,分析胡应麟《诗薮》之诗体流变观。
一、“辨体”与“体变”
“辨体”是明代诗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胡应麟诗学理论的重点。要研究胡应麟对于七言体诗歌流变的认识,首先应对诗歌体式加以考察。考察胡应麟的诗论可以发现,胡应麟对古今诗体流变有相对系统的认识,但这一认识往往具有模糊性与概括性。
从《诗薮》一书的具体论述来说,其分类较为宽泛,对于相关概念的论述往往具有概括性。这样的论述可以较好地概括某一阶段、某一诗歌体式的流变,以充满跳跃性的论述包容古今,使之具有形象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跳跃性的论述往往是零散的,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相关概念的模糊,古体七言即是其例,所谓“七言古诗,概曰歌行”[2]41。由此可见,这种分类是极为宏观的,具有概括性,既言“七言”,有字数之别,又言“古体”,涉及古近之别。葛晓音先生认为,“歌行样式层次的流动性使这种分野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差异,从而使前人得出了‘七言古诗,概曰歌行’的模糊判断”[3]。
从全书体例上说,胡应麟所论诗体,从古体、近体两方面展开,古体之下分杂言、五言、七言,近体之下分五言、七言、绝句。胡应麟这一分类方法具有概括性,对于了解古体内部流变、近体内部流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此法将古体、近体分别置于不同的章节中。在这种体例限制下,胡应麟并没有对古近体之间的流变作整体表述,仅有“古风不能不变而近体”[2]23这样散见的认识,具有模糊性。因此有必要对其诗歌流变加以整体考察。在胡应麟诗论中,古近体七言之论较为明显地体现了其诗体流变观的特点,笔者以七言为例加以考察。
二、复杂性与宏观性:以古体七言之变为例
《诗薮》对于歌行概念认识的模糊性不仅与歌行体本身的流动性有关,也与其起源的多样性有关。多样的起源既造成了其起源的复杂性,也使其拥有了复杂而模糊的内部结构。从歌行源头上看,胡应麟曾指出“骚实歌行之祖”[2]6,进而加以宏观判断,指出“《离骚》变而为五言,五言变而为七言”[2]1这样一个流变过程。胡应麟在模糊地概括之外,也曾有意识地对歌、行加以简单辨析,在这一辨析中,涉及歌、行之变,表现出了他对于古体七言演变的一些认识,他认为:
“歌之名义,由来远矣。南风、击壤,兴于三代之前……皆七言古所自始也。汉则安世、房中、郊祀、鼓吹,咸系歌名,并登乐府。或四言上规风、雅,或杂调下仿离骚,名义虽同,体裁则异。孝武以还,乐府大演,陇西,豫章,长安,京洛,东、西门行等,不可胜数,而行之名,于是著焉。较之歌曲,名虽小异,体实大同。至长、短、燕、鞠诸篇,合而一之,不复分别。……则知歌者曲调之总名,原于上古;行者歌中之一体,创自汉人明矣。”[2]41
可见,胡应麟对于歌、行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一个初步认识,所谓“行者歌中之一体”,行与歌“名虽小异,体实大同”。但这一认识是在行之名为人所称道之后,即所谓“孝武以还”之世。 向前追溯,汉武以前还是以歌作为主导,而歌这一诗歌体式内部又有区别,胡应麟认为汉代之四言与杂调“名义虽同,体裁则异”,可见四言与杂调之间有别,二者之别有其复杂性,而杂调本身亦有其复杂性。胡应麟对歌行的源头作了阐释,从远源来看,歌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歌谣,对于这样一个远源,胡应麟作出“七言古所自始也”的宏观性论述;而从近源上看,对歌行影响更为深刻的是汉代乐府,所谓“创自汉人”。
在谈及歌行起源之后,胡应麟又谈到了七言歌行的起源问题,他指出了纯用七字诗体之起源:
“今人例以七言长短句为歌行,汉魏殊不尔也。诸歌行有三言者,……四言者,……五言者,……六言者,……纯用七字而无杂言,全取平声而无仄韵,则柏梁始之,燕歌、白纻皆此体。自唐人以七言长短句为歌行,余皆别类乐府矣。”[2]41
胡应麟对歌行体与杂言的关系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所谓的“概曰歌行”只是一个大致的认识,并不是单纯地将七言与歌行划等号。在像上述引文这样的具体论述中有对于歌行多样性的认识,他对于歌行之三言、四言、五言等形式已有宏观把握。更重要的是,胡应麟认识到了歌行在盛唐以后的一些变化。《诗薮》中关于歌行变迁的论述屡见不鲜。例如,《诗薮》中有关于汉魏歌行与盛唐歌行的差异的论述:
“白石歌浑朴古健,汉魏歌行之祖也,易水歌遒爽飞扬,唐人歌行之祖也。”[2]42
“杜兵车、丽人、王孙等篇,正祖汉魏,行以唐调尔。”[2]42
“李杜歌行,广汉魏而大之,而古质不及,卢骆歌行,衍齐梁而畅之,而富丽有余。”[2]47
考察这些内容可以发现,胡应麟已认识到汉魏歌行与唐代歌行在风格上的差异,这一差异显然是极为复杂的,而胡应麟各以四字概括之,所谓汉魏以“浑朴古健”为祖,唐人以“遒爽飞扬”为祖。与此同时,胡应麟认识到了卢骆之时歌行延续齐梁之富丽,可见,他既注意到了异代之异,也注意到了同代之异,他对歌行体流变的复杂性有自己的认识。
《诗薮》论及李杜歌行时有“正祖汉魏,行以唐调尔”以及“广汉魏而大之”的论述。可见,在胡应麟看来,虽然唐代歌行有所变化,但还是从“祖汉魏”“广汉魏”出发的,这一点与中国古典诗学中“本色辨体”的观点是相通的。
胡应麟关于诗歌流变的讨论并不只是简单地宏观概括,而是在总论性质的概括之后作具体论述,这些论述往往是零散的,这与其诗话属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些论述中,胡应麟一方面对歌行的起源加以分析,但这些分析往往是散见的,具有复杂性;另一方面,就歌行体的流变而言,胡应麟认识到了其流变过程中重要的时代节点,以汉魏比之唐,大跨度分析,具有宏观性。
三、运动性与规律性:以近体古体七言之变为例
胡应麟论七言古体,以七言歌行为主,然而七言并非仅有古体,古体之外,尚有七言律诗等体式。胡应麟曾论到“七言变而为律诗”[2]1,这一点在《诗薮》一书中表现得并不明显。《诗薮》内编论及诗歌体式,将诗歌分作古体、近体。“在探讨诗学问题时将诗歌区分为古体与近体,是明人比较普遍的做法。”[4]67就全书体系来说,《诗薮》一书中并没有为讨论古体、近体之间的流变提供充足的空间,很多认识体现在一些具体的论述中。这样的探讨也造成了对于古体、近体之间关系的认识既模糊又零散,只是简单提到“古风不能不变而近体”[2]23“七言变而为律诗”[2]1,而对古近体七言之间的流变并没有整体的论述。但是,这些零散论述中也包含着胡应麟对于古体、近体流变的认识,在此不妨试举几例加以梳理。
《诗薮》内编卷五开篇云:
“七言律于五言律,犹七言古于五言古也。……五言律宫商甫协,节奏未舒。至七言律,畅达悠扬,纡徐委折,而近体之妙始穷。”[2]81
“七言古差易于五言古,七言律顾难于五言律,何也?……”[2]81
胡应麟将七律与五律类比,又五古与七古类比。考察这些论述可以发现,《诗薮》关于诗歌体式流变的论断受古近体分类的影响比较明显。胡应麟认识到从五言律到七言律这一变化,并将五言古体与七言古体的关系与之作比,但对于七言古体与近体的关系并没有作相对具体的论述。
而七言古体与近体之间确实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葛晓音曾引述赵昌平《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渊源》一文的研究成果,指出七律脱胎于赋律化的歌行这一结论令人信服。她指出:“盛唐七律有一种特殊的声调美,与乐府歌行比较接近,其根源就在于七律本来起源于乐府,和歌行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5]其后,葛晓音又从体调特征上加以论述,指出“七律源于乐府歌行、形成于应制体的背景决定了盛唐七律的声调风格特色,同时也导致其结构和表现方式的单调少变化”[15]。而《诗薮》于七言律诗与歌行的关系较少论及,但对其体调特征却有一定的论述:
“初唐七言律缛靡,多谓应制使然,非也,时为之耳。此后,若早朝及王、岑、杜诸作,往往言宫掖事,而气象神韵,迥自不同。”[2]81
因此,从体调特征上来说,胡应麟认识到了七言体调之繁缛并非由应制造成,而是有其历史性的原因,乃是“时为之耳”。但是,胡应麟在此并未提及歌行对初唐诗风的影响。胡应麟没有从体调上对歌行与七律的关系加以讨论,而是以“时”解释了诗歌体调变化的原因,他指出:
“四言不能不变而五言,古风不能不变而近体,势也,亦时也。然诗至于律,已属俳优,况小词艳曲乎……”[2]23
胡应麟指出了古体、近体之间的流变关系,并对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他再次强调这一趋势,指出“势也,亦时也”。对于所谓“势”,涂光社先生认为,“‘势’常常体现着事物变化的趋势和规律”[6]257。这一趋势与其对四言、离骚、五言、七言、律诗、绝句这一变化过程的认识是相符的。在这一过程中,“势”不仅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动力。涂光社先生论及艺术之“势”的属性时曾提到,“处于运动之中或者有引而未发的潜在动势的事物才可以说是有‘势’的,所以有‘因动成势’和‘势是动态的形’一类说法。不平衡的格局产生‘势差’,其中蕴蓄着运动的能量,显示着发力的方向”[6]257。诗体流变过程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诗体有其前进的动势,胡应麟的这一论断是合理的。就七言之古体、近体流变而言,从其发展动力看,古体与近体之间、诗体与时代要求之间、文学与音乐之间,种种不平衡形成了诗体流变的过程中的“势差”,因而促成诗体流变这一过程,使之具有运动性。就发展道路而言,这一流变过程有其规律性,所谓“宋人不能越唐而汉……元人不能越宋而唐……”[2]23,胡应麟认识到诗歌发展遵循着历史规律。但对于所谓“时”的认识有其局限性。胡应麟认为:“诗文固系世运,然大概自其创业之君。”[2]23在此,胡应麟认识到时代背景对诗歌流变的影响,但他将诗歌发展趋势与历代帝王联系在一起,不免夸大了帝王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再者,胡应麟认识到了在这一“时”的影响下产生的律诗“已属俳优”。所谓“俳优”,说明胡应麟对诗歌演变到律诗时所具有的音乐性有所认识,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指出七律跟与之密切相关的歌行的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胡应麟诗论的这些特点并非某一诗体或者某一流变阶段所独有的,应当说在某一流变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特点之间相互联系,体现出胡应麟对整个诗歌流变过程的认识。虽然胡应麟关于诗体流变的认识受到时代以及《诗薮》体例的限制,但瑕不掩瑜,《诗薮》之宏大规模与详尽评论以及胡应麟的学识是值得后世注意的。
[1] 袁震宇,刘明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 葛晓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J].文学遗产,1997(5):47-61.
[4] 王明辉.胡应麟诗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5] 葛晓音.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5-19.
[6] 涂光社.因动成势[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赵青
10.3969/j.issn.1673-0887.2016.04.007
2016-01-19
赵鹏程(1991—),男,硕士研究生。
I207.222
A
1673-0887(2016)04-002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