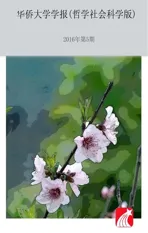“经”“文”视阈下的中国文论话语范式研究
2016-03-06潘链钰李建中
○潘链钰 李建中
“经”“文”视阈下的中国文论话语范式研究
○潘链钰 李建中
“经”与“文”是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两个重要维度。依刘勰“释名以章义”考察“经”与“文”可知,“经”之本义是“经营”,“文”之本义是“纹身”。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里,“经”之经营乃是一种返道之力,是文论话语的本根。“文”之文采乃是一种诗性之风,是文论范式的泉眼。“经”与“文”的相交发展促使古代文论话语范式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对中国文论发展有着极大影响。
经;文;文论话语;范式研究
一 “经”乃文论本根,“文”是范式泉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经”与“文”有着极高的评价。刘勰论“文”则曰“文之为德也大矣”,论“经”则曰“经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经”与“文”在刘勰看来,是天地之道传授天地之心的两仪。因为道、圣、文三者,所依之据乃是经,所播之道乃在文。所以,无论是古代文论的话语生成,还是整个文化的话语范式,“经”和“文”都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而且这两个维度,是骨肉相连,紧密相关的。刘勰论文心的思路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目的是“振叶以寻根,沿波而讨源”,因此,欲要追寻古代文论的话语范式,探颐当今文论话语建构之方法,还须依此“旧地重游,以观新景”。
(一) 经者,文论之本根
1.“经”之本字为“巠”
“经”乃中国文化元关键词之一,其关键性之所在,一是文化元典之命名,二是文化根柢之指称,三是文化精神之确证。欲把握“经”之大旨,应追溯“经”之本义。《说文解字》:“经,织也。从系,巠声。”段注“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44页。,强调“经”之“织之纵丝”与“天地之常经”的双重义旨。刘师培称“盖经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衡丝为纬,引申之,则为组织之义”*刘师培:《刘师培讲经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8页。,皮锡瑞称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辗转相授谓之说,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乃孔子所手定,得称为经”*[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页。,显然是对《说文》段注双重义旨的分别阐释。
实际上,经之本字为“巠”。“巠”与“经”起初是两个单独的字,“巠”的出现似应早于“经”:“巠”是西周早期的字,“经”则是西周中期的字(史料明确记载此时纺织之术大盛*《诗经》中早有周人关于纺织的记载,比如《诗·大雅·瞻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诗·豳风· 七月》:“蚕月条桑……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扬,为公子裳”;《诗·郑风·出其东门》:“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陈风·东门之扮》:“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等等,都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纺织技术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广泛的运用。)。西周中后期二字开始通用,似因二字之取义皆有纵横、贯穿之象。而且,西周中期有“经维四方”,西周后期毛公鼎又有“肇巠先王令”,亦可证“巠”与“经”二字至西周中后期才得以通用,并延续至今。据考证,“巠”后与“经”还有“陉”皆通。如黄侃《声韵略说》“凡此诸文……而巠脉明白可寻”*黄侃:《黄侃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88页。。
“巠”为川水之貌,此乃天地营构之象;而“经”为纵丝之织,此乃人事治理之道。中国文化向来就有“天人合一”的传统,而“天人合一”心理根源,是诗性智慧的万物有灵、物我同一。“经”与“巠”的创制者,在心理上会认为有天帝在统治万物,有天道在经营万世。从形而下的层面论,西周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时人对“经”与“巠”之词义的认识。“经”,作为“纵丝之织”,显然是属于“家事”;而“巠”,作为“川水之貌”,则是天下之事,属于“国事”。
2.“经”之本义为“经营”
周代铭文有“经维四方”和“肇雍经德”,透出一股经天纬地、经邦治国的帝王之气,今人考此处“经”义为“经营”*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从目前的材料来看,“经”字做“书籍”解,最早也要到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说“经营”之义才是“经”的本义,而非后世认为的“经籍”或者“经典”。
从现有材料看,春秋战国之前,“经”无“经籍”之义,更无“经典”之义,更多的是“经营”之义。除前文所引周代金文之“经”为“经营”之义外,还有更多传世文书的证据:
《书·周官》:“论道经邦。”*姜建设:《尚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2页。(郑玄注,经者,经营也)
《周礼·天官·序》:“体国经野。”*[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页。(郑玄注,经者,经营也)
《周礼·天官·大宰》:“以经邦国。”*[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37页。(贾公彦疏引《治典》,义为经营)
《周礼·地官·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经市。”*[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515页。(郑玄注,经者,经营也)
以上四条语料,“经”皆作“经营”解。《书》和《礼》都是周朝重要的文献,记载着当时的制度和风俗,天官、地官都号称周朝的“信史”。当然,周代“经”除了“经营”之义,还有其它义项:(1)“经”为南北之义。比如《周礼·春官·龟人》:“南北为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932页。(郑玄注,义为“南北之向”),又如《周礼·考工计·匠人》:“国中九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1663页。(贾公彦疏:南北之道为经)(2)“经”为二十八星宿。比如《周礼·春官·大宗伯》:“以二十八星宿为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648页。(贾公彦疏:经为二十八星宿)(3)“经”为常、道之义。如《书·大禹谟》:“宁失不经。”*姜建设:《尚书》,第303页。(孔安国注:常也)
无论”经”作何解,西周之时,“经”都不可能作为“经籍”或者“经典”解。而从周代铭文上“肇雍经德”等等言语上仔细分析,可以认定周朝“经”之义,因天地授命之思想而具“统治”之内涵,乃特立经为“经营”之义。由以上分析可知,“经”最开始是“经营”之义,而非“经籍”之义。也就是说“经营”之义先于“经籍”之义。
“经”源于“巠”,本义作“经营”。《诗》序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讽谏上”也。可见,古人重视“经”,并非仅仅是重视圣人之道,更是因为圣人之道之体用乃是经营天下,造福万民的。那么,为文之道亦然。反观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论史,举凡大家,的确是“文章合为时而作,诗歌合为事而作”。因此,文论话语的建构,也应该仅仅抓住“经营”之意旨。这应该成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理论之根。
(二)文者,范式之泉眼
1.“文”义流变:从自然到人文
相对“经”而言,“文”之本义则得到了较多研究。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对“文”的解释是这样的:“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至金文错画之形渐伪而近于心字之形。”*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996页。可见,徐先生认为“文”之本义乃是“纹身”。此论尤确。
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之义,大致能做如下几种分类:
(1)文,错画也。——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注。*[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425页。“文”最开始就是两笔错画而成,是一种符号标识。这种错画性质,应该是目前所知的“文”的最简单的形貌。
(2)物相杂,故曰“文”。——《易·系辞下》。*[清]李道平撰,王承弼整理:《周易季解纂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446页。“物相杂”跟“错画”相比,已经相对复杂一些。按照逻辑推断则是“错画”的进一步延伸。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相杂”,已经有了“堆砌”“藻饰”之意蕴的萌芽。
(3)颜色相杂谓之文。比如《易·系辞上》:“青赤相杂谓之文。”*[清]李道平撰,王承弼整理:《周易季解纂疏》,第216页。又如《淮南子·时则》:“黑赤为文”*赵宗乙著,孟庆祥等译注:《淮南子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4页。(高诱注)。很明显,跟第二条的“物相杂”相比起来,“颜色相杂”之物象更具体,表意更精细,也显露出了审美观照的端倪。说明此一时期人对“文”之认知有了审美的抽象感官。从时至今日流传下来的部落内成员的颜料纹身可以推测,“颜色相杂”的“文”或许是全世界民族在原始社会共有的心理认知。这种“颜色相杂”的“文”,或因动物崇拜,或因阶级区分,他们与审美感官是否有直接联系还尚待考古界进一步论证。
(4)织丝彩饰为文。比如《楚辞·招魂》:“披文服线”。*[汉]王逸:《楚辞章句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王逸注曰:文,谓绮线也。以“文”为绮丽之线标明那一时期纺织技术取得了极大发展,也表明人们对衣物有了除却温饱之基本求生心理之外的审美自觉感知。这一层面的“文”尚在物的方面,跟文学、文论无甚关联。
(5)文辞、文义、文章等。《书·尧典》:“钦明文思安安。”*[汉]郑玄注、姜建设校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38页。《论语·子罕》:“博我以文。”*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99页。谓“文”之义为文辞、文章之例者,比比皆是。《论语》中多次出现“文”。“文”之“文辞”义最开始应该跟随文字的产生而产生。文字的组合变自然成为“文”,它能表达一段意思,即使是简单的、粗浅的意思,也不妨被称之为“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里早就提出过这个看法:“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宗福邦:《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75页。此说很有道理。文字产生之初,其音、形、义三者基本上是一体的,而文字组合由少到多是随着人们语用表达的习惯约定俗成。在文字组合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有其内涵意义的语句之后,语篇则宣告完成。一个语篇就是一个简短的文章,包含了若干文辞。
(6)文采,非鄙陋之言。如《荀子·性恶》:“多言则文而类。”*[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34页。杨琼注曰:“文,谓言不鄙陋也。”*[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点校:《荀子集解》,第434页。这是强调“文”的审美意味,属于文学风格的范畴,也是针对文章言辞之好坏标准而言。孔子有文质之论;老庄谓“文采”之言乃巧言,因而对之表示反对。魏晋时人针对玄言诗之味同嚼蜡而有意凸显声色,“文采”由人之品评变为文之论衡,“文”的自觉程度大大提高:“夫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岂无文欤?”*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3页。(《文心雕龙·原道》)这种对“文采”的强调跟“文”当时还是绮丽之线之含义有内在的关联。二者之特征皆表现为一种赏心悦目的华美。人对美的追求是一种不自觉的审美感知,是从悦耳悦目之外物,到悦心悦意之体验,再到悦神悦志之精神层面的逐渐提升。如果说“绮丽之线”乃是停留在悦耳悦目之感官享受层面的话,那么有彩(采)之“文”则是进一步升华到悦心悦意之层面了。要之,“文”之“文采”义的生成,标志着文学风格与文学审美的全面展开,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7)诗歌、诗书、六艺之文、五经六籍。《论语·述而》:“文行忠信。”《论语·颜渊》:“君子以文会友”。这里的“文”乃是一种文体与典籍的合称。诗歌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文采。
(8)礼法、礼物威仪、器用仪式、祭祀节文。《国语·周语》上:“以文修之。”韦昭注曰:“文,礼法也。”*曹建国:《国语》,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这里,“文”上升到一种文化的层面,一种礼法的外在表现形式。
(9)文德。仁恩、美善、缓柔。《孙子·行军》:“故令之以文。”李筌注:“文,仁恩也。”*邹德金:《名家注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65页。将“文”解释为仁恩,是一种将“文”之形象道德化的手法。文者,柔也。有文化的人都显得文质彬彬,因而跟沙场征战的人相比更加温柔,由此引申出“文”的仁恩之义。这里已经开始用“文”形容人的品德。
(10)谥号。慈惠爱民谥曰“文”;锡民爵位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谥号是对去世之人的追尊,是将“文”义品格化的表现手段,是第九条形容人之品德的进一步升华。古代有地位有贡献的人才配享有谥号,而且其人多表现出恩柔贵礼的品格才得以赐封。比如唐德宗李适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宋欧阳修谥号“文忠”,王安石谥号“文正”,可见“文”在古代其实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称谓。
从以上对“文”之含义的梳理可以看出,“文”之义有着从自然到人文,从外在到内在,从名理物器到风格审美,从礼仪德行到文化文明的一个清晰的转变过程。文字的出现点燃了文明与文化的火把,“文”之含义发生了由自然到人文的质的转变。“‘文’作为具有美饰性内涵的语素,内化在文明、文化、礼义、文章、文教、文德、文学、文辞等等语汇当中,使得这些语汇之间有了某种共通性,它们相互影响、渗透乃至叠合,含蕴日渐丰富。”*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3页。
2.“文”在文论语境中的特性
“文”在中国文论语境里,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文艺审美范畴,而是一个更大更宽的范畴,是极具功利与物质的范畴。这里说的功利与物质当然毫无贬义。季羡林先生曾经就论中西方美学之区别谈到说:“西方的美偏重精神,而中国最原始的美偏重物质。这同平常所说的西方是物质文明,而东方是精神文明适得其反。”*季羡林:《禅和文化与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97页。这里引用此语意在说明,中国文化里“文”的修饰性一开始就跟物质性的东西挂钩,最明显的则是为政治经学服务。因而历史上配合政治与经学而来的,则是用“文”不断的丰富和诠释“经”的存在。尤其是在经学与政治关系日益密切之后,“文”几乎成了“经”“经籍”“经典”的代名词。这种情况在隋唐时期尤为突出,因为隋唐开创了中国封建时代以文取仕的先河。“文”逐渐成为政治、经学、文化,甚至文明的代名词。
在文学审美领域之外,随着“文”之地位与价值的不断提升,对于人物品评而言,有“文”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文明时代的诗人们在夸饰外物时,首先是为了文学修辞和艺术审美的需求,所谓‘壮辞可得喻其真’。”*李建中:《文心雕龙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页。汉赋可以表达赋家内心华丽场景与瑰奇的想象。因而武功卓著的汉武帝尤喜以言辞华美之文来满足他的狂傲之心,汉赋亦由此兴盛。历代帝王多对“有文之言”暗自喜爱。纵然圣明如唐宗宋祖,其雅爱风骚一直是历代佳话,由此可见,“文”在历史文化中意义十分重大。
实际上,中国文论之“文”乃是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独特的诗性智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文论话语理论的生成从来不是独立的,而是与文化有着紧密之联系。甚至可以说,古代文化与古代文学和文论皆因“文”而出,龙生九子而个个不凡。所以,“文”可谓是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润身泉眼。其次,中国文化中的“文”从自然到人文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极具民族性的审美视角。不仅是文学史中的诗词歌赋,还是文论史中的诗言画境,这些都与“文”同生一原,息息相关。可见,“文”乃是中国文学与文论话语建构的理论甘泉。第三,中国文化中的“文”始终与人文关怀紧密相连。中国文化中的“文”从自然到人文,从名物到审美都跟“人”生死相依,不离不弃,表现出极为崇高的人本关怀。正是中国古代文士强烈的人本责任感,才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顶峰。甚至作为软实力更加增进了国家实力与民族影响力。
二 “经”主返道,“文”秉诗性:文论话语的理论品格
既然“经”乃是文论话语的本根,而“文”是文论话语的泉眼,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则应该仅仅抓住“经”与“文”。然而,除却曾经辉煌的中国文化与文学,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话语却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无论是世纪初中国古代文论学科构建的兢兢努力,还是随着西方批评方法热的浪潮勤袭而兴起的古代文论话语反思,这些都表明中国文论话语需要持续的建构之力与累土之功。
当然,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产生的,中国文论亦非例外。中国文论是中国文化语境下研究中国文学的理论。然而,中国文论之语境生成,却绝非这样简单明了。不仅仅是因为近两年学者们普遍意识到西方“强制阐释”的不利*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12页。,更因为中国文论的产生和发展,其自身有着非常独特的路径。换句话说,中国文论的生成语境也是非常独特的。关于这一点,季羡林先生早就有了论断:“我们中国的文艺理论不能跟着西方走,中西是两个不同的思维体系,用个新名词,就是彼此的‘切入’不一样。严沧浪提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与禅宗结合起来的文艺理论,西方是没法领会的。再说王渔洋的‘神韵说’,‘神韵’这个词用英文是翻译不出来的。袁才子的‘性灵’无法翻译,翁方纲的‘肌理’无法翻译,至于王国维的‘境界’,你就更翻不出来了。这只能说明,这是两个体系。”*季羡林:《东方文化复兴与中国文艺理论重建》,《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6期,第12页。可见,中国文论话语语境非常独特。
从“经”与“文”的角度出发,可以说,之所以说中国文论的研究语境非常独特,是因为中国文论话语语境具有两种独特的品格。而这两种独特的品格,均与“经”“文”之内涵一脉相承,可谓“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一)返道之动,求旨归“经”
中国文论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悠久的文学传统,这是文论研究取之不尽的源泉。正如“经”之本义乃在“经营”一样,文论话语本来就与经学同出一源,因此“经”本身便是文论话语建构的不竭源泉。所以,“取次花丛懒回顾”并非是一种积极的理论建构态度。相反,“众里寻他千百度”才是中国文论建构应该守望的目标。而这样的目标身在何方呢?“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这个“人”,正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先贤古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去追寻中国文化里优秀的精粹,而一直追着西方话语的脚步,我们不会有所进步。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早就告诉我们一个“欲进须返”的道理。“中国当代文论研究应当回到中国思想文化和文论的原点去理解和阐释传统文论,并以此为基础强化中国文论的文化身份意识,树立中国文论的文化主体性。”*党圣元:《传统文论的当代价值与民族美学自信的重建》,《中国文化研究》2015秋之卷。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的首句非常值得注意:
反(返)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老子认为天下万物都是从“无”到“有”,是一个过程。如果去追溯他的“有”,实际上要考察他的“无”。而“无”,实际上乃是一种虚空,一种虚空就需要散动,一种散动就是一种寻求。寻求去哪里?寻求到本源。也就是老子所谓的“反”(返),这个“反”(返)就是返回与回归。那么,“道”,实际上既是一种不断寻求,不断返归,不断升华的过程。这个观点,与伟大的马克思所谓社会发展乃是一种循环式的上升的观点正是不谋而合。我们一方面惊讶于这种观点的巧合,另一方面也惊讶于我们古老文化中很早竟存有如此优秀而先进的思想!
“返道”之“道”,核心在儒家,释道之思也是“返”的重要部分。之所以认为儒家之道乃是核心,是因为儒家之道的确对于中华文明之发展有着不可估量之效用。“也许可以这样说,在西方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文明诞生以前,儒家学说是人类思想体系中最具生命力的一个体系。在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支配下,它以实现有等级的仁爱为最高价值观念,创造了一套高度完善的道德伦理规范。它以理性的光辉抵御了宗教统治的愚昧和黑暗,儒家学说积极干预生活,提出并实践了自己的国家理论,更加令人惊叹的是,儒家强调和谐精神的调节作用,强调人的思想、社会行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家庭、国家、社会也应该是和谐的整体。这种立足于和谐并强调人的道德力量的学说,使我们民族成为古代最重视文化和教育的民族,两千余年间创造和维持了独特的文明体系。”*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5页。
综上所述,欲求中西文论思想有着融通之可能,欲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之大厦,则必先以自身文化资源之壮阔为前提。欲壮阔自身之文化资源与理论话语,则必先以返归为策。返归,是一种冷静澄澈的回望。返归,是一种深沉的濡沐与洗礼。返归,是一种文化的坚守与灵魂的重塑。
(二)诗心千古,大德为“文”
华夏民族悠久长远的诗性智慧对中国文论之建构一直深有影响,而随着工业发展,这种诗性精神有着衰退的现象。其实,中华民族的诗性精神,是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之发展紧密相关的。把握诗性乃至融通诗性,实际是一种回归与重建。“话语方式是思考和阐述问题的方式,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是思想的外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也就决定了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来阐述。”*代迅:《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危机与变革》,《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第23页。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方式乃是一种诗性的文论。它涵盖着古人的诗性智慧与民族的诗性光芒。无论是《诗经》本身具有的风雅之美,还是汉服携带的庄华之气;无论是陆机字字珠玑的《文赋》,还是司空图诗眼画境的《诗品》;不论是论诗的精妙,还是旁批下注的谐趣,中国古代文论始终保持着民族诗性的文明之光。因此,作为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基本问题,文论本身的书写,其实更应该偏重于文化与传统本身带有的诗性之灵。反观西方文论,“一味从概念出发,从概念到概念进行演绎,越是向抽象的高度、广度升华,越是形而上和超验,就越被认为有学术价值,然而,却与文学文本的距离越来越远。文学理论由此陷入自我循环、自我消费的封闭式怪圈。文学理论越发达,文本解读越无效,滔滔者天下皆是,由此造成一种印象:文学理论在解读文本方面的无效,甚至与审美阅读经验为敌是理所当然的。”*孙绍振:《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文艺报》,2013年9月6日。其实,之所以文学理论与审美阅读经验越来越远,既是理论现代性的产物,更是诗性脱离的产物。因为“当代西方文论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差异、伦理差异和审美差异,这决定了其理论运用的有限性。”*庄伟杰:《中国文论的当代性反思与本土性建构——兼及对当下文学批评存在问题的思考》,《文艺争鸣》2015年第3期,第35页。
从文体与风格的角度而言,诗性之文也可以是一种极其符合民族特性的要求。从“说什么”到“怎么说”,中国文论始终紧跟西方文论的步伐,文论话语表达也是紧跟西方。但是,这种“紧跟”并不十分符合中国文论的话语传统。中国古代文论的简短之美、含蓄之美、内敛之美、静穆之美、转喻之美、灵动之美,全部在紧跟西方文论表达之下失去了应有的色泽。甚至很多中国文化传统中早就成熟的文论范畴,成为了当下文论话语建设为“匹配”西方话语而刻意摆出来的精美古董。如果因为不自信而刻意寻求自身具有的物品,用以跟西人取得同等的话语地位,实际上有一种掩耳盗铃之无奈。
三 “经”正“文”成:文论话语范式的结构表征
“经”主返道,“文”主诗性。可以说,“返道”与“诗性”乃是“经”与“文”的显象品格。中国文论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返道与诗性两个维度交相更迭、互相影响的历史。如果说先秦两汉的文论话语相对侧重政治营构的“返道”意识的话,那么魏晋南北朝则相对侧重审美语境的诗性言说。同样的,如果说隋唐两宋的文论话说相对侧重诗性智慧的话,那么明清两代的文论话语则相对侧重伦理道德的叙述。当然,这种论述并非绝对,而是相较而言。而且很多时候,经之返道与文之诗性甚至可以相互融通,交相辉映。比如盛唐时期在经学重建之后,诗歌出现了极为繁盛的盛唐气象,正是“经”“文”交融的典型时期。
“返道”即返经学之道,“诗性”即宗诗学品性。所以,“经”与“文”的理论品格很大程度上可以浓缩为经学与诗学的理论品格。在中国古代文论史的话语体系中,“经”与“文”、经学与诗学常常表现出同幅共振的结构表征。“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国传统诗学思想与儒家的经学期和理学期大致相合。”*萧华荣:《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实际上,从中国经学与诗学的结构表征就可以管窥“经”“文”关系下古代文论话语范式之概貌。
(一)两汉:“经”尊“文”从
“六经”原本是华夏民族古老的文化典籍,自孔子发扬光大则成为儒家文化教旨。然而孔子生活的时代未能允许孔子的思想得到推行,“六经”一时成为诸子百家中散溢微光的陈集。春秋动乱与战国烽火让统治者看到大一统的政权才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但这一任务在统一六国的秦代未能完全完成。秦施恶道,背离仁政,反而给了后来的汉代以历史警醒与前车之鉴。有汉一代,儒家得到全面发展因而后世称其为“经学隆盛之时代”。
汉代经学隆盛,皆因帝王重视儒学教化。汉武帝年幼所学,正集百家数术,他能明晓法家儒家之真正用途,因而即使汉武帝独尊儒术,实际上也是“外儒内法”。“外儒内法”四个字其实已经表明儒家已经转变了原始性质,失却了原先肇雍经德、公则仁义的美好理想,变成为世俗化的儒家。但此意亦属“经”之“经营”之旨。
若言汉代诗学是经学的附庸,此论未确。“客观考察分析可知,汉代儒学与文学的演变,大致说来,从同幅共振趋于失衡;两汉儒学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巨大,但它没有左右汉代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陈松青:《试论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之附庸》,《唐都学刊》2007年第1期,第11页。因而此处用的乃是“从属”。尊者,贵也;从者,属也。“附庸”则是毫无主见毫无地位可言,而“从属”则是地位稍次。之所以用“从属”,是因为汉赋纵然是因为经学功用“劝百讽一”而发展起来,但是很明显,汉赋在后期发展中,个人情感之因素越发增强,以致后来抒情小赋的流行,标明汉赋找到个性审美的最终归宿。因而在这个层面来说,汉赋并非完全没有主见和地位可言。更何况,在汉代精通经学之大家,绝大多数都是写赋能手。扬雄、张衡、司马迁、司马相如等等,在经学政治受挫之时,往往能将内心愤懑诉诸文辞,借赋消愁。汉代大量的《悲不遇赋》的产生往往因此而来。这也标明汉赋不仅具有重要的抒情作用,同时赋家的批评标准亦由图物写貌变为自我抒情。汉代经学源自《诗经》里的规劝讽谏传统一直影响着汉代文论,因而汉赋无论多么华美,最后的曲终奏雅还是必须回归到经学的苑囿里来。两汉文论不仅秉持规劝讽谏的儒家之道,还给后来魏晋山水诗之写貌手法以极大助力,甚至给“以文为诗”或“以诗为文”之论提供了借鉴。
(二)六朝:“经”隐“文”显
有汉一代终因政权旁落而淹没于历史长河,两汉经学的隆盛景象成为碎影。代大汉几百年大一统而来的,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荡。没有了大一统国家政权的维系,经学失去了安定生长的土壤,显得孤诣飘零。的确,跟两汉相比,经学在魏晋南北朝未能拥有为国家政权直接服务的显贵位置,没有能调和古今文经学之争的经学大师,没有了皇帝直接参与的经学会议,只有形似诸子般的谋士奔走于各军阀之间,传递夺取天下的筹谋,只有汉后私家隐蔽流传的经学专著以供少数文化传承人去保存,而各军阀忙于征战无暇顾及文化教育与意识形态之建设。由此对比可以清晰看出,经学在魏晋时期处于一种低迷的状态,他如游丝之气流于寰宇之内。其“经”之旨好似游离于返道之外。正是魏晋时期经学处于低迷衰微之境遇,因而经学意旨发生了显著变化。又因为魏晋玄学的兴盛,儒家经学的确境遇堪忧。汉代“劝百讽一”“温婉讽谏”的儒旨之中断成为可能。“思想上玄学时代的开始,就是批评上讽喻传统的中断。它从魏晋开始,贯穿整个南朝,并延续到唐代。”*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2页。此论尤确。
魏晋时期,世乱经微,儒家风化之旨停于长空而不散于民间,两汉长期绷持的意识形态逐渐松绑。加上玄学清谈的兴盛与世风华糜的景象,因而魏晋时期文学文化受到极大影响。首先受到极大影响的是文学诗歌。魏武帝诗歌内含强者的雄霸之气,这样骨气刚强的诗歌自然不似儒家温柔敦厚诗风教旨。魏文帝之诗情质温柔,陈思王之诗情兼雅怨,有《诗》风之流韵而无《诗》志之伟岸。两晋逐步将诗风推向雕琢浮华,即使“竹林七贤”文辞繁简适中,但整个两晋文学作品崇尚雕缛藻饰已是不可挽回。左思、陆机、潘岳等著名文人之诗歌赋作,或内容庞杂,或情感细腻,或辞美文妍,或刻工情思,已然不再是儒家“温柔敦厚”与“辞达而已”的美学标准。
在经学与文论相对比的情势下,可以说,随着文学的自觉意识的不断加深,魏晋文论之发展远远超过经学。因此,魏晋“文”的诗性之力得到极大突显。魏晋诗歌走出了两汉诗歌古朴沉质、埋哀言怨的狭小空间,为古朴雅致的诗学领域增添了不少虚华的色彩。这大致是赋体写物入诗之流变所致。而魏晋诗歌题材的极大扩展与体裁的大量出新,直接为后来唐宋诗歌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丰富的写诗手法。这一时期的玄言诗、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五律、五绝、七律、七绝,还有骈文、散文、辞赋等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魏晋经学衰微带来的还有小说的繁荣。这当然也于东汉佛教传入后,佛经义理里面故事的讲述方式之影响有关。魏晋文论实际取得了长足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场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等,皆为魏晋时期的文学发展指出了方向。凡此种种,都清晰表明魏晋时代是一个文学文论大发展的时代,也都表明文学不再是引经据典的章句之学,而是充满着个人情感与活脱生气的私家之言。
魏晋时期的经学局势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但庆幸的是南北朝时期对魏晋时期经学低迷、文风虚糜的局面做了反思。这种反思并非来自统治阶级之主观意愿,而是在政治格局分为南朝与北朝之后,两方分立对峙、互相参照的形势下开始的。正是南朝与北朝存在两种政治格局,因而南北朝之经学各具特色。北朝延续汉代训诂考释之风,因而尤为重视名物考释。南朝则因楚地玄风之盛,因而偏重义理清谈。不仅仅是经学研治上,在文论思维上,南北朝也是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北朝尚质,南朝尚文,这些已是众所周知。南北朝受到佛教思想之冲击也是史有所载。具体到经学与文论之关系上来说,能够清醒认识到儒家教旨之重要,而又能借佛家精思言理之思维著说文章的,只能是南朝齐梁间的刘勰。
刘勰对于“经”与“文”的关系,在其千古大作《文心雕龙》之开端三篇中已经讲述得十分明白。所谓“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旨在恢复儒家《诗》教。刘勰此处所言之“道”,虽然有着道家自然之旨的意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说的主要还是儒家之道。杨明先生认为刘勰的“道”,“不限于道家,而是儒释道三教都认同的宇宙本体”*杨明:《刘勰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7页。。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三教都认同的本体之“道”,其关键还在儒家。因为杨明先生还明确指出,刘勰“道”的提出不是为了宣扬三教本体,而是借助“道”来提高文学文章的地位,继而为他将要提出的“征圣”“宗经”的文学主张做铺垫。*杨明:《刘勰评传》,第78页。
正因为恢复的关契乃是儒家之道,因而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处处显示出对儒家“六经”的重视。《宗经》一篇对儒家“六经”做了详细的分析。称赞“经”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可见刘勰心目中经及儒家地位之重。而《序志》言他幼年攀采祥云之事,更是直接明了的标明对孔孟之教的推尊,希望自己是孔子事业的继承人。但刘勰跟周孔及两汉时代的儒者关于传播儒教教旨有着极大的区别。前人对儒家之“六经”所作的乃是道德仁政之推重。刘勰跟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刘勰乃是从“依经立文”的角度把经学与文体做了具体的勾连。在《宗经》一篇,刘勰就说了“六经”各自禀赋的文体特性:“《易》唯谈天,《书》实记言,《礼》以立体,《诗》以言志,《春秋》辨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29页。(《文心雕龙·宗经》)因而在写作不同文体之时,“六经”之文体风格成为了一种模板与范式:“论说辞序,《易》统其首;诏策章奏,《书》发其源;赋颂歌赞,《诗》立其本;铭诔箴祝,《礼》总其端;纪传铭檄,《春秋》为根。”*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30页。(《文心雕龙·宗经》)这种从“六经”中找寻文体依据的思维虽然早在荀子时期已经有所提及,但刘勰才是真正从体系上系统梳理了不同文体与经学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刘勰系统梳理了经学与文论的关系。“六经”从刘勰开始不再是简单的道德宣讲或者仁政纲领,而是变成了一种文学写作的模板。刘勰认为的经文关系,简单说,就是依经立义、经体文用。
如果说“经”与“文”在汉之前是“经”重“文”轻,在魏晋南北朝是“经”轻“文”重的话,那么在刘勰这里,“经”与“文”形成了一种和谐的统一。如果说,刘勰之前,“经”是制约“文”、规范“文”的,那么到了齐梁刘勰《文心雕龙》这里,“文”成了“经”的理式的化身,成为了“经”的本体之用,这对于后来唐宋之文学观与经学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 隋唐:“经”定“文”炳
与六朝不同,唐人对“经”及经学之意义有着极为清晰的认知。唐代统治者开国之初,便对儒家经学表示重视,对经学教育与礼仪制度之建设极为用心。高祖武德七年,李渊诏令兴学:“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崇儒·兴学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37页。
高祖之重振儒家经学之决心在《置学官备释奠礼诏》中表露的更为明显:“ 六经茂典,百王仰则;四学崇教,千载垂范。是以西胶东序,春诵夏弦,说《礼》敦《诗》,本仁祖义,建邦立极,咸必由之。”*[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崇儒·兴学诏》,第537页。这篇诏书详细说明了汉末六朝儒学不振,经学凋敝的景象:“雅道沦缺,爰历岁纪,儒风莫扇”,“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塾之仪,泯焉将坠。”这种对儒家经学情势发展的清醒认识,标明唐初统治者意欲恢复周孔之教的决心甚大。“经”在唐代不再是处于边缘和衰迷的境地,而是重将升起的新日。唐人对“经”的重新重视,标志着经学发展在唐代焕然一新。可以说,经学走向一统,“经”之致用重新归于正位,是历史之必然,也是唐人选择之必然。
与“经”之归正同轴共振的乃是“文”之新成。“文”在汉代是经学的从属,五言诗与汉大赋明显有着《诗》之风旨。魏晋南北朝之“文”则绮丽藻饰,情感丰富而姿体妩媚。华而不实成为魏晋“文”之整体风貌。经过齐梁文学之发展,尤其是刘勰对“经”“道”与“文”之关系的阐述,“文”乃是“圣”发明“道”之物器,这“道”自然是儒家之道。“文”也是“道”之文。对“文”本身而言,“道”之文乃因“文”之道而成。“文”之道,在刘勰看来也是儒家之道,在隋唐之际四海一统之后,更是儒家之道。此为其一。
其二,刘勰对“经”与“文”之关系做了新的阐释:经体文用。文章写作不仅在内容上要延续《诗》《骚》风雅,文体形式上则可以依据“五经”为模范。这种把“文”提升为与“经”同等地位之看法在当时极有创新性。“经”之经典意味变成“文”之写作意味宣告了一个极重文思、融经入文之时代的来临。
因而“四杰”及子昂在唐初极力呼唤《诗》之风雅,以“经”救“文”。他们希冀革除六朝文学奢华风貌,而推唐代“风骨”“兴寄”之新声。盛唐诗人“经”“文”并修,经立其本而文统其身。中晚唐诗人以文救经、文以载道都是将“文”作为一个极为重要之因素看待。这跟宋代理学家认为的“作文害道”有着截然不同之理解。
综观上述可以看出,唐代“经”之归正与“文”之新生乃是沿袭汉魏以来“经”“文”关系发展而来的必然趋势。唐代诗学在“文”之苑囿里亦随着文学理念的更新而不断发展。杜书瀛先生曾就唐代文论之要成总结道:“唐代诗学文论有自己的重大贡献,如在‘唯美’一系,进一步深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形式运动’,提出‘对偶说’,促成了律诗、绝句的建立;提出‘诗境’论,成为中国‘诗文评’核心理论思想之一‘意境’的起始;晚唐司空图提出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观点,影响深远。在尚用一系,则有元白诗论,韩柳文论等等很有特点的思想。”*杜书瀛:《唐宋金元文论“衰落”、“隆起”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1页。唐代“经”与“文”之交织,有其自身之轨迹,经学与文论的发展在相互影响中铺开大唐繁华璀璨的天幕。
(四)宋明:“经”理“文”则
传统儒学的训诂考释的风气并没有在宋代经学里泯灭,传统经学里那种讲求通经致用的精神始终在宋学中保持,传统经学与政治密不可分的特性依旧在宋学里显现。另一方面,宋代经学放置在整个经学史上来讲,宋代经学超越了传统经学讲求训诂考释而更加偏爱义理,宋代经学经历了六朝隋唐三教文化融合的漫长时期因而在极具通经致用的儒者风范的同时又有着明显的释道身影。宋代经学在与政治紧密联系的同时又跟文化科技教育紧紧相连,这些相对于传统经学而言,的确是十分难得可贵的新特质。其次,在研究宋代经学与文论关系时,还需明确的乃是宋代经学与文论之关系相对前代而言更加紧凑,经学对文论的影响更加明显和直接。这是因为宋代经学作为传统儒学的变革,有着从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认知方面深入的变化,这些都属于文化范围之内的、属于人的观念认知思维的东西跟同属文化范围的文学文论的观念认知思维有着不可剥离的属性,因而诗论文论也都带有着清晰的变革特色。他们如同花与叶,都是被同一阵风吹过,因而同时在抖动。第三,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经学带给人的直观印象往往是理学与心学,宋明心学的深入人心以及研究的深度的确是整个经学史上的奇葩,可是,我们始终不能忽视的乃是宋代经学一而惯之(更是整个中国经学史一而惯之)的“通经致用”的经学精神。相对王阳明、陆九渊对心性之学的深思,范仲淹、王安石一类敢于将先秦儒者致用之精神发挥用以补救民弊之风范更加让世人赞叹。因而,我们在高度赞扬阳明心学、朱熹道学的同时,更要始终将重心放在“经营”之大道的“通经致用”之经学观上来。
明代经学与诗学的关系紧紧依托由汉到宋经学转型下诗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如果说汉唐经学与诗学发展侧重于一种“日神精神”的表达的话,那么宋明经学与诗学发展则更多的可以归入“酒神精神”的情志表达。因为宋明经学发展突破汉唐经学重训诂考释的苑囿而朝章句义理的方向奔腾。由此,明代经学经由心性之学的弘扬,将诗学心性之论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有明一代诗学体系的核心部分。这是明代经学与诗学发展关系的第一重要义。
其次,明代经学的核心乃是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带来的乃是政治意识的重新营构与人格素养的重新要求。而明代诗学承前启后,以格调论作为诗学揭橥,实际上是对心性之学要求的政治营构与人格重塑的侧面回应,是与经学心性之学同幅共振的诗学理论。这是明代经学与诗学发展的第二重要义。
第三,明代诗学在理论建构问题上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唐宋抉择问题。诗学理论上的“宗唐”或者“宗宋”,不仅是明人为自身找寻诗学维度的必经之路,其实更是对明代经学发展做出的紧密和声。经学心性之学的发展,本就承接汉唐而来,而唐代经学作为汉宋两大经学高峰的分水岭,实际上已经有了宋明经学发展之暗指。因此,作为特殊时期的唐代经学意识与作为宋明时期经学发展首领的宋代经学意识,必将同时给予明人经学与诗学发展双重影响。诗学是对经学的能动性互动。因此,诗学宗唐或者宗宋也是明代经学发展之能动互动。这是明代经学与诗学关系发展的第三重要义。
第四,明代经学发展维度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经科考试中的八股文制度。当然,八股文是经学应试不断发展的产物,隋唐而起的经科考试,到宋代基本成熟。至明则转为对经学的章句义理的重新阐释,甚至很多层面乃是一种代圣人言。因此,在多数人心目中,八股文成为僵化的经学解读。然而,实际上,八股文对于明代诗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五经文本解构与结构,对于促进明代诗学尊体意识与文学形式策略有着被人忽略的、却又意义非常的价值。因而可以看做是经学发展对于诗学发展的又一功劳。这是明代经学与诗学发展的第四重要义。
【责任编辑 南 桥】
A Paradigm Research on Chinese Discourses of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ing and Wen
PAN Lian-yu,LI Jian-zhong
“Jing” and “Wen” are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According to Liu Xie’s investigating “Jing” and “Wen” in “ShiMing ZhangYi”,“Jing” originally means “management” and “Wen” primitively means “tattoo”.In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system,the management of “Jing” is a force for returning and the root of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The literary grace of “Wen” is a kind of poetic wind and a fascinating place from which literary theory paradigm stems.The intera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ing” and “Wen” promotes the ancient literary discourse paradigm to present different features in different periods,which exerts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Jing;Wen;the discourse of literary theory;paradigm research
2016-09-15
潘链钰,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湖南 长沙410006)。李建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论及文化元典(湖北 武汉 43007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12&ZD153)
I206.2
A
1006-1398(2016)05-0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