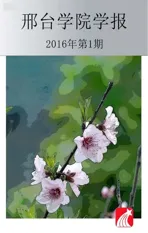胡如雷对陈寅恪史学的继承与发展
2016-03-02李俊生
李俊生
(邢台学院,河北邢台 054001)
胡如雷对陈寅恪史学的继承与发展
李俊生
(邢台学院,河北邢台054001)
胡如雷是陈寅恪史学的继承者,他继承了陈寅恪索隐探微的治学方法,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敏锐的洞察力,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进一步拓宽了史料范围,重视新史料的挖掘与运用,主张开展跨学科研究,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胡如雷;陈寅恪;历史学;继承
胡如雷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长期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目前,研究胡如雷的学术文章并不多,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任何成功人物的产生都同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结合胡如雷的生活成长经历,分析他和陈寅恪史学的渊源,探究其对历史研究的贡献。
一、借鉴陈寅恪索隐探微的治学方法
胡如雷从小就喜欢历史,长大后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清华大学的良好校风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理念成为他日后在学术上大展宏图不可或缺的条件。清华大学大师云集,人才济济,良好的学术氛围使他积累了丰厚的知识,为日后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寅恪先生早年曾在清华大学任教,是隋唐史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其渊博的知识和别具一格的治学方法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胡如雷在清华求学时,陈寅恪已离开清华,但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胡如雷非常崇拜陈寅恪,经常说“陈寅恪先生是当代治隋唐史的泰斗”,[1]他反复认真研读陈寅恪先生所撰写的文章和著作,认为“了解、掌握陈先生的成果是追踪学术发展历程的起点。”[1]胡如雷不但认真学习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果,还努力钻研陈寅恪先生“那种索隐探微的治学方法,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极端敏锐的洞察力”。[1]正是这一努力让胡如雷成为继陈寅恪之后研究隋唐历史的又一大家。因此,掌握前辈的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继承他们好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学习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只有这样才能够出成果。胡如雷就是很好地处理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
胡如雷195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北邢台工作,在邢台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师。邢台是个小地方,属于革命老区,工作、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胡如雷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搞学术研究,先后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论武周的社会基础》 《唐代均田制研究》等文章,初步确定了隋唐史作为其主要研究方向。关于武则天建立周朝这件事,胡如雷在陈寅恪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地主阶级中这两大集团的矛盾必然日益尖锐,最后成为剧烈的门争,武则天正是在这一门争已经明朗化的时候,逐步掌握了政柄,终于建立了武周。在这一门争中,她正是地主阶级中这一新兴的集团的代表”。[2]为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就应该尝试从新的角度去考虑、去探索,才能有新的发现。一个人如果想搞学术研究,没有必要的学术基础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没有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就会在研究中迷失方向,走弯路,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够看得更远。然而,满足或局限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不思进取也不行,那样就会丧失前进的动力。因为,如果没有创新,就不能进一步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开辟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在创新中求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要积极继承前辈们的学术成果,就要多读书,会读书。读书也是一门学问,不能漫无目的地去读,要讲究读书的方法,才会有更大的收获。胡如雷结合自身的读书体会,介绍了他自己总结的读书方法,说“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汗牛充栋的古籍中必须划清精读和粗读的范围。我觉得《资治通鉴》、《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亦称《五代史记》)和《大唐六典》是应当精读的基本史籍”。[1]也就是说读书要有所侧重,有的书需要精读,有的书则粗粗地浏览一下就可以了。在涉及唐代史料的书中,《资治通鉴》是重中之重,是需要研究隋唐史的学者反复阅读的,胡如雷认为此书“案头不可一日或缺。”[1]
二、拓宽史料范围,贯通古今
胡如雷认为读书除了要精读基本史籍以外,还需要进一步扩展范围,阅读一些笔记、文集、小说和诗歌,因为这里面也会存在一些我们需要的,能够反映当时社会风貌的内容。陈寅恪先生就提倡“以诗证史”。胡如雷在陈寅恪的基础上,认为“《太平广记》中那些纯属虚构的故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经济、人情状况等。”[3]P4所以说任何文学作品都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杜甫的诗就被很多人称为“诗史”。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贴近人民生活,有很多反映下层人民群众生活疾苦的作品,很值得一读。陈寅恪先生就非常推崇杜甫和白居易的诗,认为他们的作品值得反复精读。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中有“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4]P53的语句,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状况。杜甫更是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白居易的《观刈麦》中“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5]P259的语句,同样反映了当时赋税繁重的情况。所以说多读一些唐代的文学作品,对于研究唐代历史是很有帮助的,可以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
胡如雷认为读书的同时,要加强对古籍的研究,借鉴前人对古籍的研究成果,要把各种古籍结合起来进行阅读,这样才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要注重读书的顺序,“譬如先读《隋书》和《通鉴》的隋朝部分,同时涉猎《全隋文》及《大业杂记》等书。其次读有关唐初武德、贞观时期的史书,并且每个人物都同时对照两《唐书》的本传来读。这样一段一段按时间顺序读下去,其好处是:首先,印象深刻,便于记忆;其次,便于精读,能够仔细考虑问题,读书的同时就随手可做一些研究。”[1]这样相互参照地来看书,有助于对历史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弥补各种史书记载的不足,也可以纠正个别史书记载上的错误之处,避免我们在研究中误入歧途。研究隋唐历史,不能只看有关隋唐时代的书,还要贯通古今,只有这样才能把问题彻底搞清楚。胡如雷认为“搞断代史如果不把目光放大一些,单纯地就事论事,至多只能描绘一些历史现象的发展脉络,而不可能找到引起这种发展、变化的社会根源。”[1]所以说做断代史研究,也必须要精读通史,只有前后联系起来研究,才能把问题研究透,绝对不能在研究中搞“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胡如雷专门搞了几年中国经济史研究,做到了在经济史方面贯通古今,所以在后来撰写《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时能够得心应手。
三、提倡开展跨学科研究
1956年,胡如雷调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工作,两年后转到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工作,工作环境的改善为他从事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历史学家,阅读到更多珍贵的历史资料。随着胡如雷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他在学术界的声望逐步提高,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唐史学会会长。胡如雷认为“今后搞隋唐五代史,不妨研究一点跨学科的课题,这也是放大一下眼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发展过程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方面分科越来越细,门类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这种辩证发展过程就使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既有必要,又有可能。”[1]胡如雷认为自己没有去搞跨学科的研究是自己的遗憾,要把历史问题研究透,必须具备跨学科的知识,所以说任何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越多越广泛,对今后进行学术研究就会越有利。陈寅恪先生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师,通十几种语言,曾在清华大学同时任历史、中文、哲学三个系的教授,他国学功底深厚,又熟悉西方文化,所以他的见解,一直被国内外学人所推崇。因此,只有学识渊博、涉猎广泛,通晓古今中外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大师。
在继承前辈研究成果问题上,胡如雷提出要“充分尊重前辈的史界权威,大胆解放自己的思想。轻率地否定、贬低前人的成就和轻易地妄自菲薄,都是错误的。每一个人的学术道路都应该是由自己走出来的,任何人都不应当模仿权威或跟在先辈的后面亦步亦趋。”[1]所以说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就要大胆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基本史料出发,结合最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大力推进学术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学术研究永远没有止境,真理都是相对的,即便是再熟悉的研究领域,也完全可以有新的发现。隋唐史研究已经进行了一千多年,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涌现出很多隋唐史大家,基本史料也被人们研读了无数遍,写出的有关隋唐历史的论文可以说是铺天盖地。那么既然这样,隋唐历史还有没有继续进行研究的必要呢?还有实现创新的可能吗?胡如雷的回答是“一千年后还会有人研究隋唐五代史,而且还能够做出前人所没有做出的新结论,应当说,隋唐五代史的待研究领域是十分宽广的,在这里大有英雄用武之地。”[1]批驳了隋唐史研究领域的悲观论,指出隋唐历史研究大有可为,是不会穷尽的,进一步增强了青年学者从事隋唐历史研究的信心,鼓舞了斗志,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四、重视考古新发现,挖掘新史料
历史学者不仅要从事历史研究,还肩负着普及历史知识的使命,胡如雷主持编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名家文库·唐史》,图文并茂,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非常适合普通老百姓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和学习。比如他在书中关于“国子监”进行了这样的介绍,“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和官府名,晋武帝时,始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和博士各一员,掌教导诸生。北齐改名国子寺,隋文帝时,改寺为学。不久,废国子学,唯立太学一所,省祭酒、博士,置太学博士,总知学事。炀帝即位,改为国子监,复置祭酒。唐沿此制,国子监下设国子、太学、四门、律、算、书等六学,各学皆立博士,设祭酒一员,掌监学之政。”[6]P13用简练的语言系统介绍了国子监的功能、来源和发展历程,从这里可以看出,历史学者确实需要知识上的上下贯通,特别是从事断代史研究的学者,不仅要熟悉自己所研究的特定朝代的历史,还要了解其他朝代的历史,只有通晓古今才能做好工作。
胡如雷认为,历史研究必须重视最新出土的文物或文书,“除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手实、户籍证明这两个地区确实实行过均田制外,内地这方面的史料和记载比较少。这件文书说明长安附近的雍州不但实行过均田制,而且在农民受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有权量彼贫富,均彼有无。即对已受田进行调剂。”[3]P5胡如雷积极运用出土文书进行唐代均田制研究,以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因此,历史研究必须重视发掘新的史料,积极利用最新考古成果,同时大力开展田野调查,从民间发掘史料。要重视各种碑刻、家谱、文书的整理和收藏,因为其中可能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很多正史中没有记载或记载不清的内容,或许可以在碑刻或历史文书中找到答案。因此,每一次考古重大发现,都可能会对某一历史现象产生新的认识。客观地说,散落在民间的文物资料还是大量存在的,需要我们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加强搜集、保护和整理。目前,社会史已经成为一门学问,随着研究的深入,必然会对历史研究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坚持史学生产力标准
胡如雷认为,要重视历史研究中的生产力标准,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评价历史现象进步与倒退的基本依据。“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事物都是反动的,而反动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迟早要垮台。因此,野蛮的征服者或者遭受挫折或失败,不得不最后撤出征服区,或者被迫改弦更张,实行同化政策,争取适者生存的前途,以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北魏孝文帝之所以必然实行均田制,其原因正在于此,所以他的汉化政策才具有进步性。”[7]P30生产力标准是评价社会进步与倒退的基本标准,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都可以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的,就是进步的,反之就是倒退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都是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历史时期,汉文帝和唐太宗的轻徭薄赋都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起到了积极作用。相反,历史上有些皇帝的大兴土木、横征暴敛行为,严重超出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破坏了生产的发展,造成土地荒芜,民不聊生,起到的就是消极作用。生产力标准和劳动人民利益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属于农业社会,发展经济主要就是发展农业生产,民以食为天,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8]P256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就难以保证社会的稳定。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所以唐太宗李世民非常爱惜民力,在他统治时期,“轻徭薄赋,民殷财阜。”[9]P169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唐太宗因此而成为后世皇帝学习的榜样。
六、结语
胡如雷继承了陈寅恪史学的精髓,实现了历史研究中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创新。胡如雷在撰写《唐末农民战争》时,就提出“过去,我颇有志于研究唐末农民战争,但苦于摆不脱一般研究农民起义的下述公式:土地兼并——赋役苛繁——天灾——农民起义——让步政策——经济发展。个人感到把每一次起义都凑点类似的史料填入这个框框,实在没有意思。”[10]P3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事物都是在创新中发展的,要勇于打破旧的思维方式,尝试从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有新的收获,新的发现。农民战争现在一般都不去研究了,但是胡如雷在研究农民战争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思路却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需要不断改进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胡如雷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继承与发展了陈寅恪史学,并有所创新,从而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许多研究理念和方法,很多到今天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1]胡如雷.怎样研究隋唐五代史[J].文史知识,1983,(7).
[2]胡如雷.论武周的社会基础[J].历史研究,1955,(1).
[3]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方笑一,选注.唐宋八大家散文选[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
[5]刘怀荣,等.唐诗宋词名篇导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胡如雷.中国大百科全书名家文库·唐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7]胡如雷.抛引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8]张力.管仲评传[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9]胡如雷.李世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M].北京:中华书局,1979.
K061
A
1672-4658(2016)01-0131-04
2015-11-14
李俊生(1970-),男,河北邢台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