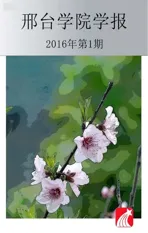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局限性
2016-03-02张春城
张春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刑事诉讼法学,北京 100038)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局限性
张春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刑事诉讼法学,北京100038)
近年来,一些影响全国的冤假错案碰撞着国人的神经,人们经常发现,冤假错案往往与刑讯逼供联系甚密,社会上下对刑讯逼供嗤之以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势而上,以遏制警察非法行为为主要推动力的排除规则犹如一剂“灵丹妙药”,被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是,通过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史及我国的司法实践,我们不难发现,排除规则并非人们想象的完美无缺、“对症下药”,其具有自身固有的局限性。必须通过侵权制裁、内部惩罚等方式,合理引导利益流向,才能有效规范警察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局限性;警察权
1914年,通过威克斯案(Weeksv.United States)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联邦司法体系范围内的适用。1961年,通过马普案(Mappv.Ohio),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由联邦扩大到各州。排除规则始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高举人权大旗。但是,伴随排除规则产生、发展的过程,其例外情况不断出现,进而影射出排除规则的局限性。
一、非法证据本身的认定具有主观性
以违反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为例,在刑事诉讼中检方使用通过政府强制手段获得的被告人、供述应予以排除。但是,关于“强制手段”、“自愿标准”,法庭往往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境决定被告人供述是否可以采纳。在某些案件中,警察讯问的方式是非常粗鲁的,供述的非自愿性显而易见,无需争议。但是,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强制手段不是特别明显甚至是隐蔽的。法官需要根据每一案件中的具体情境加以判断。例如,在切姆伯斯诉佛罗里达州(Chanbersv.Florida309U.S)一案中,法官以“被告被关押且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警察延长讯问时间”为依据,裁定获得的证据不可采纳;在罗杰斯诉理查门德 (Rogersv. Richmond)一案中,法庭根据“连续超过一天的讯问,威胁嫌疑人如果不招供就将其妻子拘禁起来”的情境,认为该供述是非自愿的,不得在审判时采纳。
面对“自愿性”审查中存在的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例如,警察应将被逮捕人及时送到司法官面前,如果警察没有这样做,而是拖延了一段时间,在拖延期间获得的证据即使自愿,也应该排除;“米兰达规则”,为供述的可采性设置了相关标准。但是,推延期限的判定、“米兰达规则”告知程度的认定标准等问题随之而来。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1]、五十四条[2]的规定,对于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的言辞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通过法条我们不难发现,在“非法证据的认定”、“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存在较大歧义。具体而言,即我们如何认定法条中提到的“非法方法”。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5条[3]对“非法方法”作出了相关规定,但显然异议仍然存在;再者,如何认定“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5条认为:应当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司法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显然过大,容易引发争议。
非法证据认定的复杂性会加大裁判者的主观性,进而导致排除规则适用的不确定性,这将导致司法权威的下降。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警察自由裁量权之间具有紧张关系
遏制理论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基础,即遏制警察的非法行为——警察会因自己的错误而导致其收集的证据在法庭上失效,那么警察会更加谨慎。但是其对警察威慑的影响力正在下降。根本原因在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警察的自由裁量权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从美国非法证据排除“善意例外”的产生发展可见一斑。
1976年,在斯通诉鲍威尔案(Stonev.Powell) 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怀特指出:“如果警察是善意的,并非故意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不能达到有效遏制警察违法行为的效果,不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84年的利昂案(UnitedStatesv.Leon) 以及之后的克鲁尔案(Illinoisv.Krull),其分析思路都是:排除规则的目的聚焦在威慑有责的警察,由于警察之外的人的错误所产生的非法证据,因对未来警察不端行为不会产生威慑效果,不应被排除。
但是,200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赫尔英案(Herringv.UnitedStates) 创设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善意例外”的新类型。与其他案例相比,警察的合理信任是基于其同事的疏忽大意的错误,发生在警察机关内部,并非其他司法部门。这无疑缩小了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范围,排除规则威慑功能正逐步弱化。
在赫尔英案之前,法院主要采取结果主义立场:只要警察的非法行为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取得的证据就予以排除。而在赫尔英案中,法官首次将警察违法取证时的心理状态考虑在内。联邦最高法院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应仅限于警察故意的、存在重大过失的行为,或者在一定情况下可能重复发生的、系统的失误。这折射出:排除规则在规范警察裁量权方面的尴尬、无奈。
一方面,警察的执法活动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应急性,且追求反应的迅速、破案的效率,而规范警察执法权的规章制度具有详细性和条理性。两者之间的矛盾随即产生。如果事后,我们拿规章制度去审视警察的执法行为,甚至将其冒着生命危险收集的有关证据予以排除,似乎有“事后诸葛亮”、“鸡蛋里挑骨头”之嫌,这对警察也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警察的制约具有事后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看到这样的情景:警察抓获犯罪嫌疑人后,锦旗“拍马赶到”,上级主管部门表彰随即而来。但事实却是,案件只是宣告侦查终结,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此时的犯罪嫌疑人并非法律上的“真正的罪犯”,必须经过法院的审判才能最终确定其有罪无罪。那么在警察已经受到嘉奖的情况下,事后在法庭审理阶段将其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阻力可想而知。
三、惩罚犯罪的社会期待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矛盾
排除规则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控制犯罪的社会需求与保障人权博弈的过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对宪法的自由派解释非常盛行,以沃伦为首席大法官的联邦最高法院借助司法权发展了许多有利于个体的规则,旨在帮助个人对抗政府。1961年的马普案(Mappv. Ohio)就是一个例子。该案例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由联邦法院扩大至各州法院。排除规则挥舞着人权大旗,惩罚犯罪是法院退而求其次的目标。从70年代开始,在伯格法院与伦奎斯特法院时期则更倾向于惩罚犯罪。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创设并发展了一系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排除规则适用范围不断缩小。“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对犯罪控制的要求猛然增强,以保守著称的罗伯茨法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又有一些新的变化。2009年,赫尔英案(Herring v.UnitedStates) 将其对排除规则的态度表露无遗,罗伯茨亲自撰写多数意见,他认为:适用排除规则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警察的非法行为是故意为之;二是警察非法行为的可归责性必须达到值得以可能让罪犯逃脱惩罚为代价。这无疑释放了这样一种信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更加谨慎,法院更倾向于惩罚犯罪。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属于一项程序性的制裁措施。一般而言,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具有较高的证明力,甚至是案件侦破与否的关键。排除规则的适用使政府不会从自己的错误中获益,却剥夺了社会因此而享受到的收益,极易导致放纵罪犯的不利后果,社会为政府的行为买单,这大大降低了社会的期望值。
在信息交流日益快捷、频繁的时代大背景下,司法机关承受着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这导致舆论绑架司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排除规则,将明显犯罪的人减刑或释放,必然招致社会的强烈反对,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法院的裁决有可能被改判,这将导致司法公信力、独立性的严重丧失。反之,如果法院对排除规则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尽量避免对其加以适用,以减少类似状况的发生,求得司法审判与社会预期的平衡,那又必然导致在实践中的排除规则使用率偏低。这使得排除规则只具有理论上的光鲜外衣,却面临“播种种子,毫无果实”的尴尬局面。
四、结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的动因主要是遏制警察的非法行为,保障社会中潜在的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进而促进司法公正。每一种法律原则、规范在设立伊始出发点和想法是好的,但从静止的条文过渡到活生生的司法实践,现实远没有想象的顺利,排除规则也不例外,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排除规则的例外不断产生,从中我们就可窥探一二。经上文分析,排除规则在诸多方面具有局限性,并非完美无缺。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加以改进:
(一)增加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制裁的种类。首先,在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这种程序性制裁措施之外,应引进侵权赔偿的制裁方法,即对某类案件,如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对使用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在保证其真实性、可靠性的基础上予以应用。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真正的罪犯,其可能因为排除规则而受益,从而逃避法律的制裁;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辜时,排除规则虽未使其遭受更深伤害,但是他本来就不应该被侦查,被追究。所以排除规则的利益流向了应该受到惩罚的罪犯,并非以恢复受害人损失为导向,故应当赋予被伤害人及其近亲属提起民事侵权之诉的权利。其次,扩大对非法证据进行程序性制裁的种类。增加程序性制裁的种类,形成对非法证据处理的过渡地带,不仅可以避免“过渡制裁”和“威慑不足”的尴尬,为裁判者提供根据违法行为轻重程度进行选择适用相应手段的机会,而且可以避免由制裁方式单一引发的回避适用问题。如责令警察恢复名誉、恢复原状;责令警察重新进行侦查行为。
(二)实行警察内部审查与惩戒。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警察的非法行为具有滞后性,对其本身的威慑作用也是有限的,如果警察的违法行为轻微,其既受不到排除规则的干预,又不会受到实体惩罚,极易产生“打擦边球”的情况。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是侦查、检查机关,侦查人员并没有直接受到制裁,本应受到惩罚的个体被集体或国家责任所替代,责任自负的原理没有得到基本体现。只有当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后,其才可能受到实体法律的制裁。但即使被追诉,侦查人员被起诉的罪名往往是刑讯逼供等职务性犯罪,被追究为故意伤害的少之又少。所以大量的非法侦查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及时的监督和惩罚。而通过内部审查和惩戒来规制警察权,具有诸多益处:首先,将警察的规范执法行为与其职务、工资福利挂钩,使其成为业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会更加直接有效地遏制警察的非法侦查行为;其次,有利于保障警察充分且正当的行使警察权。警察面临的工作往往具有突发性、紧急性、暴力性,所以警察的行为须应时、应景来考量,通过司法部门来审查警察,可能是不专业的。由侦查机关内部进行审查,更能恰当地拿捏尺度,使其心服口服。
当然,为了避免警察袒护警察现象的发生,尝试建立侦查机关与诉讼结局直接联系的侦查模式,促使侦查机关有足够的动力追查本系统内部的违法行为也是十分必要的。
[1]《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2] 《刑事诉讼法》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的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
[3]《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5条:“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害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4]马明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警察自由裁量权[J].政法论坛,2010,(7).
[5]陈虎.程序性制裁之局限性——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例的分析[J].当代法学,2010,(2).
[6]贺红强.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威慑功能的弱化——兼评赫尔英案对“善意例外的扩张”[J].河北法学,2013,(4).
[7]姚莉.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J].法律科学,2012,(1).
D925.2
A
1672-4658(2016)01-0082-03
2015-10-28
张春城(1990-),男,河北沙河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院刑事诉讼法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