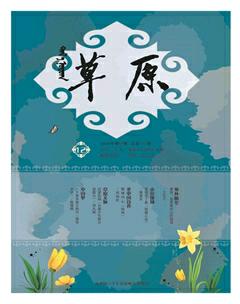归来三题
2016-01-05赵健雄
赵健雄
归来三题
赵健雄
回家
旧事如梦,也早就像梦一样逝去了。这么些年来,我很少回顾,甚至刻意忘记。
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说,掉下两片树叶,就会砸到一个诗人的脑袋。不管正常不正常,那时几乎遍地诗人。这当然比再早些日子,随处可见身着绿军装的红卫兵更接近一个伟大的年代。
我在那个年代,凑巧写诗。
其实也不完全是凑巧,那个年代,凡有理想的青年,谁不写几句诗呢?舍此也无以施展你的理想与才华。
就因为写诗,我从一个插队知青,当上报社副刊编辑,最后落到《草原》,在恰当的气氛与条件下,创办了《北中国诗卷》。
现在想来那真是个如梦一样的年代。
有幸在那个年代留下足迹与记忆无疑是此生的福气。
但我已很久不想这些事情了。勾起旧忆,乃至又把我引入当年气氛中的,是“呦呦诗社”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是当初的搭档贵荣。
当初我俩协同办刊,让《北中国诗卷》成为一面飘扬的旗帜。小尚本不写诗,却很快适应与担当起稿件编辑、版面设计与组织诗歌活动等一系列工作,对当年只有二十几岁的他,无疑是个挑战。正是从那里起步,他逐渐成长,最终成为内蒙古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的重要组织者。
夏天,我正在北戴河度假,他似乎无意间向我发来讯息与邀请:重返诗歌的草原。
这些年,我很多次回到塞上,但与诗歌几无关联。我与知识青年一起来回乡,陪导演去草原挑演员,做内蒙古电视台的新春晚会,我也参与过一部反映鄂尔多斯的政论片的制作。
尽管这里面也有些诗歌因素,却从来没有一次是以诗歌的名义进行的。
记得那次做晚会,我就带着一本自己早年的诗集,从中吸取灵感与养分,甚至为晚会写了不止一段诗歌供斯琴高娃等朗诵。至于卓·格赫的电影,本身就是一首影像织出的纯美诗歌。
如今回到真正的诗人中间,面对着大街上即使相遇也不一定都能认出的老脸,我感到十分亲切与坦然,仿佛岁月并没有消失,仍为诗歌所浸染。
居然看到一则将近三十年前写给白涛与梁粱,说打算来包头与呦呦诗人接触与交流的纸条。它们已是有关诗歌的文物。
在游逛了真正的草原再回到呼市时,文化活动家范枚子女士在她的沙龙里,组织了别具一格的诗酒晚会,山西诗人潞潞闻讯与朋友专程从太原赶来相聚,叫我非常感动。他带了一本新出的旧著《无题》,其中作品均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令人觉得时光并未流去,而被诗句凝固下来。
先后见到了仍在写诗并大有长进的张天男、阿古拉泰、蒙根高勒、蒋静、塔娜、温古等老朋友,也见到了热爱诗歌却以小说名世的白雪林与现在成了茶叶之路研究专家的邓九刚;更多是新朋友,包括一路安排我们采访的《草原》现任主编任建、编辑部主任阿霞、办《传承》的黑梅等;几个年轻女诗人与艺术家上台展读我的旧作,更叫人想起许多往事,感慨之余恍若隔世。
充满诗意的时代不再,岁月老矣!
但新人还是辈出,这次结识了以主持人身份名世的王锦江,新旧诗皆出色,更合我意的是,他把诗歌当作对社会的宣言与面向大众的表达,而不只是圈子里的自我玩味。从中看到诗歌进一步拓展与光复的希望。还有许多新进诗人,则来不及相会。贵荣不再是当初的翩翩少年,却依然风度与气质俱佳。与我说起这些年来经营《草原》的过程,一路走来,呕心沥血,极不容易。如今担子已交给后任,舒一口气的同时,能觉出他还是十分怀念那段岁月。
对我来说,《草原》只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于贵荣而言,却是半辈子的奋斗。酒席上不免感慨,仅有七年工作经历,却在二十四载后仍受如此礼遇。目下中国还能找到这样的老东家吗?
记得当年说过一句多少有些狂妄的话,即“凭着自己是《北中国诗卷》编辑,走到国内任何一个偏僻的县城都可以找到同道”。事实上我从来没有以这种身份去四处游历,时过境迁,它也成了有自嘲意味的笑话。但回到内蒙古,却时时处处仍可感到朋友们如当年一样的热情。这不像如今的现实,却正是现实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恐怕也无力回归了,我早就是诗歌的逃兵,尤其在旧日诗友面前,感到非常惭愧。
即便有原因,就算当初我已认识到一个理想与浪漫的时代结束了,冷峻的现实需要有更加直接的应对和表达方式。但诗歌不也同样可以成为“直接的应对和表达方式”吗?
所以只能怪自己三心二意,只能怀抱着一份歉疚之情为诗歌与所有热爱诗歌的朋友祝福,而我已是一个回不了家的旅人。
腾格尔的草原
腾格尔,蒙古语音译,汉语的意思是天,所以上述这个词组也可以解读为“天上草原”或“天堂草原”。至于大家熟悉的腾格尔是位流行度很广的歌手,具有标志性意义。他唱的《蒙古人》几乎就是民族精神的写照与张扬。
腾格尔的家乡坐落在从前的伊克昭盟,现在改称鄂尔多斯市,近年来因为经济迅猛发展与随后碰到的问题举世闻名。
仅仅花费十年时间就平地而起的新城康巴什,走进它时真有跨入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尤其晚上,灯光闪耀,描画出如梦如幻的夜景。那些年,当地经济年增长达40%,GDP总量很快超过香港,这就像步步登天,我开玩笑说,如果按此速度发展,用不了多少时间,鄂尔多斯就有可能成为全球的首都。事实上,康巴什也确实显示出此种气度,城市规划与建设,极有派头。身临其境与身处其时,几乎无人不为之鼓舞与疯狂。
几年前有朋友筹拍一部总结鄂尔多斯发展经验与精神的多集电视专题片,叫我参与策划与撰稿,正因为完全是局外人,我才保持了某种程度的清醒,这种清醒却遭到质疑。如果当初就来此地体验实景实况,(制片方提出了这个要求,以为非如此不能准确写出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让感性淹没了理性,恐怕也难免陷入痴迷。其时此地随后遭遇的问题已有所显露,但当事人仍不大愿意面对。
有雄厚的资金支持,那一阵儿鄂尔多斯就开始了相当力度的草原治理与沙漠改造,但比较一座城市的崛起,这是大得多的工程,也不太容易取得具有震慑性的效果。
就在不远的腾格尔家乡,便处于几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状态,仍可看见传统的草原与草原生活。
我们是在告别康巴什后来的鄂托克旗,一边漫游,一边往额尔和图赶路,原想当天到腾格尔家住宿,因为耽于沿途美景而未至,第二天才抵达。
腾格尔父母都已去世,留下一排粉饰得很整洁的房子请人代管着,屋后有一片覆盖了“腾格尔林”的小小丘陵,树着的石碑上,是原自治区政府主席布赫的题词,周围郁郁葱葱。
随处都可看见牧民日常生活的许多痕迹,简单而深沉,我喜欢。
腾格尔写过一首歌叫《天堂》,唱的就是这种原生态:
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哎耶
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哎耶
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哎耶
还有你姑娘这是我的家哎耶
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
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
在他心里,额尔和图无疑比康巴什更像天堂,而这两种相距甚远的文明状态竟如此靠近。是不同历史时期与背景下人们追求、努力及苟延的结果。
事实上,天底下并没有完美。
有一种说法叫发展才是硬道理,康巴什奇迹曾经令几乎所有鄂尔多斯人兴奋并受益。可是高速发展并非能够永远保持持续的状态,随着外在形势的起伏变化,煤炭与房地产价格滑落,资金链断裂叫差不多所有当事人陷入难堪的境地,类似故事如今比比皆是。当年谁都在挣大钱,即使不挣钱的居民也有数额不算很小的政府补贴,现在又几乎谁都有债务在外面要不回来,被欠了几个亿的债权人所在多有。鄂尔多斯法院专门调集一批人来加紧处理此类事务。但即使如此,当地居然仍有雄心与财力举办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并弄得十分气派。我们到的那天,正是闭幕式,碰到道路管制,百姓似乎对此颇有意见,也叫人想起一句老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而额尔和图尽管看起来像是与世完全隔绝,却也未能逃脱一波又一波人间纷争的干扰与侵入,很难想象这么偏远的地方,也会有和其他地方一样的“文革”动乱。苏木范围内最有文化的腾格尔父亲,就曾在运动中被当成“国民党特务”打断两根肋骨,还叫人捅了六刀。老人是佛教徒,对当初残害他的人很宽容,认为他们也是受害者,不准儿子们有报复举动。不久到来的改革开放中,当地生活水平提高并不算慢,但腾格尔姐弟五人还是都离开老家,其中有两个还去了国外定居。
显然额尔和图也不见得就是天堂,否则为什么要离乡出走呢?
但即使到了远方,腾格尔仍然思念着故土,他的歌也确是真情流露。生活就这么奇怪,人也这么奇怪。
那么,到底是康巴什更接近天堂,还是额尔和图本身就是天堂?
作为一个远方的行者,我当然喜欢草原,因为自己只是过客。但如果长久耽于草原,恐怕也会和腾格尔与他的姐弟一样,寻找外出的道路。
如今留在草原生活不易,像腾格尔父母生前那样养二十多头牛、两百只羊不易,下一代孩子从小就得去旗里上学也不易。世界不一样了,人们对生活的理解与追求也不一样了。现在牧民也很少住蒙古包,他们的房子大多宽敞明亮,装修得甚至比城里人还好,这是一种自愿的选择,而生活同时失去了若干传统的韵味。
家家门前的飘扬的禄马风旗仍在,喝的也还是奶茶炒米吃的还是手把肉,但大量现代化因素确实已经渗入了现实。
那么,腾格尔的天堂是不是仅仅属于幻象?
作为一种生产与生活形态,草原文化无疑是历史遗存,由来已久,却渐渐淡出主流。正因为不甘于它的消失,才有像腾格尔这样的歌手,唱出《天堂》,试图挽回其亡魂,也有无数如我这样的旅行者,到这里来体会地球与人类更近于远古的韵味。
眼看着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改变,仅仅唱出心中的梦想显然不够。腾格尔发声之外还选择了种树,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诗意地生存——读王万里诗集《北方的时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草原》编诗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市场经济,人们在生活中所能作出的选择极其有限与单一,这是诗人辈出的前提。至于此前,连转动一下自己脑子的自由也没有,动辄得咎,谁敢胡思乱想与胡作非为?
那时候已经可以有限度地思想了,历史上把它称作“思想解放”的年代。至于是诗歌而不是其他表现形式成为许多人首选,也许与其更高的精神性有关。
后来时代就变了,思想的领地并没有进一步拓宽的迹象,现实操作性却一下子丰富起来,乃至本来热衷写诗的年轻人,有不少做生意或干实业去了,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等过了若干年,有个潮流,是挣足了钱的早年诗人们,又回过头来重新从事精神上的创造,这一定是他们对过于现实与庸俗的生活感到了餍足。
年龄大致与之相当的王万里不在此列,他一直从事实际工作,当干部与后来做生意,直到六十岁,突然对诗歌发生兴趣,乃一发不可收,几年时间出了三本诗集,并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在我的经验里,这是个罕见的例外。
就诗论诗,他的一些作品,写得不错,譬如这首《小草望着大地上的事物》:
小草望着大地上的事物
芨芨草、马兰花、三叶菜
亲切的面孔多么温暖
仿佛兄弟姐妹
守着自然的血脉
小草望着大地上的事物
一阵风吹过,草尘摇着大地
小兔支出耳朵
哦,有多少心跳
需要另一颗心的倾听
小草望着大地上的事物
一阵雨落下
这疼痛多么清凉
一只蚂蚁
在雨中搬运着闪电
小草望着大地上的事物
一群牛羊缓缓走来
它们的目光是一颗颗晶莹的露珠
无辜而又充满忧伤
小草望着大地上的事物
然后是久久的沉默
大地深处
珍藏着汗水
和所有生命的根
首先让我从中感受到的,是一种精神性,用古人的说法,天人合一,王万里以最微不足道的小草的眼光来观察与体会眼前这个纷繁的世界,叫自己的灵魂得以升华。可以想象在当下这个社会,他的日常生活之忙碌和杂乱,更多当事者用虚荣与酒色来平衡自己的心境,只有极少人想到诗歌也能充此大任,并且颇有成效。
这首小诗自成一个世界,你说不清楚它讲了些什么,却又感到什么都在其中。而凡是能够自创一个世界,即使只是小小的世界者,必有宽大的胸襟。
在诗歌领域,王万里当然是后来人,却又是先行者。他代表了那些即将和终于明白金钱与权力并非人生全部,甚至不能作为主要依托的觉悟者,在行将进入暮年时,重新体验与领悟人生,某种意义上,获得了一次重生。
至于选择诗歌还是别的什么载体,则充满了偶然性。
王万里选择诗歌,是因为他对语言有特别的敏感,更因为如今他那些单纯而有些混沌的愿望,以诗句来表达无疑更加合适:“我要做一个无忧无欲的人/愿湖水再洗一次灵魂/朝阳的辉煌只是眨眼一瞬/草原湖啊,我的母亲/天高远,青山永存/我将永远浸润在一座湖的/清澈里。”
以理性的话语或其他手段,能表达这种情绪于万一吗?
一个偶然机会,让我看到王万里新书《北方的时光》,我也是一个对时光敏感的人,当年出的两本诗集,题目就都与之有关,它们叫《明天的雪》和《最后的雨》。
如今雨雪过后,我耽于江南的生活中几乎已没有诗歌了,翻看王万里的集子,想起过去的北方时光,难免百感交集,于是写下这些文字,算是以他人之酒来浇自己的块垒,也表达对一个并不年轻的年轻诗人的衷心祝贺。
生活能够给予我们的,到底是些什么?并非不可或缺的诗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领有的高贵礼物,那些得以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诗意地生存着的人,有福了!
(责任编辑杨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