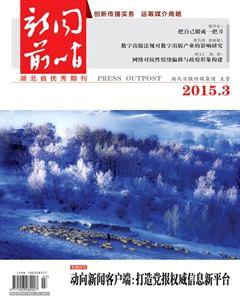“贝娜周”带来的新闻伦理思考
2015-12-23潘锡珩
◎余 彬 潘锡珩
“贝娜周”带来的新闻伦理思考
◎余 彬 潘锡珩
1月16日,33岁女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去世,引发的舆论关注长达一周,人称“贝娜周”,大大超出了该歌手 “应该享受的待遇”。奇特的是,关注的焦点不在死者本身,而在新闻伦理之争。
一、姚贝娜病逝引发舆论“贝娜周”
早在姚贝娜病重期间,已有不少纸媒和网媒对她的病情连续报道,进行了预热。她病逝后,更是掀起了超常规的信息大轰炸。
我们检索了她病逝次日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市民类报纸。深圳当地的晶报、深圳晚报,姚贝娜家乡的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北京的新京报、京华时报等,各报基本上都拿出了至少一个版进行大篇幅报道,深圳晚报甚至多达11个版面。网络上的报道更是铺天盖地,从传统的门户网站,到新兴的微博、微信自媒体,信息数量多到难以统计。不仅信息数量多,热度保持时间之久也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由姚贝娜病逝引发的诸多话题,在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中持续发酵,时间长达一周,堪称舆论的“贝娜周”。其间,不断有新的事实被曝出,新的话题和观点被引出。
一个歌手去世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报道和关注,在信息碎片化、易逝化的今天,十分反常。我们注意到,与她同时去世的有高官、院士,各媒体都是常规处理,形不成舆论热点。
有人分析可能是与姚有关的机构在背后操纵炒作,一次又一次挑逗媒体的“敏感部位”,引发媒体阵阵尖叫,自然而然造成舆论热点。有人指出,保持姚贝娜的舆论热度,也就是保持姚机构的知名度。与姚相关的机构仿佛在说:看看我的炒作实力,我可以用唱歌得第一炒她,也可以用乳腺癌炒她,甚至也以用死亡来炒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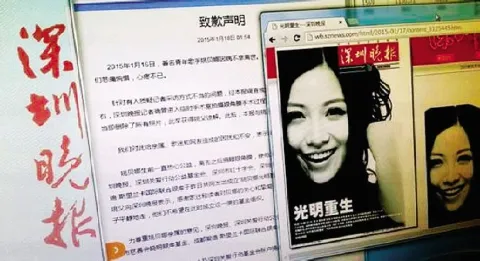
为何媒体的伦理话题容易成舆论热点?中青报评论员曹林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1.媒体人是舆论界最活跃的群体,行业话题易引爆;2.参与门槛低,且容易让讨论者有道德高地的满足感;3.骂媒体很安全。
这种炒作手法很像旧时大户人家老爷做寿,要想隆重热闹,就请戏班子唱它几天几夜,让周围十里八乡的人们听个够,而不是让老爷自己登台表演。
二、“记者在病房外等她死”引爆舆论
引发这场持续一周大讨论的导火索,是有网友撰文斥责大批记者写好稿子在病房外“等待姚贝娜死亡”。
就在姚贝娜病逝的当天 (16日)晚8时许,@掀起你的头盖骨(自称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准新闻人)的网文《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文章开篇第一句便是:“姚贝娜去世之前,病房外挤满了记者,他们在等,等她死。”还配有众记者眼巴巴盯着病房的现场照片。
记者们对工作的热忱和坚守,竟然在此人眼中变成了盼着姚贝娜死,变成了可恨可恶的冷血行为。不管怎么说,结果是@掀起你的头盖骨利用媒体的敏感,成功设置了议题。顿时引发无数转发和评论,有的斥责,有的辩解,很快形成了第一波新闻伦理之争。
那么问题来了。你是如何知道记者们在“等她死”?记者在门外等待的,是姚贝娜的一切最新消息,包括死讯,也包括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并不是一门心思在等待她的死亡。
作者提到1994年黑人摄影记者凯文·卡特拍了苏丹一个濒死的儿童,作品《饥饿的苏丹》获得普利策奖,随后被指责见死不救。在作者笔下,等待死讯的记者,一如虎视眈眈盯着小女孩的秃鹫。 “新闻记者可不就是秃鹫么,一只只盯着普罗大众苦难的、欢乐的、生老病死的掠食者。”
但这两件事显然不能相提并论。且不说卡特在拍摄完那张照片后,为女童赶走了秃鹫,当医生在病房里全力救治姚贝娜时,记者们不等在病房外,难道应该进去“帮忙”?所以,记者们等在病房外是正常采访,没有不当之处。
时间前溯至一个月,手术室自拍事件也曾引发过人们对职业伦理的讨论。事情刚被曝出时,很多人骂医生冷血,后来医生方面回应,当时整个手术团队不吃不喝7小时,为患者保住了一条被其他医院判截肢的腿,一则是很激动,二则是为了纪念在老手术室里最后一台手术,此外,在行业内部也有术后拍照的惯例,基于这几个原因,医生们拍摄了合影。
这两件事情很相似——很多时候,业内人士的职业习惯,在外人看来,是冷血,是无情。
三、“记者伪装医生偷拍尸体”火上浇油
就在网友们还在争论记者们能不能在病房外“等她死”的时候,次日(17日)凌晨,@娱乐圈揭秘在微博上曝出另外两个题材,再次煽动大众的情绪,将舆论的指责声迅猛地引向了深圳晚报:其一是“深圳晚报记者扮成医生助理进入太平间,对遗体进行惨无人道的偷拍”,其二是“深圳晚报擅自倡议成立姚贝娜光明基金”。17日上午,还有网友还曝出“记者偷拍被现场揭穿后高呼 ‘新闻自由’”、“混乱中推倒姚母”等猛料。
这就好比是,快要熄灭的炉火又被浇上一瓢油,争议再度升温。主流的观点认为,深圳晚报击穿了新闻职业道德底线,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深圳晚报第二天(18日)被迫发表简短致歉,承认该报记者确曾进入临时手术室拍摄眼角膜手术过程。当亲属表示拍照不妥时,记者删除了所有照片,获得了姚父谅解。至于以姚贝娜命名的基金,报社方面及时撤回了倡议,并将已经捐助的两笔款项予以退回。
事情没有完,4天后奇峰突起,1月22日出版的深圳晚报全面“翻供”,在头版用粗体字打出“没有偷拍遗体”“没有高呼新闻自由”“没有推倒姚贝娜母亲”等并列标题,配发数千字的社论《我们为何一直保持沉默》,又用两个版还原了各方口中的姚贝娜角膜捐献采访过程。总之,该报声明自己的记者不是进太平间拍尸体的小人,而是进手术室拍角膜捐献手术的爱心人士。
真相到底如何?现在或许还不能下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热了整整一周还是“娜”么热。
四、怎样看待持续不断的新闻伦理争议
报道死亡这一类 “白色新闻”,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应该成为新闻同行的共识:
1.记者采访应遵循基本的伦理和道德,让对象知情并同意。
2014年8月,美国著名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自杀后,美国广播公司(ABC)出动直升机对罗宾·威廉姆斯的家进行航拍直播,结果招致了公众的激烈批评。迫于压力,ABC在第二天就道歉并且撤下了视频。
戴安娜被“狗仔队”疯狂追拍,奔逃中出车祸身亡,记者的行为颇具负面色彩,招致了广泛批评,以至于独家拍摄的临死前的表情照片卖不出去,没有一家媒体采用。
在西方,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的观念深入人心,都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权利却常常发生冲突,记者采访要做到知情并且同意。记者应该在公众对信息的需求,与可能造成的潜在伤害或不适之间寻找平衡点。骗采或强采都是要不得的。
进行新闻采访,并不等于不顾及采访对象的感受,尤其是在报道公众人物死亡的新闻时,不得逾越道德和伦理的底线,应当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
但也应该注意到,用泛道德化和滥情的视角去看待一切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当人们以特定职业承担社会分工时,普通人的情感是需要做出一定取舍的。无法想象,外科医生拿着手术刀,为等待救治的患者啜泣;验尸的法医因为同情可怜的死者,而不忍举刀。一些特定的职业中,工作状态的他们必须要把悲悯暂且收在心中,用职业的、专业的方式来体现自身价值。
2.记者的职务行为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
(1)从科学角度理解“秃鹫”,生态链中的一环。
在一些人的批评声中,把记者比作秃鹫。在这些人看来,动物是分好坏的,就像幼儿园里小朋友说小白兔好、大灰狼坏,没有完整的生态观。其实,自然界动物哪有好坏之分?各有各的作用,大家相互竞争而又彼此依存,都是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秃鹫食腐,是大自然的清洁工,是生态中重要的一环。秃鹫如果改食素,它的名声倒是好听了,但整个生态就毁了。
经纪公司希望媒体帮忙炒作、亲属希望媒体帮忙留点念想、读者希望看到真实细致的内幕、记者希望更快更多地获取独家信息——而这,正是新闻传播中最常见的生态。
具体到这次事件中,记者守在病房外的做法无可厚非。一来,记者报道姚贝娜去世的新闻,满足了大众知情权。二来,记者没有扰乱就医秩序,更没有影响医生对姚贝娜的抢救。三,记者没有伤害姚贝娜家人的情感。
一朵鲜花是怎样凋零的?众多媒体持续数天的同题报道,唤起的是人们对生的热爱。
(2)如何看待职务行为与“攫取利润”,挖新闻不能伤害对方。
获取利润是每一个行业存在的充要条件,不是坏事。医生治愈病人,正常收费,天经地义,如果治愈了病人分文不取,这一行就不可能持续发展。但如果多开药品,做不必要的检查,赚黑心钱,就会被谴责。关键要看获取利润的后果,是对当事人和社会有益还是有损。
全世界每天都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死亡事件发生,媒体无视一些,淡看一些,突出报道一些,记者和编辑是基于这样一个考量:大众是否关注,这一条新闻有没有市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媒体挖新闻时要尽量避免对采访对象的伤害。要在二者之间走钢丝。
至于为什么媒体能在人去世一分钟就发出那么多报道,纯粹是新闻操作层面的技巧,是新闻界的惯例,目的是在第一时间把又多又好的信息传递给受众,与道德无关。新闻事件本身决定记者的报道,新闻人物何时死,报道就何时发出,记者编辑没有盼着早死早发的动机。
同时,对受众来说,哪家媒体最快报道鲜活丰富的新闻,受众就认同谁。而那些事先不做功课不准备素材,新闻发生之后才开始写稿的记者和媒体,必定慢一拍,不可能生存下去。
3.寻找当事人、公众和媒体的共同需求,谋求共赢。
媒体的根本属性,就是传播信息,满足大众知情权。姚贝娜是公众人物,她的一些事外界想知道,包括病情。既然经纪公司发布了消息,记者就必然会到场。如果像高仓健去世时封锁消息,媒体在一周以后才获悉,那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反过来看,如果没有一个记者到场关注即将离开人世的姚贝娜,她的家人会感觉凄凉,经纪公司会被指人走茶凉。
来看看牛星丽病逝后家属的表现。2009年的最后一天,牛老在家中病逝。得到消息的记者赶到他家的楼下,却都不忍敲门打扰。后来,牛星丽的女儿主动招呼记者进屋。记者陈博回忆道,他永远记得每个记者进门后先道歉的情形:“金老师,打扰您了”“金老师,您节哀”“金老师,我们问几个问题就走”。牛星丽的妻子金雅琴道:“我知道你们都是记者,这说明牛星丽还有人关注,你们问吧。”
姚贝娜病逝后,不同角色有不同需求——经纪公司希望媒体帮忙炒作、亲属希望媒体帮忙留点念想、读者希望看到真实细致的内幕、记者希望更快更多地获取独家信息——而这,正是新闻传播中最常见的生态。
(楚天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