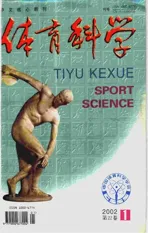体育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身份认同感、解释水平的调节和抑郁情绪的中介
2015-10-18王新新
黄 赞,王新新
1 问题的提出
纵欲消费行为是指消费者过度满足短期欲望需求,而忽视长远利益的消费行为[42]。纵欲消费行为的诱导因素是营销学的研究热点之一。Wilcox等人发现,与只包含不健康食物的选择菜单相比,消费者会从同时包含了健康和不健康食物的菜单中选择更多的不健康食物[55]。因为,消费者将后一菜单中的健康食品当成了纵欲消费(消费更多的不健康食物)后的弥补措施。在进行决策之时,消费者所考虑的信息类型也会影响了纵欲消费行为:当激发了自控信息之时,消费者更倾向于进行纵欲消费;而当激发纵欲消费信息之时,消费者将会约束纵欲消费行为[27]。这是因为,消费者需要找到自控与纵欲之间的平衡点——考虑了自控(纵欲)信息,就会倾向纵欲(自控)行为。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例如,May和Irmak发现,以往约束纵欲消费的经历会成为消费者进行纵欲消费的理由[32]。
观看体育比赛是人们重要的休闲和娱乐方式之一,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45]。因此,体育比赛对观众消费行为的影响是体育消费行为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涉及了比赛服装或纪念品的购买行为[12,44]、酒精消费行为[39,40]、对赞助商(品牌)的评价及其商品的购买行为[8,1]。但是,尚未有学者研究体育比赛对观众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本文选择体育比赛结果对观众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作为研究主题,是对现有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体育比赛结果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前沿性。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1)体育比赛结果是否及如何影响观众的纵欲消费行为;2)如何减少纵欲消费行为,引导消费者进行更为理性的消费。运用成就需要理论、社会认同理论、解释水平理论和自我损耗理论,本文推导了相关假设。以2014年巴西足球世界杯的电视观众为样本,本研究运用两个现场实验研究验证了假设。首先,本文研究了体育比赛结果对消费者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效果,并探究了这一因果关系的中间机制。本文还研究了有效控制纵欲消费行为的策略。本文认为,相比于获胜的情况,失利的结果更容易促使消费者进行纵欲消费。原因在于,由于观众的成就感需要,他们都希望自己所支持的运动队(员)能够赢得比赛;若比赛的结果是被对手击败,消费者就会产生抑郁情绪。抑郁情绪抑制了消费者自我控制能力,从而导致纵欲消费。本文还提出,在输掉比赛的情况下,激发观众的高解释水平状态能够有效地减少纵欲消费行为。
1.1 体育比赛结果与抑郁情绪
成就需要是一种内化的、出人头地的愿望[13],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要之一[38]。人们不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成就需要(直接方式),也可以通过自己所属组织的成功来获取成就感(间接方式)[30]。体育比赛是一种满足成就需要的间接途径[25]。在观看体育比赛之时,观众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情感倾向性——选择支持某一方,希望其获胜,而希望另一方被打败[57],并将比赛结果视为自己的胜利或失败[22]。但是,体育比赛没有剧本和彩排,是一个真实进行的过程[14],胜负结果难以预料。因此,在体育比赛进行之时,观众时时都体验着希望成功和害怕失败的情绪[11]。在赢得比赛胜利的情况下,观众得到了其所希望出现的结果,获得正向的情绪体验;而在输掉比赛的情况下,观众得到了其所害怕出现的结果,陷入负向情绪之中。那么,与赢得比赛的情况相比,输掉比赛的结果对观众的消费行为有什么影响呢?本文将比赛失利结果对观众情绪的影响作为切入点。
抑郁情绪是由于对现实和自我的消极偏见而导致的一种负向情绪状态[7]。显然,成功是成就感的来源。但是,不管做何事,人们都必须面对可能失败的风险。在失败的情况下,人们就会陷入抑郁情绪之中[35]。这是因为,在追求成就感受挫的情况下,人们可能降低对自我能力的信心,从而产生对自我的消极偏见,也就是抑郁情绪反应。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Metalsky等人发现,在期中考试之后,考试成绩可以被用来预测学生的抑郁情绪反应——考试成绩越差,抑郁情绪反应越大[35]。Abela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在进行大学的入学申请之时,申请的成功与否能够预测申请者的抑郁情绪反应[2]。在本研究的情境中,成就需要是人们观看体育比赛的主要动机之一[33]。在观看体育比赛之时,成就需要促使观众将自己视为比赛中的一份子,并将自己所支持运动队(员)的输赢视为自己的失败或胜利。根据已有的研究,在比赛失利的情况下,观众必然陷入抑郁情绪之中。据此,本文认为,相比于获胜的结果,观众对比赛失利结果的抑郁情绪反应更大。
身份认同感是指人们认同自己归属于某组织的心理状态[15]。Wann和Branscombe发现,身份认同感调节了观众的沾光行为[53]。具体地,相比于一般的支持者,死忠支持者(高身份认同感)的沾光行为更明显。不仅如此,在失利的情况下,高身份认同感的观众也不愿意“抛弃”自己所支持的运动队(员),而是极力为其进行辩护,并在公共场合故意地贬低和谩骂竞争对手[9]。不难看出,相比于低身份认同感的观众,高身份认同感的观众具有更高的忠诚感;即使在失利之时,高身份认同感的观众也愿意追随自己所支持的运动队(员)。基于此,本文认为,在比赛失利的情况下,高身份认同感观众的抑郁情绪反应更大。也就是,观众的身份认同感调节了体育比赛结果与抑郁情绪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地,相比于身份认同感低的观众,身份认同感高的观众对失利结果的抑郁情绪反应更大。
1.2 抑郁情绪与纵欲消费
在面对诱惑之时,消费者需要保持较强的自控力,才能保证长期利益的实现。比如,消费者不能因食物味道好而进食过量,不能贪图短暂的快乐而吸食迷幻类药物,不能因一时冲动而无节制地购物[47]。只有有效地控制冲动行为[17]并抵制即时欲望和需求[36],人们才能实施目标导向行为,实现长期目标[16]。在自控失败的情况下,消费者往往进行更多的纵欲消费行为,也即牺牲长期利益而满足即时欲望和需求。从本质上看,纵欲消费行为就是在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消费者选择及时享乐的短期目标[54]。那么,体育比赛是否影响观众的纵欲消费行为呢?
自我损耗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进行一段时间的自我控制活动后,人们的自我控制能力会下降,从而发生自我控制失败的现象[24]。这是因为,在进行自我控制之时,人类需要消耗某种资源,而这种资源是有限的且随着自我控制时间增长而衰竭[3]。自我损耗的直接后果是自控能力的下降,并将导致自控失败[4]。自我损耗现象可以借用肌肉疲劳的现象来解释:在一段时间的活动之后,人体的肌肉就会出现疲劳现象,导致肌肉力量的下降[20]。
根据自我损耗理论,本文提出,抑郁情绪反应将使得观众更容易进行纵欲消费。当处于负面情绪之中,人们需要努力控制住这种负面的心理感觉,以使自己迅速地摆脱负面情绪的纠缠和干扰[47]。根据自我损耗理论,人们的自我控制行为必然需要消耗有限的自我控制资源,导致自我控制失败。具体到本文中,在比赛失利的情况下,观众处于负面情绪——抑郁情绪之中;抑郁的情绪将加速观众消耗其有限的自我控制资源,从而导致自我控制能力的下降。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人类的情绪反应与自控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关系[19]。例如,负面情绪(如,尴尬、生气等)将导致更多的风险偏好行为[28]、暴力倾向[56]甚至暴饮暴食[43],原因就在于负面情绪降低了人们的自控能力。因此,在自我控制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观众更容易进行纵欲消费。
综合前文对体育比赛结果、身份认同感、抑郁情绪反应和纵欲消费行为之间关系的梳理和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图1)。
假设1:相比于比赛获胜的结果,比赛失利的结果增加了观众的纵欲消费行为。抑郁情绪反应在比赛结果和纵欲消费行为的因果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而观众的身份认同感调节了抑郁情绪反应的中介作用。
1.3 解释水平的调节作用
假设1提出,在比赛失利的情况下,观众容易产生抑郁情绪,进而导致消费者进行纵欲消费。与正常的消费行为不同,纵欲消费行为对消费者和对企业都是有害的。从消费者角度来看,纵欲消费之后,消费者往往陷入愧疚和后悔等负面情绪之中,并将减少再次购买行为[42,5]。从企业角度来看,后悔感不仅大大降低了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评价[23],而且也降低了消费者的满意度[46]。消费者的满意度被认为是重复购买、口碑效应和品牌忠诚等的关键影响因素[6]。另外,在后悔感较强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品牌转换意愿也较高[26]。因此,纵欲消费行为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影响了企业的营销绩效。不管是消费者还是企业都应该减少这种非正常的消费行为。那么,在自控失败的情况下,如何引导消费者进行理性消费呢?
在自我损耗发生之后,如何恢复自控能力也是自我损耗理论的研究主题之一。研究发现,激发被试的高解释水平状态有助于恢复自控能力[18]。解释水平就是个体对外界事物的心理表征状态[48]。当更多地使用本质的、核心的、抽象的特征来表征事物之时,个体就处于高解释水平状态;反之,当更多地使用次要的、具体的特征来表征事物之时,个体就处于低解释水平状态[49]。心理距离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解释水平,进而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决策[29]。Fujita等人发现,在高解释水平状态下,人们能够做出更冷静、谨慎、理性的决策,从而避免因短期目标而牺牲长期利益[18]。这是因为,高解释水平唤起个体的长期目标追求意识,增强了人们实现长期目标的动机,从而有利于自我控制能力的恢复[34]。纵欲消费行为的本质就是在自我控制失败的情况下,消费者在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选择了及时享乐的短期目标[54]。因此,激发被试的高解释水平状态能够恢复自我控制能力,从而减少纵欲消费行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如图2所示)。
假设2:观众的解释水平能够调节抑郁情绪反应在比赛结果与纵欲消费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具体地,激发观众的高解释水平状态能够显著地减少纵欲消费行为。

图2 本研究假设2的理论模型框架图Figure 2.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Hypothesis 2
本文将利用两个现场实验来验证假设。以2014年巴西足球世界杯的电视观众为样本,研究1主要验证了体育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以及身份认同感的调节作用和抑郁情绪反应的中介作用;在研究1的基础上,研究2则重点研究了如何引导消费者进行理性消费——减少纵欲消费行为。
2 研究1:体育比赛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
2.1 实验设计
研究1的目的在于验证体育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并验证其中间机制。研究1运用了现场实验的研究方法,采用2(比赛结果:输与赢)×2(身份认同:高与低)的双因素组间设计。与实验室研究相比,现场实验研究具备较好的外部效度。为了避免比赛队伍成为组间影响因素,研究1共涉及了3场比赛(6支不同的队伍)。
研究1利用了现场直播的巴西世界杯足球比赛作为实验材料。被试是比赛的电视观众,来自中国东部某城市。在巴西足球世界杯比赛期间,大量球迷聚集在诸如酒吧、大排档等场所观看现场直播的比赛。这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在比赛期间,本研究选择球迷聚集地展开实验,现场实验在每场比赛结束之后进行。为了掩盖研究的真实目的,被试被邀请参加一项“我的世界杯”活动,要求其根据自己真实的观赛经历和体验,填写实验问卷。所有被试需要独立填写问卷任务。
首先,被试需要填写自变量的测量问卷。被试需要报告其支持的球队(仅限于当场比赛的两支球队,实验员需要记录当场比赛的输赢情况),并填写身份认同感量表。身份认同感的测量参考 Wann和Branscombe的量表[51],采用九分利克特量表设计,“1”代表非常不同意,“9”代表非常同意。Wann和Branscombe的身份认同感量表共包括7个测项。在与两位教授讨论和商量后,研究1删除了其中的两个测项,主要原因是不适合中国观众的实际情况。剩余的具体测项包括“我很看重XX球队是否赢得比赛的胜利”、“我认为,自己是XX球队的忠实支持者”、“在世界杯期间,我经常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途径获取XX球队的信息”、“在生活中,我很看重自己作为XX球队支持者的身份”和“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XX球队的支持者”等5个测项。
紧接着,被试需要填写抑郁情绪反应的量表。参考Burroughs和Rindfleisch的研究[10],抑郁情绪反应的测量参考了Lovibond和Lovibond的抑郁情绪量表[31]。抑郁情绪量表是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的子量表,被心理学研究者广泛地用来测量正常人群(非精神病人)的负向情绪,具备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抑郁情绪量表采用九分利克特量表设计,“1”代表非常不同意,“9”代表非常同意。具体测项包括“我觉得没什么可期待的”、“我感觉很沮丧、心情低落”、“我感觉生活缺乏意义”、“我感觉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我感觉万念俱灰、心灰意冷”、“我感觉生活毫无生气”和“我感觉缺乏工作的动力”等7个测项。
最后,被试需要完成纵欲消费行为的测量任务。参考Mehta等人的研究[34],纵欲消费行为采用情景模拟法——要求被试想象一个决策场景。具体的决策情境是“一个好朋友就要去外地工作了,今晚准备邀请几个好朋友进行聚会。作为好朋友的你同意参加。然而,就在当天下午,公司老板打来电话,要求你准备一份明天上午就要用的重要文件。这份文件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才能完成,因此在参加聚会和准备文件之间,你只能选择1项。”研究1利用被试参加聚会的可能性(“1”代表非常不可能,“9”代表非常可能)来测量其纵欲消费行为。在这之后,被试还需要报告其性别和年龄等信息。
2.2 结果与分析
研究1共回收有效问卷169份,其中,男性131人占77.5%,女性38人占22.5%,平均年龄29.7岁,最小的被试19岁,最大的被试45岁。
检验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主效应。研究1对参加聚会的可能性进行单因素(比赛结果)ANOVA分析。结果显示,在比赛失利的情况下,被试参加聚会的可能性(=6.74,SD=1.23,n=83)显著地大于比赛获胜的被试组(=6.07,SD=1.27,n=86),F(1,168)=12.25,P<0.001。参加聚会的可能性对比赛场次和人口变量信息进行单因素ANOVA分析,没有发现比赛场次、性别和年龄对被试参加聚会的可能性存在显著影响。这表明,比赛结果显著地影响了被试的纵欲消费行为。具体地,在比赛失利情况下,被试更容易进行纵欲消费。
检验身份认同感的调节作用。在主效应存在的基础上,研究1还检验了身份认同感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1对参加聚会的可能性进行双因素(比赛结果×身份认同感)ANOVA分析。参考 Wann等人的方法[52],研究1运用中位数均分法将被试分成身份认同感高和低两组。双因素ANOVA分析显示,被试的身份认同感(α=0.93)显著地调节了比赛结果对参加聚会可能性的影响(F(1,168)=9.24,P<0.01)。具体来说,在身份认同感高的组别,比赛失利的被试参加聚会的可能性(=7.26,SD=1.00,n=43)显著地大于比赛获胜的被试组(=6.02,SD=1.12,n=42),F(1,84)=28.73,P<0.001,但是,在身份认同感低的组别,比赛结果对被试参加聚会可能性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失利=6.23,SD=1.31,n=43;获胜=6.12,SD=1.35,n=41),F(1,83)=0.15,P>0.1。这说明,身份认同感显著地调节了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作用。
检验抑郁情绪反应的中介作用。假设1表明,由于调节了自变量(体育比赛结果)与中介变量(抑郁情绪反应)之间的关系,观众的身份认同感进而调节了自变量(体育比赛结果)对因变量(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关系。为了检验假设1中的中介作用,遵循Preacher等人的建议[41],研究1建立了第1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其中比赛结果为自变量(虚拟变量:0=赢,1=输),抑郁情绪反应为中介变量,被试参加聚会的可能性为因变量,身份认同感为调节变量,而比赛场次、性别和年龄被设为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回归方程的协变量。按照Hayes提出的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检验程序[21],研究1估计了模型的回归系数(见图3)。回归结果显示,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26(SE=0.07,P<0.01),具有显著性。但是,在加入中介变量之后,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回归系数为0.09(SE=0.08,P>0.1),不再具有显著性。另外,抑郁情绪反应的中介效应系数为0.16(SE=0.05,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630,0.2560),不包含零,且比赛结果与身份认同感的交互项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12(SE=0.05,P<0.01),具有显著性。这说明,在模型中,抑郁情绪反应的中介效应显著地存在,并且是第1阶段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综合对研究1的分析,假设1得证。

图3 本研究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研究1)Figure 3.The Estimator of Model Including a Moderated Mediator(Study 1)
2.3 研究1小结
研究1的目的在于验证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作用及中间机制。研究1利用现场实验方法,获取了所需数据。研究1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检验了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主效应,在此基础上还检验了身份认同感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在检验中间机制之时,研究1建立了一个第1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利用bootstrap的方法估计了模型的回归系数。研究的分析结果较好地支持了假设1的观点。
3 研究2:解释水平的调节作用——如何减少纵欲消费行为
3.1 实验设计
研究2的目的在于验证假设2,即解释水平对纵欲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且研究2的结果也可以为假设1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证据。研究2运用现场实验的研究方法,采用2(比赛结果:输与赢)×2(身份认同:高与低)×3(解释水平:高、低与控制组)的三因素组间设计。为了避免比赛队伍成为组间影响因素,研究2一共涉及了7场比赛(14支不同的队伍)。研究2改变了纵欲消费行为的测量方法,以此提高实证结果对假设验证的可靠性。
与研究1相同,研究2利用了现场直播的巴西足球世界杯足球比赛作为实验材料。被试是比赛的电视观众,来自中国东部某城市。为了排除参加了研究1的被试,研究2选择了与研究1完全不同的球迷聚集区。现场实验在每场比赛结束之后进行。为了掩盖研究的真实目的,研究2也以“我的世界杯”的主题活动展开,要求被试根据其真实的观赛经历和体验填写实验问卷。所有被试需要独立完成问卷填写任务。
首先,被试需要报告其支持的球队(仅限于当场比赛的两支球队,实验员需要记录当场比赛的输赢情况),并填写身份认同感量表和抑郁情绪量表。两个量表的题项和设计与研究1一致。
而后,被试需要完成解释水平的操控任务。解释水平的操控方法参考自Wakslak和Trope的研究——启动被试思考事情的不同方向——目的或方法[50]。操控任务要求被试完成“我的看球故事”的回忆任务——回忆自己与其所支持的球队之间的故事。在高解释水平组,被试需要回答其支持球队的目的;并且,被试需要以自己给出的目的为线索,再回答“目的”的“目的”,至少重复3次。而在低解释水平组,被试需要回答其为了支持球队而做过什么;被试需要以自己给出的方法为线索,再回答“方法”的“方法”,至少重复3次。在控制组,被试不接受解释水平操控。
最后,被试需要完成纵欲消费行为的测量任务。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在测量纵欲消费行为之时,研究2采用了与研究1完全不同的方法。具体方法参考和改编自 Wilcox等人的研究[54]。被试被告知“由于参加了‘我的世界杯’的主题活动,每人可以获得一张20元的商场购物券作为回报。购物券可以用来购买两类食品:第1类是面包、饼干和水果等,第2类是啤酒、碳酸饮料和零食等。”被试需要在两类商品之间分配20元的奖励额度。第2类商品是纵欲消费商品。在此处,购物券所涉及的商品需要满足3个条件[37]。首先,两类商品的吸引程度适中且无差异;其次,两类商品属于同一品类,且价格无明显差异;最后,在生活中,两类商品的长期(短期)价值存在明显差异。在正式实验之前,根据这3个标准,研究2邀请43位被试对两类商品进行了前测实验。前测结果显示,两类商品的吸引力(第1类=4.48,SD=0.93,第2类=4.82,SD=0.80,F(1,42)=1.69,P>0.1)和感知价格(第1类=5.14,SD=0.79,第2类=4.91,SD=0.75,F(1,42)=0.99,P>0.1)无显著差异,但是对生活的长期价值(第1类=5.61,SD=0.85,第2类=3.91,SD=0.87,F(1,42)=41.89,P<0.001)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两类商品的选择符合实验研究要求。之后,被试还需要报告性别和年龄等信息。
3.2 结果与分析
研究2共回收有效问卷458份,其中男性363人,占79.3%,女性95人,占20.7%,平均年龄31.7岁,最小的被试19岁,最大的45岁。
检验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2对被试分配给第2类商品的金额数进行单因素(比赛结果)ANOVA分析。结果显示,在比赛失利的情况下,被试分配给第2类商品的金额数=12.78,SD=2.88,n=233)显著地大于比赛获胜的被试组(=11.21,SD=2.13,n=225),F(1,457)=43.96,P<0.001。被试分配给第2类商品的金额数对比赛场次、人口变量信息进行单因素ANOVA分析,没有发现比赛场次、性别和年龄的显著影响作用。这说明,研究2的结果再次支持了假设1中的观点,即比赛结果显著地影响了被试的纵欲消费行为。具体地,在比赛失利的情况下,被试更容易进行纵欲消费。
检验身份认同感的调节作用。在主效应存在的基础上,研究2检验了身份认同感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2对第2类商品金额数进行双因素(比赛结果×身份认同感)ANOVA分析。与研究1中处理方法一致,研究2运用中位数均分法将被试分成身份认同感高和低两组。双因素ANOVA分析显示,被试的身份认同感(α=0.92)显著地调节了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作用[F(1,457)=29.66,P<0.001]。具体来说,在身份认同感高的组别,比赛失利的被试分配给第2类商品的金额数(X=13.92,SD=2.92,n=117)显著地大于比赛获胜的被试组(=11.12,SD=1.97,n=114),F(1,230)=72.30,P<0.001;但是,在身份认同感低的组别,比赛结果对第2类商品金额数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失利=11.64,SD=2.35,n=116;获胜=11.30,SD=2.28,n=111),F(1,226)=1.23,P>0.1。这说明,观众的身份认同感显著地调节了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作用。
检验解释水平的调节作用。在二维交互作用的基础上,研究2还检验了比赛结果、身份认同感和解释水平对第2类商品金额数的三维交互效应。三因素ANOVA分析结果显示,在研究2中三维交互效应显著地存在[F(2,456)=9.08,P<0.01,表1]。具体来说,在高解释水平组中,比赛结果对第2类商品金额数的主效应[F(1,152)=0.74,P>0.1]以及比赛结果和身份认同感对因变量交互效应(F(1,152)=0.05,P>0.1)不再具有显著性。然而,在控制组中,比赛结果对第2类商品金额数的主效应(F(1,151)=27.77,P<0.001)以及比赛结果和身份认同感对因变量(第2类商品金额数)交互效应(F(1,151)=25.78,P<0.001)都具有显著性。从分析结果可知,被试的解释水平显著地调节了比赛结果和身份认同感对第2类商品金额数的交互影响作用。特别值得注意,在高解释水平组和控制组中,失利结果对第2类商品金额数的影响效应也存在显著差异(高=10.62,SD=2.22,n=78;控制组=13.55,SD=2.51,n=77),F(1,154)=59.35,P<0.001。这说明,激发被试的高解释水平状态显著地减少纵欲消费行为。

表1 本研究三维交互效应一览表Table 1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Three Factors
排除替代性解释。在研究2中,操控解释水平的方法是启动被试思考事情的不同方向——目的或方法。实际上,实验的操控任务调节第2类商品金额数的原因可能存在两种解释。首先,在完成解释水平的操控任务之后,被试的解释水平状态确实发生了改变,进而影响了第2类商品金额数,这是研究2希望的结果。其次,操控任务也有可能引起被试其他方面的变化(比如,思考的努力程度),进而发生了调节作用。因此,研究2有必要排除第2种解释。在研究2中,高和低解释水平组的被试都完成了解释水平的操控任务,但两组中的操控任务对解释水平的影响方向不同。如果操控任务的第2种影响作用确实存在,那么比较高和低解释水平组被试的纵欲消费行为能够达到排除第2种解释的目的。ANOVA分析发现,在高和低解释水平组中,比赛失利结果对第2类商品金额数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高=10.62,SD=2.22,n=78;低=14.19,SD=2.54,n=78),F(1,155)=87.46,P<0.001。这说明,解释水平显著地调节了被试的纵欲消费行为,而非其他的可能解释。
验证抑郁情绪反应的中介作用。本文认为,失利的比赛结果能够让观众产生抑郁的情绪反应,进而导致了更多的纵欲消费行为。观众的身份认同感调节了自变量(比赛结果,虚拟变量:0=赢,1=输)与中介变量(抑郁情绪反应)间的关系,而解释水平(虚拟变量:-1=低,0=控制,1=高)则调节了中介变量(抑郁情绪)与因变量(纵欲消费行为)间的关系。为了验证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研究2遵循Preacher等人的建议[41],建立了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比赛场次、性别和年龄被设为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协变量。按照Hayes提出的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检验程序[21],研究2估计了模型的回归系数(图4)。回归结果显示,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29(SE=0.05,P<0.01),具有显著性。但是在加入中介变量之后,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回归系数为0.08(SE=0.05,P>0.1),不再具有显著性。另外,抑郁情绪反应的中介效应系数为0.20(SE=0.03,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15,0.25),不包含零,且第1阶段的交互项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15(SE=0.03,P<0.01),第2阶段的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12(SE=0.04,P<0.01),都具有显著性。这说明,抑郁情绪反应的中介效应显著地存在,并且是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综合对研究2的分析,假设2得证。

图4 本研究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2)Figure 4.The Estimator of Model Including a Moderated Mediator(Study 2)
3.3 研究2小结
研究2的目的在于验证解释水平对纵欲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研究2利用现场实验方法,获取了所需数据。研究2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检验了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主效应,在此基础上还检验了身份认同感和解释水平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不仅如此,研究2还排除了解释水平操控方法影响纵欲消费行为的替代性解释。在检验中间机制之时,研究2建立了一个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利用bootstrap的方法估计了模型的回归系数。分析结果不仅较好地支持了假设2的观点,也再次验证了假设1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测量纵欲消费行为之时,研究2采用了与研究1完全不一样的方法,并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相关假设。这也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4 讨论
观看体育比赛可以成为人们获取成就感的途径之一。显然,当所支持的运动队(员)输掉比赛之时,观众的成就需要就得不到满足。本文的研究主题是体育比赛结果对观众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以及如何减少纵欲消费行为,引导观众进行理性消费。运用成就需要理论、自我损耗理论和解释水平理论,本文推导了相关假设,并利用两个现场实验验证了相关的假设。研究1主要验证了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作用及中间机制;研究2则重点研究了如何减少纵欲消费行为。
1.本文研究了体育比赛结果对观众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采用了现场实验的方法来验证假设,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具备较好的外部效度。实证研究结果较理想地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在研究1中,比赛失利组别的观众参加聚会的可能性(=6.74)显著地大于比赛获胜的被试组(=6.07);在研究2中,比赛失利组别的被试分配给纵欲类食品的金额数(=12.78)也显著地大于比赛获胜的观众(=11.21)。两个研究的结果一致地表明,体育比赛结果显著地影响了观众的纵欲消费行为。值得一提的是,本文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测量观众的纵欲消费行为。这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具备了较高的可靠性。
2.本文研究了身份认同感和解释水平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认为,在面对失利结果之时,观众会产生抑郁的情绪反应,从而增加了观众进行纵欲消费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观众的身份认同感加剧了体育比赛结果对中介变量(抑郁情绪反应)的影响,而激发观众较高的解释水平状态,能够削弱观众因抑郁情绪反应而进行纵欲消费的可能性。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为身份认同感和解释水平的调节作用提供了较好的支持证据。在研究1和研究2中,身份认同感在体育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关系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F研究1(1,168)=9.24,P<0.01;F研究2(1,457)=29.66,P<0.001)。在研究2中,三维交互效应具有显著性(F(2,456)=9.08,P<0.01)。这说明解释水平的调节作用显著地存在。
3.本文研究了体育比赛结果影响纵欲消费行为的背后机制。本文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了体育比赛结果影响纵欲消费行为的中间机制。在研究1和研究2中,体育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0.26(P<0.01)和0.29(P<0.01),具有较好的显著性,然而,在加入中介变量之后,体育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0.09和0.08,不再具有显著性。另外,在研究1和研究2中,体育比赛结果与身份认同感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2(P<0.05)和0.15(P<0.01),具备较理想的显著性。在研究2中,解释水平与抑郁情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2(P<0.01),也具备较理想的显著度。因此,模型回归结果能够支持本文的相关假设,即在体育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关系中,观众的抑郁情绪反应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且抑郁情绪的中介效应受到了身份认同感和解释水平的调节作用。
4.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营销实践指导价值。首先,企业的营销人员应该关注体育比赛对消费者的负面影响,并需要站在长远角度减少这种负面影响。纵欲消费行为是消费者过度满足短期欲望需求而忽视长远利益的消费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决策行为。在进行纵欲消费之后,消费者往往感到愧疚和后悔。这些负面情绪影响了消费者的福利,也降低了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和满意度。其次,为了达到减少纵欲消费行为,引导理性消费的目的,企业可以采用激发观众高解释水平状态的策略。高解释水平唤起了个体的长期目标追求意识,增强了人们实现长期目标的动机,从而有利于自我控制能力的恢复。因此,在高解释水平状态下,人们能够做出更冷静、谨慎、理性的决策,从而避免因短期目标而牺牲长期利益。
5.本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以后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首先,本文的两个实证研究都利用了现场实验方法。尽管现场实验方法能够确保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但现场实验不允许本研究对复杂的环境因素进行控制。这有可能降低了本研究结论的内部效度。在今后的研究中,希望能够在实验室中检验本文的假设,进一步明确自变量(比赛结果)与因变量(纵欲消费行为)的因果关系。其次,本文的因变量是观众的纵欲消费行为。本研究利用了假想情境来测度被试的纵欲消费行为,但是这种方法获取的数据可能与真实的消费行为存在差异。尽管如此,在未来研究中,还是希望能够获取真实消费数据,进一步验证和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5 结论
1.体育比赛结果显著地影响着观众的纵欲消费行为。在比赛失利情况下,被试更容易进行纵欲消费。
2.在体育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关系中,身份认同感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身份认同感较高之时,失利的结果显著地影响了观众的纵欲消费行为;而在身份认同感低的情况下,比赛结果对纵欲消费行为的影响作用不再显著。
3.在体育比赛结果与纵欲消费行为的关系中,抑郁情绪反应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体育比赛是一种满足成就需要的间接途径。在其支持的运动队(员)失利之时,观众的成就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此时,人们可能降低对自我能力的信心,从而产生对自我的消极偏见,也就是抑郁情绪反应。
4.提升观众的解释水平能够有效地减少纵欲消费行为。高解释水平能够唤起个体的长期目标追求意识,增强了人们实现长期目标的动机,从而有利于自我控制能力的恢复,达到减少纵欲消费行为的目的。
[1]刘英,张剑渝,杜青龙.赞助匹配对赛事赞助品牌评价的影响研究——解释水平理论视角[J].体育科学,2014,34(4):70-77.
[2]ABELA J R Z.Depressive mood reactions to failure in the achievement domain:A test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hopelessness and self-esteem theories of depression[J].Cognitive Therapy Res,2002,26(4):531-552.
[3]BAUMEISTER R F,BRATSLAVSKY E,MURAVEN M,et al.Ego depletion:Is the active self a limited resource?[J].J Personal Soc Psychol,1998,74(5):1252-1265.
[4]BAUMEISTER R F.Ego depletion and self-control failure:An energy model of the self's executive function[J].Self Identity,2002,1(2):129-136.
[5]BAUMEISTER R F.Yielding to temptation:Self-control failure,impulsive purchasing,and consumer behavior[J].J Consumer Res,2002,28(4):670-676.
[6]BEARDEN W O,TEEL J E.Selected determinants of consumer satisfaction and complaint reports[J].J Market Res,1983,20(1):21-28.
[7]BECK,A T.Cognitive Therapy and Emotional Disorders[M].New York: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6.
[8]BISCAIA R,CORREIA A,ROSADO A F,et al.Sport sponsorship: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loyalty,sponsorship awareness,attitude toward the sponsor,and purchase intentions[J].J Sport Manage,2013,27(4):288-302.
[9]BRANSCOMBE N R,WANN D L.Physiological arousal and reactions to outgroup members during competitions that implicate an important social identity[J].Aggressive Behavior,1992,18(2):85-93.
[10]BURROUGHS J E,RINDFLEISCH A.Materialism and wellbeing:A conflicting values perspective[J].J Consumer Res,2002,29(3):348-370.
[11]CARROLL N.The paradox of suspense[C].In P Vorderer,H J Wulff,M Friedrichsen(Eds),Suspense:Conceptualizations,Theoretical Analyses,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s[M].Mahwa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6:71-91.
[12]CIALDINI R B,BORDEN R J,THORNE A,et al.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Three(football)field studies[J].Personal Soc Psychol,1976,34(3):366-375.
[13]COON D,MITTERER J O.心理学导论——思想与行为的认识之路(第十一版)[M].郑钢 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455.
[14]DEIGHTON J.The consumption of performance[J].J Consumer Res,1992,19(3):362-372.
[15]ELLEMERS N,HASLAM S A.Social identity theory[C].In Kruglanski A W,Higgins E T,van Lange P.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2,(2):379-398.
[16]FISHBACH A,LABROO A A.Be better or be merry:How mood affects self-control[J].Personal Soc Psychol,2007,93(2):158-173.
[17]FUJITA K,HAN H A.Moving beyond deliberative control of impulses the effect of construal levels on evaluative associations in self-control conflicts[J].Psychol Sci,2009,20(7):799-804.
[18]FUJITA K,TROPE Y,LIBERMAN N,et al.Construal levels and self-control[J].Personal Soc Psychol,2006,90(3):351-267.
[19]GIFFORD JR A.Emotion and self-control[J].J Economic Behavior Org,2002,49(1):113-130.
[20]HAGGER M S,WOOD C,STIFF C,et al.Ego depletion and the strength model of self-control:A meta-analysis[J].Psychol Bulletin,2010,136(4):495-525.
[21]HAYES A F.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Moderation,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M].New York:Guilford Press,2013.
[22]HIRT E R,ZILLMANN D,ERICKSON G A,et al.Costs and benefits of allegiance:Changes in fans'self-ascribed competencies after team victory versus defeat[J].J Personal Soc Psychol,1992,63(5):724-738.
[23]INMAN J J,DYER J S,JIA J.A generalized utility model of disappointment and regret effects on post-choice valuation[J].Market Sci,1997,16(2):97-111.
[24]INZLICHT M,SCHMEICHEL B J.What is ego depletion?Toward a mechanistic revision of the resource model of selfcontrol[J].Perspect Psychol Sci,2012,7(5):450-463.
[25]KIM S M,GREENWELL T C,ANDREW D P S,et al.An analysis of spectator motives in an individual combat sport:a study of mixed martial arts fans[J].Sport Market Q,2008,17(2):109-119.
[26]KRISHEN A S,BATES K.Modeling regret effects on consumer post-purchase decisions[J].Eur J Market,2011,45(7/8):1068-1090.
[27]LARAN J.Choosing Your Future:Temporal Distance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self-control and indulgence[J].J Consumer Res,2010,36(6):1002-1015.
[28]LEITH K P,BAUMEISTER R F.Why do bad moods increase self-defeating behavior?Emotion,risk tasking,and self-regulation[J].J Personal Soc Psychol,1996,71(6):1250-1267.
[29]LIBERMAN N,TROPE Y.The role of feasibility and desirability considerations in near and distant future decisions:A test of temporal construal theory[J].J Personality Soc Psychol,1998,75(1):5-18.
[30]LIPMAN-BLUMEN J,LEAVITT H J.Vicarious and direct achievement patterns in adulthood[J].Counsel Psychol,1976,6(1):26-32.
[31]LOVIBOND P F,LOVIBOND S H.The structure of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Comparis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DASS)with the beck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ventories[J].Behaviour Res Therapy,1995,33(3):335-343.
[32]MAY F,IRMAK C.Licensing indulgence in the present by distorting memories of past behavior[J].J Consumer Res,2014,41(3):624-641.
[33]MCDONALD M A,MILNE G R,HONG J.Motivational factors for evaluating sport spectator and participant markets[J].Sport Market Q ,2002,11(2):100-113.
[34]MEHTA R,ZHU R J,MEYERS-LEVY J.When does a higher construal level increase or decrease indulgence?Resolving the myopia versus hyperopia puzzle[J].J Consumer Res,2014,41(2):475-488.
[35]METALSKY G I,JOINER T E,HARDIN T S,et al.Depressive reactions to failure in a naturalistic setting:A test of the hopelessness and self-esteem theories of depression[J].J Abnormal Psychol,1993,102(1):101-109.
[36]METCALFE J,MISCHEL W.A hot/cool-system analysis of delay of gratification:Dynamics of willpower[J].Psychol Rev,1999,106(1):3-19.
[37]MUKHOPADHYAY A,JOHAR G V.Indulgence as self-reward for prior shopping restraint:A justification-based mechanism[J].J Consumer Psychol,2009,19(3):334-345.
[38]MURRAY,H.A.Explorations in Personalit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
[39]NEAL D J,FROMME K.Hook'em horns and heavy drinking:Alcohol use and collegiate sports[J].Addictive Behaviors,2007,32(11):2681-2693.
[40]PALMER C.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sport and alcohol:On the contemporary agenda of research on alcohol within the sociology of sport[J].Int Rev Soc Sport,2014,49(3-4):259-262.
[41]PREACHER K J,RUCKER D D,HAYES A F.Addressing moderated mediation hypotheses:Theory,methods,and prescriptions[J].Multivariate Behavior Res,2007,42(1):185-227.
[42]RAMANATHAN S,WILLIAMS P.Immediate and delayed emotional consequences of indulgence: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type on mixed emotions[J].J Consumer Res,2007,34(2):212-223.
[43]SAYETTE M A.An appraisal-disruption model of alcohol's effects on stress responses in social drinkers[J].Psychol Bulletin,1993,114(3):459-476.
[44]SNYDER C R,LASSEGARD M A,FORD C E.Distancing after group success and failure: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 and cutting off reflected failure[J].J Personal Soc Psychol,1986,51(2):382-388.
[45]SUN T,YOUN S,WELLS W D.Exploration of consumption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ties in sports marketin[C].In L R Kahle,C.Riley(Eds),Sports Market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M].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4:3-26.
[46]TAYLOR K.A regret theory approach to assessing consumer satisfaction[J].Market Letters,1997,8(2):229-238.
[47]TICE D M,BRATSLAVSKY E.Giving in to feel good:The place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l self-control[J].Psychol Inquiry,2000,11(3):149-159.
[48]TROPE Y,LIBERMAN N.Construal-level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J].Psychol Rev,2010,117(2):440-463.
[49]TROPE Y,LIBERMAN N.Construal level theory[C].Lange P A M,Kruglanski A W ,E T Higgins(Eds),Handbook Theories Soc Psychol[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1,(1):118-134,.
[50]WAKSLAK C,TROPE Y.The effect of construal level on subjective probability estimates[J].Psychol Sci,2009,20(1):52-58.
[51]WANN D L,BRANSCOMBE N R.Sports fans:Measuring degre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team[J].Int J Sport Psychol,1993,24(1):1-17.
[52]WANN D L,KOCH K,KNOTH T,et al.The impact of team identification on biased predications of player performance[J].Psychol Rec,2010,56(1):55-66.
[53]WANN D L,BRANSCOMBE N R.Die-hard and fair-weather fans:Effects of identification on BIRGing and CORFing tendencies[J].J Sport Social Issues,1990,14(2):103-117.
[54]WILCOX K,KRAMER T,SEN S.Indulgence or self-control:A dual process model of the effect of incidental pride on indulgent choice[J].J Consumer Res,2011,38(1):151-163.
[55]WILCOX K,VALLEN B,BLOCK L,et al.Vicarious goal fulfillment:When the mere presence of a healthy option leads to an ironically indulgent decision[J].J Consumer Res,2009,36(3):380-393.
[56]ZILLMAN D.The mental control of angry aggression[C].In D M Wegner,J W Pennebaker(Eds),Handbook of Mental Control[M].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93:370-392.
[57]ZILLMANN D,BRYANT J,SAPOLSKY B S.Enjoyment from sports spectatorship[C].In J H Goldstein(Ed),Sports,Games and Play: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Viewpoints[M].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9:241-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