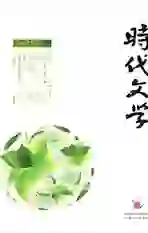从河溪到大海
2015-09-08韩嘉川
韩嘉川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耿老的文章,是讲他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文学写作,到在全国产生影响的过程的,其中沿着他的散文诗创作脉络,捋出了从最初发端,像小河溪的涌流到大海一样的汹涌澎湃。现在看来,那篇文章还显得粗陋了些,耿老的散文诗写作,尤其是对散文诗的建树是历历在目的。这次《时代文学》要推出“名家侧影”的栏目,希望我写一篇他的侧记,于是又想起那篇文章。
1987年的秋天,在南通市召开海洋文学笔会,因当时青岛的《海鸥》文学月刊也曾改版出版过《海洋文学》,于是青岛市文联便派出耿老和我出席了那次会议。辖属南通市的如皋县是耿老的故乡,南通市文联主席季茂之是耿老青少年时期的文友。耿老在文学上早慧,1939年他13岁时便在邻县泰州的报纸副刊发表了第一首诗《槐花树下》,继而又投去了小说《赤豆》。都是反映当时抗战的,《赤豆》讲的是几个农民进城,被日本鬼子从几个人的口袋里翻出了几颗蚕豆,疑为是抗日游击队员的联络暗号,将那几个农民抓起来杀掉了。这是当年轰动一时的“蚕豆案”,耿老根据这个真实事件,将蚕豆改为赤豆,也就是红小豆。之后不久,也就是刚上初中的时候,便与几个同学办起了文学刊物《血湖》,发刊词也是他写的。虽然刊物只薄薄几页,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便找他谈话,这位书记的笔名叫林流,是一位比较成熟的诗人,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进步作品。“和我谈话那天,是一个秋日的午后,坐在操场边的田塍上,淡淡的阳光照在身上。他侃侃而谈,谈抗日,谈党,也谈文学……”这是耿老在《我的两位诗歌老师》中写到的情节。对于初涉文学的耿老,这位老师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1987年秋天的南通,与当年的文友相会,于耿老无疑是一次回顾的精神盛宴。在场的还有著名诗人沙白。大家共同的回顾,唤醒了若干记忆中的细节。
会后,我随耿老到了如皋。那是一个小巧的南方小城,灰蒙蒙的房瓦与老旧的白墙,结构着岁月痕迹浓重的街巷,老虎灶的烟尘与白铁匠敲打烟筒的声音,将生活细节拉回多年前的印象。
当他哥哥等人陪同他一起回到当年读书的如皋县安定小学时,61岁的耿老有些激动了,他在这里读书时,作文写得特别好,老师对他的表扬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诱因。那是秋天一个明媚的星期天下午,校园里静悄悄的,校门外的池塘边,有几个垂钓者,让那个下午显得格外纯净。
水绘园与定慧寺,还有老城墙,尽管也都引起了耿老的无限回想,但是在那个小城里,令他最为感怀的,是在一条青石板巷子里的一个栅栏门里,几间地方特色风格的房子,那是耿老早年的居住地。两棵无花果树遮蔽着窗子,房门前有一个绿色釉面的水缸。在这里,我知道了耿老一生中有两怕,一怕神庙里的金刚神像,再是怕他父亲的强权。对他最好的一个人是他的母亲,母亲不仅带着他躲避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他们家原来有一处相对好一点的住处,便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的——而且是家里唯一支持他搞文学创作的人。后来耿老之所以用耿林莽的名字刊发作品,是用了母亲的姓,也是以此作为对母亲的纪念。父亲常年在上海一间糖行做账房先生,每年春节回来一次。在父亲的观念里,文人都是非常穷困的,他坚决反对耿老走文人的道路,因此父子俩的关系很紧张。后来耿老还是在父亲的“强权”下,去了徐州,到堂兄的一家货站当学徒,再后来到了堂兄朋友的私人银行做练习生。
是姐姐送他离开如皋的。穿过一座门廊走进了姐姐家的小院,院子虽然小,却种植了不少植物。如皋是一个做园林盆景很有名的地方。一口小井在院子中,旁边有一只打水的水桶。已经褪色的门板向南大开,11月的江苏已经渐渐显出寒冷的气候。姐姐从阁楼上缓缓地下来,从敞开的门窗射入的阳光利刃一样剖开了室内的影像。木制座钟在条案上仿佛还在度量着旧日的时光,木板墙壁上挂着的相框里,有各个时期的照片,其中姐姐的儿子,也就是耿老的外甥蹲在田野里的照片略显得新一些。外甥在另一个县的学校当教师。一幅尺寸比较大的是已经过世的姐夫的遗像。耿老与姐姐的话题便是沿着姐夫生前的物事展开的。
长江从南通入海,境内遍布河湾港汊,如皋小城亦不例外。在当年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水路是人们通向外面世界的重要通道。秋天,苇荡森森,芦花飘然,掩映其间的木船仿佛以岁月缓缓移动的速度航行着。多年前的晚上,姐姐送当时年轻的耿林莽离开如皋的时候,一盏清冷的马灯映照在篷船里,撑船人将竹篙深深插进河水,将船撑离小城的堤岸,在撑船人赤脚在船板上往返的节奏中,年轻的耿林莽向徐州驶去,从此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那年他17岁。
那次在如皋城里,我们去寻找耿老当年走出如皋的河道。在一棵大树下,踩着暴露在地面的树根,耿老恍惚了,河道已经干涸,搁浅的船只在两岸挤挤挨挨,船篷顶上歪歪斜斜地探出了各种方式的电视天线——当年,小城的人们通过河道走向外面的世界,1987年的人们已经开始通过电视天线与外面的世界沟通了。
在千里之外的徐州,耿林莽当学徒、店员、银行练习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工者。孤身一人远离了那些文学朋友以及写作的环境,耿老情绪十分低落,但同时也离开了极力反对他搞文学创作的父亲,那时他父亲已经从上海回到如皋定居了。于是,工余时间,耿老便敞开地搞起了诗歌写作。在初到徐州的两年中,他写了大量的作品,是整个青少年时期文学创作的高峰。其中诗歌《小村》、长诗《大地,我歌唱》、万字小说《魂的流浪》等,先后在上海的《文潮》和《潮流》月刊等发表,这个时候便开始用耿林莽的名字登上文坛了。
那段时间,他几乎没有可交流的朋友,形单影只的孤独,不仅是生活上的,也是文学创作上的。有一位叫夏穆天的徐州诗人,耿老在家乡的时候曾读过他的一首长诗,极为欣赏,到徐州后便千方百计打听他,终于得知他哥哥开了一家西药房,通过这家药房得知了他家的住址,于是耿老便在一个早上贸然造访了。此人不拘小节,待人接物十分随便,但很真诚,耿老将抄在一个小本子上的两首长诗《叶子》和《果园城》给他看,他看过后非常欣赏,称誉耿老是“文学天才”。这之后又有过几次接触,他曾在当地报纸上发过一篇文章,题为《古城七彩记》,介绍当时徐州的七位文学青年,将耿老列为“首席”。
在还没有青霉素的时候,世界上大面积流行肺结核,而且传染性极强,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年轻的耿林莽不幸也得了肺结核,不仅仅是身体的虚弱令他不能再工作,而且人们对传染性的肺结核也视若猛虎,失业的耿林莽只好寄居在一个工友的家里,那位工友的妹妹是一个纺织女工,就是在这位纺织女工的照料下,耿老才渐渐好起来。当时除了青霉素的治疗,营养也很重要,陷入病困的耿老十分艰难,是那位工友兄妹的接济照料才令耿老活了下来。
徐州解放比较早,解放军进驻了徐州后,工友便告诉渐渐好起来的耿林莽,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到人事部门请求参加革命工作。耿老就写了一个书面的申请,提出想到报社工作。很快他便得到了答复,让他到新徐日报去见负责人。当时的负责人是沙洪,他与耿老谈了大约半个小时,最后说过几天就给你消息。过了几天,耿老便到报社工作了。在《新徐日报》编新华社的电传稿。在报社工作期间耿老的心情很舒畅,报社一百多人,军事化管理,耿老的待遇是供给制,不仅穿军装,所有的生活所需都是公家配给。
当时徐州属于山东,刚解放的山东需要文化干部,耿老便跟随沙洪来到山东济南,到了《大众日报》,还是编新华社电稿,但是须上夜班。身体刚刚恢复不久的耿老便有些吃不消,恰逢此时沙洪又被派往青岛接受《胶东日报》,于是耿老便于1950年分到了青岛,到了后来的《青岛日报》做副刊编辑,在那里工作了十多年,主要工作是编发诗歌小说,写一些遵命文字,期间写了不少影剧评论与杂文。后来调到了文化局的戏剧研究室,从事戏剧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搞传统戏整编,再后来便在创作组里搞戏剧创作,其中有一个叫《北京》柳腔传统戏上演了。这段时间在宣传部文艺科科长的孔林主持下,成立了一个“葵花诗社”,并且编辑出版了一本《葵花集》,是由耿老与诗人张见一起编辑的。
不久“文革”开始了,耿老受到了一些冲击,陪斗、抄家等等,然后便是下放到工厂劳动,后来到新华书店站柜台,也属于劳动的范畴。
1966年的暑假后,我该升四年级了,可是教室被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占领了,他们把桌子一张张拼接起来,白天在上面写大字报,晚上当床用来睡觉,我和同学悄悄回到学校看到这种情况很伤心。这个期间我特别迷恋绘画,我们的美术老师也被揪斗了。有个同学住的与我家隔着两条街,他哥哥有一本俄罗斯画册,我非常喜欢,几乎每天都到他家去,希望能再看到那本画册。他哥哥是老知青,也就是文革前下乡的,不仅有画册,而且有许多藏书没有随着“破四旧”的浪潮被烧掉。为能从他家借出一本书,我帮同学劈木头、倒垃圾、买煤买粮草等等,但是大多的时候是失望而归。没书读的日子特别漫长,我常常走在路上看到有纸张,赶紧捡起来看看上面有没有文字,也确实曾在泥水里捡到一叠被打湿的纸,居然是半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曲唱本……
从同学家往回走的时候,路过人和路,当时的台东新华书店便在人和路上。每次路过的时候总要进去看看。而那时的新华书店除了一些画像外,没有任何书籍。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新版的某一款画像发行也要敲锣打鼓庆贺,人们半夜到新华书店“抢购”。记得是5分钱一张,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一个高个的女人在发售,旁边一位瘦瘦的中年男子将每一幅画像卷起来,套上一个用旧书页做成的纸套。那人清瘦,说话很轻很轻,南方口音,戴一顶呢帽子,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去书店次数多了,便与那位中年人相熟了。那种熟悉仅仅是书架上或柜台上新来了读物,他主动拿给我。记得柜台里的书架上曾摆满了《南方来信》,是一种丛书,刊登胡志明领导的抗击美军侵略的纪实性文章,多是揭露美军暴行的。中年人见我又慢慢靠向柜台,便拿给我看,满足了我强烈的阅读欲。再后来有了《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小说,还有《阎一强诗集》、《太行炉火》、《枣林村集》等等。尽管这些书没有我与同学们私下里偷偷借阅的书籍有意思,但是毕竟是文学书籍啊。
有一次在我家的楼道里见到那位中年人,他是来通知我的邻居下午到书店开会学习的。那位邻居是剧团的琴师,也是被下放到书店劳动的。我新奇地问:“你来这里干吗?”,他回答“你在这里住?”这是我们首次在书店之外的对话,从此我们进一步相熟了,这人便是耿林莽。
后来耿老回到了文化局,又被分配到了图书馆阅览室,做书刊杂志管理,他给我办了一个借书证,是用家属的名额办的,那时我还在上学,没有资格在市图书馆办借书证。每周去一次借阅,当时被“解放”的书很快就读完了,见我依然很“饥渴”,耿老下了很大决心地说,把我自己的书借给你看吧。于是,我知道了耿老在金口路11号的住址。他的藏书是被抄家以后返还的。还是每周去一次,在他家窗外的小院里,一只小方凳上放两只茶杯,我把阅读中不懂的地方向他请教,他便一一向我道来……
1978年文联恢复了文学期刊,耿老便到了还被称作《青岛文艺》的编辑部工作了,我依然每周去他家。一次我写了两首诗,自己觉得很满意,已是晚上九点多了,又下着雨,我还是忍不住敲开了他的门,他已经睡下了。见我冒雨赶来赶紧起身,把我的诗稿展开在台灯下,认真读过后,耐心地提出了他的意见。大致意思是,模仿别人是可以的,但只能作为练笔,不能算作成熟的作品。从那以后,他便有针对性地给我讲述诗歌的创作,并且推荐诗歌书籍。
1980年,柯蓝到青岛,在文联举行了一个座谈会,提出了散文诗的写作与发展,从那以后,耿老便开始散文诗写作,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很快便在国内引起了反响。《诗刊》推出了“散文诗六人谈”,并配发了作品;《星星》诗刊也推出了专辑,推介散文诗作家与作品,耿老很快成为其中的代表作家。
有一章散文诗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题为《我是骆驼》,大意是天上的鹰如何具有至高的优势,而我是沙漠里默默跋涉的骆驼。当时在读者中反响强烈,文联有同事说,老耿,这章散文诗写得很好,很令人震撼,可是一位诗人一生中能流传下来的,也仅仅是脍炙人口的几首,你不要太劳累了。那时耿老的眼睛出了问题,医生说可能导致青光眼。耿老很紧张,但是对于散文诗创作正处于上升期,不用说让其放弃,即便让其放缓写作节奏,都是难以忍受的。前面说,他每天晚上躺下很早,但是并不是躺下就睡着了,他睡得很少,而是一直在思考,常常半夜起来把自己思考的佳妙诗句,或某一个观点记录下来。他的这个习惯,我是在与他一起到哈尔滨、四川乐山等地参加散文诗的会议时了解到的。
经中医药的调理,耿老眼压过高的毛病逐渐得到了好转。他之所以如此,其中与他的性格有关系,耿老的性子比较急,像他在报社工作的时候那样,他从来不加班,手头的工作他总是赶着完成,从来不拖沓。在《海鸥》月刊做编辑也是这样,只要觉得来稿有价值,特别是年轻人的来稿,他都是在看过后的第一时间写回信,效率很高。搞散文诗创作也是如此,他潜心于散文诗的写作与思考,几乎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与写作上了。除了读书、写作、编稿子之外,他几乎没有其他所好。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中,一杯茶、一碗饭、一张床足矣。对于各种应酬很犯愁,特别不愿意参加那种推杯换盏的场合。但是对于老朋友和青年作者则不同,不仅很有耐心,而且每次外地来了朋友他总是要在家里招待吃饭,而对于青年作者,常常登门谈作品,令若干已不年轻的当年青年作者感慨不已。
我为他的急性子与其认真讨论过,耿老的观点是,时间留给他的不多了,他要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说到这里令人心酸,耿老少年早慧,具有文学创作的灵性,然而他的才华在其盛年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其五十多岁以后,才进入创作的黄金时期,他怎么能不抓紧所有的时间呢?
做人低调,是耿老的另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他很腼腆。他不仅可以说桃李满天下,即便在青岛,经他培养的作者也很多,其中不乏有做官的和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的。然而,对于自己的孩子工作安排,他却显得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去托人情给孩子解决一个相对满意的工作。
回顾三十多年来耿老的散文诗创作与建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总结。一是他自身的创作,这是一个不断攀登发展的过程;二是关于散文诗的观点,也就是对于散文诗的定位,耿老在这方面的积极思考与研究,使散文诗沿着精品的方向健康地发展;三是对于年轻人的培养,这是如我一代所受益匪浅者有目共睹的。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星星》诗刊的执行主编带领编辑们专程从成都来青岛,为耿老颁发首届“鲁迅散文诗奖”。而正式的颁奖仪式是在成都,他们知道1926年生人的耿老不能去成都领奖,便亲自来青岛举行专门给耿老颁奖的仪式,这不仅令耿老感动,更令整个散文诗界,甚至文学界的同仁感动。我认为,这个奖来得正当其时。耿老对于散文诗的贡献,从作品实践到理论探求,都是开拓性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文体本身,而是对于文学事业的发展与推进;而当年鲁迅先生之所以对其《野草》特别看重,就是看重对文体的开拓(甚至说实验性也可以),而耿老三十多年对于散文诗精品化的探求,让散文诗缘着诗歌的本体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就像唐诗向宋词的过渡一样,耿老的作品提供了一个过渡的典范,入围鲁奖在全国引起的反响,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这个奖的颁发是对耿老探索成就的肯定。
我感恩于耿老,而更感恩于他的为人之典范,他为文学而向善!
2015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