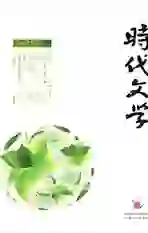我们去串联
2015-09-08胡平
胡平
关于文革初期的记忆,对我来说,称得上愉快温馨的还是有一段的,那就是串联时光。
我小时候,大家择校观念没那么强,我就读的北京东城区西花厅小学是新建校,了无名气。作为第一批入校生,我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毕业时考试,居然考上了二中。全校六年历史上只有我们这届有我和一个姓闵的同学考上市重点,当时为学校争了光。几年后小学老师悄悄告诉我,我升学考试的成绩是双百。
没想到,在二中刚读了一年,就来了文革,停课了,搞运动了,斗校长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了,这样我们就亏了,好学校白考了。二中隔壁有个七十二中,算个比较次的学校,校里一些学生贴出标语,把七十二中谐称为“气死二中”,十分欢呼——所以,文革是有它一定的群众基础的,不是毛主席一个人想发动就能发动起来的。社会上只要有不同利益和不同利益的分层,就总能找到搞运动的依靠力量。现在的小说写文革,总写不像,就因为里面写的造反派都是另类分子,极少数。其实不然,极少数能发动起文革来吗?
但二中学生里人才多,仍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发起者之一,还率先发动了串联,包括全国大串联。串联的意思是革命大串联,先动手四处游说,把革命的火种洒向各地。毛主席的这一招很管用,一下子全国包括乡镇都热闹起来。
在中学,运动的主力是高中生,红卫兵也主要是他们组织起来的,因为他们毕竟大几岁。那时我初一,说实在话也看不懂周围发生了什么,人家也不带你玩,在运动中就基本是逍遥派,属于看热闹的,当然有时也看得心惊胆战。但有一件事是大家能看明白,都乐意加入的,那就是去外地串联。一开始,异地串联只有少数大学和高中红卫兵,到后来,毛主席反复接见各地来京红卫兵,报上发了社论,明确予以鼓励,中学以上的学生就都有了介入的资格。
那是1966年10月的一个上午,我们照例零零散散地踱入教室,看看有什么事可做,这时教室里已有同学在热烈议论了,说是只要有红卫兵领头,就可以自由组合去北京以外地区搞串联了。这使我们很兴奋,因为,我们基本都既未去过外地,也没坐过火车,眼前竟然有这样的好事来了,谁都不愿错过。
那天上午的组合是匆忙而有效率的。用不着谁提醒,各自都会找平时走得近的同学商量,三一群、五一伙。二中是男校,组织起来更为方便。我和王小龙等五人是朋友,很快凑到一起,达成共识,临时成立了一个命名“风雷激”的战斗队。那时,成立各种名目的战斗队是不需要批准注册的。我们还需要找一个人做首领,他必须是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而且跟我们合得来,于是就有人提出刘保华。刘保华据说出身“革军”,但在运动中很低调,从未上台慷慨激昂,也从未批斗过老师学生,所以给我们很随和的印象。我们四处找他,还准备去他家,但他终于出现在楼道里,一脸惺忪,似乎昨晚没有睡好。大家把事一说,他完全赞同,责无旁贷地担任了“风雷激”战斗队队长一职。我们立刻去校文革办事机构开到了介绍信。那个年头,还没谁敢私刻公章,所以这封介绍信会是很管用的,信上注明刘保华等六位革命师生将前往广州进行革命串联,希望有关部门予以接待是荷。
家里人听说我要去串联,都很高兴,似乎没有太多的担心。那时我14岁,虽然不大,但街上相同年龄的红卫兵已经比大人还威风了,谁也不敢当小孩子对待。比我再小一点儿就不行了,我们院里另外两个男孩差我一岁,上小学六年级,而对小学生的政策是能停课但不能串联,所以他俩都很羡慕我。
已经记不得家里给我带了多少钱和粮票,总之我们出发了,集合地点是北京火车站。这座火车站矗立两座醒目的钟楼,拥有宽阔的站前广场。当年的那一天,广场上密密麻麻坐满了中学生和大学生,等候进站的时刻到来。我们手中的临时车票上只印始发和终点站,不印车次,站里来一趟车放一拨人进去,我们起码等了八九个小时。这座车站至今矗立在建国门西,一切竟还和当初一样,毫无改变。我每经过那里,总还是会想起那一年那一天的情景。我把车站钟楼视为我们的一座纪念碑,纪念我们14岁少年的独立远行之旅。
进站时是一通疯狂的奔跑,争取抢到座位,可我们只做到了六个人登上同一节车厢。100人的车厢必须挤进200多人,我们六个人有的坐在过道,有的占据厕所,有的睡在行李架上,有的躺在两排座位之下。我是睡行李架的,那半空中的行李架很窄,需要侧卧,上去了就不能轻易下来,防止被别人占据。可是凌晨,一泡尿憋得我实在难忍,只好把宝贵的卧铺出让,下地解手。厕所门下往外流着黄汤,里面便池旁也有人打盹。看到车上女生也有不少,我没搞清这种处境下她们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这是一种有益的生存训练,两年多后,我上山下乡去西双版纳,除坐四天火车外,又坐五天汽车。汽车是那种拉猪的带篷卡车,知青密密麻麻地站在车上,一路红尘滚滚,刮得满面红土,但没人坚持不住,没人太多抱怨,这大约就与串联的演练有关。
我们终于熬到武汉站,深夜从车站步行前往武汉大学红卫兵接待站住宿。四外空寂无人,路程显得无穷无尽,一直走得心虚腿软,走得无人说话。那一夜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不知为何记得那么深刻。大约因为那段路正是我们初次走上社会的人生之路的开端吧。
接待站的住宿和伙食都是免费的,只需要交粮票,很有共产主义味道,也体现了毛主席的博大胸怀。次日,我们花了一天时间在武大抄大字报。武大是我父亲的母校,环境幽美典雅,现已成为大字报的海洋。大字报的内容以揭发和攻击为要务,引人注目,但看多了也会麻木。我们终于发现,偌大的校园里人头攒动,没人注意我们,也没人需要我们,我们对这里一无所知,只能抄写点大字报带回北京,其实,带回北京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依然置于运动之外。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我们几人就开始转向参观和游历为主了。人性就是如此,当我们最初升起串联的冲动时,潜伏的原动力已经就是旅行了。
不过,那时候的串联旅游与现在的商业旅游还是有区别,串联旅游更重视革命圣地、革命遗址,对纯粹的游山玩水还是有点顾忌。为了避免广大师生游山玩水,各地许多著名的风景点能关闭的都关闭了。我们住在东湖边,却没有正经到东湖走一走,而是去了毛泽东旧居、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八七会议旧址等处。记得在农讲所的大课堂上,我看到悬挂着两面国民党旗,感到很惊讶。
当然,去参观长江和长江大桥不在禁止之列。我们很快赶到江边,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到浩瀚的江面。那时的长江水比现在充沛许多,一望无际由天边涌来,看得大家心潮澎湃。武汉大桥是我们见过的最宏伟的建筑,桥面江风很盛,我们在桥上跑了一个来回,兴头不减。身为一个少年,面临那么广大的场面,那么辽阔的视野,我自然而然生起许多关于未来的畅想。
我们拿到前往广州的车票时,计划中就包括经停武汉和长沙。能到长沙,当然要去韶山。如果刘少奇没打倒,也可能去花明楼。
我们见识了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和爱晚亭,前者是毛泽东读书的地方,爱晚亭是他青年时代与人讨论天下大事的地方。第一师范没什么意思,还是爱晚亭让人留连忘返。它八柱重檐,三面环山,四外紫翠青葱,流泉不断,不愧为中国四大名亭之一。到了爱晚亭,自然到了岳麓山,到了岳麓山,玩水和游山还是都有了。
省里早就安排了庞大的汽车队,确保全国师生随时去往韶山。正是从1966年下半年起,参观韶山的人数陡然激增,并保持着相当数量至今。毛泽东旧居是世界上所踏足迹最多的几间农舍,房子宽敞,风水更好,参观后,都相信领袖家不会是贫农。在门前的池塘边,我用木棍蘸黄泥水在日记本上写下纪念字样,去年偶尔翻见,看到字迹依然清晰可辨。日期呢,算算已经隔过了四十八年。
此后,我们更加自由,到达广州后,又从广州杀向上海,从上海前往南京,从南京来到郑州,从郑州奔去西安,从西安到达延安,沿途见闻自然不可尽数。
那时我牙口很好,在广州,可以毫不费力地撕咬一米多长的紫甘蔗,它和香蕉都五分钱一斤,叫人大饱口福。上海小吃的精致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城隍庙的一种素菜包和一种酒酿圆子,让我回味了好长时间。上海的外滩和南京路,则象征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人走在街上,显得矮小了很多。面临那种商业气势,心灵多少有些震动。后来,我在云南农场交了一些上海知青朋友,他们大都小我一岁,没去过北京,而我到过上海,有能力和他们聊到上海的大世界和小吃,无形中占据了些许优势。
在上海期间,我们认真讨论了一下,是回北京还是继续前行,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接着串联,足见人的求知和想见世面的欲望是难以克制的。忘记从何时起,我们不大关心大字报了,也不发怵提出去何方。都已经知道,只要有一张学生证,证上有相片,走到哪里都不发愁,还可凭这个证件借粮借钱。这张学生证我现在还保存着,上面盖有各地的戳记,价值仅次于今天的身份证。
在西安古城,我们不满足于只看街上的钟楼和鼓楼,寻去瞻仰了大雁塔。大雁塔虽不开放,外观却无从掩盖。那时我已能背岑参的“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盤虚空”诗句,望着那恢宏的砖仿木结构的四方形楼阁式巨塔,心中不能不称颂唐高僧的丰功伟绩。
那时天已渐冷,在西安接待站,我们每人用学生证借到一件崭新的蓝色棉袄,帮助我们前往延安。
路上,几个人走散了,结果到延安后有人住在杨家岭,有人住在王家坪。夜里,我们跨延河去会合。那时四周万籁俱寂,人走在河边,竟能听到河水流过卵石的叮咚响声,如木琴般悦耳,加之望见身右宝塔山上塔身轮廓闪烁着的光芒,如入诗境。在那个情境之下,不知怎么我产生了将来要争取去一趟佛罗伦萨的愿望。有这个念头是很奇怪的,而且到现在也没实现。
从延安到西安的路上,有一个叫铜川的地方,那里出产一种四瓣的柿子,像野柿,很便宜,又很甜,无涩味,从未见过。来回经过铜川两次,我都在路边买来吃,很喜欢。1973年,我在云南参加一个会议,遇到有一位姓田的与会者,就因为他是铜川人,和他谈到了四瓣柿子,使我们俩一见就熟络起来,此后保持了约一年的联系。
必须承认,串联是容易走火入魔的,我们尝到了甜头,很想走遍中国。也许因为太累了,也许因为怕家里不放心,终于还是在纠结一阵后于11月返回北京。当然,我们也约好,回京后歇一歇再出来。人是越跑越野的。
大家还是后悔了。回京后形势就变了,中央到底发现,这种大规模串联所付出的代价、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冲击过于严重,哪怕再持续半个月,后果都可能难以承担。所以,普通学生的串联被三令五申制止了,学校不停地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虽然回到学校的学生很不整齐,但再想出去是困难很多了。在家里的催促下,我去邮局把那件已洗干净的蓝棉袄寄回了西安。结束串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的初衷业已实现。
对文革是该彻底否定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否定,倘若现在还找哪种理由为文革说话,我们这个民族就希望不大了。但文革中,只有串联这一件事,使我心存好感。我知道,这是一种一己私利的感情,不顾国家大局的感情,不过也确实是一种感情。
有一次,到广州出差路上,我和同行的评论家牛玉秋谈起到过广州几次,得知我们初次来此都是在串联中,时间也差不多。不同的是,我们只在广州待三天,而牛大姐他们却在广州常驻下来,几乎没再去过什么别的地方,原因是他们参加了当地的运动。我笑起来,觉得他们亏了。又想到,我哥哥也是如此,他也是跟同学一起跑到山西,就在山西的一个小市扎下来闹革命了——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串联。那么,牛大姐、我哥和我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当时他们是大学生,而我只是中学里的初一生;他们已经有革命的头脑和资质,而我对革命还懵懵懂懂。所以,我把串联当成了玩的机会,也是奔着玩去了。然而,现在看来,牛玉秋和我似乎都同意:那时候,脑子里东西装得多了倒可能不如没装多少,学的东西多了倒可能不如没学过什么。
我们这一代后来被称为“老三届”,比之老大学生一代,过早地失去了就学机会,下乡后沾染了不少农民气息,工作了许多年还在补课。但我们也有一点点幸运之处,就是观念上少了一些定型的东西,串联中敢四处游到处跑,以后在工作中也少些框框。习总书记和几个常委也是“老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