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无”论的哲学价值和人文意义
2015-08-26青萍
青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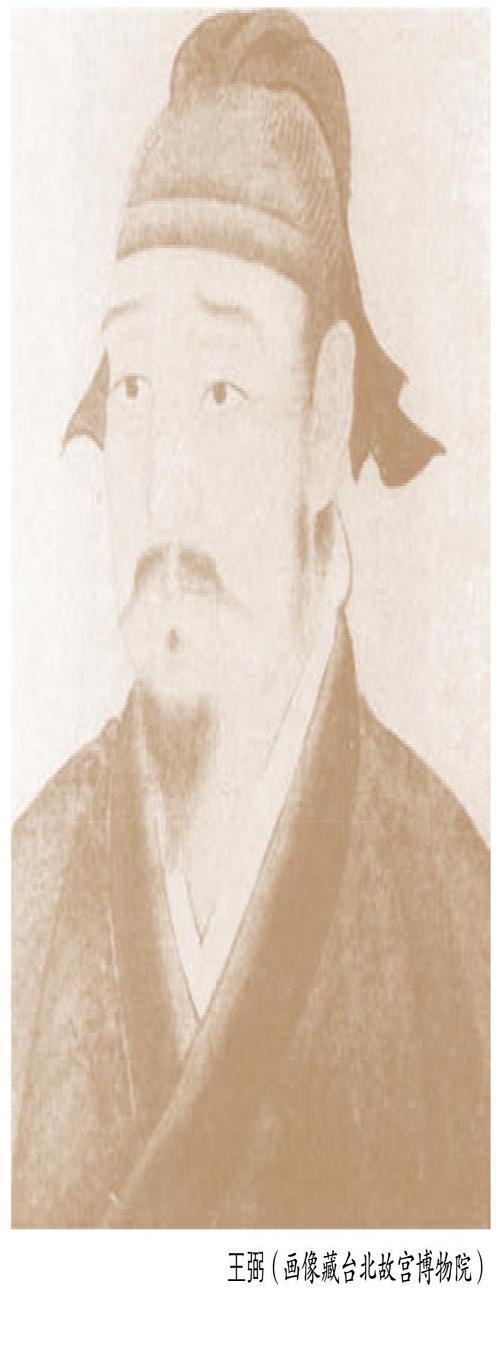
摘 要:三国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提出的“贵无”论已进入对人性和个体的讨论,导引出一种合乎自然人性的自然生活态度。与此相应的“言”“意”之争,则使魏晋时代知识阶层作为“人”和“士”的主体意识悄然形成。后来“竹林”中人又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展开深入论辩,以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最得人心。“贵无”论促成了魏晋之际以建立理想人格、争取精神自由和超越为目标、为实践的人文主义大波的兴起。
关健词:“贵无”论;生活价值观;得意忘言;越名教而任自然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它主要是用老庄思想来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衰微的两汉经学。玄学家大都是当时的名士,其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与虚无玄远的清谈(一作清言,又称玄言、玄谈、谈玄)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这种风气始自曹魏何晏、王弼而贯穿于两晋南北朝。何晏与王弼以及夏侯玄等主要活动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公元240年—249年),一起开创玄学清谈之风,世称“正始之音”。
一、“贵无”论导引出合理的生活价值观
何晏(?—249),魏国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人,是东汉灵帝时国舅何进的孙子,才貌出众,学识渊博,官至尚书要职,并娶曹魏公主为妻。他性格豪放,自我感觉良好,生活奢侈,还要经常傅粉化妆,美容修饰,行走间常自顾自怜。他在学术上的建树是《道德论》《无名论》《无为论》和《论语集解》等著作。史称他“好老狂言”,“善谈易老”,上承西汉扬雄《太玄》,远绍先秦老、庄“玄之又玄”而开魏晋玄学。
王弼(226—249),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从小聪明异常,十几岁就能解析深奥的《老子》;擅长辩论,思维敏捷。著作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略例》和《论语释疑》等。
何晏、王弼的玄学核心是“贵无论”,这是他们关于对宇宙本源认识论的核心命题。在他们看来,“无”是一种超越一切物质世界的虚静本体。实际上,他们的“无”,就是老、庄的“道”或“玄”,也相当于《老子》第四十章里的“无”。那里面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何晏在《无为论》中阐述道;
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在何晏看来,超越物质而先天存在的“无”,不但是化育生成万物的根本,更重要的还是人生哲学的基础。所以,人们应当以“无”或“无为”为上,无条件地效仿它、遵循它,做事方能合理而获得理想的结果。如果统治者遵守“无为”,就可以成功地治理天下;一般民众信守“无为”,当然就会接受现实的一切而不致犯上作乱,遭遇不测。成功地把握“无”并运用它,就可以化解一切矛盾冲突,成就大业。这样的观点,与老、庄的“自然无为”论,并无什么差异。在这一点上,倒是王弼有所前进,有所发展。他在 《论语释疑》中说:
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
这段话意在说明,“无”虽然未曾存在过,但存在中的“有”却是由它生出。这样一来,“无”就成为“有”之本,而“有”乃“无”之末;因此,“无”便为世间一切“有”提供了其赖以存在的根本基础。很明显,王弼的阐发为老、庄的“自然无为”论补充了合理前提;同时,也将老、庄的“无”“道”“玄”三个核心概念直接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一目了然的同等式。王弼还在《老子指略》中说:
夫物之所生功之所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万物之宗也。
在这里,王弼认为,“道”和“无”是万物的“宗主”,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本体和原则。它们不是某种具体事物,而是万物的抽象,是万物的一般。一般就是“道”或“无”;万物是“有”,是个别。这样,王弼就超越了包括老子在内的先秦至秦汉的宇宙结构论的话题而向宇宙本体论(即关于宇宙、社会、人类本质或本体的讨论)递进,从而跨入哲学本体论的范畴,进入对人性和个体的讨论,对人的存在方式的讨论。这是王弼对中国哲学史的一个贡献。当然,也必须承认,对于一生以研究老、庄为乐趣的王弼来说,他开出的哲学思路仍然遵循着老、庄的“追求简易与根本”的方法。是老、庄之学给了他及其他魏晋玄学家寻找自我、解析人生的钥匙。正如王弼在《周易注》中所感叹的:“天下之理,莫不由易简而各得其方位也。”“各得其方位”,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生,它们都是在“无”这个“天下万物之本”的安排下获得各自的位置。
当王弼、何晏亮出“贵无”论之后,吸引来一大批厌恶经学章句、神学谶纬的学者向老、庄靠拢并参加关于“有”、“无”的讨论。譬如裴徽就求教于王弼,荀彧与荀粲也展开了激烈论辩。蜀中的秦宓则“自比于巢、许、四皓”而自言“安身为乐,无忧为福,处空虚之名,居不灵之龟,知我者希,则我贵矣!”[1]
“贵无”论之所以成为魏、晋玄学的一个核心点,成为魏晋人学的一个闪光点,不仅在于它适应了汉末清议以后知识分子集体理想主义普遍转向个人理想主义,追寻个体心灵超越与精神自我释放的步伐;还在于它导引出一个合理的生活价值观,即与“无”相一致的、合乎自然人性(人的本色形态)的混沌、质朴的自然生活态度。而这是同与“有”相应的、合于社会人性却是尔虞我诈的社会生活截然相反的。以个体独立和精神自由为底蕴的魏晋风度就是这样显现于世的。
二、“言”“意”讨论催生出士的主体意识
当建立起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后,何晏、王弼等又在认识论上乘势提出新理论。何晏在《无名论》中说:“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道本无名”,就是说,作为天地万物之本的“无” (在何晏、王弼即为“道”),和世间所有实际存在都有别,是不可以用语言概念来指称的。其潜台词是:言或名对意来说,是人们根据主观需要而强加的东西,并不能反映或完全反映事物的本真状态。
差不多同时,曹魏的另一位名士荀粲则明确发表“言不尽意”的观点,认为“象外之意,系表之言”都是“蕴而不出”的。意即在语言概念所表达的“象”之外,还有“意”存在,而这即是语言概念所不能表达的;所以“六经虽存,固圣人之糠秕。”[2]对此,王弼说得更为痛快。他在《周易略例·明象》里指出: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在这里,王弼将意、象、言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梳理,即“象”(现象、表现)是表达“意”(事物真相)的工具,“言”(语言概念)是说明“象”的载体。在此基础上,王弼阐述道,言、象其实只是一种指代符号,并不能反映或代表事物的本真形态与本真意义,“言”只是“象”之蹄(捕兔用的绳网之类),而“象”则是“意”之筌(捕鱼用的竹篼之类)。王弼因此得出结论说:
然则忘象者,乃得意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
这样轻飘飘的一段话,就摆脱了言、象对意的羁绊而去直抉事物的本真——意(在王弼们眼中,也就是无)。末了,王弼为自己的轻松超脱而颇为快意。他借用《庄子·外物》的话并发挥道: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
何晏、王弼与庄子一样,都认识到言、象的局限性而主张放弃它,因为“意”或者“无”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是统摄万物的“宗主”,不是具体的物象所能包容与反映、具体的语言概念所能展示和说明的。其实,《老子》也讲过“道可道,非常道”(如果道可以用语言描述出来的话,那么,“道”就不是本体意义上的“道”了)的话,认为那是“玄之又玄”的东西。王弼们的“无”,也像老子的“道”一样,被悬于虚无飘渺之中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却给了魏晋士子、士大夫阶层以无限想象的机会和空间,去尽量发挥作为人、作为士的主体能动性。顺着这条思路,王弼在《老子注》等著述里提出了天道即自然,自然即无为,无为就是“顺自然而行,不造不施”,而万物则“以自然为性”的主张,试图指引人们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去探索和恢复自然人——自然的我的本真。这就是王弼们与“贵无”论相配套的“得意忘言”、“言不尽意”论的哲学意义。这一立论也因此在魏晋士子中获得相当多数的响应。其中如嵇康还写过《言不尽意论》(惜已亡佚),进一步拓展内涵。当然,也不乏反对者,如欧阳建就写过 《言尽意论》,认为“形不待名而圆方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即宇宙万物是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但语言概念却是人们用以反映、说明客观存在的工具。尽管如此,欧阳建也不得不无奈地承认当时思想学术界的事实,即“世之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
但是,王弼们的“贵无”论及“得意忘言”、“以自然为性”的理论在现实社会中却受到以正名定分为主旨的礼教即“名教”的阻滞。因为那时的社会秩序、人性关系自有一套由来已久的浸淫着儒家“三纲”“五常”道德伦理的法律、法规及习俗来掌控与维持。王弼们要顺自然之性去自由地抒发个性(体现出道家性情),就必然要过“名教”这一关。先是何晏出来调停儒、道间的矛盾。他在《论语集解》注释《雍也》中的颜回“不迁怒,不贰过”时说:“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回任道,怒不过分。迁者,移也。怒当其理,不移易也。”他又在注释《子罕》时说,关于“毋意”,应是“以道为度”;关于“毋我”,应是“述古不自作,处群萃而不自异,惟道是从,故不有其身”。何晏的意思是说,儒家所谓的圣人、贤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和平常人一样是有情有欲的;只是这种情欲是有控制、有分寸的,不会超过限度,是“以情从理”,“不以物累”的。
不过,王弼却不尽然同意何晏的观点,他发表了一番在玄学史上极其重要的言论: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3]
在王弼看来,既然“圣人”是人而不是神,那他当然就具有一切人都有的生理特征和心理需要;然而,正因为他是“圣人”,那么他的心理调节能力就必定会胜过普通人。这样来看,儒家的圣人实际是既同于常人(具有五情)而又异于常人(茂于神明)的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可望并只要通过完善自身便可即的对象了。于是,王弼就将儒、道两家关于圣人的形象描绘、糅合在一起了,并将它视作当时士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范本。由此我们又可看出魏晋时代知识阶层作为“人”和“士”的主体意识已在悄然形成。
我们说王弼的上述言论在玄学史上极为重要,还不仅限这层意义。更为要紧的是,王弼指出了圣人的感情或性情乃“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即是说,圣人的性情均出自自然(出自天性,出自人的本真),不受外物包括名教的束缚。这样一来,王弼在“自然”与“名教”之间,便自然而然地导出了先“自然”后“名教”的时间顺序和价值顺序,从而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这一观点,贯穿于他的《老子注》里。例如他在注释“始制有名”时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在这里,王弼已然消除了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因素,而把名教看成是自然的产物。在《老子注》里,王弼在肯定了“礼教”规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后,又提醒人们说,“礼教”是人类“不能无为”以后的产物,并非宇宙万物包括人的自然本性。“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既打通了儒、道间的间壁(老子是主张“弃圣绝智”,强调“自然无为”的),又高扬起“道法自然”的旗帜,将更多的士子聚拢于这杆旗帜之下。
三、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说
后来“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受何晏、王弼的影响,写了《达庄论》、《通老论》和《通易论》等以道释儒、“叙无为之贵”、张扬“道法自然”的著作。他的自然观十分明确,即天地、万物和自然的存在与发生都有着自身的规律,而天地、万物、自然是一体的;至于名教与自然,则是可以协调好的。在此基础上,他在《通易论》里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见解,说“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而“天人之理”“自然之分”只在《庄子》的远古真人那里才最纯粹,最本真。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说:“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表达出他对庄子提倡的思想人格的向慕。
嵇康则将王弼“名教出于自然”与阮籍“名教本于自然”论更推进了一步,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他在《释私论》中写道:
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
在这里,嵇康表明了他厌恶“名教”的立场,要求回到自然;要求超越世俗功利去舒张人的自然性情,从超越中获取本真的自我形态。
稽康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因此,学校是停尸房,读经是说鬼话,六经是污秽,仁义是臭腐,经常看书会瞎眼睛,学礼义会变成曲背。他以老庄的“自然无为”论、“自然人性”论去批判儒学、圣人和名教(礼法),高唱生命之歌而鞭挞世俗社会,令当时正提倡礼法的司马氏集团和拥戴司马氏的礼法之士大惊失色,惶恐不安。
嵇康还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阐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绝对性,即个性自由的绝对性。他说:
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
在这篇著名文章里,嵇康反复表明自己之所以拒绝为官,“入山林而不返”,乃是为了获得自己的人格尊严,在“长林、本草”间去体味不受名教羁绊的真正自我。为此,怎么能够“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与嵇康论辩的向秀则比此前的文学家迈出了更大的一步。他在《难嵇叔夜养生论》里对“自然”内涵的概括,一反老、庄以来的简约、淳朴、恬淡、清静和无欲、无为,认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这“自然”甚至包括人们的权力欲、富贵梦及其实践状态。到了郭象那里,就更走到了极端。他在《庄子》之《大宗师注》里称“所谓无为之业非拱默而已;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又在《天道注》里说:“臣能亲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当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故各司其任,则上下咸得,而无为之理至矣。”郭象被史家记为“好老庄”、“善清谈”,是所谓庄学研究大家。可是,他却在庄学的最基本点上冒犯了庄子。庄子要超脱世俗功利,复归自然;郭象却将包括现存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在内的世俗现象都认做“天理自然”,要人们去违心地顺应它,不要反对它。很显然,郭象已经走向魏晋玄学精神的反面;因为魏晋玄学的主流“所追求和企图树立的是一种富有情感而独立自足,绝对自由和无限超越的人格本体”。[4]
何宴、王弼的“贵无”论多取《老子》,阮籍、嵇康的“自然”论则多学《庄子》,因此后人视何、王之论为老学,阮、嵇之论为庄学。而“无”这条玄学主线则把这四位玄学先锋、主将先后连接起来,在魏晋之际掀起以建立理想人格、争取精神自由和超越为目标、为实践的人文主义大波(以“竹林七贤”为主角的所谓“竹林之放”风尚是其标杆)。到了向秀、郭象那里(郭是反对“贵无”论的),这种目标则开始走向模糊,继而转向;这种实践也开始异化,并最终与世俗功利拥抱在一起,造成西晋前期为人诟病的“元康之放”(一种打着老庄及何、王“贵无”论旗号的伪人性、伪自然的纵欲主义思潮)。
注释:
[1]《三国志》卷三十八《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
[2]何邵:《荀粲传》,载《全晋文》卷十八。
[3]何邵:《王弼传》,载《全晋文》卷十八。
[4]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