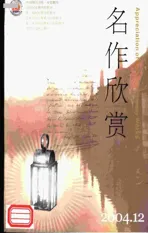永恒的诗歌和音乐
——细读欧阳江河诗歌《一夜肖邦》
2015-07-12韦黄丹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武汉430074
⊙韦黄丹[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武汉 430074]
永恒的诗歌和音乐
——细读欧阳江河诗歌《一夜肖邦》
⊙韦黄丹[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武汉 430074]
欧阳江河《一夜肖邦》是一首充满悖论、含混、张力,既复杂又统一的新诗。本文运用新批评的细读法来解开诗歌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依次读解与回溯性阅读分析,发现抒情主体有着共同的情感指向:音乐、诗歌乃至艺术,以一种“最弱的”“最温柔的”“虚无的”状态,存在于万物之中,又超越于万物之上,穿越时空,于一代又一代个体的艺术感悟中重生,最终实现艺术的永恒。诗歌所有复杂的悖论、矛盾与对立,在“艺术的永恒”中实现协调统一。
欧阳江河诗歌新批评音乐艺术永恒
欧阳江河是八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倡导者,自称为“词语造成的亡灵”,注重诗歌的语言魅力,在语义蕴藏和内在视域方面呈现出一种超验气质与复杂性。①欧阳江河的《一夜肖邦》正像是亡灵穿越了时空,透过词语在弹奏。笔尖划过,字符组合成“欧阳的诗”;指尖弹动,音符串连成“肖邦的曲”,似曲又是诗,字符与音符的交错中构成一首自足的诗歌。在新批评看来,一首优秀的诗歌必须既复杂又统一。由是,本文运用新批评的细读法来解读《一夜肖邦》这个复杂的有机文本,试图透过词与词、句与句、节与节以及整体的关系,探寻这个复杂文本背后的情感指向,聆听音乐与诗歌合奏出怎样的一支曲。此诗共五节,下面依次读解。
一
只听一支曲子,/只为这支曲子保留耳朵。/一个肖邦对世界已经足够。/谁在这样的钢琴之夜徘徊?
诗歌开头,毫无理由并且不容置疑地提出:“只听一支曲子,/只为这支曲子保留耳朵。”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哪一支曲子?它有何种力量让人的一生只为听这支曲子?此处,“耳朵”的全部意义被浓缩在“一支曲子”里,明显背离了常态。
接下来的一句给出了答案,“一个肖邦对世界已经足够”。首先,这是一支肖邦的曲子。肖邦是谁?保罗·亨利·朗著在《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提到:肖邦,是19世纪欧洲的伟大钢琴家、作曲家,被誉为“钢琴诗人”,是音乐史上最富创造性的音乐家之一。其次,“已经足够”,如此斩钉截铁的肯定,可以推测,“肖邦”的意义远超字面之上,绝非一个人名、一支曲子那么简单,其意义应与“世界”相当。由此,“只为这支曲子保留耳朵”便具有了可释性与合理性。然而,这是谁的世界?又是怎样的世界?诗歌没有顺势给出答案,而是抛出另一个疑问:“谁在这样的钢琴之夜徘徊?”谁呢?听琴人抑或是弹琴人?为何事“徘徊”?他是否也在思索着肖邦对世界的意义?
诗歌开篇点题,首次提到肖邦,便赋予他世界性意义,由此产生了许多悬而未解之谜。那么,带着对肖邦真正意义的追问,进入诗歌的主体部分:
从诗的第二节始,每一节的首句都呈现出相似的悖论性结构:“可以把已经弹过的曲子重新弹奏一遍,/好像从来没有弹过。”“可以把肖邦弹得好像弹错了一样。”“可以/把肖邦弹奏得好像没有肖邦。”“可以把肖邦弹奏得好像没有在弹。”都采用了“可以A,好像没有A”反逻辑的结构,恰恰是新批评中悖论的典型体现。语义不再是“A”或“否A”那么简单,而是“A”且“否A”的复加,“相互丰富,互相补充成为一个整体”②,极大增强了诗语的复义性与张力。肖邦或音乐艺术的意义,正是在这些矛盾对立的复杂关系中,得以诠释。
二
诗的第二节,是对肖邦音乐的初次探寻:肖邦,这种经典音乐,因重复而消解,又在消解中重获新生。死生转化,超越了时间,实现音乐艺术的永恒。
可以把已经弹过的曲子重新弹奏一遍,/好像从来没有弹过。/可以一遍一遍将它弹上一夜,/然后终生不再去弹。/可以/死于一夜肖邦,/然后慢慢地、用整整一生的时间活过来。
谁在重复弹琴?或许正是前面那个“徘徊”着的“谁”。经典音乐具有不可复制性,一方面,每一次弹奏确实是在重复;另一方面,重复的只是曲子,因为不可能有两次完全一样的演奏,所以,“已经弹过的曲子”“好像”“从来没有弹过”。另外,短时间内(一夜)的机械重复,会不会因感觉钝化而“弹死”肖邦?“当一个人两次听到的是同一次演奏时,要不要捂住耳朵呢?”③重复即消解,肖邦被“一夜弹死”后,便“终生不再去弹”。正如一首喜爱的歌曲,经过上百遍的单曲循环后,是否有种这辈子再也不要去听的冲动?
“可以”一词,单独成行,诗歌出现转折。原来,还有另一种意义的重复,它具有凤凰涅般重生的力量!“死于一夜”与“用一生活过来”又是一组强烈的对立矛盾体:“死去”与“复活”“、一夜”与“一生”,如何相互转化,融为一体?在重复弹奏中融入个体自身的生命体验,从中发现新灵感,获得新的艺术感受。原本的肖邦确实被消解了,但这个消解的过程亦是重生,它能让死去的肖邦穿越时间,重新在每一代人的艺术感受中“复活”。另外,让肖邦由死到生的艺术体验并非易事,需要“慢慢地”“用整整一生的时间”去努力。由此,在每一代人对肖邦的重新感悟中,肖邦音乐突破了“死生”界线,走向永生。
三
诗歌第三节,追求“弹错音”,而“此错”非“彼错”(一般意义上的判断词),“此错”足以造出一个永恒世界!
可以把肖邦弹得好像弹错了一样,/可以只弹旋律中空心的和弦。/只弹经过句,像一次远行穿过月亮。/只弹弱音,夏天被忘掉的阳光,/或阳光中偶然被想起的一小块黑暗。/可以把柔板弹奏得像一片开阔地,/像一场大雪迟迟不肯落下。/可以死去多年但好像刚刚才走开。
对具体的乐谱而言,例如肖邦有名的《g小调夜曲》,把该弹do的音弹成了la音,那确实是弹错了。这种蹩脚的失误,如何实现“一个肖邦”对“世界已经足够”?因此,可以断定,诗中的“弹错音”并非针对某一具体的曲子,而是面向真正的音乐艺术。真正懂音乐的人,毕生所追求的正是“弹错”而产生的“不谐和音”。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提到:“对于艺术上性质相近的不谐和音,我们正是如此描述这种状态特征的:我们要倾听,同时又想超越于倾听之上。在对清晰感觉到现实发生最高快感之时,又神往于无限,渴慕之心振翅欲飞……”④欧阳江河在《蝴蝶钢琴书写时间》中也有相似的观点:“我承认我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弹错的和弦,寻找海底怪兽般耸动的快速密集的经过句中隐约浮现的第十一根手指……因为那是显得孤立的声音,有冷和痛的边缘,它逆耳而行。”⑤“弹错音”逆耳而行,超越于倾听之上以趋向无限,用“第十一根手指”激起感受音乐的敏感度。更何况,在艺术世界中,没有纯粹的对错!“弹错”是为了发现另一种美的可能性,当寻找到这种更高的和谐音时,错亦是对。因而,要“把肖邦”“好像弹错了一样”,才能发现音乐艺术的无限之美。
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更高的境界呢?诗歌用反复出现的两个词“可以”和“只”所呈现的画面来实现音乐的无限可能性。“可以”“只”弹经过句,像“一次远行穿过月亮”,将时间转化为可感的距离;“只弹”弱音,像“夏天被忘掉的阳光”或“阳光中偶然被想起的一小块黑暗”,音乐有了微弱到甚至“被忘掉”的温度与光亮,需要极其敏感的生命才能发现它;“可以”把节奏舒缓的“柔板”,弹得“像一场大雪迟迟不肯落下”,承接上一句的“阳光”,表现音乐世界里既有夏天,又有冬天,四季变迁。音乐超越时间之上,“可以”“死去多年但好像刚刚才走开”。在音乐的世界里,死生不再受自然时间所控,死亦是生。
诗中把“音乐”与“月亮”“阳光”“大雪”等特性鲜明的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这种异质性比喻的运用,使得语象在相互叠加中丰富充盈。音乐,包含了时间与空间,既有声又有光,既有骄阳又有冰雪,四季分明。因而,“一个肖邦对世界已经足够”,在与音乐的心灵对话中,可以自己造出一个永恒的世界!
四
诗歌第四节,进一步探寻音乐与时间的关系。诗中说“这已不是肖邦的时代”“肖邦是听不见的”,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走进肖邦抑或是音乐艺术的世界?
可以/把肖邦弹奏得好像没有肖邦。/可以让一夜肖邦融化在撒旦的阳光下。/琴声如诉,耳朵里空无一人。/根本不要去听,肖邦是听不见的,/如果有人在听他就转身离去。/这已不是肖邦的时代,/那个思乡的、怀旧的、英雄城堡的时代。
“把肖邦弹奏得好像没有肖邦”,是进入肖邦、理解音乐的途径。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演奏大师作品的钢琴家,如果他把大师忘掉,显得他好像在倾诉自己的生平或此刻正身历某境,就弹奏得最好。”⑥“让一夜肖邦融化在撒旦的阳光下”,“撒旦”是《圣经》中堕落的天使,是罪恶的魔鬼,象征黑暗;而天使代表“阳光”,象征光明。正如上一节提到,艺术超越纯粹的对错,正误纠缠在一起,才能实现更高意义的和谐。而“撒旦”本身就是这样的合体,象征音乐艺术的至高境界。
诗的开头要我们“只听一支曲子”,而此处却说“根本不要去听,肖邦是听不见的”,这不是自相矛盾么?其实,“此听”非“彼听”。我们既要“听”,又要超越于“倾听”之上。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你走上你的伟大之路:这里不许有任何人尾随你!你的脚本身擦去了你身后的路,在路上写下大字:不可能。”⑦同样,肖邦,也在他的伟大音乐创作之路上写下“不要跟随我,要跟从你自己”。在感受肖邦抑或是音乐艺术的过程中,若仅仅只是尾随、聆听、模仿,那只会沦为盲目的奴隶,因而“肖邦是听不见的”,“如果有人在听他就转身离去”。只有融入自身的生命体验、个体的独立思考与创作,才能真正听懂肖邦/音乐艺术。从这个角度看,欧阳先生似乎比许多钢琴家更懂肖邦,更懂音乐艺术。
“这已不是肖邦的时代,/那个思乡的、怀旧的、英雄城堡的时代。”涉及到音乐艺术中瞬间与永恒、具体与抽象之间的关系。肖邦曾是那个年代的伟大钢琴家,虽然那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早已逝去,但是,他在那个年代所创作的音乐,因为足够优秀与经典,所以能超越“肖邦那个时代”的限制,存活在每一代人的艺术体验之中。由此可以解释诗歌开头,“只听一支曲子”,“一支曲子”不再是肖邦的某一支具体作品,而是抽象为音乐艺术符号,这种抽象的音乐艺术,只要生命不息,只要对音乐艺术足够敏感,它便能世代相传,实现艺术的永恒。
五
诗歌的最后一节,从肖邦的“实”,上升到音乐乃至艺术的“虚”。艺术可以超越世间万物,化为“最弱”“最温柔”的虚无状态,却足以“震撼”每一代人的“灵魂”,长存不息。
可以把肖邦弹奏得好像没有在弹。/轻点,再轻点,/不要让手指触到空气和泪水。/真正震撼我们灵魂的狂风暴雨,/可以是/最弱的,最温柔的。
诗歌结尾,从肖邦的“实”,过渡到艺术的“虚”。“可以把肖邦弹奏得好像没有在弹。/轻点再轻点/不要让手指触到空气和泪水。”从“有”到“无”,但“无”不是不存在,而是如空气般无所不在,是一种最高的存在。诗歌、音乐正是以“最弱的”“最温柔”的“虚无”姿态,存在于万物之中,又超越于万物之上,成为最高的艺术形式。正如莎士比亚在诗歌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Day中写道:“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est./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So long lives this,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只要生命不息,同时拥有一双发现艺术的眼睛,那么,诗歌、音乐便能超越世间一切,以一种最高的存在方式存活在每一代人的灵魂之中,万古长青。
六
至此,诗歌所有的矛盾对立、悖论、含混与冲突,在“艺术永恒”这个情感倾向中实现协调统一。从开头“一个肖邦对世界已经足够”的“实”,到结尾肖邦的消失,抽象为音乐艺术的“虚”——这种超越于万物之上的最高存在方式,欧阳江河用肖邦写诗的同时,也在向肖邦乃至艺术致敬!
欧阳江河曾谈到自己“家里CD一万多张,古典音乐”,他热爱音乐并常以音乐做诗,《一夜肖邦》可谓其中的经典之作。整首诗结构回环反复,“可以A,好像没有A”的复沓结构,出现在第二节起每一节的句首。相同位置、相似符号的重复出现,像极了音乐演奏中的旋律重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欧阳江河——这位音乐诗人,在用诗歌创作音乐,以诗人的方式用文字来弹奏不朽的“肖邦”呢?“肖邦”不仅仅只是“一支曲子”、一个时代那么简单,而象征着真正的音乐或永恒的艺术世界。
整首诗围绕着音乐艺术与时间的关系进行展开。时间流逝,乃自然规律,任何时代或是伟人,都无一例外被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之中,包括“那个思乡的、怀旧的、英雄城堡的(肖邦)时代”。因此,诗中出现了大量“死”的语象:“死于一夜肖邦”“可以死去多年”等等。在自然的线性时间中,肖邦以及他创作的音乐早已成为过去时,“这已不是肖邦的时代”,“耳朵里空无一人”。然而,真正的音乐艺术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它能超越于时间之上,只要生命不息,体会音乐的敏感度还在,音乐便长存于我们的心灵之中。当世间万物被时间吞没失去生命,世界为何没有因此消亡?那是因为音乐艺术以“最弱的”“最温柔的”“虚无”状态穿越时空,“震撼”每一代人的“灵魂”,在这个过程中,音乐实现永生。从这个角度来看,欧阳江河之所以要以“肖邦”做诗,似乎也有这样的写作雄心:一首好诗,只要足够经典,便会穿越时空,抽象为诗歌符号,以无所不在的方式存在,与肖邦一起成为永恒的艺术。“音乐诗人”与“钢琴诗人”穿越时空,携手合奏“永恒艺术”的乐章!
①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0—91页。
②赵毅衡:《重访新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③⑤欧阳江河:《谁去谁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第251—252页。
④⑥[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6页,第190页。
⑦[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2页。
[1]王毅.细读穆旦《诗八首》[J].名作欣赏,1998(2).
[2]王毅.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文本——细读伊沙《张常氏,你的保姆》[J].名作欣赏,2002(5).
[3]傅小平.欧阳江河访谈[J].诗歌月刊,2013(6).
[4]陈仲义.特殊的逻辑智慧:悖论诗语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4-50.
[5]余志超.肖邦夜曲研究[D].上海音乐学院,2008.
作者:韦黄丹,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