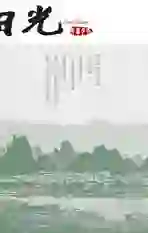续命
2015-05-30孙青瑜
由于先天心疾,我刚一出生,生死难卜的信息就传遍了整个颍河镇东街,很多邻居得知我的病情后都说:“肯定养不活,送人都没人要!”
或许正是这个定论,让目不识丁的母亲笼罩上了从未有过的恐怖和担心,面对我,就像面对一个灵魂早已出窍、肉体随时都会幻灭的病危之人,危险到让从未见过生死迭变的母亲随时都会目睹一次阴阳交替的残酷消息。除去喂奶,她几乎不敢抱我。也就是说,从我出生到十个月大,一直处在自生自灭状态,没人抱我,没人理我,一直被“圈”在床上,嗓子哭哑,母亲怯怯的心也不敢亲近我一点儿——那一刻恐怖战胜了母爱,让我从一出生就受寒流的侵袭,不想我却没死,仍奇迹般地活着……只是由于心跳猛烈,将小肚子震得一起一伏,如同拉动的风箱,时时都给母亲传递着垂死挣扎的危险信号,再加上我天生大眼,一难受,眼珠上吊,剩下一片眼白,形如正翻眼毙命的小狗,动不动把年轻的母亲吓得魂不守舍,将我朝床上一撂,夺路而逃。正是由于这挥之不去的恐怖,母亲每次喂饱我,一刻也不敢让我在她怀里多待……爷爷和爸爸知道后,一次次地叮嘱母亲说,既然生下来了,就不能虐待她,活一天是一天!从爷爷和爸爸仁慈的口气里可以听出,那时候我们整个东街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我能长大成人。
虽然长大成人了,可由于先天心疾,抵抗力差,几乎无一日不病,镇医院的医生、护士来来走走了多少茬,被我层出不穷又久治不愈的各种杂症缠败多少茬。记得其中有一位性情非常温和的黄医生一看到我就叫着我的小名儿感叹说:“小海霞,你算是把我给缠败了!”虽说是笑言,却透出一位医者的无奈和尴尬。除去医生,医院的护士们也一个个与我相熟。由于我长年打针,两胯的疙瘩终年不消,其中一个护士对我特别好。每次妈妈带着我去打针,她总是一边给我揉,一边推,半管药水常常要推十分钟——这个护士就是后来的周口市作协主席柳岸姑姑。
当时父亲在文坛上已经小有名气,由于创作成绩突出,一九八五年从农民转成为国家干部,供职于淮阳县文联吃上了皇粮。虽然有了工资,可父亲为了尽快给我续命,仍是日夜不停的写着……每年的三伏天,因为没有电扇,我们一家就躺在院子里,父亲看着天上的星星,对我说:“待有钱了,就带着你去上海做手术。”
事实上有钱这件事儿和上海一样,离我们很遥远。
因为母亲身体也极度糟糕,父亲挣的钱不但要养家糊口,还要给我们娘儿俩看病续命。在我前半生的记忆里,父亲不是坐在书房里写作,就带着我和母亲东奔西跑,求医看病。常言说“能养千口,不养药蒌儿”,更何况我们家一下子有两个药蒌儿。当时父亲刚刚转正,工资才四十多块钱,而一年的稿费加起来才四百多元,这两笔大钱除了一家人的吃饭所需,基本上都用在了给我们娘儿俩求医续命上了。病让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盖堂屋欠的三百块钱外债,让父亲还了三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一直拉不起院墙,盖不起门楼,安不起玻璃。到了冬天,父亲便用塑料布将窗户糊上,寒冬腊月的贼风挡在了外面,却挡不住窘迫的日子天天溜进我家。
父亲从来没有抱怨过,除了写作,还要照顾终年卧病在床的母亲和我。
为了有钱给我们娘儿俩看病,父亲每天笔耕到深夜。
我家的罩子灯很亮,直到全公社的灯光都灭了,它仍在倔强的亮着……睡醒一次,看到一个宽大的背影坐在书桌前,再睡醒一次,书桌前还坐一个宽大的背影……三九天,父亲每天上床睡觉时,只剩下胸口一点儿热气,母亲、我和我哥一替一个抱着父亲的双脚暖,只觉得脚不再是脚,而像一块刺骨的冰块儿,很快冰透了胸口,随后,母亲急忙接过去……就这样一替一个,一直暖到五点左右,父亲的双腿刚刚暖出一点儿热气,又要起床背诵诗文了。三伏天,父亲伏案写作的后背上,总是汗如雨流,母亲给他擦拭的毛布刚刚走过,又一身雨水般的汗珠拱了出来。除去难耐的酷暑,还有驱之不尽的蚊虫。因为我们家住在大坑边,所以蚊虫也繁殖成灾,万般无奈,爸爸就把双脚插在水盆里……尽管父亲努力奋斗的事迹不胫而走,成为众乡亲学习的榜样,可有病还是常常让我们家无分文,吃不上菜叶的清水日子三天两头出现。如果逢到青黄不接的时节生病,父亲就会一筹莫展,四处借钱。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们家搬到周口的第二年,当时父亲的工作还没有调到地区,由于一直埋头创作,职称也从来没评过,一九九三年仍拿着一个月二百块钱的低薪,和刚毕业的大学生相差不多。我们买房所需的首付,是卖了颍河镇的老屋交上的,一共一万两千块钱。开发商是熟人,买房时说好了,啥时候有钱啥时候交。不想等我们家卖掉老屋,举家搬迁到周口后,开发商变脸了,三天两头去我们家催账,为了尽快打发走讨债的小鬼,父亲将能借到钱的朋友都借了一个遍。挖东墙补住了西墙,西墙上的大窟窿虽说不着急还,可父亲和母亲都是欠不得别人债的,攒够一千,还一家,攒够一千还一家。不想有一次刚刚把新攒够的一千元还了债,正值家无分文之际,我又不知时节地病倒了。为了尽快盼来一点儿给我看病的银钿,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跑两次文联,文联在周口的河北,我家在周口的河南,相距有十多里,父亲焦急的身影往返于文联与家的路上,没有人知道那是一个急着为女儿凑钱看病的父亲,只知道他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作家。有一位叔叔见爸爸一天蹿来几趟,开玩笑地说:“大哥,你咋比我们上班的人跑的还勤快?”尽管父亲如此勤快的奔跑,一连几天,仍没有盼来一分钱的稿费……当父亲两手空空地回到家,看着躺在地上的我病得一动不能动,突然哭了:“孩子,爸真的没有办法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坚毅的父亲流泪!
因为无钱为我求医续命,父亲整整看了我一夜。记得那天夜里,父亲不停地喊我的名字,我知道父亲唯恐我在他眨眼之际无情地离开了他,给他留下终身的痛悔,在以后绵长的日子里,让他天天活在无力给女儿续命的内疚和自责里。或许正是那一次无力给我看病的内疚和自责让一直写小说的父亲转向电视剧写作,也正是这次写作的转型,让父亲暗藏在心间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终于有钱给我动手术续命了!
屈指一算,父亲的这个愿望从我出生一直到一九九七年才得以实现——整整十八年!
那一年我上高二,阳历的五月份,爸爸拿着刚刚接到的稿酬,带我坐上了北上的列车。动手术的那天,妈妈和三叔也从周口赶来了,因为陪护没有床位,三个人就委屈在医院的过道里。父亲和三叔都没有说什么,他们和众多家长一样躺在楼道里,还要时刻警惕着随时都会来驱赶他们的护士。或许那时候,他们什么也没想,只盼着我手术成功,让我危机四伏的生命走得长远一些,再长远一些……
动手术之前,我和爸爸已经在医院里住了半月有余,各种续命成功的幸运和续命失败的噩耗,听了不少。当盼了半个月的手术临近之日,恐惧和担忧笼罩着我们爷儿俩,唯恐手术有什么闪失,将我的小命断送于手术台上。
父亲的担忧是沉默,我的担忧却是有声的,不停地喊着“我害怕!我害怕!”
“有啥怕的,破上了就不怕了!”母亲用她的方式安慰我说。
不想“破上了”三个字,像是将死亡这件事推到我跟前,吓得我哇哇大哭起来。父亲斜了母亲一眼,没说什么,随后眼圈儿也红了。我知道父亲和我一样的惧怕,害怕他的宝贝女儿一眨眼死在手术台上。一直担心到院方让家属签字。看着那张生死条约,父亲才知道续命的危机不只是在手术台上,手术成功后,心胞发不发炎这个未知数也决定着续命能不能成功!父亲拿着签字笔,从心哆嗦到手,看着生命危机四伏的手术死约,父亲犹豫着还做不做?时间一直在推移,父亲的犹豫不决让医生等得焦急难耐,几番催促,父亲才填上“孙方友”三个字。父亲的名字不知道被他书写过多少次,唯有那一次书写的凝重让他流出了眼泪。听母亲说,父亲那一天签了字,一个人跑到广场上担心地哭了两个多小时候,才擦干泪回到病房。
手术从早晨八点多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一点半才结束。
我不知道这几个小时父亲、母亲和三叔在手术门外是怎么熬过来的,直到父亲去世的那一天,我在急救室外面仰天长吼着等待父亲的续命消息时,才知道“生死离别”的担忧是什么滋味,世界上没有一个词可以精准地形容它,只有心中泣血的呐喊、祈祷和情不自禁喷涌的泪水才知道它有多沉,每一分钟都被喜马拉雅山压着,每一秒都像刀子一样在剥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一天,在手术室外面的父亲全身冰凉,一直凉到心口,直到三点多钟,我醒来的消息通过监护室的门缝传出去的时候,父亲、母亲和三叔才草草吃了点儿午饭。
不想,我动了手术,心脏病不但没好,反而更加严重了,没等出院连续昏厥多次。
从此,生命危机四伏的信号开始从“偶而”变成了“天天”……父亲再一次带我踏上了漫无边际的续命之路。
从一九九七年到二○一三年,爸爸带着我跑遍了各大医院,找遍了众多名医,可医生一看复查结果,不是说我没事,就是说啥都好着嘞!药都不开,更有甚者还建议我去检查精神有没有问题,让我哭笑不得。
事实上,我不但有病,还时刻存在着病到阎王殿的危险。从一九九七年动了手术,十几年没有停歇过闹腾,动不动卧床不起,不能动弹。年纪轻轻,说病倒就病倒,还需花甲老母老父为我端吃端喝。病痛经常让我彻夜难眠,我总是忍不住的担心,今天脱了鞋,明天的命不知道还能不能续得上?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光“后事”不知道交待了多少次。
每次父亲听后虽然不说什么,可心里肯定比谁都担心,为我续命这件事仍像巨石一般压在他的心上,像火老虎一般追赶着他,让他不敢停笔,不敢歇息,到了身似漏船的年龄仍像老牛一般耕耘着,才能勉强填补我和母亲吃药看病续命的“钱洞”。可尽管如此,仍挡不住我一次又一次病到交待后事,逢到我交待后事的那几天,父亲每天深夜都要起来无数次,为我把脉,查看有无漏跳和早搏的迹象。看着父亲越发老迈的身影进进出出,我知道他每天深夜不唤自来,都是为“女儿还有没有了”这件事担心醒的。
眼看着我病情日益严重,父亲为了给我续命,让我多活一些年岁,只得求助中医。不想由于长年喝中药,心脏不但没有医好,胃也糟到极点,稍稍一动,心跳立即蹿到一百五六,同时还有胃炎、胃下垂、十二指肠堵塞,胃食管反流四种病联合攻击吾胃,把我折磨到随时都想撞墙而死。
为我续命这件事还没有成功,一晃父亲也到了身似漏船的年龄,心脏病也日益严重了……连续心梗两次,拉到医院从鬼门关上拽回来——父亲的续命任务从两个变成了为三个,从日常续命变成了紧急续命!
父亲第二次心梗抢救过来后,为了父亲的紧急续命问题,我们全家人坐上北上的列车,带着谁也不说的沉重和恐惧来到阜外医院。阜外医院里一位百岁的老医生看了我爸爸的CT片子,吓了一跳,随后同情地看了看父亲。因为那时候父亲的血管钙化面积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搭桥和支架这两条续命路子都被堵死了,唯一能救父亲的就是中医的血气理论了。气为血帅,气通则血畅,气滞了头一个反应就是血淤,血走不动了,憋出一身病,不死也得让你难受到想撞墙。父亲血脂稠引起的血管钙化,在中医这里也属于气滞血淤的范畴。而血淤的形成原因,中医有一个俗语叫“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上生”。也就是说,中医看百病,看的不是“百病”,而是在寻根溯源,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治本”。由于西医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零整思维已经续不动父亲的命了,我们一家人带着对中医的顶礼膜拜,对那个老中医投去感激的目光,只要有让父亲活得再长久一些的希望,别说喝中药,拿吾命换父命,我也会毫不犹豫。
那一天老中医给父亲号了脉,一再叮嘱父亲不能吃饱,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胃与心脏病有什么关系,但医生的安排,无疑是在告诉我们:父亲已经病入膏肓。因为我和父亲对中国古典文化都略知一二,知道中医号脉问诊不是隔布袋买猫,从《黄帝内经》起,甚至更早,中国的医学和解剖学就相当的发达,古人对人体的构造以及经络血象的运行状况早已了如指掌,机体的各个部件在发挥各自的作用时,中医从不孤立对待,而是按经络气象将其贯串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让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神话传说不绝于世——而眼前这位中国一流大医院里的百岁老中医说不定就是一个当代华佗,兴许就能让父亲不可逆转的生命走向柳暗花明呢!
事实上,父亲吃了中药后,不但没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或许正是因为来自身体直觉的种种不妙,父亲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又毅然给我买了一套房子,加上原来的那一套,一共两套。父亲的用意全家人都知道,好让我在他百年之后,病吃房租,维持住吃喝拉撒等基本的续命所需,至于看病续命那件事,就看天意了。
为此,父亲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又开始“授之于技”,加强了我的文学技能教育,天天逐字逐句地教我写作技巧和虚构大法,小到虚词的用法,大到虚构技巧,一讲半夜,目的就是让一直沉迷于学术自研的女儿走向更广的生存之路,有一手化知为用,以用挣钱,拿钱续命的生存本领。开始,我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直到父亲去世一年后,我随便看到一个物件,一个镜头或一句话都能虚构成文、换钱吃药之际,才恍悟出父亲的“高瞻远瞩”在我续命之路的价值和作用。
或许父亲授我于技时,并不知道他的傻女儿有没有化知为用的能力,所以愁云仍不能散去。因为我没有工作,母亲也没有工作,为了多给我们留下一点儿吃饭续命的钱,父亲带着重病,直到去世的那天早上,还在伏案创作。正是因为放心不下,父亲不知道给妈妈说过多少次:“我要是能凑合到七十岁,你们就不怕了。”可父亲没有凑合到七十,于二○一三年七月二十六号上午,丢下他正在书写的《戴仁权》,心衰走了!
用生活和文字为别人打了一辈子续命仗的父亲,却成了我们整个大家族第一个仙逝的人。
先前,父亲为了十多口人的基本续命问题不知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后来由于生活所迫,又去新疆当盲流,本以为能讨到一点儿生存下去的希望,不想却一直落不上户口,日子再度陷入绝望,只得于第二年返回到镇上,重新拉起架子车,搞人力运输。有一次父亲和一个邻居拉着两千多斤石头的架子车上桥,邻居拉着,父亲在后面推着,不想爬到半道,拉车的邻居没劲儿了,双臂发软。如果邻居此时手一松,正在后面推车的父亲肯定被千斤巨石砸进阴间,那一刻求生续命的欲望让年轻的父亲撕心大喊:“别丢把——坚持一会儿!就一会儿!”那个邻居为了让父亲逃生续命,果然用尽全力又坚持了两秒钟。正是这两秒钟,让父亲有了逃生的机会——身子刚刚一闪,几千斤巨石已经从几米高的地方滚了下去……或许那次的续命成功,就是为了让父亲在生活中、在文字里,为别人的续命问题劳碌一生,笔耕至死。存在者和不存在者都被他的一杆笔续活了、可一生忙碌着为别人续命的父亲,却因超负荷的劳动加速了命赴黄泉的速度。父亲突然心衰而亡的那一天,我们全家人像疯了一般——不相信!因为父亲还不到六十四岁,父亲的突然离世,不但终结了他自己的续命步伐,终结了他小说人物中的续命步伐,同样也终结了为我续命求活的艰难步伐,让我本来就朝不保夕的生命变得更加生死难卜。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父亲至死不能合眼,我和母亲几番给他扒上,可手一丢,眼睛又睁开了,浑浊的双眼直瞪着天花板,带着死不瞑目的担心和牵挂,身子一点儿一点儿地在僵硬着,可手却一直是软的,横跨阴阳两界,死死地拉着我这个残疾的女儿,不舍得松开,不舍得僵硬……让我再多感受一会儿从此再也奢望不到的父爱……
父亲的去世,对我打击太大了,大到生命没了保证,我几次险些哭死,可在生命垂危之时,再也盼不回那个天天半夜起床为我把脉的身影了,我只能一个人默默的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在生不如死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不哭,笑对人生。可每次病到生不如死之际,泪水又总是于无意识间滂沱而出……为了续写父亲的艺术生命,我不但带着重病和排山倒海的悲伤和三叔一道为父亲整理出二十三本编年书稿,还躺在病床上开始了小说创作,让父亲笔下那些没有续完的生命和人物,再次有了起死回生的气息。随后我为父亲续写的《小镇人物》和《陈州笔记》遍地开花地发表在诸多期刊上,换来的稿费,继续着我吃药续命的战争——
由于压力山大,就在微信上作诗发泄:
前三十年不识钱,
后三十年拿命换。
共产主义不共产,
饱汉不管饿汉饭。
昔日厅中乐开花,
不知愁苦在谁家。
今天墙草黄巴巴,
万般疾苦心间发。
也就是说,从父亲为我打续命仗到我自己为自己打续命仗,才知道“续命”这件事背后的沉重和压力。因为我的病情越来越重,病到说一句话就需躺在床上生不如死两个多小时,一动不能动;走一步路,就得换来半天痛不欲生的严重后果。因为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处处需要照顾。母亲和哥嫂看我病得越来越重,又开始拉着我四处求医——看病——续命。
不想病到这般田地,西医心科仍说我没病,可哪个长眼睛的人看到我的惨状都不会再相信西医的鬼话。万般无奈,哥哥又托人帮我找了一个名中医,一号脉,脉沉气滞到让医生吓了一跳,立即提议让我住院,可我没有舍得!我知道我朝医院里一躺,不朝里投五六千块钱,出不来。可钱呢?我带着愁肠百结的隐痛拒绝了医生住院的提议。可不住院,药还是要吃的,因为来自身体内部的病痛直觉告诉我,再不吃药,我随时都会命断魂散!可吃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起的,因为是名医,每次看病的挂号费将近五十元,再加打的费和药钱,看一次病就要一千出头。原因就是中医需要时常把脉调方,每次五十元的挂号费最多换来十天的药。也就是说,一个月我要看三次病,拿三次药,就是三千块,而我躺在病床上浴血奋战来的稿费才两千多元……那个时候我才发现一向温顺如羊的日子原来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一只用钱喂养的老虎,一天不给它喂钱,就有吞食我的危险。这只老虎追得我不敢停笔,当我病到卧床不起,一动不能动的时候,仍侧着身子躺在床上“笔耕不辍”,很多人夸我坚强,夸我勤劳,暗地里把我树成劳模和榜样,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不是坚强,我只是在生活,因为我不但要吃饭续命,还要吃药续命,两项续命任务把我压得随时都有窒息之险,每天早上三点半就起床,一动不动地写到深夜,写出来文字却不一定能换来一天的药钱和饭钱……在父亲走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治病续命这件事,让我对钱与命的关系比别人多出了许多泣血的理解。也就是说,直到父亲走后,我才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日子,在我病到生不如死的时候,我真想一死了之,跳楼自杀,用逃避的方式了结续命的压力。可年迈的母亲每每听到这话,总是老泪纵横。爸爸刚刚不在,如果我再死了,妈妈说她也不活了。听到这儿,我们娘儿俩禁不住相拥而泣,抱头痛哭。可泪干之后,发现自己暂时还没死,没有死,就得继续生活,继续强忍着病痛折磨朝前挣扎,熬一天算一天!也就是说病到这个时节,“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不需思考,便从病痛直觉中自显出来了。
一个月三千元的中药,不但没有缓解我的病情,反而越吃越重了,将拿钱续命这件事逼得更加刻不容缓,动不动心跳加速到一百五六,有一天夜里,竟蹿到二百下,身上大汗珠滚着小汗珠,像小绿豆和小黄米一颗接着一颗从汗腺里朝外拱,随后滚滚下坠,两眼一黑,昏厥过去了。本以为一去不再返,驾鹤去西天找父亲了,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身上一阵久违的舒服袭来,又舒服开了双眼。屋子还是那间屋子,床还是那个床,自己还是原来的自己,只是短暂的舒服之后,又开始死去活来的难受。难受是难受,毕竟还没有死,既然没死,就得继续“续命”。看着对面床上熟睡的母亲,我不由泪流满面,或许她一醒,就没有女儿了,就像去年我突然没了爸爸一样,我们全家人趴在父亲身上,悲天的号啕声能传遍整个医院,回想起爷爷悲不能行,奶奶昏死过去的场景——让我害怕,我已经不再是怕死,而是害怕年迈的母亲再一次经历生死离别的哀痛,我害怕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凉因为我的突然去世再次在我家上演——续命求生的欲望让我强撑着挣扎起来,从床头摸来速效救心丸,才算挺了过来。第二天在微信里写了一首自嘲的打油诗:
夜里心跳一百八,
险些蹬腿回老家,
今天一早又醒了,
继续奋力把钱抓。
直到这个时候,可以说仍没人理解我的痛苦与挣扎,众多的亲朋好友打来电话,一次次地安排我,不能这么拼,身体第一。无人知道我拼命是为了更好的续命,无人知道病痛折磨和经济压力早已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入不敷出的尴尬让我日益自责,躺在床上,从不敢停笔,仍侧着身子,将平板电脑竖起来,用手指头写,因为我不但要吃饭续命,还要吃药续命,没有钱,一切都是泡影,续写生命这件事也不例外。如果小心脏再如此疯狂下去,很快我就会心衰致死。可西医心科仍坚持说我没病,中医的血气调节不但没效,反把胃病也整到了瘫痪状态,一天能喝半碗粥已经谢天谢地……眼看生命垂危,就在我强颜说笑给老母交待后事时,二叔的学生程姑姑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郑大医附院的医生季峰博士去她们家串门,闲聊间说起最近西医也打破了头痛治头,腿疼医腿的单向度的思维模式,开始了综合考察病情的新思维,光他的研究方向——胃食管反流就能引发多种病症:如心脏病、哮喘、高血压、咳嗽……等几十种,同时他还通过临床经验发现了胃病引发的更多并发症,加起来大概有一百多种。因为这些新的医学研究成果还没有形成共识,很多医生不知道,仍在头痛医头,腿疼医腿,让很多病人误诊——尽管程姑姑说的有理有据,可谁会相信小小的胃病会是心脏病的原凶?
我不信。
在程姑姑家人的坚持和催促下,我只得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让嫂嫂和弟媳带我来到了郑大一附院。去的时候,我已经好多天没有洗脸,因为洗不动,也走不动,头发乱得如同丐帮帮主。嫂嫂说,戴个帽子吧!我不由暗想,人之将死还讲什么样子?可为了不让路人见笑,只得听嫂嫂的话,戴了一顶帽子。可尽管如此,我从门诊楼前下了车,那副生不如死、偻腰捂心、走一步比百步还难的可怜状,还是没能挡住众多异样的目光聚焦而来。就这样,嫂嫂挽着我一步三歇地坐上电梯,来到八楼的胃食管反流科室,进门一看,迎门坐的是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让我不由再次泄气,多少名医都治不好我,这么年轻的人会中?如果当即回去,不但辜负了程姑姑对我的关爱,也是给医生难看。
万般无奈,就再试一次吧。
季医生看了我的各种检查报告,并没让我住院的意思。可我却主动要求住院。我住院的本意并不是让季博士给我看病,而是想借机试试能不能来个专家会诊,给我多年的疑难杂症来个定性与确诊。谁料季医生也和其他心科医生一样,坚持说我心脏没病,不需要会诊,当天晚上给我挂了三瓶治胃的吊针。吊针挂了,虽然当天晚上还是粒米难进,可近一年不能安眠的我,竟然一觉睡到大天亮,太奇怪了。第二天季医生来查房问我怎么样,我说太奇怪了,今天夜里睡的很好,像是一点儿病都没了。不善言笑的季医生一听,禁不住笑了,说你这就是恶性循环,胃不好,睡不好觉,心脏病就会越来越严重,实际上病不在心脏上,而是在胃上。果然如季医生所言,随后他又连着给我保守治疗两天,一点儿心脏的药都没用,光治胃,心脏竟然不治而愈了。仅仅三天,我就能从十七楼爬上爬下,心不慌气不短。
太奇怪了!
自己病情好转了,可一层楼千里迢迢来续命的命友们,彻夜难眠的呕吐声、呻吟声,带着生命垂危的信号遍布整个大厅,我听着,看着,忍不住泪如雨下,身体的内部直觉体验和直观旁悟不一样,可续命的求生欲望却让我们从五湖四海聚在了一起。与我同屋的是一位肺癌晚期的阿姨,门口的加床上躺的是一位胃癌晚期的大爷,再远处是一位心梗搭桥的大叔……一楼的垂死挣扎,一次又一次的昏死——醒来,醒来——昏死,身体直觉告诉每一个生命垂危的人,自己之所以还活着,就是还没死,不死就不得不继续活着,倾其一生治病续命。可续命的沉重负担,却像大山一样压着每一个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有一次,一个女儿为了给父亲看病续命,因为钱和丈夫在大厅里大打出手——看到那一幕,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病不起,书写在每一个在场的病人和家属脸上。
因为来此求生者都是大病,哪个进来,没有十万八万的也甭想出院或死去……听了这个可怕的数字,让我心里一紧,这才知道自己一直没舍得动父亲给我留下的房租是对的!因为母亲老矣,我也老矣,父亲留给我们的续命钱,就让它在我们续命无力时当救急之需吧!所以当我重新回归亚健康后,除了吃饭续命这件事,我仍不敢乱花钱,不敢动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房租,因为我和母亲都还暂时活着,仍步履艰难地挣扎在续命的路上……
孙青瑜:女,汉族,1979年生于河南淮阳。发表散文《雅兴》,评论《孙方友文学的独特魅力》《论孙方友的小小说》《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的个性》《泡沫写作》《向艺术的最高层次迈进》,中篇小说《找老婆》,报告文学《是谁逼你为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