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四则
2015-04-20苏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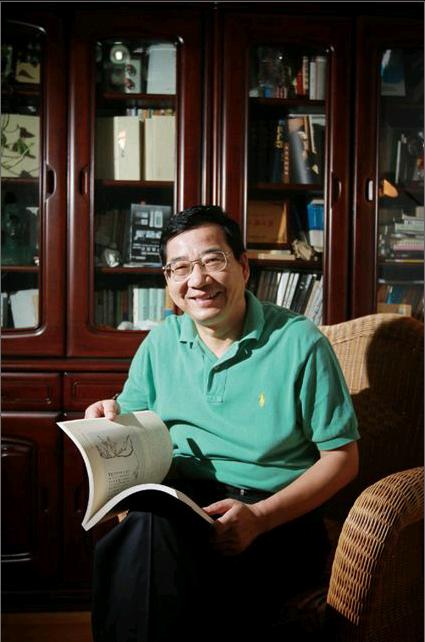
苏北,著名散文家,汪曾祺研究专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本。著有小说集《蚁民》、散文集《那年秋夜》和《一汪情深 回忆汪曾祺先生》、《忆·读汪曾祺》等。曾获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小说月报》第1 2届百花奖入围作品等多种奖项。苏北文字冲淡、平和,十分有情趣。现居合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些旧东西,都是缓慢的——给一个朋友
我似乎没有觉得自己生命的变化。和少年时一般,总是想往新鲜的事物,为一切新奇的东西所吸引。20多岁跑到北京,为了梦中的文学,睁一双好奇的眼睛,披着一头蓬乱的头发,奔走于京城的大街胡同;30出头,又因同样的原因,得到一个偶然的机缘,又二次上京,去办报纸。最初的冲动只是为了多认识两个朋友,以期在文学上能有所帮助;这样的设想似乎是荒唐的,但对于一个文学青年来说,又是非常的实用和要紧的。没想二次上京,却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从一个县城的孩子而混进了省城(似乎还差点调到北京,可天知道!),坐在有空调的大办公室里,T恤系在裤子里,头有时还有点斜着,嘴角有些似笑非笑的模样。
我本没有任何的基础,少年就是一个顽劣的小儿。可是神使鬼差,在某一日受了冰心和朱自清等人的蛊惑,喜欢上美丽的文学,如此一好而不能弃,受到了终生的折磨。这种折磨是痛并快乐着,类似于人生的某些生理的活动;又似吸毒般不离不弃。看看街上走动的人们,又是谁人在为文学而奔走?再瞧瞧书店里的那些纯文学杂志,也都静静地睡在那里。从世俗的方面看,内心知道,文学解决不了我们的生活。
我在平日的生活中,有时像一只小小的甲虫,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小心着过好每一个日子。可是正如朋友所说,老大不小了,还生活在梦幻中。这样的梦幻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自己的内心却坚持着,比如在自己的身后,能像沈从文、废名等一些作家,自己的文字能得以重印,使更多的人去阅读。自己县里的人,或者后人什么的,能提起一个名字:他的文章很好读啊!他的文字,给我以美的教育。其实现在已经有人在欣赏这些文字,我知道一些,好像还给过某些人以希望。有一个人,因这些文字,而生活得更好,更快乐一些。这些都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生命中的些许光辉。
现在并没有长时间的出门的机会。有时想啊,是不是可以到曾经工作过的城市去住些时候。和朋友们多呆一会,把新老朋友都会它一遍。和那些旧朋友呆在一起是幸福的。可我没有勇气,总是为平庸的生活所羁绊,梦中的行走永远是个梦。我并不为衣食忧,也不为稻梁谋。我整日怀揣着梦想,去做一个无尽的梦。也许有人说,有梦的人是幸福的。可是为梦所累,人似乎不是生活在现实中。
有一句说,活着活着就老了。人不能数着日子过,那样便没有了信心。可是生活的压迫总是存在的。好日子过得快。一年转瞬就溜走了。有些生活在记忆中,保存它,就留住了美好。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活着,就像河流,只能以一种方式去流淌。琐碎的生活用心去过,也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四季中,总有开花的日子,也有落叶的时分;下雨时,能在湖畔看雨是最幸福的,落日时,能在山中看住那一轮巨大的灿烂,慢慢坠下去,内心是极其庄严和神圣的。那其实就是生命。我们看着一轮灿烂的日头沉入西天,知道一天过去了。
可是我们更多的是在城市。城市的特点是匆忙的。这样我们多数时候,是忽略了我们自己。我们赶着日子。以周算,一眨眼,一周过去了。几个一周,一个月过去了。几个月,一年过去了。我们就这样的老去。古人说,山中日月长。人,一闲下来,就会感觉到,时光原来是如此悠长而缓慢。比如给你一天,坐在偏远山区的一个小镇的老街,一把竹椅,一只蒲扇,你的耳朵中,都是一些传统的声音;你的眼睛,看到的也都是一些简朴的生活。那些旧东西,都是缓慢的,这时你的心就会沉浸下来。我们的日子也同时给抻长了。有时我们从一个古镇上过,见那些坐在家门口的老人,他们或者都有了八九十岁的年纪,可是他们还很健康着。人的一生,什么是意义呢?有时就想:就这般静静的,像一只千年老龟一样。也许是一种真正的生活。
可是我们并不能都这样去生活。可不管是在哪里:都市,还是乡村。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关键是要用心,一用心,生活中的美就显现出来了。我们就会感到幸福。人一幸福,生命的意义也就有了。
一张徽菜单
笔记本里夹着一份徽菜单,是几年前在绩溪吃的一顿午饭。菜单如下:
石耳石鸡。臭鳜鱼。毛豆腐。胡适一品锅。红烧石斑鱼。树叶豆腐。青椒米虾。红焖野猪肉。火腿焙笋。
主食有:双味蒸饺,挞粿和麻糍。
我之所以留下这份菜单,是想留住一份记忆。这是一次让人愉快的、难忘的午餐。
在八大菜系中,现如今徽菜应该是最弱的。除食材难得之外,主要是徽菜重油重色,和以清淡为主的流行风尚相左。不过也不是完全式微,在北京就有好几家徽菜馆,我去过的徽州人家和皖南山水都不错。皖南山水还开了好几家分店呢!年前在北京,几个朋友在皖南山水中关村店小聚,点的菜都甚好。其中红烧土猪肉尤佳,肥而不腻,吃得大家满口流油,还一个劲叫好。
绩溪的那顿午餐,在一个幽静的不出名的小馆子。馆子外两棵高大的香樟树遮住了堂内半屋子的夏日阳光,香樟树的气味充斥四周。这一顿午餐当然要比北京的好。撇开厨艺不说,主要是在食材的原产地。所有的烹饪技艺,原材料的新鲜,当为第一要义。
比如就“黄山双石”吧。石耳与石鸡,两者清炒可以;清炖当然更佳。这都是难得的原料。石耳在悬崖石壁之上,采摘之难可想而知。石鸡在山涧小溪之中,都藏于阴暗幽静的地方。《舌尖上的中国》说石鸡与蛇共居,这我们在徽州早有所闻。事实如何?没有亲见,也只有姑且听之。但石鸡之难逮也可见一斑。我每次在徽州,只要桌上有石耳炖石鸡,我都当仁不让,先弄一碗;瞅准机会,再来一碗。这样的美食是难得的。石鸡是蛙类,状如牛蛙,可比牛蛙小多了。其味与牛蛙也相去十万八千里。我在外地吃饭,也见有以牛蛙充石鸡的。这蒙外行可以,如我辈,只一眼即可辨出。牛蛙的腿要比石鸡粗多了。
问石耳炖石鸡什么味?两字即可回答:清凉,鲜。
臭鳜鱼是徽州菜的代表了。取新鲜鳜鱼腌制而成,工序之复杂,不去赘述。在一些饭店,也有冒充臭鳜鱼的,以腐卤浇其上,肉质稀松,入口稀烂无味。辨别臭鳜鱼的真假,方法很简单:筷子一翻,叨出蒜瓣肉,肉色白里透红,肉质新鲜,入口有咬劲。必定是臭鳜鱼之上品。
毛豆腐是徽菜的另一代表。可我一直喜欢不起来。不置喙。
胡适一品锅是大菜。有九层的有六层的。主料是五花肉、蛋饺、熟火腿、鹌鹑蛋。辅料香菇、冬笋、干豆角。胡适一品锅既是大菜又是细菜。几层料叠加,需文火炖出,颇费功夫。我曾在绩溪的紫园住过好几天,每顿必有此君,可仍十分喜欢,
红烧石斑鱼。除在绩溪之外,我在太平和徽州区(岩寺)都吃过。红烧石斑鱼,我以为,以我们单位的干校烧得最好。吃石斑鱼,要在水边,鱼要活,要新鲜。每次去我们干校,都会端上一盆红烧石斑鱼上来。盆下点着酒精炉,热热地烧着。鱼只寸长,淹在红红的汤里咕嘟着。红烧石斑鱼没有辅料,只见鱼。吃一条,再吃一条。足矣!
树叶豆腐。徽州人吃树叶,历史很久。他们什么树叶都吃,花样很多。在徽州,我吃的多为橡籽豆腐和板籽豆腐。烧上一碗,乌黑的,但味道很好。滑,爽口。现在讲究绿色食品。这本来就是绿色的。
双味蒸饺。双味蒸饺有豆腐馅的和南瓜馅的,将豆腐或老南瓜和老黄瓜捣碎入馅。一拎起来,皮薄透明,入口,真是清爽!包的都是素的,能不好吃。
挞粿是徽州的特产,主要在绩溪。挞粿的特色是馅,香椿,干萝卜丝,南瓜,新鲜茶叶,都可以入馅。这些当地的材料做成的馅,特别香,也特别经饱。我的女儿在徽州读书四年,现在一提起挞粿,就流口水。
打麻糍什么地方都有。越打越有咬劲。徽州的麻糍在糯米外面滚上芝麻,猛火大笼,蒸出一屋子香气。
青椒米虾,红焖野猪肉,火腿焙笋。也各有特色,不一一记。
说是一张徽菜单,却去议论了一通徽菜。因我对徽菜太偏爱,又多有了解。所以在此胡嚼。写诗有“出律不改”,这里也任其跑题,由它去了。
汪曾祺的闲话
汪曾祺哪,真是说不尽的话题。在北京的一个饭局,大家说要成立汪研会,出一套汪曾祺研究文丛,之后在北京,开一家小酒馆,名日:汪曾祺小馆。由汪先生令公子汪朗坐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东榔头西棒槌的胡说,每人都说到兴头上。
说老头每到一地参加活动,喜写字,正如黄裳所说:“曾祺兴致甚高,喜作报告,会后请留‘墨宝,也必当仁不让,有求必应”。一次在浙江写字,写到高兴处,见几个漂亮服务员在一边忙着,老头捏着笔,模仿着浙江方言边招呼起来:“孤兰孤兰(过来过来),涅么(你们)几个小姑灵(娘)过来,我给涅么(你们)写幅字……”姑娘们便丢下活儿,一拥而上,正在这当儿,叶文玲走了过来,见老头得意的劲儿。叶文玲佯装生气:“去去去,涅么(你们)这些小妖精跑过来搞(干)什呢(么)!”
说老头饭后参加舞会,跳起来还挺有风度,不愧在西南联大“潇洒”过几年。有时舞场上有几个姿色出众的女性,老头都会心中有数。有一回王干将其中的一位请入舞池,在人丛中跳了一圈,回来坐在老头身边,老头儿虎着脸说:“你刚才跑哪儿去了?”王干笑说:别看老头儿不动声色,美女,会引起老头注意的呢,眼睛的余光瞄着呢!
有时老头酒后,兴奋劲还没过去,走到酒店大堂,见迎宾小姐在那站着,老头走上去,带几分顽皮,将胸一挺,模仿了一下,说: “应该这样站着。”将人笑翻。
偶尔老头儿开会带着老伴,老头就不敢这么嚣张,要收敛得多。稍有出格,便会被老太太训斥,老头有一次偷偷地说:“你们以后开会,可别带着老婆。
带着老伴出差,比赶一头牛还累!”
之后说到老头在家没地位。说上世纪七十年代,老头还不是老头,住在三里河一带,老邻居后来对汪朗说,总是看到你妈脚高高的跷着看外文书,而你爸,在那炒菜或干活!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老头博得文名,有一次酒后狂言:你们可得对我好一点,我将来可是要进文学史的。几个兄妹都大为惊奇,异口同声说:你,老头?别臭美了!
这绝非玩笑,因为在那个年代,几个兄妹所处的环境及所受的教育,与老头的文风是迥殊的(是啊,那时候有些作家,可比老头儿火多了)。电台里的文学欣赏节目里,所播的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长江三日》和《小橘灯》等散文。有一次正播《荔枝蜜》。老头听到了,很愤怒,冲过来说:关掉!关掉!中国的散文,一坏杨朔二坏秦牧三坏刘白羽。
散文配乐!叫怎么回事儿!
说到老头儿做的最出格的一件事,是一位女作家到老头家蹭饭,还带着自己离婚后新交的男朋友,老头儿给做了几个菜,现成的有薰肠啊泥螺啊等,自己再做一个煮干丝之类。女作家和男友喝白酒吃干丝,老头儿则站着,喝葡萄酒,很少吃菜,有时猛喝一口,才就一点小菜。吃到一半,老头儿一抱拳,说:你们慢慢吃,我小睡一会儿,于是就进到里面的卧室。女作家和男友在客厅继续喝酒。过了一会儿,女作家丢下筷子,悄悄走进里面的房间,老头儿正眯着呢!女作家坐在了老头儿的床头。老头儿睁开眼,深情地看着女作家,之后轻轻抓过女作家的手,在自己的手心里反复摩挲着,边摩挲嘴里边讷讷地说: “我不配我不配……”
这些笑谈,发生在农历癸巳年十月二十七,小雪后七日。地点是北京新东路沈记靓汤。参加者汪朗、王干、邢春,作家陈武,出版人崔付建,媒体人于一爽,文学博士刘涛等。大家一边吃着可口的江浙菜,一边笑言老头,气氛温暖而亲密。席间诸君兴致空前。
这些酒桌闲话,纯粹可以看着是掌故、笑谈。不必当真。即使有人信以为真,也只是关于老头儿的雅谑而已。说句最无趣的俗话吧,是老头儿的正能量,更增添老头儿的魅力呢。
与母亲啦呱记
“扁豆炒成虼蚤斑,豇豆炒成两头弯”,
元旦在老家,老婆买了扁豆回来,正在院子里掐扁豆,老婆边掐边说:扁豆不好炒,炒急了不熟,会有一股青味。她的婆婆正在屋檐下梳头,她刚洗了头,婆婆说:炒扁豆油要热,下锅大火炒。扁豆炒成虼蚤斑,豇豆炒成两头弯。炒扁豆,要炒出糊虼子。
母亲说的“糊虼子”,就是过去我们在农村被窝里见到的跳蚤掐死后的血斑。扁豆的正反两面要炒出一点糊虼子(糊斑),才好吃。
多年元旦没有回过老家。人过五十,才对元旦越发在意。今年元旦天气好,在老家过了三天。天天坐在院子里,看看天,看看书,与母亲聊聊天。
母亲今年已离八十不远,身体是大不如从前。这几年腿又不好,柱个棍子,在院子里忙东忙西。
她忙了好一阵子,感到累了,便“噢呦”一声,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这一声表示感叹,表示一项工作告一段落。可以歇一会儿了。于是便能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东一搭西一搭的,聊聊天。
先是说到邻居的孙子。这个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小时候特别好玩,爷爷奶奶惯得很,我记得他爷爷在世时,整天把他扛在肩膀头上。没想十几年一过,这孩子不成器,跟社会上不三不四的小混子学坏了,吃喝嫖赌,一样不拉。母亲说,小虫子小时候蛮好的一个孩子,没承想长大了是这么一个东西。真是“跟好人学好人,跟马虎学咬人。”这孩子算是废了。
说到小虫子的奶奶,年青时真是一个美人,高个白脸,相当有模样。待人又仗义又宽容,很是得人缘,家里就像个客栈,总是来人不断。她那时在电影院卖电影票,到她家里求票的人踏破门槛。夏天每天一开门,即有人进门,有的在帮电影票盖戳子,有又为她家捡菜洗菜的,有扫地的,有打水的(那时还得井里取水)。小院子里总是人声鼎沸。小虫子的奶奶就在那里指挥,笑着大声地说话,又亲切又干练,很有一点《红楼梦》里的王熙风的范儿。可是几年前突然老年痴呆了,走路柱根棍子,后来棍子也柱不住了,整天瘫在椅子上。我妈说,现在她家里是门庭冷落,“鬼都不上门”。真是“一口气在干般用,一朝散去万事休”。人呢,真没有意思。母亲叹息着。
说到表姐的孩子小玲莉大学毕业两年了没有工作,只在私人的广告公司打工,一个月才拿一千多块钱。本来参加一个学校的招聘已经面试,可是无钱找人送礼,最后还是被别人挤了。表姐买了两箱古井贡去打点,结果档次太低,没有起到效果。一气之下,表姐上门讨要,把两箱酒又要了回来,到今天还堆在家里,既舍不得自己家喝,又送不出去。表姐今年已六十多岁,四十出头才得子,表姐夫几年前癌症去世,就这么一个闺女,表姐的后半生可就依着她了!母亲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你说小玲莉连工作都找不到,你表姐靠她咋靠得住!二十大几了还没个对象,这么大的姑娘嫁不出去,急人不急人?老话说“早生儿子早享福,早生闺女早坐席”,这个“席”,到哪一天才能坐上呢。母亲又凭空叹了一口气。
说着说着太阳偏西了。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和冬日的花木都已在阴影里。母亲站起来,将晒在院子里的衣服和鞋袜拿了回去。她柱着棍子,拖着一只腿。一忽儿院子东,一忽儿院子西,十分的自得。她在这个院子已经生活了将近五十年了。这个院子是她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