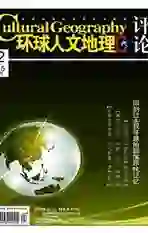仁者之情怀 诗家之史笔
2015-04-07王辅政
王辅政
摘要:《兵车行》以史家视角入而以诗家之笔成,寄寓了仁者情怀和济世之意,并通过“七重呼应,八转双合”的结构艺术以及师古而不拘泥、更重创新的艺术追求,树立了“诗史”类诗歌创作的典范。
关键词:仁者情怀;诗家史笔;七重呼应;八转二合;即事名篇
《兵车行》自问世以来,深得世人推崇,成为各种诗辑教材的上选之备,现当代更是赏析文章如云。该诗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这篇杰作至少有以下几个看点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品味:
一,史家视角,诗家之笔
杜甫的诗歌被后世称为“诗史”,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诗圣”。在诗坛,这种评价是至高无上的。为什么杜诗会被视为“诗史”?关键还是因为杜甫的关注视角大多在家国天下、黎元百姓身上。杜甫虽然不是史家,但他却始终关注现实、反应现实,并把他所观察所体味到的现实生活用诗歌的方式记录下来、展现出来。不必身临其境,透过杜甫的诗歌就能感受到时代生活和社会变迁。正是这种史家视角,使得这首诗具备了概括性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它从十二个角度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扩边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对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点行频”“未休关西卒”道出了兵源短缺、频繁征兵的事实;“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则从非龄服役和长久服役两个视角进行了揭露;“边庭流血成海水”“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则控诉了扩边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生命损失;“武皇开边意未已”则直接批判唐玄宗的穷兵黩武;“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描绘出了战争给农业生产造成的重大破坏和民生的凋敝;“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则反映了战争造成的社会分工的错乱;“被驱不异犬与鸡”控诉了官府施加给士兵的非人待遇;“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道出了民众敢怒而不敢言的无奈;“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揭露了因战争强加在百姓头上的沉重负担;“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则以民众重女轻男的反常心理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耶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二,仁者情怀,济世之意
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教化和影响。以民为本、仁政爱民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和基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忧以天下,乐以天下”[2]则是儒家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和主导;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仁者情怀,也是儒家的自觉担当。杜甫把对国家的忧虑、对民众的同情、对统治者的劝谕和警示尽寓诗中,这不是仁者的情怀和任者的担当又是什么?可惜当时的唐玄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没有把这类善言纶音纳入心中,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和大唐的衰败。不过,这种醒世之言、忧戚之情、济世之意,终究还是被后人所珍视。大清乾隆皇帝评价《兵车行》时说:“此体创自老杜,讽刺时事而托为征夫问答之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小雅》遗音也。篇首写得行色匆匆,笔势汹涌,如风潮骤至,不可逼视。以下出点行之频,出开边之非,然后正说时事,末以惨语结之。词意沉郁,音节悲壮,此天地商声,不可强为也。”[3]能让一代帝王发出“此天地商声”的赞叹,说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的警醒之语,难道不是大成其功吗?
三,七重呼应,八转二合
从层次上看,《兵车行》可分为三个部分:开头至“哭声直上干云霄”是第一部分,写将士出征、亲人送别的场面;从“道旁过者问行人”到“生男埋没随百草”是第二部分,从十一个角度揭露和控诉扩边战争;其余为第三部分,以虚笔写战殁者凄惨悲凉的处境,揭示战争的结果和残酷。层次十分鲜明。从结构手法上看,开头和结尾两部分的七重呼应尤其令人叫绝——内容上的“人”与“鬼”、“人哭”与“鬼哭”、“生离”与“死别”以及场面上的“悲怆”与“凄惨”、意境上的“尘埃”与“阴雨”、立意上的“实写”与“虚写”和表现手法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描写相呼应,使这首诗如丹炉契合,严密精绝。中间的主体部分则如丹在炉,聚而成金。从行文线索上看,全诗的内容经历了八次转承——从第一部分的送别场面到“过者”发问是诗歌的第一转;“行人但云点行频”到控诉非龄服役、长久服役是第二转;从非龄服役、长久服役到批评唐玄宗的穷兵黩武是第三转;接着写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民生凋敝和社会分工错乱,这是第四转;随后士兵倾诉非人待遇和敢怒而不敢言的愤懑则是第五转;继而写官府逼租、民众无计,进入第六转;第七转写民众反常的社会心理,揭示人民对战争的深恶痛绝;最后转入对战死者的描写,收束全诗,这是第八转。八个转承,贯穿起了全部内容,使得全诗有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此外,作者又用双重关合使全诗结构更显完整严密。第一重关合是首尾呼应的关合。第二重关合是问答关合,即诗歌第二部分的“道旁过者”与士兵之间一问一答所形成的关合(除“道旁过者问行人”一句外,从“点行频”开始到“生男埋没随百草”均为士兵的回答)。这首诗三个层次、七重呼应、八次转承、二重关合的结构艺术,无一不匠心独运,无一不令人叹服。
四,师古不泥,创领非凡
沈德潜说此诗“设为问答,声音节奏,纯从古乐府得来”,乾隆说“此体创自老杜,讽刺时事而托为征夫问答之词”。二人正好道出了《兵车行》师古与创新的妙谛。从内容上看,该诗与“我徂东山,慆慆不归”(《诗经·东山》),“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汉乐府民歌《十五从军征》)、“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秦始皇时民谣)等古代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精神一脉相承、神气贯通,体现了杜甫对《诗经》和汉乐府民歌等优秀创作传统的继承;从艺术形式上看,虽然歌行体诗歌早已存在并长期流传,但这首《兵车行》却感于时事,即事名篇,不拘古制,不泥古名,体现了高度的创造精神。而这种创造精神恰恰是艺术创作和人类文明发展最珍贵的所在。
总之,《兵车行》这首寄寓了仁者情怀、以史家视角入而以诗家之笔成的艺术精品,堪称“诗史”的典范,让人捧读再三而不倦。
参考文献:
[1]《孟子·尽心上》第九章。
[2]《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四章。
[3]清·爱新觉罗·弘历《唐宋诗醇》。转引自徐中玉《大学语文》第3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2012年1月第四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