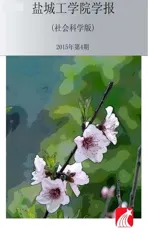从哈代的抒情诗看哈代悲观主义的成因及表现
2015-02-14焦优平
焦优平
(1.淮海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连云港 222005;2.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一、托马斯·哈代与其悲观主义
托马斯·哈代(1840-1928)一生创作诗歌近千首,体裁广泛,涉及战争诗、民谣、抒情诗和叙事诗等。他的创作手法多样,博采众长,独创了600多种诗节形式。正如哈代自己所言,诗歌是其文学成果中最能表现个人的部分,他的诗歌比小说更清楚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和体验。阅读哈代的作品,读者会震撼于弥漫其中的悲观气氛。哈代的小说,大都以乡村威塞克斯为背景,展示了人类自身特性与大自然不可知力两者结合对人类命运所产生的影响。哈代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不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他们被一些冷漠的力量所控制,这些力量操纵着他们的行为以及与其他人的关系。同时,他的诗歌也展示了不可预知的操纵人类世界的神秘力量;表明了作者对上帝这位全知、全善、全能的统治者的怀疑;流露出诗人对于生活的挫败、悔恨的心情,以及作者对于世界不可知未来的关注。他的悲观主义恰似一个谜,吸引了众多的评论家的好奇心,本文从分析哈代抒情诗入手,以探析其悲观主义的成因和表现。
二、哈代悲观主义的成因与表现
1.巨大的社会变革
哈代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是世界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发展甚至超过了过去两千年的总和。19世纪和20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获利匪浅,但是由一个农业化国家向工业转型的过程又是一段极其痛苦的历史。在繁荣的经济表面下,隐藏着极深的社会、经济、政治危机。与此同时还有科学与宗教的矛盾。天文学与地质学的发现不断地冲击着人们固有的宗教信仰。达尔文的理论也使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感到无比的孤独。他们钢筋铁骨般的哲学和宗教信仰开始崩溃。他们遭受前所未有的困惑、迷茫、异化、信仰缺失等焦虑。他们感受到一种亘古未有的悲观主义情绪。
生活在该时代的哈代也不例外。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哈代目睹了发展,也目睹了发展带来的破坏,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忠实地在他的小说中再现了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威塞克斯社会。与此同时,在抒情诗中,他也只能在他梦幻般的“威塞克斯高原”孤独、悲哀地吟唱,以对抗那残酷的现实。
威塞克斯高原(1896)
威塞克斯有高原,仿佛慈善妙手造/容我思考、梦想终老、危机时停靠,/嗨,东有鹰鹏碧肯,西有维斯奈峰,/在那儿我好像回到前世、置身来生。
平原上我无同道,更无孤独人的朋友——/她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无奈把现实接受:/在下面人们都怀疑鄙视,我知己难求,/但心的锁链不再叮当,若你的邻里是穹苍。
城里古怪的幽灵将我探究、追踪 /那幻影来自过去的生活中:/他们出语尖刻沉重,如影随形,/男子们的嘲笑冰冷,女子们的诽谤无情。
在下面我似乎不再是我,过去单纯的人,/也不是现在的我,他观察、惊异于造化弄人,/把他变成现在的模样,如此沉沦/虽然他依稀仍与自己——我的幼年相似。
灰色大平原我无法前行,因那儿月下有一人影,/除我以外没人看见,令我胆战心惊;/教堂尖塔林立之城,藩篱重重,我无法通行/可别人却能,在我的异象中他们长久禁食站立。
……
故我置身鹰鹏碧肯,或西在维斯奈峰,/或者在温馨的布尔山,或是在小匹斯顿顶,/那里男子不愿出没,女子也不来追踪,/幽灵都退避三舍,我也有了些许自由[1]567-568。
诗歌开篇表达了弥漫在哈代诗歌中的普遍意识——他常作为一个旁观者低吟、独唱着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从“危机”中抽身,他重返威塞克斯高原。这里危机一词值得注意,它是指事物向好或向坏发展的决定性的时刻、转折点。这样的危机,哈代遇到过,是当《徳伯家的苔丝》被评为“可耻”时,是当《无名的裘德》被大加鞭挞时,是当他对宗教权威所持的不可知论观点使他遭受到“不忠”的毁谤时,是当他和爱玛的婚姻日渐恶化时。这些危机足以使他沦入极端的孤独境地,他站在高原,以全景式的视野俯瞰众生。鹰鹏碧肯是英格兰最高的白垩地质山脉;维斯奈峰是夸桃克山脉的最高峰,形成了哈代威塞克斯高原中心区域的东西边界。他自囿于这片神奇的土地,在文学创作中寻找精神的自由。在那里,诗人已经来到一个空间外的空间,时间外的时间。高原就成了一个去思考、去梦想以终老的理想所在。在平原上,他既没有知音,也没有当一个人孤独时,才会选择的朋友——基督教信仰(这里反映了诗人的宗教观)。第二诗节第二诗行暗指新约福音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暗指基督教信仰。至此,诗人一直描述他在平原上的隔绝,诗人的孤独似已达到了高潮。他继而转向那些生活在他记忆中的幽灵。然而即使他们也无法逃脱思想的枷锁。他们嘲笑冰冷,诽谤无情,以一种古怪的、探究的方式对待诗人。
下一诗节中时间倒置了。现在的意识不再是跳出圈外,审视过去自我的旁观者,而成了被观察的对象。这样的情感如此的不适、痛苦。审视来者,过去的自我不由得惊叹飞逝的时光所带来的巨变,正像是由蛹到蝶的巨变一样。从简单到复杂,从单纯到世故,带着控诉和对罪的坦白,现在和过去的自我越过时空的界限彼此正视、互相触及,所带来的是虚空和难以愈合的创痛。接着诗人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游走。无论他去哪里,做什么,都会有重重叠叠的幽灵不断涌现,挡住他的去路。在恐惧和自我厌恶中,诗人饱受他们的非难和自我悲痛情绪的折磨。最终他从多年的折磨中走出来,不再有孤独和痛苦的记忆。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幽灵也退避三舍,他于是得享些许自由。
正如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2]292在这首诗中,哈代的思绪或在高原地,或在平原,穿梭于过去和现实之间。他的巨大的想象力使他能够以鹰般锐利的眼光,站在一个高度来观察下面的芸芸众生和过去的自我。他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从过去的自我的角度来审视今天的自我。在他的理想国里,在黎明或在梦中的威塞克斯高原,他保持着一份孤独。在那里,他可以远离尘嚣、摆脱巨大的痛苦。在平原,他是孤独的,因为没有人像他那样思考;在高原,他更孤独,因为他无法逃脱无穷尽的记忆和掌控世界的神秘力量的束缚。孤独与怀旧两种情感交织,构成了贯穿整首诗歌的主线。相对而言,前者更清晰,后者较隐晦。它们两个聚合在一起,构成回响于整首诗的主题。读者似可看到诗人站在高山上,独作浮云游,以躲避残酷的现实,腐朽的神学和时空的虚幻。在他的梦的高原,他思索,梦想以终老。他不禁产生了一种幻影,如庄周般惊叹:“庄生夜梦迷蝴蝶,庄周之梦为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3]42
2.宗教信仰的缺失
哈代一生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反映在许多诗歌中。他的家人在他童年时就负责家乡教堂的看管,自己也很虔诚考虑过当牧师。但1888年被一个牧师问及怎样理解上帝的纯全良善与人世间的恐怖的矛盾时,哈代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向他推荐了达尔文的书。在诗歌《自然的疑问》中,“自然”提出了关于宇宙起源的困惑与推测,诗中的答复是:“我没有回答… …”——这个回答反映了哈代自己的宗教观的改变[1]525。为什么他的宗教观变化这么大呢?
审视维多利亚时代,宗教正被疑惑、淡化。疑惑有二:一是《创世纪》中有关神创造世界的记述;二是新约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的神性。1859年,查理·达尔文(1809-1882)《物种起源》的发表,给人们的宗教信仰带来了巨大冲击,也使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感到无比的孤独和亘古未有的悲观。他们钢筋铁骨般的哲学和宗教信仰开始崩溃,并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困惑、迷茫、异化和缺失。进化论改写了《圣经》中关于人类起源和神创造世界的神秘记载,极大破坏了人们心中上帝的全知全能者的形象,并且也带来了科学与历史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的新趋向。当时德国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发现更多关于耶稣生平的真实历史记录。但这样做的结果是耶稣的神性光环渐渐减弱而变得世俗化。耶稣的不可否认的存在越被确立,他就越像一个凡人。身处历史的漩涡,哈代对当时的这些事件非常关注。在他的许多诗中,他表达了对福音书中所记叙内容的崇敬,但又有意避开对其真实性做任何评论。
牛
圣诞前夜,十二点钟/“它们正在跪拜,”/一位长者这样说,那时我们一群人,/正舒适地围坐余火。
我们想像那温顺的生灵/安然卧在圈内/没有人想要探个究竟/它们是否在下跪。
美丽的传说,很少有人再编撰,/近年来!可是,唉,/平安夜若有人来召唤:/“走;去看牛跪拜,就在远山那边,孤寂的仓房,/儿时熟悉的所在”/我会带着忧郁与他同往/希望那或许存在。[4]33-34。
本诗被认为是哈代一首最怀旧并富于哲理的诗[1]35。有这样一个传说:平安夜的午夜,牛会屈膝向基督敬拜。前两诗节将读者带回质朴的乡村生活,一群敬拜者,像羊群一样围坐在熄灭的炉火边。第一节中的长者宣讲那有关牛的屈膝敬拜的古老传说,听众也都深信不疑。第三诗节将时间从过去带至现在,少有人再相信“美丽的传说……,近年来!”全诗以歌谣体的形式流畅地行文,这是记叙民间传说时常用的韵律。但是这种流畅被怀疑打断,而这种怀疑破坏了人们对于这一古老传说的信任。而同时,基督教某种程度上是受这些传说支撑的。不过这种打断只是暂时的。歌谣体的韵律继续在第3、4诗节展开。哈代也再次回到对古老传说的陈述。他说若是遇到一位相信这一传说的老朋友,他会与他同去山那边的牛棚,但却是带着忧郁。
在哈代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那些美丽的圣诞故事似乎与当时的实证主义科学研究成果相悖。不过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诗人仍希望这些传说是真实的。哈代试图大声说出他的这种失落感,以寻得解脱,但又不能允许自己这样做。诗中所持的微弱的希望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基督教真实性的深深的怀疑。内心的冲突来自于他信仰的缺失,也成为他悲观主义的一个成因。
3.悲观主义哲学
当代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对人类信仰的冲击,使哈代反思这个与人类情感和固有价值观相悖的世界。哈代广泛地阅读同时代的哲学著作,以期寻求解答,叔本华、尼采这样的悲观主义论者,也在哈代的仔细研读之列。1924年他写了一本有关自己作品的书,有人评论说这本书更像是一篇关于叔本华的论文,只是加了有关哈代的注释而已[5]80。哈代承认他的字里行间显示了与达尔文、孔德(1798 -1857)等人的一致观点[5]80。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观的影响,哈代的《意志与意念的世界》(1819)中的一些诗歌展示了命运的多舛,灾难和具反讽意味的偶然。人类是一种好矜夸的生物,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他们创造了人类的文明,但实际上又极其软弱、渺小。当面对掌控他们命运的内在于宇宙的神秘的力量时,灾难和偶然可以出人意外地毁灭人类,悄无声息、不可逆转。哈代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切,以感伤、敏锐的方式,为他的抒情诗增添了些许独特的色彩。
两相会合
(关于泰坦尼克的沉没)
在孤寂的大海里
远离人类虚荣的深处
“生命之骄傲”设计的她,静静躺卧那里
钢屋,后来的火场
曾有熊熊烈焰飞扬
已被冰冷的海水漫过,任由潮汐把乐曲奏响
那边的镜子,原要
把奢华与富有炫耀
现海虫正爬行——古怪、粘滑、笨拙、冷傲。
钻饰原为欢乐设定
去满足享乐的心灵
现在却黯然,光芒尽失,漆黑、幽冥。
海鱼迷蒙地盯着
近处镀金的齿轮
奇怪地问:“这虚荣的家伙下到这儿做什么?”
噢:当它还只是雏形
这个两翼分开的生灵
“不可控的意志力”就已激发、催促着每件事的发生
为她准备了一个仇者
为伴——如此庞大、欢乐
那是冰山的身影,从远方游弋而来,为了这一刻。
当这漂亮的船渐长
不论声誉、外貌和身量
在幽暗的远处,冰山也在不断成长
他们真像天外来客
肉眼凡胎未曾见的
紧密地在后来的历史事件中融合,
或者叹息命运使然
被导入歧途
不久前那个整体的船被庄严地分成了两半
直到“岁月的织者”
说:“开始!”且两个都听到了,
船体也戛然裂成两段,就这样完成了会合。[4]63-64。
这首诗记述了1912年4月15日所发生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在从英国南安普敦出发跨越大西洋到纽约的首航中,遭遇冰山沉没,1500人因之丧生。泰坦尼克号是当时最大也最奢华的班轮,曾自诩为永不沉没。但具讽刺意味的是不可沉没的却最终沉没。在这首诗中,哈代没有以该事件所揭示的人类悲剧为中心,而是从它的悲观主义寓意着手去书写。该诗揭示的是:人类,尽管他们很伟大,但仍然处于未知命运的掌控中。
该诗结构巧妙,每个诗节看起来都像是一艘船。该诗分为三部分。前5诗节有关船的建造(其中,前四诗节结构一致,前2诗行是船的往昔,第3诗行是它的现状),中间3个诗节有关冰山的渐近,最后3诗节有关二者的聚合。前5诗节生命的骄傲和不可控的意志形成强烈的对比;还有奢华与人类奢华的化身——泰坦尼克号和它邪恶的同伴——冰山。出于人类的虚荣,人类建造了这艘惊人庞大的钢铁怪物,装备了连罗马时代皇帝都未曾梦想到过的奢侈品。但出人意料地,自然亦叫命运,或叫掌控人类命运的未知的力量——岁月的织者伸出了它的手指干预,悲剧发生了,一切都化为乌有。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铸成这一切,不为人知,不可预见。最终,泰坦尼克号,人类所创造过的最伟大的东西,躺在了大洋底部,完全成为了一团毫无用处的废铁。
整体来看,哈代在诗歌中描述了一些弥漫在整个宇宙中的某种力量。在这种力量的严密掌控下,人类似乎是无助与完全盲目的,他们不能感到和预言他们应去哪里。他们尘世的悲欢在这种力量下都归于无有。人类有时或许可以夸耀他们的创造,他们的文明和智慧,然而那不可控的内在于宇宙的意志力更强有力,是它激起了和催促着每件事的发生。在那静默的深处,他们可以改变左右人类命运的每一件事。
4.痛苦的婚姻
哈代的悲观主义也与他和妻子爱玛·吉福德的痛苦婚姻有关。哈代的许多诗起于对爱情得失的冥想,他的许多诗也被两人近40年的不和谐关系重重着色。1870年,哈代的首部小说《绝望的补救》(The Desperate Remedy)发表了。这一年,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对哈代而言也是关键的。在一次去康沃尔修缮教堂的旅行中,他遇到了爱玛·吉福德,教堂牧师的妻妹。他对她一见倾心,自此展开一段浪漫的爱情,但仅持续了4年,后来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据说两人再也没有一起回过康沃尔。1912年爱玛突然出人意外地去世,让哈代极度痛苦。他写给一位朋友:“生命中没有了她,我极度悲伤。最痛苦的莫过于走进花园,走上山顶的直道,你知道,她常在薄暮前到那儿散步,猫也总会忠实地跟着她快走,有时我甚至期望看到她像往日那样手里拿着小铲从花坛走出。”[5]22
这段描述极富诗意。数月后,1913年春天,哈代孤身一人再度前往康沃尔,重新游历40多年前他初遇爱玛的地方。尽管这次旅行是痛苦和追悔的,但对诗人来说,其诗集《诗歌1912-1913》中却有不少作品受到这次旅行的启发。它清晰展示了哈代的痛苦、懊悔和失望,不仅被誉为哈代最美的爱情诗歌集之一,也被公认为是英语诗歌中最富表现力的挽歌的一部分。这些诗作表达了哈代的爱与痛苦的紧密渊源。当死亡留下大段空白,需要他的爱去填补的时候,哈代的创造力被激发,因而写出了大量的爱情诗。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不肯受安慰的负罪感、攻击、忧伤、反责、自我责备,爱怜与憎恨都赤露敞开在读者面前。这里,哈代试图逃离现实,回到早期相恋的美好时光。这些诗歌充满强烈的自问,无望的自我安慰。这种不安与躁动或许构成了他的这些作品的主要美学力量。从这些强烈的内心狂乱中,哈代呈现出心理的重负和矛盾。一方面是他的悼念,另一方面是他强烈的要表达这些情感的愿望。
离开
为什么那晚你什么都没说/紧接着次日刚过黎明时刻/悄然,仿佛出于极度的冷漠,/别了这尘世路程,升天去了/我却不能同去/如燕展翅跟随/好不时地看看你!
从未道别离,/或将我轻声唤,/或说出哪怕一句心愿,/清晨日光已照亮墙垣,/我麻木、茫然,/你伟大的离开/将那刻定格,全然改变。
为什么你引我离开房屋/刹那间以为又见到了你/在那枝蔓覆盖的小路尽头/你薄暮时常去的所在;/直到在阴湿处/那幽暗的虚空/景象令人发昏,让我心痛!
你是那姑娘,住在遥远西方,/有着红色血脉的石旁——/你姿态婀娜,迤逦骑行/沿着突出的壁尼山顶,/且与我并驾齐驱,/你会沉思、把我注视,/那时生活为我们展开最美的画卷。
为什么,后来,我们不再谈起/难道从没有想过那起初的时光,/也未在你消逝前奋力寻求/那时光的再新?我们本应说:/“趁这明媚的春光/让我们一同游历/那曾到过的地方。”
哦,噢!修合只在昨天,/现已无法改变。无力挽留。/我似已垂死,苟延残喘到最后/我行将就木……噢,你哪里知道/你快捷的逃离/无人预知——/我也难料——会把我如此毁掉![4]67-68
诗歌以问句开篇以表达哈代对逝去的妻子的责问。他似在控告她的安静的离去,近乎无情,出于极度的冷漠。无视生活和她丈夫的情感,她结束了尘世的历程,不辞而别。哈代震惊、麻木,因为他再没有机会道别、和解。因为她的离开,把那一刻定格,改变了一切。这一次,生者反而成了这一情境的受害者。接着诗人重拾青年时代浪漫爱情的永恒美好记忆,将读者带回40多年前的康沃尔。壁尼是爱玛故乡附近的一处壮观的悬崖。她少女时代常常在那骑马游历。他让带着力量与丰富色彩的过去活灵活现于纸间:她住在西部有红色血脉的巨石边,沿着海岸婀娜骑行。好像生活在那时向我们展开最美的画卷。他们本应和谐地生活,但后来谁也不再谈、也不再想那逝去的好时光。他们本应在这明媚的春光里,再度游历那曾游历过的地方,但她却一去不返了。最后诗歌以韵律的打破而结尾,其口语般的语调极其深刻,反映了哈代对现状的清醒认识。同时诗人以惊人的有关自己死亡情景的想象来惩罚自己:“我似已就木,坚持到底,行将淹没。”
在分析忧伤的自责和悲痛的悼念时,弗洛伊德认为哀悼者的自我谴责的原因是他曾经无意识地希望对方死去。这样的负罪感甚至可以进一步发展为一种自我惩罚的幻象。在《离开》中,诗歌以对哈代妻子的悼念始,却以哈代的自我悼念终。他的痛苦的婚姻赋予他诗歌以悲观主义色彩。这种悲观主义是对他们婚姻的失败和爱玛突然离世的责备与自责,负罪与懊悔,及痛苦情感的混合体。悔恨是难以愈合的,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所言:“没有何处能找到良方治愈悲伤/不论法律、福音、溯源或草药。”[6]29
三、独特的悲观主义
哈代诗歌呈现复杂的特点。他的诗歌呈现的是:命运的多舛;灾难和具有反讽意味的巧合;疑惑、沉重、悲伤、失丧、受挫、追悔和有时候极力控制的哀婉情感。在上述诗歌中,读者可以体察到他那挥之不去的悲观情调和其独特的悲观主义特点。
《威塞克斯高地》中,哈代创作了另一个“乌有乡”——威塞克斯高地,以脱离、逃避他在所谓低地所遭遇的严酷的现实。然而“高地”也不能使他宁静,因为他的思绪中可怖的记忆仍然挥之不去。他的灵魂由于对别人的背叛,对年青时自我的背叛而导致的负罪感而折磨。时空在诗中被倒置。他的孤独、怀旧情绪弥漫于整首诗中,并达到了情感的顶峰。是否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对哈代而言,是另一个难题。在诗歌《牛》中,哈代展现的是由于对宗教信仰的怀疑动摇而产生的苦恼。受进化论和实证科学思想影响虽深,哈代无论从情感上和道德上仍无法成为完全的无神论者。关涉到神学,他清醒而又不安地保持着怀疑的态度。他无法使自己完全与传统的信仰决裂。他保持着参加教会崇拜活动的习惯,直到1922年。对他而言,教堂是一个可以给人类灵魂提供终极安慰的所在。《两相会合》展现的是人类命运受宇宙间无常的力量所摆布这一具有反讽意味的现实。那不可控制的内在于宇宙的意志力,像不可理解又冷酷无情的怪兽,在哈代的诗中萦绕不去。控制人类命运的这股力量如此强大,与之相比,人类的一切行为、筹算都显得荒谬可笑。《离开》这首诗中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刚刚发生的死亡自身,他们之间长期的爱情的死般挣扎和最初强烈的爱。它们在这里交织在一起,也同样出现于哈代众多的哀悼亡妻的诗歌之中。过去的经历是痛苦的,诗人只能从记忆中重拾那最美好的原初的爱。而现在却总是那样的悲观与空虚。
综上所述,身处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加之科学迅猛发展,人们宗教信仰面临危机,各种哲学思潮风起云涌,个人婚姻的不幸等影响,哈代诗歌呈现出一定的悲观主义特色,在他的抒情诗中具体表现为:孤独、怀旧;有神论与无神论的碰撞;自然界内在于宇宙中的意志力与人类意志的矛盾;爱玛的去世所带来的痛苦与懊悔。
(注:文中诗歌、英文资料由笔者翻译。)
[1]Moynahan,Julian.The Portable Thomas Hardy[M].England:Penguin Books,1977.
[2]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清]王先谦撰,陈凡整理.庄子集解[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4]Gibson,James.Chosen Poems of Thomas Hardy[M].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1975.
[5]Ward,John Powell.Thomas Hardy’s Poetry[M].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1993.
[6]Ramazani,Jahan.Poetry of Mourning:the Modern Elegy from Hardy to Heane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