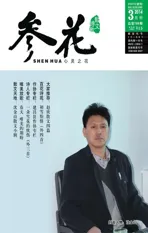草原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里快长篇小说《狗祭》评析
2014-12-12吴玉英
◎吴玉英
草原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
——里快长篇小说《狗祭》评析
◎吴玉英
《狗祭》是著名作家里快先生创作的一部小说。小说最后那一场神圣的仪式所完成的,既是对草原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祭奠,同时也是对生态文明的呼唤和憧憬。而对于作家来说,则是一种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狗祭》 草原 工业 生态
著名作家里快先生的小说《狗祭》讲述了动物世界中“人类忠实的朋友”,草原上的优秀生命哈日巴拉被卑鄙完全俘获后,丧失本性,背叛灵魂,走向罪恶,主人巴图老人无奈之下只能选择结束它的生命,以此阻止它在罪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小说最后,在神圣的狗的祭奠仪式中诠释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对草原文明的眷恋、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对生态文明的呼唤。
一、对草原文明的眷恋
作为一名生活在草原上的汉族作家,里快先生与草原有着深厚的血脉关系,对草原文明更是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小说开篇就为我们展现了大草原独有的魅力,“沿着库伦图草原月牙形的边缘,恩格尔河把蓝天白云深情地揽在怀里,在肥美的草地上描绘出一个九曲十八弯的图案,然后泛动着碎银般的涟漪,悠然自得地向着远方流去。沿河两岸密匝匝的牧草和鲜花,托起一层乳白色的水雾,顺着我河道堤岸依次展开,……然后融入那片没有边际的绿色里。”[1](P1)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们进入这充满无限生机活力的草原后,立即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悦,“在享用和感受了这片得天独厚的草甸风光之后,他们便怀着一种像牧人在黄昏到来时的惬意,仔细地回味、咀嚼着一天的爽快和愉悦,然后朝着意想中的安然走去。”[1](P1)这就是辽阔壮美的大草原,蒙古族牧民自古以来劳动、生息的摇篮和沃土。从遥远的年代一直到现在,草原总是一点也不吝惜地养育着这里的所有生灵。草原是蒙古民族的生命之根,久而久之,便成了蒙古人的一种性格。“这种性格、品质像蓝天一样宽广,像高山一样挺立,像大河一样坚毅”[1](P29),这是蒙古人身上从小就有的像金子一样珍贵的东西,是蒙古人做人的根本!这种草原文明是一种纯朴的、本真的、粗犷的文明,是一种推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一曲不屈不挠、顽强生存的生命赞歌!
“哪里的水草肥美,就从勒勒车上卸下哈娜、毡子、皮绳,把毡房扎在哪里,这就是家了。”[1](P11)草原文明始终坚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蒙古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草原文明价值观赖以生成的源泉。作为草原文明的坚守者,世代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骆驼“总是头上顶着这座毡房,眼里一没有了牛羊和花草,心理就好像住进了一窝兔子,整天价闹得慌。”[1](P11)对他来说,摒弃了草原,就意味着摒弃了生存之根,所以他数落搬离草原的儿子和儿媳是“数典忘祖”,拒绝到城市里安度晚年,同时还坚决要求自己的孙子重新回到草原上学,“阿如汗从小就长在城市里,如果再不回到草原上把小学、中学念完,好好吃几年毡房里的手扒肉,喝几年恩格尔河里的水,在高高的宝格达山上练一练筋骨,将来一考上大学,那就永远不再是咱库仑图草原上的人了。这样,咱蒙古人身上从小就有的那种像金子一样珍贵的东西,还能在他的身上闪闪发光吗?”[1](P12)而所有这些,都是草原文明的根本,草原文明的精神特质!这些朴素的草原文明,是蒙古民族与草原长期的朝夕相处中总结出的生存智慧,体现了草原人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
二、对工业文明的批判
小说《狗祭》的切入点是对所谓“先进”、“发达”的工业文明的批判与反思,但是作家没有直接批判,而是引导我们从另一种文明即草原文明的视角来审视我们所置身其中的工业文明。虽然大草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曾发生过破坏性极大的灾难,但那些灾难基本是来自于自然界本身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是人为破坏造成的,所以总体看来,蒙古民族一直都能够与自然和谐地相处。而工业化的大规模进驻使草原人民的生产实践活动和草原生态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虽然工业化一定程度上让草原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改变,但潜在的威胁也正朝他们逼近。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可持续发展是工业文明致命的缺陷,草原人民的欲望也在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受到刺激而膨胀,精神和诗意的存在正逐渐在草原上消逝。
在《狗祭》中,随着工业生产队的进驻,一种潜伏在草原中的完全不同类型的“灾害”慢慢逼近,它要比干旱、虫害更为可怕和恐怖。“就是这群怪物,让哈日巴拉这条优秀的生命失去了自己的灵魂”[1](P162)。 天性善良、机智勇敢的哈日巴拉经过阿如汗的严格训练,又受到纯朴草原文明熏陶,成为一只“有根”的草原英雄,成为整个草原牧民的忠实朋友。击退来势凶猛的狼群,营救埋在雪下的绵羊,寻找暴风雪中走失的牛群,引领大家逃脱夏日的山洪,高地上的守望,夜半的警戒,脖子上的红花,摆动着的尾巴,处处表现出哈日巴拉的高贵、勇猛、智慧、忠诚、情意、正义、向善、坚守。正是凭着这些高尚的品质,哈日巴拉成为人们所称道的精灵;而当哈日巴拉接受了工业项目推行者的再一次驯化、诱导后,却变成了草原上人人嫌恶的瘟神、疯狗、恶犬。现在的哈日巴拉脖子上的长毛竖起,四个尖牙外露,牧人们孩子们谁见了都会流露出愤恨的表情,就连牛羊见了也会害怕地仓皇逃跑,这都是源于其残忍、粗暴、邪恶、卑鄙、疯狂、背叛。是什么把草原英雄、人类忠实的朋友变成了危害人类的敌人?这是值得深思的。工业文明异化了人,毒害了哈日巴拉的心灵,这样看来,哈日巴拉变节的实质是草原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对抗。
草原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对抗同样反映在人与草原关系之上,“就是这群怪物,让草原走进了惶恐”[1](P162),“当它疯狂运转起来以后,这些牧草,这些鲜花,这些气息,这片腾格里赐给蒙古人的美丽,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1](P162)因为开始兴起的工业“用的全部是库伦图草原上的牧草、芦苇、树木,还有眼前这道清凌凌的河水,这道从遥远的年代起就哺育着无数生命的圣洁之水!将来如果这项政绩一旦显赫起来的时候,这块草原,这道河水,还有这里的许多生命,它们的命运还会像以前一样充满生气吗?”[1](P164)这正如弗腊斯所言:“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2](P383)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同样做了分析,他们认为目前的工业大生产是导致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产生种种难以调节的矛盾的根源所在,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困境,正是由人类自己所热衷的工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生活方式造成的。人类由于过度迷信工业科技力量,过度追求利润的增长,导致人的欲望极度膨胀,人的主体性极度扩张,甚至游离于自然秩序之外,仿佛已经成为了自然界的主宰,而忘记了人类仅仅是大自然中与万物平等的一员而已。人类盲目地、不顾一切地追求现代工业文明,严重地损害了大自然生态的平衡,使得资源枯竭,环境受到污染。
三、对生态文明的呼唤
工业文明那种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实践方式,不仅严重破坏着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而且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持续长久生存,于是,人们很自然地便呼唤着生态文明的到来,实现对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
所谓生态文明,指的是人类在改造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的过程中,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发展与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并能以此态度来安排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真正摆脱人类“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进步的文明发展进程。对生态文明更为形象一点的描述,应该就是海德格尔为人类设想的崭新的生存方式和境界——“诗意栖居”,即“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3](P107) 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意栖居”是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和最高境界,人类要想真正进入“诗意”之境界,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物质利益的功利性追求,这样才能保证一切生命存在的整体性的和谐。“栖居”也不仅仅是指“居住”,而是生存的另一种境界:自由,一切生命的自由是其本质所在。所以“栖居”的基本人物就是保护和尊重所有生命存在的自由自在。21世纪是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开始,我们不可否认,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科技力量和人类的主体性仍是我们应该大力加强的,但更需要的是重新唤起人类心灵深入的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草原文明能够真正把敬畏与尊重之情融入大自然,形成了以“自然为本”的人文精神,这种文明应该是人类最早的生态文明,或许这样一种情感才是中华民族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支柱。
蒙古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限制,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高度的生态文明理念——“天人相谐”。在蒙古人意识中,天地是父母,水草是衣食,从而形成了天地崇拜、水草崇拜等自然崇拜,而破坏环境是与草原上世代生活着的牧人们的生存理念相悖的一种恶性举动,这是一种与游牧相适应的大生态观。对于自然的破坏最后等于破坏人类自己,这一意识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非常生态的,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是说自然界同人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P95)而且在漫长的游牧生活中,蒙古民族早已把草原上的一切生命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草原的生态和谐是生命的根本。正因为如此,尊重生命、敬畏自然是草原人民生产与生活中不言自明的生存哲学。“腾格里最初安排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存在的权利问题上,每一类生命都是平等的……而没有提供任何能够成为这一类生命的歧视或灭绝另外一些生命的理由。各类事物共同配置在一起,世界才会丰富多彩。”[1](P175)但是人类时时刻刻都渴望征服自然、战胜自然,而过度地征服带来的却是长远的破坏和失衡。“连家园都没有了,那富裕还不是从遥远的戈壁刮过来的一阵风?连自己、后代都不存在了,这样的工业项目还有什么意义呢?”[1](P118)
小说的高潮是对哈日巴拉的祭奠仪式,其时,在一片庄重和肃穆中,巴图老人将哈日巴拉的皮高高举过头顶,将身子向前一倾,送到恩格尔河道中,“漂吧,漂吧,一直漂到一个谁也见不到的地方去。沿途,不要哪怕是留下一点痕迹。到那时,所有的事情就会都改变了样子!”“而当终点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东方,那轮金色的太阳就又辉煌地升起来了!”[1](P176)在这里,一场神圣的仪式所完成的,既是对草原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祭奠,同时也是对生态文明的呼唤和憧憬。而对于作家来说,则是一种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1]里快,狗祭[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3]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冯雪峰)
访 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