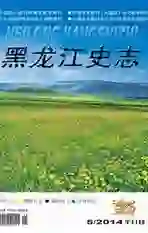章学诚“史德”说再探
2014-11-25王子初
王子初
[摘 要]章学诚“史德”说的内涵应当综合学界几种意见之长分析,它表达了史家在肯定名教前提内,如何以自己的本性特色最大程度地表述有意义的历史的问题。章氏“史德”观念中的“心术”以及“天”与“人”等重要概念是借用了理学分析框架,说明史家要在撰述过程中融入个性及资质,同时避免性情的做作与泛滥。在具体历史写作过程中,要“慎心术”和“养心术”,就是尽可能多方面地展现历史事件因果,含蓄地表达褒贬抑扬,借以表达对历史的难理解性的充分尊重。
[关键词]章学诚;史德;天人关系;慎心术;养心术
在对章学诚史家素养理论中“史德”含义的探讨中,学界目前形成三种主要观点。一、客观态度说。(1)认为章学诚主张史家在历史写作过程中要尽量克制主观认识使得主观最大程度地反映客观事实。二、封建道德说。(2)认为它是要求史书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指导准则的陈腐思想,旨在维护清朝统治。三、史家主体说。(3)认为这是强调史家主体在与历史客体互动的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和能动作用。三种解释各有道理,随着认识的深入出现了一些折中的说法(4),而在三种主要解释内部也存在一些差异。客观态度说和封建道德说看到了章学诚《史德》和其他文章中的“据事直书”和“君父大义”的字样,但忽视了章氏学说的整体性和贯通性因而割裂了史德与章氏一系列重要观点的联系,封建道德说的一些观点有教条和附会倾向。比较而言史家主体说理论见长且注意到了“史德”与章氏学说一贯性的协调。以往研究从材料上主要依据《史德》、《文德》、《习固》、《质性》等章氏理论文章而对章学诚史学实践中体现的“史德”理论检讨较少;在对“史德”的理论分析上对“心术”、“天”、“人”等概念的界定的考实与从理学视角对这些概念的分析仍有拓展余地(5),对章学诚强调的“六义比兴之旨”的例证也较少。本文认同“史家主体说”并试图吸取前两种观点的合理成分,从章氏史学理论整体的贯通性视角出发,把理学分析和实例论证结合对“史德”内涵有所新的揭示。
一、“心术”与“天”、“人”内涵析论
章学诚在《史德》首段肯定刘知幾“才”、“学”、“识”史家三长说与史学“文”、“事”、“义”三要素的重要关联:“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但他认为在三长指导下的史学创作存在形式上的确是属文述事凸显宗旨,而实质上却是似是而非的可能。他认为把文采、记诵、专断当作良史的“才”、“学”、“识”是错误的,随后他把刘知幾“有学无才”引作“有学无识”。(6)笔者认为这正是章氏有意识地把刘知幾以“著述成家”为良史标准的理论作为其未明言的“史识”进行批判,章氏以为刘氏之“识”只是“文士之识”而非“史识”,进而提出己之新解惟有“史德”之深层素质才能形成真正的“史识”。(7)章氏认为“德”乃著书者之心术,如魏收、沈约之史人人可见其卑劣品行,因而这类著者心术不在实斋讨论范围内。章氏焦虑的心术问题是除圣人以外的大贤君子都难免的修养未至纯粹的状况。他提出著述者心术的标准是“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并劝人勉力为之。(8)理解“心术”与“天”、“人”的内涵是理解章氏“史德”说的关键。
从《史德》全文看,“心术”乃就史家及论史者双方而言。末段言“养心术”提出“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可以讲”即说明论史者和著史者双方都必须注意六义比兴问题。(9)笔者遍检《章学诚遗书》“心术”语句并推测其含义,认为“心术”在章学诚语境中应当是有关表面背后的真实本性的概念,道德是其基点但并非全部内涵。(10)下面举出“心术”几个层面含义的例子,有关道德的如:
擒盗而喜……盖得情而喜,有伤于心术也。
仆尝谓读书作文,求为可知而已;揣摩而欲其必得,无是理也,而有害于心术。所谓定命无毫发增,而道德有邱山损也。
阳魏阴刘褒贬异,造奇蹈秽心术殊(自注:沈约魏收)。(11)
有关表面背后本质的如:
张汤严延年之徒,亦清苦自守士,然其心术尚可问耶?
夫不论心术,而但求体貌,则王通且拟六经,不较子史诸家为更进耶?(12)
有关真实的本性,笔者以为“心术”一词用于评价表象和实质是否一致的场合,可以以章氏对戴震和袁枚的批评为例。章氏以为戴震“心术未醇”对于求学者颇有害处所以作《朱陆》篇。(13)按《朱陆》篇批评了“实为伪陆王却自标朱学攻击陆王”以及“实为朱学却否认渊源攻击朱子”的两种门户之见,其中对后者(戴震)的批评着眼点在于戴氏对朱子书面只有微辞然而口头却丑诋之;《书朱陆篇后》的批评除了指出戴震学术上的饮水忘源以外又胪列了戴氏在学界不同人群中的不同表现使人捉摸不定其究竟为何种学问;而《朱陆》指出朱子语录大旨与其著作相合,因此朱子之学正是古人表里如一之学,章氏认为就以此标准(表里如一)来要求戴震也可见其远不如朱子。(14)章益国由此推断实斋论断戴震“心术未醇”乃指戴震治学中未把自己的性情彻底贯彻。(15)笔者以为章益国所说得失参半,章学诚批评戴震“饮水忘源”,由此可知实斋不会赞同戴震无论在考证还是义理方面因为“贯彻性情”而与所受渊源决裂的态度。(16)章益国看到“心术”确指本性的一面但忽略了“心术”是受学术沿承框架(道德前提)限制的另一面。章氏对袁枚的批判逻辑亦可类推。章氏说“心术倾斜之无品文人”(17)招收学诗的女学生表面上是表彰她们的诗作实际“其心实大不可问”。(18)也反映了“心术”指外表与实质的统一性问题。
“心术”在章氏语境中又与风气相关,章学诚明确表示当风气盛行时,学者坚持本性所宜而不侚风气以求名,则其心术可称,诸如:
学者惟当慎辨于心术,欲其近实而远名,则世风淳而天下享其利也。
好名徇人而忘己……则人品心术,皆无所取也。(19)
综上可见章氏之“心术”是与个人独立真实之本性有关的概念,道德和抵制外界干扰都属其内涵,笔者以为章学诚追求的是在道德、名教框架内的个性的独立的完满的实现的理念,章学诚尊重权威和主张个性自由的矛盾心态于“心术”内涵中有所体现。(20)所以不难理解章学诚把“名教”作为著述的理所当然的前提:
夫立言于不朽之三,苟大义不在君父,推阐不为世教,则虽斐如贝锦,绚若朝霞,亦何取乎!(21)
持章氏“史德”说为坚持封建纲常为史学指导思想的学者看到章氏“心术”的基点是名教范围之内,而其问题在于“名教”问题不是章氏要重点探讨的对象也不足以尽“心术”的全部内涵。(22)至于为何章氏把名教视作当然之前提,笔者以为章学诚固然以为纲常秩序的出现是“不得不然之势”,但其出现是顺应自然的,所以他又说:“天地自然之象,《说卦》为天为圜诸条,约略足以尽之。”而《易·说卦》明说“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因此这种血缘宗法在章学诚看来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天理”。(23)而且从章氏推本《周礼》官师合一看,尊崇名教正是章氏“权威主义”倾向的必然结果。(24)因此名教已经融化在章学诚的血液中不成为问题了。(25)
从“心术”一词表示的概念范围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坚持独立的真实的本性,坚持它与“史德”有什么关系?这就要继续分析《史德》篇第二段引发的“天”、“人”内涵及其之间关系。首先需要考察“天”、“人”概念。章学诚指出虽然人人都知道善善恶恶、褒正嫉邪,但仍要考虑心术,因为“天”“人”参杂于心术之中,其端绪之精微以致并非想当然的辨别力就足以依靠。(26)笔者考章氏相关文字中“天”、“人”的含义,认为“天”取“自然”义而“人”取来自于天但禀赋不纯粹且有偏私之性之义。试举几处例证:
朱先生(朱筠)曰:科举何难,科举何尝必要时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举未尝不得。
婴孩不满一尺,而面目手足无一不备,天也。
善为教者,达其天而不益以人,则生才不枉,而学者易于有成也。(27)
这些充分表明“天”乃自然禀赋之义,章益国以为是“天性”、“天质”,笔者以为仍有未尽之意。章学诚说:
近撰《史德》诸篇,所见较前有进,与《原道》、《原学》诸篇足相表里。(28)
也就是说宗旨上《史德》与《原道》、《原学》这些章氏史学本体论性质的文章相发明。而《原道》、《原学》宗旨章氏有清楚论述:
鄙著《原道》之作,盖为三家(考订、义理、文辞)之分畛域设也……故知道器合一之故,方可言学。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于周孔之分,此实古今学术之要旨……《原学》之篇,即申《原道》未尽之意。其以学而不思,为俗学之因缘;思而不学,为异端之底蕴。(29)
章学诚《原道》、《原学》描述了三代道器合一的知识圆满状态逐渐崩溃并走向后世道器分离出现义理、考据、辞章三种不完全知识形态形成风气循环与门户对立的状况的历史。倪德卫以为《史德》恰好解释了这种病症的由来,对笔者下面的分析很有启发。(30)笔者以为《原道》与《史德》篇之“天”意义相通:
道之大原出于天。……《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31)
也就是说阴阳运动产生之际道就存在了,因此道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天”即道即自然即事物内在依据,章益国以为“天”指天性不能用来解释《原道上》“道之大原出于天”。
笔者认为应当通过章学诚的质性论来分析“人”的特点与“天人关系”。先看性之形成,章学诚以为“阳变阴合,循环而不穷者,天地之气化也”。阴阳互动循环不已,其表现就是“气化”即天赋予万物以资性和形体的过程故而人生所禀有得自于天者。而“人之异于物者,仁义道德之粹,明物察伦之具,参天赞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人有他生物所无的道德聪明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知觉运动和心知血气却与他物无别。(32)人类生而有“三德”的分别,对应儒家人格概念中的中行、狂、狷。(33)“人秉中和之气以生,则为聪明睿智”即“三德”之“正直协中”即“中行”,只有圣人才能保持这阴阳适当的粹然元气。其余人秉气之阴阳有所偏胜因此本性即“狂”或“狷”,只是生禀有厚薄,但“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即经过努力是能通向道的。上古时代人生秉性不出“三德”。孔子所处时代已不得中行,可见绝大多数人秉性必有所偏。(34)章氏以为人之秉性体现于阴阳之气化,“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35)。吴怀祺先生指出章学诚把“气”引入心学从而修正了心学对笔者大有启发,只是吴先生没有展开。(36)王阳明打通了心、性、理、气的界限建立了完全的一元本体论:
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无条理则不能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条理者矣。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
气亦性也,性亦气也。(37)
王阳明“气”论基础在于本心良知,“气”化成万物,章学诚却没有把由良知而生的“气”作为世界形成的质料因。(38)章学诚在成全本性的问题上把心学“气”论进行完善。他认为人性本静而人感物而动,所感之发即为性之体现。人生于天地阴阳循环之中不能摆脱外物阴阳盈虚消息的影响,于是产生了合阳刚之气与合阴柔之情,情自性生而才由气出且才情依附于血气,如果不采取手段气、情就会放纵恣肆损害各自合阳刚与合阴柔的性质“昆阴昆阳”、“毗阴毗阳”。这种损伤凭借血气侵入心知循环,至于发为文辞害义违道仍难以自觉,于是人性纯真之三德因后世人心不古而被遮蔽,乡愿、伪狂、伪狷的伪性之人层出。如果对非由纯真本性(三德)所发的似是而非之学(乡愿、伪狂、伪狷)不加辨析,终究会埋没三德以致永远不见古人大体。(39)因为圣人难得,所以大贤以下都要保全本性(三德)以防止其流失入伪。
章学诚认为成全本性途径有二:从个体来说是学习,从外界来说是礼乐制度的教化。章学诚积极评价了学习的作用:
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40)
这段话充分表明“学”是沟通“人”与“天”的中介,“人”禀赋的资质具有偏狭性“分于形气之私”,“天”自然而然为公正之大全。学习的目的就是扬弃人的偏狭性,获得无限之天的大公中正的品质。学习的内容是什么?他认为天赋人以仁义礼智“天德”之性和五伦之天位,把天德贯彻于天位上,即便在未与物交隐微之地已有无过不及的中和境界即“成象”。人平日体象事至物交恰如其准而赴之就是通过在形下之器的锻炼获得形上之道的“效法”即为“学习”。这种学习是针对众人本性容易阴阳损伤状况症状下药,“刚克柔克”以成本性。(41)学习还需要外界礼乐教化,章氏认为三代先王把握了人性感物而动以及秉性有偏的特点,于是制作礼乐“以养性于和节之中”,同时“绝地天通”建官分职、官守其法、官师合一把民众纳入制度化轨道。这种状况下人人安于官守而无出位之思,本性所发中节因而得到成就。(42)内在学习和外在礼乐对于先知先觉的圣人来说是相通的,他们能谨慎对待阴阳的盈虚消息,对自身感物而发之情能够品节之,于是礼乐产生,章氏认为这是合乎阴阳运动的自然规律。(43)对于不自知成象之准的人就需要先知先觉随才成就,使之自悟成象准的。三代官师合一局面瓦解,后人性无所养于是私著始出而性受到外界诱惑,所发之意气就乐为声名。于是在学习之外君主凭借驾驭天下之术对人约束调节使人性有所复归,因此君主权威作为三代外在礼乐制度的延续,成为后世成全本性的途径之一。(44)
由上可知,章学诚认为“人”的特点在于都禀赋了天德之性,具体资质分为中行、狂、狷三德,但人因感物而发产生的气情容易失控导致本性的遮蔽以致呈现“伪性”特征。《史德》首段言良史必须要谨慎辨明天人之间的关系,“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尽其天”章益国以为贯彻天性(45),笔者认同之并有所补充。“天”指人生而有的自然天德和资质(三德),“尽其天”中除知识论意义外还有道德因素。对天性的发挥必是基于资性所近和时势所迫造成的意之不得已,如此才做到自然。(46)章氏发展王阳明心学完完全全实现本性的“致良知”理论而把它理解为完全实现天赋资性(道德是其一部分),它是超道德而不是非道德的。“不益以人”很多学者已引《庄子·山木》:“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为最早出处,但这个“人”究竟指何种范围的“人”尚需深析《史德》第二段。
第二段实际围绕史书书写中主体性的贯彻问题展开。前二句谈是非善恶的辨别实与《习固》篇相发明。《习固》批评的是一种不经过独立思考就接受定论的主体性丧失的情况,它会导致门户之见。(47)而《史德》章氏指出正是因为在心术中“天”“人”相参的端绪细微,所以是非善恶的辨别不是凭借想当然的思维方式就能解决的。笔者以为之所以心术中有天有人,因为本于《礼记·乐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可知心术可见人之性情,又据朱子所发展的张载“心统性情”理论:
性只是理。气质之性,亦只是这里出。若不从这里出,有甚归着。如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固是心,人心亦心也。横渠言:“心统性情。”(48)
朱熹“心统性情”的一个含义是心包含性情二者,道心、人心皆在心中。这种思维方式笔者以为适用于分析《史德》。因此章氏“心术”相当于“心”作为一个“容器”包含“天”“人”二者。(49)下文讲史家在对待史事的得失是非和盛衰消息时会产生气和情,史文气昌情挚为最佳但此时却要辨明其中的“天”“人”。章氏认为合于理的气、本于性的情是“天”,同时气、情具有独立于理、性的自由这就属于“人”。理、性当是同等概念指自然本体,感物而发合于性理正符合《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和境界因此是“天”。而气、情具有能够违背性理的属性是符合理学本体论的:
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50)
在章氏亦有言: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然天下歧趋,皆由争理义,而是非之心,亦从而易焉。岂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声色臭味有据而理义无形,有据则庸愚皆知率循,无形则贤智不免于自用也。(51)
章氏认为确实理义是人心所同的原则,但理义不像实在之物人人皆可依据,是无形的因而任何人都不免于自我判断进行抉择,所以出现了对理义的分歧和是非的多样化。这说明章学诚认为尽管天赋人性但现实抉择却是要由人自由选择的,秉性不能决定人的表现。章氏认为史义来自“天”而史文由于生禀所限只能靠人力书写,这时存在前文分析的如果缺少学习的把持,人的气情就会沉溺遮蔽本性,以致史文害义违道犹不自知。章氏以为气胜情偏就是动于天参于人。
在分析方法上,章学诚受理学影响很大。如有关“气”、“情”的作用在理学中可找到依据:
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但波澜有好底,有不好底。(52)
合理的气、情与违理的气、情可比作水之流与水之波澜。又心术中“天”“人”相参类似于理学心中兼有“人心”“道心”的论断:
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53)
心术中“天”、“人”可分别对应“道心”、“人心”,表示容易把握本性和气情的能力。以上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心术”与“天”“人”的概念及其关系,“心术”以道德为前提的独特的个性,“天”是自然禀赋的资质,“人”是不稳定的把持性情的能力。“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当指在道德框架下充分实现资质与个性,同时避免性情的做作与泛滥。可见章学诚把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名教因素顺畅地纳入其知识论中,并以理学演绎方法表达了史家主体性的贯彻对于史书编纂的重要意义。正因如此,学界产生了对史德“封建道德说”和“史家主体说”的分歧,笔者以为应当站在后说基础上吸纳前说更为符合章氏本意。但章氏对客观态度说持论的记事真实是怎样态度,史家的个性具体在写作中是怎样表现的,接下来要讨论。
二、“慎心术”与“养心术”涵义析论
“慎心术”与“养心术”实际都是指如何把持心术,保全并实现本性的方法论问题。“慎心术”于章文主要指史文书写中的敬恕平正之功,“养心术”则指史家对《诗》六义比兴的主旨的涵养。前者学界分析已详,这里简单概述。《史德》指出史文必须藉助气和情才能打动读者,这在章氏他文中亦有见:
人之所以异于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贵者,相悦以解也。(54)
即“情”亦为人所禀赋区别于无生命者的重要因素,它作为性之动打通个体间心灵联系,由此可见章氏肯定“情”的整体意义。章氏认为气、情于燕居虚置之时都是平正的,但由于感物而发容易溺失因此要把持住情气,使之仍归平正如此所发之气情皆为合于性理的。章氏认为“天”“中平正直”(55)所以本性感物而发的气情只要是平正的就是合乎“天”之自然的。章氏认为把持住情气就要学习,“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56)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读书广识,充积义理。(57)章氏认为读书内容也包括“非圣之书”,其原因从章氏推本周官的思维方式看“非圣之书”当为官师分离后“思而不学”的异端之学的变形,从其本于王官之学又迥异王官之学的特征中可吸取教训从而使著述“是非不谬于圣人”。(58)章氏认为做到气情平正的方法在于“持敬”,即控制气使免于放纵,则文辞从容调整恰到好处地表达史事,这种“敬”是超乎道德的。(59)
关键的问题是“养心术”的解析,笔者以为章氏意在周全地考察背景后含蓄地表达事实评价。“六义比兴”本于毛诗《大序》及《周礼·春官·大师》,其含义指用委婉连类的手法表达本意。(60)后世之解释基本不违此意。(61)而章学诚“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亦是渊源有自: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62)
章氏据《左传》体悟到《春秋》作为圣人所修之史书其表达方式的委婉隐微应当成为史家之法式。为何章学诚主张史书的委婉表达学界探讨较少,笔者以为柳诒徵先生于《国史要义·史德》篇的演绎对分析此问题大有启发。柳先生推本周礼“官师合一”下的古史官兼备考信事实和道德教化的双重使命,历史主义地分析出中国史学是具直书与名教二重特征的。但史家必须以爱知其恶、憎知其善不泥一偏的心术全面考察事实背景和人物事迹本末,才可以把直书与名教统一,如此的史文一定是“劝惩之旨,在读者深思而自得之。”(63)柳先生指出章学诚“史德”盖即此义。(64)按章学诚对官师合一确有“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的评价。(65)章学诚也强调过直书和劝惩呢:
夫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春秋》之意也。
《春秋》讥佞人。
善恶惩创,自不可废。(66)
史学的这种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意义在章氏看来是统一的:
(旧《永清县志》)是不但宾主倒置,抑亦未辨于褒贬去取,全失《春秋》之据事直书也。(67)
然而章氏根据《春秋》谨严之旨对史书论断问题采取审慎态度,认为史论若非前人未发的卓见而只是老生常谈或标新立异反成赘文,至于临文必以“呜呼”为感慨时世则是不本性情触发而凑合事理。(68)章氏以为如《元史》修纂排除论赞的做法亦非公是之道,他主张效法《春秋》“议而不断”以平和之气书写论赞。(69)章氏没有贬低史论的地位,他希望把包括史论在内的列传之文用《诗》之比兴的形式含蓄地表达出来。那么,如何理解章学诚主张的审慎地含蓄地阐发历史评论70的态度呢?这与章氏对历史可理解性以及如何表述历史的思考密切相关。
章学诚认为历史的可理解性是建立在事与理的结合程度上的,事理结合愈紧密历史便愈易理解。他认为官师合一、治教合一从而道器合一的三代是事理合一的理想状态。三代官师合一,学者所学即为国家政制,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事理合一”。71这种治教合一的专家之学是表里如一之学,所想与所表达相符,学问传承中文字无法表达的部分因为亲历熟习官司掌故可以自然领会。民间通过吟诵《诗》表达中和的情志,歌咏升平并无隐而不彰之意。“事理合一”带来“言意合一”。(72)这种盛况在周末崩溃,太师太史陈诗观风执简奉讳的职责废弃,贤人抱负之隐忧只能以诗之微言表达,圣人对秩序的关心只能寄托于《春秋》谨严的予夺。自此诗才史学因为不当其位故而对其著述灌注委婉之意成就了大量文采飞扬的不朽之作,然而言意乖离却成为无可奈何的趋势,因而想理解作者本意要比三代更加困难。(73)章氏又认为人性的局限使论者论断去作者本意益远。自官师合一局面瓦解后,人原本因职守所规范的聪明才智失去了外在的限制,人性有偏的特征不可免地暴露,于是各自滋长了自以为是的倾向。(74)前文分析的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再加上因为书写工具的改进造成的读书鲁莽,因此也不可免地造成因为“义有主客”从而穿凿附会作者本意的情况。章氏举例如屈原之《东皇太一》、《橘颂》等作品本无深意,世人不明大义却于具文附会曲解为思君疾恶。(75)对待言意乖违章学诚主张用直觉与古人共情直接把握古人本意,“盖谓道同而德合,其究终不至于背驰也。”(76)
章氏还发现历史背景也构成理解历史的关键。他认为后人虽读古人之书,但不了解古人是在怎样的时代和遭遇下抱何种目的发出的言论,“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这种言论能否作为证据是值得怀疑的。即便是同一言论,因原发言者动机有异,所谓“东走虽同,其东走之情则异”单纯凭借此言论也不能发现古人之意。章氏认为对古人境遇没有同情或有类似遭遇的共感是不可能理解古人的,“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77)何况存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例子比比皆是。(78)章氏举淮南王刘安为例。章氏认为他人以为的淮南王溺于富贵所以其书诞漫华侈的评价不能尽《淮南子》之意。他认为西汉七国之乱后中央严控藩国,刘安是罪人之后且汉武帝多猜忌,又观《汉书》伍被公孙弘之攻讦可知刘安四十多年诸侯王生活日日如坐针毡于是他想用漫诞文章掩饰自己的不安。(79)这表明章学诚主张对历史进行具体的原始要终的了解后再评价其中特定的人和事。总之,章氏认为作为变动中的自我去评价变动中的历史是相当艰巨的。(80)
章氏认为表述历史的典范就是理寓事中,“理”只能在事情的展开中得到呈现。他认为著述或者为阴德之事溯已往的述事,或为阳德之理阐方来的明理,而一阴一阳之运动是道,所以著述的最佳形式就是“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81)历史著述就是阴阳运动的表现。(82)章氏认为古史本无议论,史论如果有就必须切合史事否则就是离器言道被阐发得愈支愈离甚至导致异端邪说乘机而入。(83)所以在章看来史文最好是通过完完全全地展现史事的实际情况及其本末过程,则善恶自然默含其中。综上正因为客观事实未必如论者之想当然“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论者所发很可能动机虽好但结果却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因此平日要养心术。(84)在方法上要为知人论世之学,知人之美亦要知其恶“古人叙一人之行事,尚不嫌于得失互见也”,具体分析历史环境“因地因时,别而择之,斯为论世。”(85)如何“养心术”呢?这就要对章氏的“据事直书”与“六义比兴”的关联仔细研究。前面引文“据事直书”中有“褒贬去取”的字眼,既然是“据事直书”为何也要有“去取”,难道“直书”不是书写全部的历史么?
倪德卫指出史家最重要的是展示他对事物总体的直觉,并把题材各部分形成有机整体,因此史文必须且只能涵盖所有有意义的史事,甚为洞见。(86)章学诚强调别识心裁的一家言的史著,其“直书”是服从于“史义”宗旨的。《史德》之“史之义出于天”的缘由,柳诒徵先生以为其本于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和《春秋繁露·玉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得出史家以受命于天之善善恶恶之性治史,甚为有见。(87)笔者以为既然“天”属于“心术”范畴,据前文所析其自然有名教涵义故而“史义”亦当以名教为前提。这在章学诚亦有言:
纪传之体判如方圆水火之不可相混,乃是史文体例有然,而非有关于尊卑褒贬之义法也。(88)
关于具体的“史义”内涵,章学诚有一段酣畅的论述反复被引用: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89)
也就是说“史义”之典范是“《春秋》笔削之义”。“笔削之义”的目的是经世明道,具体表现为对史料的有自家本性特色的独断去取,以自由的精神超越形式限制而成一家之言。那么,以不违名教为前提的别识心裁之史著固然直书史事然而未必是全部史事,而且不完全出于名教考虑。章学诚认为乾隆时期秩序稳定因而不存在直书批判的问题,从晚年上书批判朝政看出章不缺少斗争勇气,因而持史德封建道德说者的批判不合理。(90)持“史德”为客观态度说者的问题在于只看到章氏“据事直书”的表述,而没有深入其史学理论内在逻辑进行分析。
章学诚认为史书中融入“六义比兴”的表达形式,的确是出于“史义”考虑的:
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法《春秋》之谨严,含诗人之比兴。(91)
章氏认为以本于有为而发的比兴抑扬咏叹的形式能够使史文展现难以表达的情感,进而使书写的史事和蕴含的义理也产生至情,如此能够打动读者“由情而恍然于其事其理”从而流传久远,同时比类参观可使读者举一反三获得无限启发,“兴起好善恶恶之心”实现道德教化目的。如果单独解释义理指示情事,枯燥无味反而让人疏忽。(92)他又认为史论要具《诗》教特色,会使看似浅近的文章产生深远的意味,使激越的情感和严肃的旨趣产生平缓的效果,语无褒贬而意有抑扬,以无多之篇幅使人得意忘言。(93)章氏主张史文采用《诗》之比兴乃是在形式上意境上的效法,不是说史文写成诗的形式。(94)就比兴委婉暗指的手法,章氏概括了一些方法。以评论时代鉴别民风为论世之学,以同时代的相比照而附出的均衡编列为类次之法,以言意内部变化的张力为予夺之权如在人表中有名而列传中无名便见褒贬之意,以一事在各处叙述的详略之别和异才忽列一处为品节之理如屈贾、老庄合传而非按时代排列便是别有命意。(95)章氏对史文含蓄的表达是与《春秋》“议而不断”审慎论断的思想一致的,如他不赞成像《新五代史》尽以品目概人的做法,认为朝代改易之时的是非要留到后代才能做定论,故赞成《新五代史·唐六臣传》和《宋史·周三臣传》这种兼顾本朝国讳与前史是非之平的史家心裁。读者只能意会作者褒贬之意、无限地回味历史,但作者并不流露出褒贬的倾向,这也体现了章学诚对历史可知性、可理解性和人类价值相对性的保守谨慎的态度。(96)柳诒徵先生引恽敬《古今人表书后》可与此互相发明。恽敬认为班固自不能以本朝人差等本朝君臣故次古人以表今人如秦始皇列第六等则汉高、武帝可知。由读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即由反复深思后的直觉一下子把握住史家通过直觉意识到的有意义世界的整体,在章学诚看来历史的意义就在这种“心领神悟”中不断被阐发出来也就是用“史意”把握“史义”。(97)
通过章实斋“知人论世”的史论特点也能体会到他对历史可知性的敬畏之心。“知人论世”当为“六义比兴之旨”的内在规范。(98)章学诚史论的特点是原始要终地考察背景中的特定人、事,知其美又不讳其恶,论断有余地而不绝对。如他对吴缜的评价。王明清《挥塵录》以为吴氏轻佻故不被欧阳修所用于是吴氏著《纠谬》报复,晁公武以《纠谬》一事失检遂谓吴缜所纠多误不能作文。章氏认为《纠谬》整体高明只是偶有失误就横遭晁氏指责太不公正,欧阳修不能用这样的校雠人才则其参与修史者可知。(99)如他对元结的评价。洪氏以谓其《元子》悖理害教,章氏认为元氏高才却浮沉于世不得志到晚年始达,则其壮年愤世嫉邪当本于屈《骚》之感激怨怼,而以庄周寓言表达出来。(100)章学诚以为是非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确定的,如果条件变化,主观以为的是非就会不符合真实。因此章学诚讲“据事直书”涵义更可能是要展示史事的来龙去脉,展示历史本来是如此的,是非要由读者通过作者的心裁手法慢慢体会而不可以言传。(101)仍以柳诒徵先生所举恽敬读《史记》为例,其《读张耳陈馀列传》以为贯高为其君王试图刺杀高祖不成,为营救故主挺身而出最终自杀一事太史公断之仅仅是“当此之时,名闻天下”而已。深意是什么呢?恽敬以为由此可知汉初臣只知有己之家国而不知有天下乃是大乱之道,尽管贯高事迹可歌可泣但君子并不许之。(102)章学诚意识到了以正常经验思维把握历史可能并不准确,所以他说辨明善恶的心思患在似是而非,主观以为之真实未必是历史之真实。由此可对《史德》末段稍作分析。“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所指情、气的最佳状态是仁、义。后文讲屈原、史迁深明六义比兴之旨,虽有感慨穷遇之情但其文皆为“至文”,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他们抗怀三代之英的志向,并没有违背君父大义。章氏认为读者之心不平自不能明《春秋》笔削之义“史义”,以己意附会《骚》、《史》以为是谤君讪上。章氏的深意是强调读者必须有作者的“养心术”和“慎心术”方可以“心知其意”完成史学这种默喻意义的互动过程。至于知人论世之法,章学诚说:
君子论世知人,则于终始出处之间推微知著,由显测潜。(103)
章学诚同样提出八种史事采择之法正与此“论世知人”的方法相发明:
採择之法,不过观行而信其言,即类以求其实,参之时代以论其世,核之风土而得其情,因其交际而察其游,审其细行而观其忽,闻见互参而穷虚实之致,瑕瑜不掩而尽抑扬之能。八术明,而《春秋》经世之意晓然矣。(104)
有学者以“理性主义说”解“史德”,如梁继红。她发现了朱氏椒花唫舫抄本《章氏遗书》中《周书昌别传》后面一段其他一切章氏著作版本所无的“自记”,此文与《史德》同年写成。兹引如下:
此传文豪而气苍以凉,较前似有进步,所幸理尚胜耳。夫生平不离文墨,习久安得便无进机,学子类然不足喜也。晚岁文章贵于理胜,不欲以情胜耳。道力不进,阅涉滋多,过去未来横生感慨,所为易以情胜者也。文辞岂必不佳而萧见于笔端,则才为血气所乘,而道力微矣。此皆近年阅历有得前人所未发者,后学不可不知之也。
梁继红以为《周书昌别传》中多分析说理之文遂以为史家理性地叙述“事”且阐发史义,分析道理为“史德”全部内涵。(105)笔者以为有嫌笼统。这段自记是符合笔者本文从史家主体性角度的分析的,所表达的仍是以平和的态度以本性应有之情展现古人生平。整体理解章学诚“史德”说,可见他处理的是名教世界内史家主体在书写历史时的坚定性问题,“慎心术”和“养心术”都是为辨明史事的意义需要史家进行的具体的修养方法,史家以平和的态度,通过别出心裁的形式展现他直觉到的有机的历史整体,“史德”与“史义”是密切关联的。学界既有三种看法都看到“史德”说中某一部分而没有照顾好章氏学说的整体结构,结合三者之长庶几近于章氏本意。
参考文献:
[1]《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十四)(十六),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唐宋注疏十三经》(一)(三),中华书局1998年版
[4]阮元主编:《清经解》卷84,上海书店1988年版
[5]欧阳修、宋祁著:《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6]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7]《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8]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五),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0]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
[1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12]南开大学《中国历史与史学》编辑组主编:《中国历史与史学——祝贺杨翼骧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13]柳诒徵:《国史要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4][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5][日]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6]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版
[17]许倬云:《求古编》,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
[18]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19]罗炳良:《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泰山出版社2005年版
[20]仓修良、叶建华著:《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注释:
(1)代表性的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二章,引自《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00页;何炳松:《章实斋先生年谱序》,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引自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第86页;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五),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5—506页;[法]保尔·戴密微著,孙业山、王东编译:《章学诚及其史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中日史家》第10章,引自《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4期。白寿彝:《说六通》,引自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92页。
(2)代表性的有柴德庚:《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引自氏著《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6—309页;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引自氏著:《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7页;乔治忠:《章学诚“史德”论思想评析》,引自南开大学《中国历史与史学》编辑组主编:《中国历史与史学——祝贺杨翼骧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211页。
(3)代表性的有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德第五》,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5—121页;[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177页;章益国:《章学诚“史德”说新解》,《学术月刊》,2007年12月第39卷12月号;[日]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杨遇青:《德性视野中的文学书写——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德性与文学关系论释》,《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4)较为显著的是把客观态度说和史家主体说有所综合提出“史德”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强调史家对自身情感的克制,如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55—356页;许倬云:《说史德》,引自氏著:《求古编》,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588—590页;梁继红:《章学诚学术研究》,北京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8—99页。也有把客观态度说和封建道德说结合的观点,如施丁:《再谈章学诚的“史德”论》,引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5)比较明显运用理学方法分析“史德”的是乔治忠:《章学诚“史德”论思想评析》,但笔者对其结论并不认同。持“史家主体说”的学者对这点运用较少,如章益国、山口久和强调史家个性或者史家不受外界干扰的知识契机的重要地位,但其依据却更多是西方近代以来历史哲学的观点,忽视了章学诚生活的学术环境占统治地位的哲学理论是宋明理学。山口久和以为章学诚使用宋学分析方法表达了知识论因此与宋学貌合神离笔者比较赞同,但关键是要对章学诚在《史德》中表达的理学分析过程进行理学式的揭露。
(6)刘知幾关于史家三长说见欧阳修、宋祁著:《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22页。
(7)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20,《忤时》:“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91页。关于章氏修改刘知幾“有学无才”的原因,笔者综合山口久和、罗炳良的说法,参见[日]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第166页注16,罗炳良:《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泰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8)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见《章氏遗书》卷5,引自《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9)施丁先生已提出“心术”指读史者与著史者双方,见施丁:《再谈章学诚的“史德”论》,引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又见仓修良、叶建华著:《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
(10)“心术”一词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书朱陆篇后》,内篇五《史德》;外篇二《<唐书纠谬>书后》;《文集》三《记捕盗二事》,四《庚辛之间亡友传》,七《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湖北通志检存稿》二《复社名士传》;《外集》一《为郑翰林虎文撰沈母朱太恭人序》,《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二《与胡孚中兵部》;《丙辰札记》;《评沈梅村古文》,《与邵二云论文》;《与史氏诸表姪论策对书》,见《章氏遗书》卷2,卷5,卷8,卷18,卷19,卷22,卷25,卷28,卷29;《外编》卷第3;《补遗》;《章学诚遗书佚篇》,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6页,第40—41页,第69页,第188页,第191页,第223页,第264页,第308页,第316页,第337页,第388页,第390页,第392页,第395页,第613页,第614页;第648页。
(11)章学诚:《文集》三《记捕盗二事》,七《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外集》一《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见《章氏遗书》,卷18,卷22,卷28,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88页,第223页,第308页。
(12)章学诚:《外集》一《为郑翰林虎文撰沈母朱太恭人序》;《丙辰札记》,见《章氏遗书》卷28,《章氏遗书外编》卷3,第308页,第395页。
(13)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书朱陆篇后》,见《章氏遗书》卷2,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6页。
(14)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见《章氏遗书》卷2,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5—16页。
(15)章益国:《章学诚“史德”说新解》。
(16)学界久已达成清代汉学许多成绩都导源于宋学的共识。
(17)据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诗话》、《妇学》等多篇文字不难推定章氏攻击之“无品文人”当是袁枚。见《章氏遗书》卷5,引自《章学诚遗书》第43—49页。
(18)章学诚:《丙辰札记》,见《章氏遗书外编》卷3,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88页。
(19)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二《复社名士传》,《丙辰札记》,见《章氏遗书》卷25,《外编》卷3,引自《章学诚遗书》第264页,第392页。
(20)倪德卫已发现此问题,见氏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他(章学诚)既是独立性的旗帜,也是正统性的旗帜,他仍然难以捉摸。”第179页。
(21)章学诚:《与邵二云论文》,见《章氏遗书补遗》,引自《章学诚遗书》,第614页。
(22)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文德》,见《章氏遗书》卷2,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7页。
(23)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内篇二《原道上》,见《章氏遗书》卷1,卷2,引自《章学诚遗书》,第2页,第10页。
(24)章学诚:《与邵二云论文》:“学者慎毋私智穿凿,妄谓别有名山著述在庙堂律令之外也。”见《章氏遗书补遗》,引自《章学诚遗书》,第614页。
(25)章学诚虽然坚持名教,但时时他会十分尊重个体理性地为获得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所做出的选择,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述学>驳文》:“假而父母不道,或鬻于娼,或聘于叛逆贼盗,亦将父母是听乎?”见《章氏遗书》卷7,引自《章学诚遗书》第57页
(26)按章氏虽未明说心术中存在“天”和“人”两种因素,但通过上下文逻辑关系可确定的确心术中天人相参。
(27)章学诚:《外集》二《与汪龙庄简》;《论课蒙学文法》,见《章氏遗书》卷29,《章学诚遗书佚篇》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34页,第683页,第686页。
(28)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史馀村简》,见《章氏遗书》卷9,引自《章学诚遗书》第82页。
(29)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陈鉴亭论学》,见《章氏遗书》卷9,引自《章学诚遗书》第86页。
(30)[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第177页。
(31)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上》,见《章氏遗书》卷2,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0页。
(32)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质性》,内篇六《假年》,见《章氏遗书》卷3,卷6,引自《章学诚遗书》第25页,第52页。
(33)分别见《尚书·洪范》,《论语·子路》。
(34)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质性》;《答吴胥石书》,见《章氏遗书》卷3,《补遗》,引自《章学诚遗书》第24—25页,第608页。
(35)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上》,见《章氏遗书》卷2,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0页。
(36)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41页。
(37)王守仁:《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传习录》下,引自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2《语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第101页。
(38)如倪德卫以为章学诚之“道”是人类本质,如果承认这点,那么心学的以良知之运行解释世界的理论成立。笔者不认同这点,如果道是人类的本质那么何以理解《原道上》“未有人而道已具”的说法呢?笔者以为“道”即是“天”即是自然而然的万事万物的终极内在依据。章学诚把化生万物的本体确实托付给人类以外的规律,这点与程朱理学相近。但他完善了心学的气论并以之解决成就个性问题,笔者认为章学诚运用了理学和心学各自的很多成分来构造自己的史学理论。
(39)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文德》:“才出于气也”,内篇三《质性》,内篇五《史德》;《湖北通志检存稿》二《复社名士传》,见《章氏遗书》卷2,卷3,卷5,卷25,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7页,第24—25页,第40页,第264页。
(40)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见《章氏遗书》卷4,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2页。
(41)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上》,内篇三《质性》:“毗阴毗阳,是宜刚克柔克,所以贵学问也。”又《外集》二《与史馀村论学书》:“夫渊如高明,而心多外驰,故学问以柔克之;足下沈潜,而心多内结,岂不当以学问为刚克之具乎?”见《章氏遗书》卷2,卷3,卷29,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2页,第25页,第335页。
(42)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湖北通志检存稿》二《复社名士传》,见《章氏遗书》卷4,卷25,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5—36页,第264页。
(43)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上》;《文集》七《嘉善周氏福礼堂记》:“福则由礼生焉,犹舞愠戚,迭运循环,品而节之,斯之谓礼。盈虚消息,知者谨焉。礼生于节而乐以和之,阴阳自然之理也。”见《章氏遗书》卷2,卷22,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3页,第216页。
(44)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二《复社名士传》:“礼乐教衰,而人性不得所养,犹官师辙异,而人生不得所业(自注:官师合一,则学业即为事功),一也。生不得业,则退而著书,文字始出于私家矣;性不得养,则逐于外驰,意气遂激于名声矣。……人主操术以驭天下,亦张弛于其过与不及,俾愚弱者有所振,而俊异者得所范,而不诡于中斯已矣。”又如章氏对雍正帝的推崇也可见一斑,《外集》二《再上韩城相公书》:“宪皇帝整饬官常,未尝不留馀地,所谓王道本人情也。”见《章氏遗书》卷25,卷29,引自《章学诚遗书》第264页,第329页。
(45)章益国:《章学诚“史德”说新解》。
(46)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见《章氏遗书》卷9,引自《章学诚遗书》第84页。
(47)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习固》,见《章氏遗书》卷5,引自《章学诚遗书》第43页。
(48)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4《性理一》,引自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十四),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49)章益国以为“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中“其”为代词指前文“欲为良史者”,笔者赞同之,但《史德》第二段都是就史家主体创作中的心理活动“心术”而言,故第二段中“天与人参”的处所应当进一步指“心术”。
(50)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4《性理一》,引自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十四),第200页。
(51)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砭异》,见《章氏遗书》卷3,引自《章学诚遗书》第27页。
(52)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5《性理二》,引自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十四),第229页。
(53)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62《中庸一》,引自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十六),第2013页。
(54)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知难》,见《章氏遗书》卷4,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5页。
(55)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见《章氏遗书》卷4,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2页。
(56)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文德》,见《章氏遗书》卷2,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7页。
(57)章学诚:《外集》二《许尚之古文跋》:“读书广识,乃使义理充积于中,久之又久,使其胸次自有伦类,则心有主。心有主,则笔之于书乃如火然泉达之不可已,此古人之所以为养气也。”见《章氏遗书》卷29,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24页。
(58)章学诚:《外集》二《上辛楣宫詹书》,见《章氏遗书》卷29,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32页;《丙辰札记》:“惠士奇谓不读非圣之书者,非善读书。此可谓专己自封之学究作项门针。”见《章氏遗书外编》卷3,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99页。
(59)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文德》,见《章氏遗书》卷2,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7页。
(60)《诗大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郑玄注:“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者,谓若关雎兴后妃之类是也。”孔颖达疏《诗大序》:“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比者,比托于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惧……兴者,兴起志意赞扬之辞。”见《毛诗正义》卷1,《周礼正义》卷23,据本于中华书局1936年《四部备要》缩印之《唐宋注疏十三经》(一),中华书局1998年版,下引此书版本同。
(61)钟嵘:《诗品序》:“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寓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詠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单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引自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5页。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兴比皆喻,而体不同。兴者,兴会所至,非即非离。言在此,意在彼,其词微,其旨远。比者,一正一喻,两相譬况。其词决,其旨显;且与赋交错而成文,不若兴语之用以发端,多在首章也。”引自阮元主编:《清经解》卷84,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450页。
(62)《左传·成公·十四年》,又《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见《春秋左传注疏》卷27,卷53,引自《唐宋注疏十三经》(三)。
(63)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德第五》,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5—121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64)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德第五》,第118页。
(65)章学诚:《和州志》二《书第六·艺文》,见《章氏遗书外编》卷17,引自《章学诚遗书》第556页。
(66)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繁称》,内篇四《说林》;《方志略例》二《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见《章氏遗书》卷3,卷4,卷15,引自《章学诚遗书》第22页,第34页,第138页。
(67)章学诚:《永清县志》五《政略》,见《章氏遗书外编》卷10,引自《章学诚遗书》第487页。
(68)章学诚:《丙辰札记》,见《章氏遗书外编》卷3,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89页。
(69)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下》,外篇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方志略例》二《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湖北通志检存稿》三《徐本仙陈良翼传》:“志曰:……《春秋》所为,议而不断者也。”见《章氏遗书》卷1,卷9,卷15,卷26,引自《章学诚遗书》第9页,第80页,第139页,第286页。
(70)这里的历史评论包括对客观事实和对史学的评论以及带有褒贬倾向的叙事。
(71)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中》,见《章氏遗书》卷2,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3页。
(72)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下》:“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于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外篇二《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六艺先王旧典,以言建事,其道简易平直,人皆可知。即曰诗以言志,而正《风》《雅》《颂》揄扬功德,歌咏盛平,亦无隐而不彰之义,又何意之难求者哉?”见《章氏遗书》卷1,卷8,引自《章学诚遗书》第6页,第68页。
(73)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二《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见《章氏遗书》卷8,引自《章学诚遗书》第68页。
(74)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中》:“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外篇一《<淮南子洪保>辨》:“自来门户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质如是,皆随声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于反也。”见《章氏遗书》卷2,卷7,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1页,第62页。
(75)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二《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乙卯札记》:“古人作书,漆文竹简,或著缣帛,或以刀削,繁重不胜。是以文辞简严……自后世纸币作书,其便易十倍于竹帛刀漆……人情于所轻便,则易于恣放;遇其繁重,则自出谨严,亦其常也。读书鲁莽,未必尽由印版之多,而版印之故,居其强半。”见《章氏遗书》卷8,《章氏遗书外编》卷2,引自《章学诚遗书》第68页,第383页。
(76)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言公中》,见《章氏遗书》卷4,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1页。此说受益于[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第138页。
(77)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文德》;内篇三《辨似》,《质性》;内篇四《知难》;外篇二《读<史通>》:“有所为而言之,不必遽为定论,圣人所不免也。”见《章氏遗书》卷2,卷3,卷4,卷8,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7页,第21页,第24页,第35页,第74页。
(78)章学诚:《永清县志》五《政略》,见《章氏遗书外编》卷10,引自《章学诚遗书》第488页。
(79)章学诚:《外集》二《与史梧园书》,见《章氏遗书》卷29,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38页。
(80)章学诚:《外集》一《蔡滦州採芝图记》:“人生自少壮至老,身之所至不同,而心亦随时与为变易。是己方多幻。而又谪彼幻中之幻,不亦过乎?”见《章氏遗书》卷28,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10页。
(81)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下》,见《章氏遗书》卷2,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2页。
(82)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丙辰札记》:“《春秋》据事直书,枝指不可断,而兀足不可伸,期于适如其事而已矣。”见《章氏遗书》卷1,《章氏遗书外编》卷3,引自《章学诚遗书》第4页,第390页。
(83)章学诚:《文集》六《<四书释理>序》:“义理不切事情,则元虚飘渺,愈支愈离,而曲学横议,异端邪说,皆得乘间而入。”《永清县志》六《龙敏列传第一》:“史文有褒贬。《春秋》以来,未有易焉者也。”《史考摘录》:“自古史册,未有评论者也。自左氏传经,既具事之始末,时复诠言明理,附于‘君子设辞,史迁因之,篇终别起,班氏因而作赞,范氏从而加论,踵事增华,虽为一定之科律矣。”见《章氏遗书》卷21,《章氏遗书外编》卷11,《章学诚遗书佚篇》,引自《章学诚遗书》第206页,第490页,第655页。
(84)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古文十弊》:“不知大体,则胸中是非,不可以凭。其所论次,未必俱当事理;而事理本无病者,彼反见为不然而补救之,则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矣。……人苟不解文辞,如遇此等,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内篇五《史德》,见《章氏遗书》卷2,卷5,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9页,第40页,第41页。
(85)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古文十弊》,《湖北通志检存稿》四《文征丁集裒录近人诗文论》:“抒情本性,贵乎因地因时,别而择之,斯为论世。《关雎》说周衰盛,则美刺旨殊;《子衿》言学兴亡,则贞淫义异,贵耳而未尝贱目,以目淆耳则愚。爱古未尝薄今,以古律今斯舛。”见《章氏遗书》卷2,卷27,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9页,第299页。
(86)[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第177页。
(87)柳诒徵:《国史要义·史义第七》,第156页。
(88)章学诚:《丙辰札记》:见《章氏遗书外编》卷3,第398页。
(89)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见《章氏遗书》卷4,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8页。
(90)参见[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第178—179页。
(91)章学诚:《方志略例》二《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下》,见《章氏遗书》卷15,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36页。
(92)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六《杂说》,外篇一《立言有本》:“引申比兴,抑扬往复,可以穷文心之极变,达难显之至情;用以规谏讽喻,兴起好善恶恶之心,其为功也大矣。”外篇三《杂说中》,见《章氏遗书》卷6,卷7,卷9,引自《章学诚遗书》第55页,第56页,第94页。
(93)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永清县志》五《政略》:“《选举》有表而《列传》无名;与《职官》有表而《政略》无志,观者依检先后,责实循名,语无褒贬而意具抑扬,岂不可为后起者劝耶?”六《龙敏列传第一》:“为列传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则为人作自陈年甲状而已矣。”见《章氏遗书》卷9,见《章氏遗书外编》卷10,卷11,引自《章学诚遗书》第89页,第487—488页,第490页。
(94)章学诚:《评沈梅村古文》:“盖文各有体,六经亦莫不然。故《诗》语不可以入书,《易》言不可以附《礼》,虽以圣人之言,措非其所,即不洁矣。辞不洁则气不清矣。”见《章氏遗书补遗》,引自《章学诚遗书》第613页。
(95)章学诚:《永清县志》五《政略》,六《龙敏列传第一》,《和州志》三《列传第一》,见《章氏遗书外编》卷10,卷11,卷18,引自《章学诚遗书》,第487—488页,第490页,第563页。
(96)章学诚:《丙辰札记》,《知非日札》:“人物更多鼎革嫌讳,易代至再,公论自平。”《永清县志》六《龙敏列传第一》,见《章氏遗书外编》卷3,卷4,卷11,引自《章学诚遗书》第390页,第400页,第490页。
(97)参见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德第五》,第113—114页;[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第176页。
(98)这点从前面所引《和州志》三《列传第一》中提到的“论世之学”属于作者文中“神明之意”的一部分并与比兴的表现手法相并列可概括出。
(99)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二《<唐书纠谬>书后》,见《章氏遗书》卷8,引自《章学诚遗书》第68页。
(100)章学诚:《校雠通义》外篇《元次山集书后》,见《章氏遗书》卷13,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11—112页。
(101)章学诚:《永清县志》七《阙访列传第九》:“据事而书,总不必瑰异奇特,要必有端委可详”,见《章氏遗书外编》卷12,引自《章学诚遗书》第521页。
(102)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德第五》,第115页。
(103)章学诚:《文集》一《为毕制府撰光山县重修明少保陈公祠堂碑》,见《章氏遗书》卷16,引自《章学诚遗书》第143页。
(104)章学诚:《文集》六《金君行状书后》,见《章氏遗书》卷21,引自《章学诚遗书》第213页。
(105)梁继红:《章学诚学术研究》,北京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