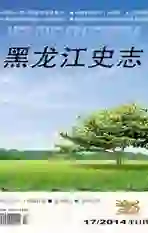古代典籍分类中之事物分类法探源
2014-11-11杨靖康
杨靖康
[摘 要]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借助典籍分类学而条分缕析,知其流变。事物分类法是古代典籍分类学所应用的主要分类法之一,其表现形式即为中国古代特有的类书。然而在类书问世之前,事物分类法已在典籍分类学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期。考查类书产生之前古代典籍分类中事物分类法的状况,探讨事物分类法在典籍分类中的应用及其流变,对前类书时代的事物分类法作一全景式描绘。
[关键词]典籍;分类法;类书
事物分类作为一种观念,很早就已产生。远古时期,人类原始思维中就有了分类观念,虽然只是先民对于自然界的事物进行最原始的归类,但作为事物分类思想之源头,已经开始影响以后整个事物分类法的发展。曹魏之时,事物分类法以其实用性之优点指导典籍整理,遂有中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之问世。而从事物分类思想产生到《皇览》问世的这段时期,事物分类法经过了多次探索与革新,最终找到了其在典籍分类学中的位置,为后世类书在典籍分类学中重要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关于典籍的最早产生时间,《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又《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曰:“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我国古代典籍在上古三代时期即已出现,只因年代久远,这些典籍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海洋中,虽有后世学者多加研究考证,然而完全恢复这些远古典籍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
在典籍产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其数量有限,不存在分类整理的问题,于是这些典籍便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世间。此阶段的“易”只是上古巫史的单篇卜筮记录,尚未筛选整理,各类术数典籍亦单篇分散流传;“书”是对所有记载历史事件之文献的统称,并无定本;“诗”则广泛传唱于宫廷与民间,其数量当远超出一百零五篇。另外各地民歌中,仅为口传,不曾书于竹帛者,亦不在少数;“礼”与“乐”是先有其制度,后有其书籍,最初只是对当时礼节仪式和乐律制度的一条条描述记录,并无定制之书籍。
一、事物分类法与“六艺”典籍分类
至孔子时代,适应知识传播的强烈需求,终于在儒家学派中产生了整理定型的典籍,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合称“六艺”。经过孔子删定整理的“六艺”,实际是儒家学派的内部教材,其内容选材以儒家思想为准绳,而非当时社会全部知识的总结。其典籍分类方法则是以事物分类思想为指导,将儒家所尊崇的典籍分为六大类。其“易”、“书”、“诗”等类目的确定,皆以该类典籍的事物名来命名,而非反映学术情况。这样看来,儒家“六艺”的典籍分类是建立在微观的儒家典籍基础上的,它所运用的典籍分类法并非着眼于全部学术,而是将微观的儒家典籍按照事物分类思想进行归类。“六艺”典籍的删定开启了事物分类法指导典籍分类学的先河,在以后不断的发展中,所指导典籍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微观的儒家典籍逐步向宏观的全部典籍扩展。
“六艺”典籍分类体系包括二级类目或三级类目,其各级类目的确立也始终遵循着事物分类法的原则,即以事物名称确定类目。如《易》类之下的二级类目即为六十四卦之名称,即乾卦、坤卦、屯卦、蒙卦、需卦、讼卦等。由此可见,其二级类目之命名均以卦名为准,而卦名是由上古巫史记录中流传下来的,属事物名称。《易》把散乱的上古巫史记录分类整理而成一部典籍,是运用事物分类法进行典籍分类整理的明证。
《书》类之下的二级类目按时代进行分类,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这种依时代分类亦为事物分类法之一种。
《诗》类之下二级类目为“风”、“雅”、“颂”,是按照诗歌应用之场合进行分类。再下还有第三级的类目,“风”之下类目按地域分类,如《邶风》、《鄘风》、《卫风》等十五国风;关于“雅”之下类目的分类标准,学界尚未有统一观点,或言按时代先后,或言按音乐特点,或言按具体场合,终有《大雅》、《小雅》之别;“颂”之下类目按宗庙系统分类,有《周颂》、《鲁颂》、《商颂》之分。此皆为事物分类法于典籍分类学中之具体应用。
《礼》最初只指《仪礼》一书,其二级类目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等,由此可见,当时对礼仪的分类已相当细致。掌管礼仪之官吏将所执行的礼仪形诸文字,遂有了一条条关于礼仪的记录。至于将零散的记录分类整理,编排成书,流传后世,孔子的贡献则是巨大的。
《乐》亡佚很早,其下属二级类目不得而知。但《周礼·春官》载:“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乐之舞曲既然包括了上述六种先代,则《乐》之典籍当亦为对六种乐舞之记录。倘实情如此,则其二级类目当为《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七类无疑,可证其分类方法亦遵循事物分类之原则。
《春秋》与《书》同为史书,但未直接连缀在《书》之后而纂为一部典籍,这也可印证孔子对典籍的分类整理并非遵循学术分类原则,而应用的是事物分类法。当时与《春秋》并列的,尚有《乘》、《梼杌》等多国史书,孔子为便于对儒家学派弟子之教育,选取了鲁国的《春秋》作为底本,而后进行加工,遂有了儒家经典的《春秋》。《春秋》下属二级类目系按照时间分类,将所载历史事件以年份统系在一起,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凡242年,其类目也相应的设为242个。
综上所述,“六艺”典籍分类学发端于儒家学派内部,其所类分典籍的范围仅着眼于儒家学派尊崇之典籍,具有局限性。当时,儒家之外诸子百家之书尚各自流传,未成系统。事物分类法的应用只能算作典籍分类领域的一次微观尝试,尚不能成为指导全部典籍分类的完善的典籍分类法。
二、事物分类法之新天地——走向宏观的抄撮之学
遇到重重困难的事物分类法虽然最早进入典籍分类领域,但在《别录》、《七略》及此后众多目录书产生之后,其地位已大大衰落,显然无法与后起的学术分类法相抗衡。要想继续指导典籍分类,就不宜和学术分类法竞争原有的领地,而应该另辟蹊径,开创指导典籍分类的新纪元。在思考与寻找过程中,肇端于“春秋”类典籍的“抄撮之学”给了事物分类法研究者巨大的启示。
前文提及的“春秋”类典籍的抄撮之学,打破了按照典籍名称进行分类的固有原则,将典籍内容拆散开来,然后按照事物分类法重新确定类目,进行再编排,结果是把大量内容相关的典籍语句集中到了一起,十分便于读者观览。最初的抄撮之学仅限在“春秋”类典籍中,当其价值被发现之后,便很快扩大开来,最终传遍了典籍的所有领域,成为事物分类法指导典籍分类学的一个新天地。
抄撮之学范围的扩大,从走出“春秋”类到指导宏观的全部典籍,几乎在东汉的二百年中实现了完美的蜕变,这个时期典籍分类学中事物分类法的应用可从以下诸方面窥见一斑:
经传典籍方面,有班固的《白虎通义》,该书是根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经学大讨论的结果撰集而成的。全书分类编述,并大量引述经传语句,是事物分类法指导经传典籍分类的一部杰作。清代陈立《白虎通疏证》,认为该书应分为十二卷五十篇,其篇目如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京师、五行等,将类目已经划分得很详细,可以认为是后世类书的雏形,只不过后世类书取材范围更加广阔,而《白虎通义》仅以经传书籍为范围。但是,《白虎通义》在经传典籍的分类整理问题上正式接受了事物分类法的指导,将扩大的抄撮之学视为一种典籍分类整理的新方法,这无疑给事物分类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支持,也为不久之后产生的类书提供了宝贵的编纂经验。
史书方面,是直接由“春秋”类的抄撮之学扩大而来。《隋书·经籍志》云:
自后汉以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隋书·经籍志》)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云:
史钞之学,起于后汉,而其书则自卫飒《史要》始。(《后汉艺文志》)
又,该书史部史钞类著录之书共六种:
卫飒《史要》十卷;周树《洞历》十篇;《古历注》;侯瑾《皇德传》三十卷;应奉《汉事》十七卷;荀爽《汉语》。(《后汉艺文志》)
又,《后汉书·杨终传》载:
(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汉书·杨终传》)
由此可见,上述诸书均为史书之抄撮,其范围已从最初的“春秋”类史书扩大为所有史书。可惜这些书现在均已亡佚,其类目已不得而知。
兵书方面,亦有抄撮之作出现,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之裴松之注云:
(帝)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裴松之《三国志注》)
又,《隋书·经籍志》著录《兵书接要》十卷,《兵法接要》三卷,均署魏武帝撰。可证曹操确实作过兵书之抄撮,惜其书未传至今,类目亦无从考索。
在综合性书籍方面,也出现了抄撮之作,就其形制而言,已与后世类书无异,只是规模稍小而已,如刘向《新序》、《说苑》,应劭《风俗通义》即是。
刘向《新序》分类编纂了上自舜禹,下自汉代的各类事迹,遍采经史诸子,涉及的典籍包括《吕氏春秋》、《史记》、《战国策》、《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庄子》、《荀子》等多种。《汉书·艺文志》著录该书但未标明卷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30卷,至北宋仅存10卷,经曾巩搜集整理,定篇目为《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二卷,《善谋》二卷,共十卷。《新序》一书虽存其残本,然而刘向原初之类目设置已不得而知。我们亦无法从仅存三分之一的残本中窥测刘向此书中的典籍分类思想。
刘向另一部著作《说苑》,与《新序》有相似之处,该书分类编辑了上古至西汉的各类事迹,涉及政治、思想、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内容,近人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录其类目如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诸条,由此可见该书涉及范围之广泛,确为综合性的抄撮之书无疑。
应劭《风俗通义》记录了大量古代神话、风俗资料,广引古书,分类编述,近人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认为“应氏书卷帙,今所存者,劣及三分之一”1,原书三十卷,现存十卷,《风俗通义校注》存其篇目为黄霸、正失、衍礼、过誉、坂、声音诸篇。
王利器在该书中又云:
其余二十篇,见于苏颂校《风俗通义》题序者:曰心政,曰古制,曰阴教,曰辨惑,曰析当,曰恕度,曰嘉号,曰徽称,曰情遇,曰姓氏,曰讳篇,曰释忌,曰辑事,曰服妖,曰丧祭,曰宫室,曰市井,曰数纪,曰新秦,曰狱法。(《风俗通义校注》)
这样,应劭《风俗通义》的全部类目就可以尽观了。综而观之,其内容搜罗广泛,对保存古代典籍中涉及风俗之资料尤为得力,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的产生。
《皇览》之编纂时间起自汉末延康元年(220年),这一年恰好也是曹丕称帝的黄初元年,历史长河由汉而魏,典籍分类学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巨著,黄初三年(222年),《皇览》终于成书。该书上承抄撮之学,并将其范围扩大到最为宏观的全部典籍,下启魏晋直至清代长期的类书编纂史,可谓影响深远。从此,类书这一形式便成为典籍分类学中事物分类法的具体体现,并一直持续到清末西学东渐时西方百科全书观念引进为止。
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质变,如果说从“六艺”典籍的分类到抄撮之学的逐步扩大,都在为事物分类法指导典籍分类学而不断探索的话,那么类书的问世就宣告了上述探索的终结。典籍分类学中的事物分类法在经过了漫长的量变之后,终于达到质变,完成了其指导典籍范围从微观到宏观的完美蜕变,同时也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典籍分类学的繁荣时代。
参考文献: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岳麓书社,2010年。
[3]张涤华《类书流别》,商务印书馆,1985年。
注释:
(1)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