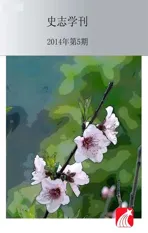铁路与近代广东古镇变迁
2014-04-11李丽娜
李丽娜
铁路与近代广东古镇变迁
李丽娜
近代以前,广东的商品运输以水路为主,铁路通行后,巨大及优越的运输性能推动交通运输方式的转换,进而改变了商品流通网络,也带动了广东城镇的兴衰起伏。本文以广东三大古镇为例,揭示铁路交通的出现对于古镇变迁影响深远,集中表现在佛山的由盛及衰、广州城市近代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石龙的愈加昌盛等方面。这一变动充分体现了以铁路为主的近代交通与广东近代化的紧密联系,预示着近代广东经济的发展轨迹,影响着其历史变迁。
铁路 近代交通 广东古镇 近代化 衰落
明清以来,广东有“佛山、广州、石龙、陈村”四大古镇,它们或以矿产资源丰富闻名,如佛山;或是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如广州;抑或是交通枢纽,如石龙。广东水路四通八达,铁路修建前广东的商品流通主要依靠水路进行。
1903年,自广州珠江南岸石围塘,经三眼桥、佛山、小塘至三水的广三铁路建成通车;1911年,连接广州至九龙的广九铁路通车运营;1906年粤汉铁路动工,1936年筑成。1936年9月1日粤汉铁路首次通车,由广州黄沙出发,历时44小时抵达武昌徐家棚。至此,广东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铁路交通为主的近代交通运输网络。铁路通车后,由于其运输量大、不受气候影响、运费相对低廉,很快成为主要的货物运输方式。交通方式的转换重构了商品流通网络,推动了广东古镇的变迁。四大古镇中,陈村因花卉业繁荣,受交通方式变动的影响较小,因此不在讨论的范围。
佛山由盛而衰
明代,佛山只是辖于南海县的一个小镇,没有行政机构,凡事听命于南海县政府。明中叶,佛山逐渐崛起,景泰年间,佛山已是四远商贾荟萃、拥有“几千余家”的规模了。佛山的崛起首先源于其拥有富裕质优的矿藏资源,佛山一带,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在南海县西樵、石冈、松子冈、和仓冈、吉水、黄借冈,新会县铁齿屏山等地,均发现了丰富的铁矿资源,佛山的冶铁工业、铁器制造业相应得到大发展,加之政府的垄断政策,佛山冶铁业随之兴盛,自明以迄清,广州、南雄、韶州、惠州、罗定、连州、怀集之铁均输于佛山,冶铁业成为佛山的支柱产业,“铁莫良于广铁”,“诸所铸器,率以佛山为良”,佛山铁器十分畅销。
随着铁器手工业的发展,佛山镇作为手工业城市开始兴盛起来,明清时期佛山镇墟市热闹,店铺林立,经济繁荣,《佛山赋》对当时的景象有详细描述:“庐橘杨梅,三墟竞卖【表冈墟(今大墟)塔坡墟(今普君墟)盘古墟】。荔枝龙目,六市争光【官厅市(今官厅脚),公正市,早市(冈心烟市),三元市,晚市,朱紫市(今朝市),为六市】。菊舍蟹黄,细桥头之持蟹可嗜好(大桥头卖谷,细桥头则海鲜罗列,明虾鲜蟹,贩者互争先焉)。竹篱梅白,新涌口之脍鲤弥鲜(新涌口上多蛋民居住,以渔为生,价颇贱)。土毛既列,工作宜知。治肆纷罗,人擅嵇公之业(乡中打铁者甚多)。锅炉旁列,世传桌氏之奇铸镬锅釜为乡土产,钟鼎皆然。钟始两栾,火铸五更之候;鼎成三足,丹逢九转之时(鼎即香炉,有三足、四足、两耳者)。赤缆几家,青烟四吐(铁线亦乡土产,有大缆、二缆、上绣、中绣、花丝)。铁丝千尺,红焰纷批(铁线、铁锅,乡多仰食于此。八景‘孤村铸炼’即此)冠履川楚(自福禄里帽店、潘涌里鞋店,弥望皆然),货贝华夷(西北各江货物聚于佛山者多,有贩回省卖与外洋者,不止佛山缎、佛山纱流行外省也)。”[1]这一时期佛山镇经济实力雄厚,远超南海县,与广州并称“岭南两大中心市场”,并与京师、汉口、苏州并称“天下四聚”,甚至冠盖景德镇、汉口、朱仙三大名镇,成为“天下四大名镇”之首。
佛山的崛起还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佛山周围环绕着大小十二条河流,它控扼西江、北江的航运通道。近代铁路和海运业兴起以前,内河航运是自古以来交通运输的主要动脉,在明清时期佛山镇的发展过程中,“西江、北江、东江”三大水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佛山通过西、北、东三江,以广东为出发点,以广西、贵州、四川、云南、湖南、江西、福建省区为腹地,是其工商业持续一千多年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条件。由于水路交通便利,佛山作为国内各省间贸易及对外贸易的中转地,头角日益峥嵘,甚至凌驾于广州之上。
随着佛山镇经济实力的增强,清顺治四年,政府开始向佛山派驻驻防官,加强对佛山镇的管理,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开始在佛山设立“广州府驻佛山分防同知”,正五品,品级比正七品的南海县知县高两级,自此,佛山镇有了自己的官署机构,在政治地位上开始超过了南海县,成为一个次府级经济重镇,而作为佛山的“上司”的南海,却没有佛山的地理优势和经济优势。
总而言之,佛山镇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实力增强,政治地位提高,实现了由明代的单一经济功能向清后期区域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双重角色的演变。
但至清末,佛山逐渐衰落,首先对佛山经济以致命打击的则是鸦片战争后来自西方的商品倾销。道光二十一年(1841),《江宁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咸丰朝以后,各国更是纷请立约,洋货充斥,中国商务愈不可问。而佛山先承其弊,铁器业首遭打击,自洋铁产品大量输入广州,佛山铸铁业作坊逐渐减少,至光绪末仅余数家,铁钉、铁针也因洋钉、洋针输入而销路大减,至于其他各类手工业,如纺织业亦由于洋布、洋纱输入而大受摧残。商业贸易也日渐萎缩。其二,畅通的佛山涌(汾江)到清嘉庆年间日渐淤浅,及至清末,佛山涌急剧淤塞,上游入口处的沙口河宽约160米,越向下游越窄,至南堤路一带河宽只有33米。西、北两面河口、河床都有礁石和很厚的冲积物。加上当时的洋货萎缩,来往船只越来越少,货运量与客运量逐年下降。河运的阻滞,使佛山失去了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理优势,给佛山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制约。佛山在失去水运交通优势的同时,同样也因铁路的出现而备受打击,广三铁路和粤汉铁路相继建成通车,改变了珠江三角洲区域原有交通线路货物的流量和流向。此前,西、北、东江等地区的货物必经佛山输广州,而广东的货物也必经佛山输往外省,铁路的开通,使佛山作为广州内港的枢纽地位丧失,广东的物流、人流也不再向佛山聚集,相反佛山的工商业和人口则大量向广州转移,由此进一步加剧了佛山的衰败。1911年,石湾人林拱宸在广州长寿街开设“游艺织造公司”;1915年,黄露堂在广州十二甫顾家社办了“裕华陶瓷公司”;同年,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广州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9年,黄裕甫将在佛山经营的市坊“泰盛”号迁广州,该厂生产的阴丹士林布享誉省、港;中成药业的“陈李济”“马百良”“李众胜”“刘诒斋”“黄祥华”“迁善堂”等,都先后从佛山迁去广州发展,佛山逐渐由盛而衰。
广州城市近代化快速发展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城市。明清以来,广州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的输入使广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并催生出城市民族工业和城市经济的产业化进程。
这一时期,除了外力的因素,近代交通的蓬勃发展也推动了广州城市的快速发展。公路运输方面,陈济棠主粤期间全省新筑公路1万多公里,形成了以广州为交通枢纽的省内四大干线系统,总长约3725公里。水路运输方面,广州港往来外洋商船吨数在1932—1936年间一直保持全国第二位的水平,通往国内沿海地区主要的客运航线有14条,主要的内河航线有40余条。广州是我国最早开通铁路运输的城市之一,1903年广州经佛山到三水的广三铁路通车运营,每日有8班列车运行,载客2000多人。广三路全长49公里,1909年的客运量达329万余人。它大大加强了广州与沿线珠江三角洲各县的往来与联系。广州经深圳至香港九龙的广九铁路,经过数年努力于1911年筑成通车。这大大便利了穗港间的陆路交通。它全长179公里,其中属广东管辖的广深线为146公里,其客运量1913年达20万人,1930年约为175万人。广州往北的大动脉粤汉铁路,于1906年开始招商集股兴建,10多年后完成了广州至韶关的广韶线,从而大大改善了广州到粤北各地的交通,它全线于1936年完全建成通车后,使广州与湖南、湖北等内地各省的联系更为密切起来。这期间,广三路、广九路均与粤汉路接轨相通,广州作为铁路交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得以进一步凸显出来。
在近代交通的推动下,广州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迅速,近代工业蓬勃发展,1920—1927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有18家,广州新创办的工业企业为25家,其中资本可计的资本总额636.1万元。据统计,1933年广州工业资本与产值均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上海,至1936年,广州已有工业企业11532家,其中近代工业企业3218家,工业产值3.43亿元[2]。广州商业也渐显繁荣,据统计,1923年广州工商业户为30702亿元,1929年店铺增至33928家,仅1933年上半年新开业的商店就多达3646家[3]。1936年广州内贸总值占全国内贸总值的6.08%,居全国城市前五位之列;1937年广州进出口贸易值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值的6.07%,仅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城市第三位。广州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几个大城市之一,其近代化发展明显走在全国前列。而且,近代广州城市的发展和变化对于周边地区也起了十分强大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可以说都曾受到广州城市近代化的促进和影响。
广州的城市格局也发生变化,清代的广州城北限于越秀山,南阻于珠江,东西阻于濠水,城池变化不大。珠江北岸淤积成陆,并成为商业区,商行林立,故清初将东西两翼城墙南伸至江边,如鸡之两翼,故谓“鸡翼城”。从经济发展来看,清代广州城已有明显的分化,有“东村西俏,南富北贫”之称。“郡城之俗,大抵尚文,而其东近质,其西过华;其南多贸易之场,而北则荒凉。故谚云东村西俏,南富北贫”[4],由于城南临近珠江,交通便利,商贸繁盛,故“富”,而城北为山地,经济落后,多为寺院、书院之所,故“贫”,东郊地区多为丘陵台地,水土不肥,农业不发达,村落不多,地理偏东,交通不便,与之交通便利的西关地区相比,整体上比较落后。铁路通行后,广州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传统城墙的限制,不断向外围扩展,陆续开发了西关、河南和东山地区,初步体现出“西拓东进”的发展趋势,尤其是随着东山住宅区的开发,城市中心区逐渐东移,市区东郊东山一带,本为郊外一村落,但广九铁路经此入市后,“欧美侨民有在铁路附近下居者,民国以来,建筑西式房屋者日众,遂成富丽地区……入城长途汽车由此至黄沙,江岭鬼岗各马路虽不及城内大路之宽敞,而树木众多,空气清洁,不若西关人烟稠密之烦嚣。”[5]
粤汉铁路及内港的修建也推动了广州城市向珠江南岸延伸。粤汉铁路终点站黄沙与河南洲头咀一带仅一水之隔,内港修筑前,广州城市扩展方向主要集中于珠江北岸,在内港修筑的同时,粤汉铁路也逐渐向广州延伸,珠江铁桥及其粤汉铁路的完筑,广州城市开始向珠江南岸延伸,“民国21年11月,广州市政府公布广州市道路系统图,确定城市道路系统的形式为棋盘式”,规划河南刘王殿附近为新市区中心,其南北干线为子午线,东西干线用以联络粤汉铁路与黄埔地区,环形干线用以联络市区各纵横干道及河北、河南、芳村、大坦沙一带。1932年8月,广州市政府公布《广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这一草案将广州全市地域分为工业、住宅、商业混合等四个功能区。河南被定为广州工业区,士敏土厂、硫酸厂等均建于河南。新辟商业区设于黄沙铁路以东、河南西北部,东山以东以及省府合署以西一带,模范住宅区也开始在河南各地设立。另外,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广州共有剧院六家,其中河南就有一家[6]。广州地区共有11家火柴厂,河南则有4家[7],不难看出,铁路与内港修筑大大促进了广州河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由于日本铁蹄的践踏,广州内港未能如期完工,但随着内港的修筑和河南地区的兴起,珠江南岸逐渐发展成广州新兴的城市增长点,广州城市发展中心开始由一个向多个转变,交通条件的改善顿使河南成为冲要之区,而这种变化奠定了后来广州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
石龙的昌盛
石龙在明代嘉靖年间开墟,原名石隆墟,清代乾隆年间改称石龙镇[8],石龙镇处于东江下游东江干流与南支流交汇处,地理区位优越,是东江运输的交通枢纽,据《东莞县志》载:“石龙……商贾辐集,当郡与惠潮之冲……东江自北岸而下,合增江、扶胥,以达虎门,其南流亦纳东莞之水来汇。”[9]明清时期,石龙镇控制着东江流域大米和木材等主要农林产品的流通,对整个东江流域和省港地区的粮食、木材价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后,石龙与香港展开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土纸、黄麻、大头菜、竹制品等商品大批由石龙运往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而洋货则由香港运入石龙,再转销内地各省。由于商贸的发展,石龙较早出现代理商行,如苏柏记代理美孚、东兴发代理亚细亚、福祥代理德士古等。清代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写道:“石龙亦邑之一会。”入清以来,石龙外来人口增长很快,人数远远超过当地居民,商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并因其“交通惠(州)、广(州),商贾如云,而鱼盐之利,蕉、荔、橘、柚之饶,亦为东南诸邑之冠”[10],石龙与广州、莞城、惠州、增城、新塘、太平等地有长行渡船往来,为珠江三角州东部重要辐射中心。
清朝末年,随着广九铁路的开通,石龙在商业和交通方面的地位更加显要,成为东江流域和省港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贸重镇。1926年,东莞第一间银行中央银行在石龙设立,1929年5月,石龙开通了至广州的长途电话业务,成为最早开通长途电话的城镇之一。东莞最大规模的当铺也开在石龙,商业的繁荣带动了手工业等行业的发展,作坊林立。形成了竹器街、面街、棉花街等产品专产专卖街市和民一布厂等私营企业。石龙也成了东江流域主要军事基地,孙中山、周恩来、蒋介石等曾多次到石龙,成了国民政府东征讨伐陈炯明的大本营。石龙最早的马路建于1929年左右,马路两旁的建筑是传统的骑楼结构,从东至西由沙边街、龙兴街、万兴街(三角市)、万安街、万胜街、东禄元、西禄元、饱街、塘头9条小街衔接而成,石龙人民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命名为中山路,是东莞最繁华的商业区,有诗云:“石龙今日市廛开,车马纷纷涌进来,午后酒阑人尽散,白云依旧锁苍苔。”这是石龙在清末民初商业繁华情景的真实写照。
小结
铁路通行后,由于其运量大、运费低廉、不受气候影响等优势,迅速打破了广东以水路为主的交通体系,逐渐形成以铁路为主的新型交通网络,进而推动了商品流通网络的改变及重要城镇的变迁。就广东古镇而言,铁路在其兴衰更替变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佛山因矿业、手工业的衰退及交通枢纽位置的丧失很快衰落;而广州因铁路中心地位的确立近代化步伐大大加快;石龙也因铁路的通行巩固了其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商业日益繁荣,延续其昔日的辉煌。广东古镇在近代的分化和命运,凸显了近代交通是引领城镇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折射出城镇近代化转型的曲折。
[1](清)吴荣光.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艺文下·佛山赋.清道光十年刻本.21.
[2]杜询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附表《历年所设本国民用工矿、航运业及新式金融业一览表(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3]广州市市政府统计股编印.民国十八年(l929)广州市市政府统计年鉴(第一回).广州市市政府,1929.335.
[4]黄佛颐.仇江等点注.广州城坊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25.
[5]叶云笙.广州工商年鉴.广州工商年鉴出版社, 1946.8.
[6][7]广州市年鉴编纂委员会.广州年鉴·文化.广州:奇文印务公司,1935.86,466—468.
[8]《东莞文史》编辑部.东莞文史.第五期.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东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部.1985.63.
[9](清)周天成修.邓廷喆,陈之遇等同撰.(雍正)东莞县志(卷二之四).风俗.见于故宫博物院.故宫珍本丛刊(163).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321.
[10](清)金烈,张嗣衍,沈廷芳.(乾隆)广州府志(卷二).舆图.清乾隆24年(1759)刻板.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李丽娜 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博士 讲师
(责编 高生记)
※ 本文为2013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铁路与广东城市近代化进程:1903—1949”(批准号:13G69)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