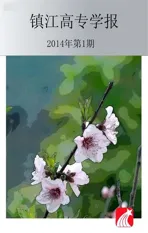论曹禺四大悲剧中象征性意象的流变与整合
2014-02-05黄梦菲
黄梦菲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对曹禺四大悲剧艺术成就的探讨,历来是曹禺研究领域的一个显要课题。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大抵立足“现实主义”的标准衡量并判定其“经典”价值,而事实上,从《雷雨》《日出》[1]《原野》到《北京人》[2],除了不断强化并一步步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外,超现实主义戏剧手法的运用,也始终伴随其中。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以“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为代表的象征性戏剧意象的构思和创造上。正是这些象征性意象的加入,使得曹禺的四大悲剧在传达深刻理性精神(暴露性与批判性)的同时,又融含着一种超现实的、形而上的追问,即:对于“命运”的体认与思索——在这个意义上,四大悲剧表现了一种深厚的“命运意识”!
所谓“命运意识”,指的是作者在对“命运”进行自主的思考之后得到的一种认知,是对“究竟是什么在左右我们命运”的一个回答。从《雷雨》到《北京人》,体现的正是曹禺命运意识的不断发展。本文试图立足曹禺四大悲剧中象征性意象的思想艺术内涵及其得失,探讨曹禺先生命运意识的发展轨迹。
1 雷雨——命运“主宰”的象征
《雷雨》源于一个“诱惑”。用曹禺先生的话来说,“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3]239而这些神秘的、不可言喻的憧憬又都集中体现在了“雷雨”这个意象中。概而言之,“雷雨”是《雷雨》这部戏剧的根源所在,既是血肉,又是精魂。
“雷雨”首先是一个景物意象,它贯穿于全剧始终,营造出一种混沌而紧张的氛围。而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之上,曹禺还赋予了“雷雨”第二重含义,即“命运”的主宰。曹禺曾经说过:“《雷雨》里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就是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他几乎总是在场,他操纵手下其余八个傀儡。”[3]252在这里,“雷雨”与其说是这场悲剧的旁观者,毋宁说是这场悲剧的推动者。它盘踞于所有人之上,冷眼旁观着他们自救而不得的可笑,并将他们导入更加无法自拔的深渊。
剧作第一幕即营造了雷雨将临的氛围:“屋中很气闷,郁热逼人,空气低压着。外面没有阳光,天空灰暗,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处于这样的氛围中,剧中的每个人似乎开篇就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压力所包围——四凤因担心被周家解雇而心事重重;鲁贵因害怕少了女儿这棵摇钱树而心怀鬼胎;鲁大海因谈判无果而忿忿不平;繁漪因周家长久的压制而感觉透不过气;周冲因心怀的美梦不得实现而失落;周萍因繁漪的纠缠而惶恐不安;周朴园因自己建立的秩序家园逐渐崩塌而愈感无力;就连还未出场的鲁侍萍,也因着女儿进到周家做丫鬟这一事实而提前预约了悔恨和愤怒。正如曹禺所说的那样,这八个人一开始便被置于“雷雨”之下,注定了其逃脱不掉的命运。
我们知道,《雷雨》中隐藏着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周萍与繁漪的乱伦之恋、周萍与四凤的禁忌之恋以及周朴园与鲁侍萍30年前的恩怨纠葛。而剧中八个人物的“自救”,又演变成全剧的主要情节——四凤一拖再拖不肯跟母亲离开;鲁贵想方设法将四凤留在周家;鲁大海企图迫使周朴园妥协;繁漪希望周萍能带她离开周家;周冲渴望着“飞”到遥远的天边;周萍希望从四凤身上重新获得生命力;周朴园一直用着一家之长的威严去维系着家族秩序;鲁侍萍一心希望女儿不要走她的老路。正是由于这八个人的“自救”,却反而推动了这三个秘密慢慢浮出水面,抽丝剥茧般变得清晰,最终酿成他们无法承受的灾难。随着繁漪知晓周萍与四凤的关系想辞退四凤,继而将鲁侍萍召回了周家,剧中的矛盾也逐渐向着不可调和的方向发展。鲁侍萍认出了周家,周朴园认出了鲁侍萍,鲁侍萍知道了周萍的身世,繁漪逼得周萍打算连夜带着四凤逃离,鲁侍萍撞破了四凤与周萍的恋情,繁漪逼得周朴园道出鲁侍萍的身份……矛盾一个接着一个地释放出来,最终抖出了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真相。天气逐渐由阴沉愤懑而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雷雨铺天盖地而来的那一刻,也正是周家所有秘密被揭开的那一刻。太多的出人意料,太多的阴错阳差,以致真相大白的同时石破天惊,一切已经无可挽回。死的死,疯的疯,毁灭的毁灭,逃离的逃离,而荡涤一切的雷雨此刻也如约而至,冷静地审视着这场早已注定的悲剧。
在曹禺的四大悲剧中,《雷雨》无疑显示了强烈的命运观念。曹禺试图在他的戏剧中显示来自宇宙中的“不可知”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因果”,也不是“报应”,而是由天地间的“残忍”交织出的一个“主宰”,雷雨,便是这个主宰的化身。在他的操控下,枉称为万物灵长的人类也显得愚蠢无能,“他们怎样盲目地执着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3]240。这堆“蠕动着的生灵”或许永远也想不明白,灾难究竟是怎样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为什么他们明明都在努力自救,却又同时被自己推进更深的深渊。他们能隐隐感到一种莫名的来自身外的力量在压迫着他们,却又完全摸不清这股力量究竟是什么究竟来自哪里。曹禺正是洞悉了这宇宙间的“残忍”和“冷酷”,于是借着《雷雨》来告诉我们,这便是“主宰”的力量。在它的面前,一切都难逃毁灭,越逃避,来得越迅疾,越挣扎,来得越惨烈。《雷雨》悲剧的精神也正是在这里显现出来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曹禺虽然也将这“主宰”与希伯来文化中的“上帝”相提并论,但实际上他并不完全承认这“主宰”便是上帝,他说:“他(指周冲)的死亡和周朴园的健在都使我觉得宇宙里并没有一个智慧的上帝在做主宰。”[3]244相对而言,这份“主宰”具有的某种不可捉摸以及“捉弄人的邪恶本质”倒是与希腊文化中的“命运力量”观念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因此曹禺一再强调要我们怀着“悲悯”的心态去理解《雷雨》,这份“悲悯”不仅仅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人物,更是给那群在命运的主宰下受难的生灵。
2 日出——末日“审判”的象征
当曹禺对《雷雨》渐渐生出一种厌倦,继之而来的便是《日出》。《雷雨》是对天地间某种“主宰”的憧憬,到了《日出》,曹禺却对这残忍的力量生出一种恨恶来。他说:“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的刺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他恨“人群中一些冥顽不灵的自命为‘人’的这一类动物”,恨他们“充耳无闻,不肯听旷野里那伟大的凄厉的唤声”,恨他们“避开阳光,鸵鸟似的把头插在愚蠢里”[3]249。所以他想对着这帮“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人们”宣泄自己的愤懑,想要有某样东西来对他们的末日进行“审判”。这个“审判”就汇成了日出这一意象。
在《日出》这部剧作中,虽然“日出”这个意象蕴含着全剧的中心主旨,但它却一直没能完全地露脸。整部剧作没有出现对“日出”这一景象的直接描写,而与日出勉强相关的描写也仅有两处,一处是陈白露遇见小东西之前,出现了“黎明前的光影”;第二处是第四幕末尾,陈白露在吞食安眠药自杀后,方达生拉开了窗帘,“阳光射满了一屋子”。这诚如曹禺先生所说,“我描摹的只是日出以前的事情,有了阳光的人们始终藏在背景后,没有明显地走到面前”。[3]250正是因为如此,《日出》招来了不少的批评,很多人认为其写得“太过啰嗦”,没有点出主旨,即没有明确写出“日头究竟怎么出来”。
事实上,虽然日出这一意象没有直接露脸,但它所代表的审判力量却一直贯穿着始终,其作为代序的八段引文就强烈地昭示了这一点。第一段引文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七章,这段引文历来被作为连接全剧的“观念”,是全文的核心主题。在奉行着“损不足以奉有余”游戏规则的社会中,即便是处于“有余”阶层的潘月婷、李石清、顾八奶奶之流,在剥削着黄省三、翠喜、小东西等“不足”阶层的同时,也逃不掉被更高的“有余”阶层(如金八等)剥削的命运。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公平没有希望,有的只是无限循环的“人吃人”。第二段引文出自《新约·罗马书》的第一章①原文所写为《新约·罗马书》的第二章,有误。,这里借保罗眼中“外邦人的种种罪恶”来隐射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事”,现实社会中充斥着“嫉妒、凶杀、竞争、诡诈、毒恨”,更加罪上加罪的是“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段引文更加具体地昭示出“损不足以奉有余”社会中的罪恶,也表明了曹禺对这个社会的失望和愤怒。第三段引文出自《旧约·耶利米书》的第四章②原文所写为《旧约·耶利米书》的第五章,有误。,在《圣经》中记载的是先知耶利米对异端邪教招致“一切毁灭”的预言,引用至此则寓意着一切罪恶必将遭到应得的报应,所有的罪人必将得到其应得的“审判”。第四段、第五段引文分别出自《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和《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均为基督的劝诫之语,而在《日出》中却是对剧中人物进行“审判”的依据:“不肯工作”的人即是包括陈白露在内的“有余”阶层,他们听不进打夯工人唱着的“要想得吃饭,可得做工”的歌,终日只想着不劳而获,而他们的下场就是“不可以有饭吃”,所以日出之时,潘月婷、顾八奶奶之流纷纷破产,陈白露也在种种债务中服药自杀;而“分党”则是这些鬼们的第二条罪状,张乔治对陈白露的心怀鬼胎、顾八奶奶和胡四之间的虚情假意、潘月婷和李石清之间的尔虞我诈、潘月婷与金八之间的明争暗斗……他们做不到“一心一意,彼此结合”,所以他们的下场就是四分五裂,各个而亡。在《日出》中,犯下最大分党之罪的即是李石清,他为了上位对潘月婷使尽了小聪明,为了稳住地位又无情地踢开了黄省三,为了充门面要自己的妻子故意输钱。他自己犯下种种罪恶的同时,还教唆黄省三去偷去抢,甚至逼迫他去跳楼。然而审判终会降临,费尽心机的下场还是一无所得——丢了工作,丢了钱财,丢了地位,连自己儿子的性命也没能保住。在基督看来,不劳而获、同室操戈均是大罪,而犯下这些大罪的群鬼们也在日出之时得到了应有的审判。第六段和第七段引文分别出自《新约·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和第十一章,昭示的是上帝对于人们的引导,只要跟着光走,就能走出黑暗。第八段引文则出自《新约·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正是上帝引导人们的终极——旧世界毁灭之后的新天新地。对应在《日出》中能够走出黑暗的只有在阳光中的打夯工人们,这也正应验了陈白露反复念叨着的“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日出之时,群鬼们纷纷遭受了应得的审判,被毁灭在黑暗中,而保有希望的人们沐浴在阳光下,建造着新的天地。
罪恶——惩罚——毁灭——新生,这便是《日出》这部戏剧的脉络,群鬼们不论怎样拒绝日出、厌恶日出、害怕日出,也终究逃不掉日出,因为日出便是对他们的审判的象征。基督教往往将“报应”推迟至天国,而曹禺先生却在日出之时直接写出了鬼的阵营的溃败,暗示了那个“伟大的未来”。曹禺先生将命运交给一种终极力量,与其说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毋宁说是当时黑暗社会“逼迫”的结果。现实太过丑恶,人的力量又太过渺小,所以曹禺先生才渴望能有一种外部力量介入,直接扫荡一切罪恶,这便是“正义的审判”。
3 原野——仇虎“心魔”的象征
在曹禺的四大悲剧中,《原野》是有些特立独行的,它显出更加明显的象征主义色彩。那片神秘幽深、布着隐隐薄雾的原野,作为全剧的“中心意象”也有着独特的内涵——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主人公仇虎心魔的象征。
仇虎和原野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们一样丑陋、一样神秘、一样充斥着原始的力量。踏进原野,我们看到的是一片苍苍莽莽的景象。在这里,“大地是沉郁的”,巨树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一切都透着幽暗与荒凉,仿佛便是人间地狱。而在这个原野上登场的仇虎也是一样地“丑陋”,有着“乱麻似的头发”“硕大无比的怪脸”“打成瘸跛”的右腿,以及闪出“凶狠、狡恶、机诈与嫉妒”的眼睛,仿佛便是地狱里的恶鬼。诚然,关于原野和仇虎的描写并非都是真实的,作者本身也无意于此,他只是通过这一系列“非真实”的描绘将原野与仇虎自一开始就紧紧联系在一起,将这两者身上共有的恐怖与幽暗展现在观众眼前。其次,正因为这诸多相似之处的存在,仇虎在原野中就显出一种和谐之美。仇虎本身是丑陋的,可“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的”。仿佛他本身即是属于这片原野的,而这片原野也是因他而存在的。原野是仇虎的起始,也是仇虎的终结。10天前逃出监狱的仇虎在原野里开始他的复仇计划,10天以后的仇虎报了仇,却还是没能走出这片林子。
有人将仇虎走不出原野的原因归为“愚昧和迷信”,而在我看来,却恰恰是因为这原野就是仇虎的内心的外化,他才注定走不出。我们知道围绕着仇虎的冲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外在的,即他与焦家的不共戴天之仇,另一个是内在的,即复仇意志与善良本性之间的矛盾。当年的焦阎王活埋了仇虎的爹,迫害死了仇虎的妹妹,抢走了仇虎的未婚妻,还将仇虎关进监狱折磨了8年之久,种种原因使得仇虎的心已经被仇恨填满,变得阴冷而残酷,就如那片幽暗不见天日的原野。他活着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复仇,向焦家复仇,向焦家代表的黑暗势力抗争。然而当他好不容易逃脱了看押回来,却发现焦阎王已经死了,焦母虽然也是狠毒狡诈,却已年老眼瞎;焦大星又是软弱善良,还把仇虎当做自己的挚友;小黑子更还是嗷嗷待乳的婴孩,要将仇恨发泄在他们身上又与仇虎的善良本性相悖。最后随着焦母的步步紧逼,仇虎终于对焦大星动了杀机,又阴错阳差地让小黑子死于焦母之手,而他自己则带着金子逃进了黑森林。然而大仇得报的仇虎却没有得到解脱,反而陷入更深的黑暗。他与森林中的幻象抗争,莫不如说是他与自己内心的恐惧抗争,他在森林里的迷路,莫不如说是他自己的内心已经没有出路。所以当他最后看到10天前被他丢弃的枷锁又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反而豁然明白过来,这片林子早已成为他内心的物化,自他踏入之时已经给他套上了摆脱不掉的枷锁。所以他说“现在那黄金子铺的地方只有你(指金子)一个人配去了”,所以他最后选择在森林中引刃而亡。想要摆脱心魔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自己也彻底毁灭。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命运还是那样的残忍与不公,但掌控命运的已然不是那神秘的不可知的力量,也不是在未来等待着的末日审判,而是一个人的内心,是多多少少能够触碰得到的。
4 北京人——理性精神的象征
《北京人》作为曹禺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剧作,其现实主义手法的娴熟运用、人物性格的逼真刻画、契科夫式平淡忧郁的意境营造历来为研究者们所称颂,更有研究者称其代表了“曹禺剧作的最高成就”[4]。剧中“北京人”这一形象身上彰显出的理性精神,代表了曹禺先生对命运的认识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北京人”这一形象在剧中实际上有着三重指代。第一,指的是过去的北京人,即是剧中出现在纸幕上的那个猿人似的黑影,他们“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他们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束缚,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礼教同文明”,他们是“快活”的,他们身上有着原始而雄强的生命力,是人类的祖先。第二,指的是现在的北京人,即是以曾家老老小小为代表的“活死人”,他们虽然活着,却丝毫没有生气,他们只会叹气,做梦,“活着只是给有用的人糟蹋粮食”,他们是他们祖先的“不肖的子孙”。第三,指的是未来的北京人,他们“抱着哀痛的心肠和光明的希望,追惜着过去,憧憬未来”。过去的北京人已经化为一种原始的力量和理性的引导,推动着现在的北京人向着未来的北京人转变,受到感召的,如瑞贞、愫方甚至曾霆,他们敢于向这个腐朽的制度发出反抗,敢于逃离这个毫无生气的“坟墓”,所以他们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北京人,在光明中获得重生;而另一部分不愿或不敢跟随着感召走的人,如守着棺木倒数生命的曾皓,抽着大烟虚以度日的曾文清,机关算尽却竹篮打水的曾思懿,自命不凡却毫无行动的江泰等等,他们没有希望没有未来,他们将随着旧的一同死去。
与其他三剧相比,《北京人》中表现出来的命运感更具有尘世色彩和现实精神,剧中的人物第一次可以自己对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而这一切都归于“北京人”这一形象所代表的理性力量的引导。这是曹禺先生在对命运的不断思考和探索中给出的最终答案,也是他一直渴求的正义力量的最佳显现。
5 四大悲剧中象征性意象的艺术得失
考察曹禺四大悲剧的创作进程,不难发现一个清晰的事实,即:作为超现实主义戏剧元素,象征性意象的创造及其运用在四大悲剧中贯穿始终,它并非偶尔为之,而是有意为之。“雷雨”意象传达的希腊悲剧式命运思考,“日出”意象传达的希伯来式命运探索,“原野”意象传达的表现主义意味,“北京人”意象传达的理性主义的思考,充分体现出曹禺先生作为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大师,其艺术趣味的“多元性”。将象征性意象引入到戏剧艺术中,既深化了戏剧的内涵,又增添了新的美学效应。
首先,象征性意象的加入使得戏剧中现实主义的控诉更加深刻有力。象征性意象并非独立地凸显于戏剧之外,而是与曹禺四大悲剧中一切现实主义戏剧元素(舞台场景、戏剧冲突、角色配置等)水乳交融,不可分割,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就使得通过戏剧反映出来的现实更加由表及里、深入本质。以《雷雨》为例,曹禺愿意追认《雷雨》的中心思想有“彰显大家族的罪恶”的意味,但在大家族罪恶的背后,还有一股更加黑暗的、无法挣脱的力量,那是一口把一切都吸入深渊的枯井,任谁都挣脱不出。《雷雨》写于1933年,那时的中国还处于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时期,曹禺就已凭借其敏感的神经隐隐感受到了这股更加可怕的力量。他以“雷雨”来象征这一力量,让其导演一出彻底的悲剧来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发出控诉,这就比单纯地对“万恶的旧制度”发起控诉要深刻得多。
其次,象征性意象的加入又使得各个悲剧故事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掺入了一丝不可捉摸的神秘美感,起到烘托戏剧氛围、引人入胜的作用,它不但从根本上揭示了一切悲剧灾难的本质,而且大大激发并强化了悲剧灾难所特有的崇高感。以《原野》为例,《原野》的第三幕可谓是全剧的高潮,也是全剧最为复杂的一部分。“原野”这一意象烘托出恐怖诡秘的气氛,不但影响着剧中主人公的心神,也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神经。观众会随着仇虎一起踏入那个阴森的原野,随着主人公一起经历恐惧和绝望,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就更能体会主人公的内心,更能领悟戏剧所要表达的主旨。
最后,象征性意象的加入,对于曹禺四大悲剧的审美效应的传达,有着莫大的“催化”作用。即如瓦雷里在《象征主义的存在》[5]一文中指出的,象征主义极为显著的创新和基本特征,就在于通过象征性意象的加入,在作者和读者(观众)之间建立某种“精神上的积极合作”,并因此推动读者(观众)参与到剧情的“重读”之中。通过对象征性意象的不同理解,可能会产生对剧本思想意涵的不同理解,这一点,正是四大悲剧能够成为常读常新的“经典”之作的重要原因。
当然,戏剧毕竟是一种舞台艺术,而象征性意象的内涵却是无法通过舞台表演完整传达的——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曹禺的四大悲剧在传播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作者、读者(观众)和论者之间的相互“误读”现象:一方面,包括评论家在内的读者(观众)群体至为看重四大悲剧传达的暴露性和批判性力量,轻慢甚至批评它们传达的非理性、超现实意味——这往往导致它们在搬上舞台之后始终存在着某种艺术表现上的“缺失感”。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曹禺始终“喋喋不休”地强调其悲剧故事传达的神秘感和超现实感,强调鉴赏过程中保持“审美距离”的必要性;除了通过舞台背景和剧情设置刻意营造,他甚至不惜一再为剧作写序、跋予以说明。事实上,《雷雨》中的“第九主人公”就因为无法作为青面獠牙的“雷公”显现而被放弃,“日出”也无法彰显出其审判力量而显得苍白,“原野”的诡秘很难完整地搬上舞台,“北京猿人”的“显身”又导致了剧情推进及其舞台表演的生硬和怪诞。这一切,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曹禺四大悲剧中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即其对于“命运”的不断思考和探索。化身为“雷雨”的命运具有的神秘感和不可抗拒性显然是受了古希腊戏剧的影响。然而同样是遇见了不可回避的命运,古希腊人给我们留下了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王式的英雄,而曹禺给我们留下的却是一群庸庸碌碌、可悲可恨的小人物,这正是曹禺借命运的残酷来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发起的控诉,是与当时社会现实结合的产物。进一步加剧的黑暗现实不断刺激着曹禺敏感的神经,在与先哲伟大而孤寂的灵魂对话之后,他也不禁渴求命运能化作一种终极审判的力量,扫荡一切罪恶,于是便有了“日出”这一意象。基督教常常把“报应”推迟到天国,曹禺似乎不满他的宽容与迟缓。他的《日出》,直接写出了鬼的阵营的溃灭,显示了“报应”的力量,可以说,这源于基督教,但又超越了基督教,这是曹禺自己心目中惩恶扬善力量的化身。报应迟迟未来,而黑暗仍在继续。曹禺对命运的探索的方向也终于由外部力量转向了内在因素,于是便出现了代表着心魔的“原野”。这是曹禺先生逐渐摆脱“二希文化”而逐步走向自己的悲剧创作的开始,也是曹禺先生对命运的思考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标志——命运其实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终于到了《北京人》中,命运化身成了一种理性力量,引导着主人公摆脱了黑暗、走向光明。这便是曹禺先生对命运的终极思考,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答案。
从“雷雨”到“北京人”,我们可以看出曹禺对命运的解读已经由外部的神秘力量掌控转向内部的理性力量掌控,这正是他命运观念逐步走向清晰和成熟过程的体现。
曹禺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但同时他的戏剧中还包含了超越现实的探索。这正是曹禺先生“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地方,也是曹禺先生真正的伟大之处。
[1]曹禺.曹禺剧作[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2]曹禺.曹禺剧本选[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
[3]周靖波.中国现代戏剧序跋集[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239-252.
[4]田本相.曹禺剧作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185.
[5]保尔·瓦雷里.象征主义的存在[G]//胡经元,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