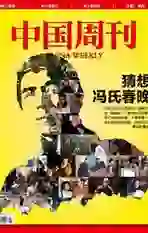夹心“港漂生”
2014-01-15

有段时间,蒋楠每天都要听《血染的风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听到热血沸腾再去上课,以此来坚定我对祖国的热爱。”她读书的城市,并不在国外,而是香港。
刚刚到香港两个月,蒋楠没想到会卷入一起新闻事件,甚至在香港和内地之间激起圈圈涟漪。
2013年10月,《苹果日报》的报道称,香港城市大学一个硕士班的内地生,选修了以广东话授课的“中国文化要义”课程,上课时却要求老师用普通话授课,引发香港本地学生不满,双方产生激烈骂战。有香港媒体将此引申为内地与香港“矛盾蔓延至课堂”。随后,该报道被内地多家媒体网络转发。
蒋楠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语言翻译学系的研究生,她是选修这门课的内地生之一。“报道的不是事实,我们并没有骂战。”那些天,蒋楠的全班同学都出动了,他们在微博上尽力解释,引来的却是大部分内地网友的责难。“他们不相信我们是受委屈了,觉得我们肯定是暴发户、素质低,才会让香港人骂,觉得我们活该去香港受罪。”
内地媒体纷纷询问实情,蒋楠和同学们却不敢轻易接受采访。到最后,每回复一条微博,同学们都会在群里讨论上一阵,“就怕引起更大的矛盾,夹在中间特别难受”。
事实上,那门课并没有发生骂战。希望一年毕业的内地研究生,须在上半年选修广东话授课的这门课程,才能修够学分。授课老师怕内地生听不懂,便在重点部分用普通话解释一遍,并在课下开了3次辅导课。10月份以后,已没有内地生反映跟不上。
随后,这则新闻被内地媒体辟谣。“这件事情是被夸大、被演绎了。但矛盾不是表现在一节课上的。”蒋楠说,作为“港漂生”,她总能感觉到“香港人并不喜欢我们”。
我们怎么看朝鲜的,他们就怎么看我们
初到香港,蒋楠一句广东话也听不懂。去超市买东西,听不懂价格,只能拿最大面值的钞票给店家。来香港之前,蒋楠也多多少少听说了一些关于“抢购奶粉”、“双非婴”、“内地人被称‘蝗虫”的新闻事件,父母提醒她,不要张扬,要礼貌,不要吵架。
蒋楠恪守着这些规范。不闯红灯、上滚梯靠右站立、不在地铁里吃东西,甚至地铁上有两个以上空座时,她才会坐下。蒋楠用到了“谦卑”这个词,“本来就被人瞧不起,就特别怕别人瞧不起。”然而,她还是感受到了一种“不友善”的气氛。
老师用普通话讲考试内容,香港同学却说听不懂。“实际上,课下小组讨论时,他们都听得懂普通话。”
到了香港,蒋楠对莫言的情绪变得复杂了。“我承认他很优秀,但是感觉有丑化中国人的嫌疑。”课堂上,讲到莫言的《雪国》,提到中国大陆的贪腐问题,老师列举了内地人的种种丑态,香港同学笑成一片。
“那感觉就是我们怎么看朝鲜的,他们就怎么看我们的。”她说。
令人难过的,是“港漂生”刘涵的车祸离世。2013年10月8日,曾经的云南高考状元、港大毕业生刘涵因车祸不幸在港离世。在纪念她的相关网页上,有香港人说她该死,将她和一众赴港求学的内地生称为“蝗虫”,将他们的父母称为“蝗族”,叫嚣是“蝗虫”和“蝗族”抢夺了他们的就业职位和香港的资源。
在蒋楠眼里,刘涵是“有追求的女生完美化身”。2007年,刘涵入读港大国际商业及环球管理学系。曾是舍堂篮球队队长并主持港大高桌晚宴。港大本科毕业后,她进入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工作。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凭什么我们就该死?”蒋楠说。这件事,在港漂生的圈子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在“资深港漂”陈嘉佩看来,“这种敌视状态,感觉不是香港人本性里发出来的那种了,有点过分了。”2002年,时年12岁的陈嘉佩随家人从内地到香港生活。“我是看到香港人怎样一步一步地改变的。”
陈嘉佩刚到香港时,也不会说粤语。“我当时在学校里广东话不好,同学们会教你讲,很nice,不会笑话你。”陈嘉佩说,十年前的香港,对内地人的想法是土,没有钱,不文明,“他们会看不起你,但是对你很友善,他们觉得你们是弱势群体,需要关注和照顾。”
2008年,陈嘉佩开始读大学。那个时候,内地生还不叫“港漂”,本地生和内地生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
2010年,香港《明报周刊》刊登封面专题故事《80后港漂》,是较早尝试定义新时代“港漂”的媒体之一:“顾名思议,就是漂泊在港的异乡人,其实更准确地说,是近十年香港放宽内地人进港读书和工作的政策下,那些漂至香港的内地族群。”
然而到了2012年,在陈嘉佩读研期间,“双非子女”、“抢购奶粉”、“蝗虫论”等问题纷纷爆发出来,她感觉到敌视的气氛已经很普遍了。
2013年5月,香港学生在Facebook上发起“反对滥收内地研究生”的活动。在陈嘉佩读本科时,全班只有2名内地生。到她读研究生时,完全倒置了,只有两名香港本地生。
作为香港在内地自主招生政策的产物,“内地生群体”已经渐成规模并成为香港社会一个独特的存在。自2003年经教育部批准后,香港高校由每年招收不到200名内地生,10年间增长到近1600人的规模。如今,包括西藏、新疆在内的31个省份都被纳入香港高校的人才战略版图。
时评人梁启智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院的兼职讲师,在公共政策分析课上,他的学生主要是内地生。他的本地学生与“港漂生”的摩擦在于生活习惯。本地生投诉内地生不整洁,内地生投诉本地生晚睡晚起。“都是宿舍生活的小事儿,有时很小的事情可以被传媒放得很大,因为社会中本身就有很多不满。”
梁启智说,公然的歧视行为不是主流,但背后对中国内地的不满意见是主流。“过去五年,香港年轻人当中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从41%跌到15%,这说明社会中对中国内地有多大的不满。”
“总的来说,收内地生本身未必是问题,但它挑起了香港社会已有的问题,大家的矛头就会容易指向内地生。”endprint
香港人变了
2001年,香港终审法院根据《基本法》确立:父母双方皆无香港居留权的中国大陆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2003年,香港和内地签署CEPA协议,放开“自由行”。每年,四倍于香港人口的内地游客蜂拥而至。大量大陆孕妇来香港产子。从2001年至2011年间,已获居港权的“双非婴儿”超过17万人,造成资源分配问题,例如产妇床位不足,引起香港社会不满,香港市民多次游行抗议,甚至引发了“蝗虫论”的争议。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在读研究生方金平认为,自由行改变了香港经济的生态。身为香港人的他很奇怪,为什么内地人来香港就很喜欢买药。于是,药房成了自由行一定会去的地方。药房开了很多家,不断上涨的租金,让许多本土的小店再也无力支撑。“前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乐见自由行再放宽》的文章。实际上,我们香港人会想,如果自由行少一点会很好,带给香港的负面影响是内地报道里很少提到的。”
方金平说:“一般人会认为内地生、内地人就是那个模样。”香港人认为的“那个模样”是没有礼貌、不尊重别人,财大气粗的“土豪”形象。“其实我接触的内地生都不是这个样子,可是自由行很多游客就是这个样子。在这种大背景下,很难把‘港漂生抽离出来看待。”
陈嘉佩曾在Facebook 上看到一个“港漂”女孩的长信:
“刚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关心一切。去年梁书记当选时,我在湾仔扭伤了脚。后来,我就不去(游行)了,因为我发现这个地方都不爱我,我干嘛要爱这里?硕士班里的香港同学,对你笑了一年,结果在心里无比的仇视你,在课上欺负内地同学听不懂,大声用广东话嘲笑内地同学和老师。你们都不爱我,那我凭什么要为你们做这么多?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定不干涉你港内政了。我遇到了困难,你们不会保护我的,我一旦撞车死了,你们会开香槟庆祝的。”
在陈嘉佩眼里,香港人变了。“以前的香港人不是这样的,内地发生天灾人祸都会捐款,很有爱心。现在说她(刘涵)该死这样的言论出现了。这不能代表普遍,但有这种想法的人出现了,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在香港出生的“双非婴儿”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每天从深圳入闸到香港上学的小学生成了“一景”。香港的学位变得紧张,一些政策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几乎香港所有的媒体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实质上,有多少香港人对‘港漂真的特别厌恶,是说不清的。”陈嘉佩说。
2012年,陈嘉佩在浸会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毛孟静参选立法会,打出来的口号便是“拒绝大陆化”。“她能直选进去,可见很多市民还是比较认同煽动性的言论。”
在一些香港人看来,香港社会内部的落差越来越大,2012年,香港的实际基尼系数高达0.537,创40年来新高,甚至超过了中非共和国。随着工业北上,政府对金融房产的大力扶植,底层人的生活越发艰难。香港已经成为零售商铺租金全球排名第二高的城市、居住成本第三高的亚洲城市、置业成本第四高的国际都市。
香港人不但感受着香港社会内部的落差,还得接受外部落差。曾经香港人眼中的“阿灿”,现在成了出手阔绰的“土豪”,买奢侈品如同买白菜。
身为编剧的香港人马焱(笔名)说:“这几年香港社会环境不太好,大家没地方发泄。与内地的矛盾就成了矛头之一。大家压着一口气吐不出来,一些媒体把矛头转向一点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爆发了出来。”
为什么不能在宿舍做爱呢
陈嘉佩在2012年底拍摄完成了五集纪录片《港漂生活微记录》。“这两年香港社会对‘港漂的争议也越来越大,‘港漂是一个夹心的阶层,夹在中间。”陈嘉佩想拿出一些东西让本地人看一看,“让他们真正了解‘港漂都在干什么,他们为香港做了哪些贡献,而不是说他们掠夺了本地人的学位资格和工作饭碗。希望两个群体之间互相了解一下吧。”
同她合作的香港导演卢兆坤在此之前并不了解“港漂”。“几年前,香港很多人不知道香港有‘港漂,现在很多与内地有往来的公司都会专门请一个‘港漂当助理。”卢兆坤看到很多内地人过来读书又留下工作,“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里”。
卢兆坤的父母都是从内地过来的上一代移民。“他们辛辛苦苦地工作,想法就是建一个家。‘港漂来香港也是想找一个落脚点和发展空间,大家都是一样的。”在卢兆坤看来,“港漂生”都是内地很好大学过来的尖子生。“‘港漂不是大陆游客,他们工作、纳税,带来的是香港的发展空间。”卢兆坤的香港朋友对他的工作评价很高。“之前的矛盾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不了解。”
马焱的身边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港漂”。作为编剧,他做的是国产剧,内地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有很多‘港漂朋友,大家没啥区别。唯一的问题是香港人普通话比较差。”马焱打趣地说。他认为能来香港读书的都是国内拔尖的,无论外貌或者谈吐都和大家一样,“我觉得有能力的人,应该拿多一点东西的,香港社会就是这样。没有人来竞争,这个社会怎么进步啊?”
来到香港之前,蒋楠以为香港是一个高效、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随着一些矛盾冲突的加剧,她想不通:为什么号称移民城市的香港会这样?更意气用事地想:“凭什么要学广东话?”她将自己的想法分享给在国外留学的一些同学们。却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她的同学告诉她,在澳大利亚找跟华人相关的工作,英语可以不好,但广东话必须要好。加拿大一些银行有汉语的特色服务,但服务的汉语是广东话。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汉语是广东话,并非普通话。
蒋楠“听懵了一样”,很多固有的观念一下子被瓦解了。
同是“港漂生”,对接触香港社会和掌握广东话的想法也不尽相同。浸会大学毕业的孙梅觉得到香港就应该掌握广东话。“难道你去英国不说英语,还要求人家对你讲普通话吗?”浸会大学硕士毕业的王维维见过香港学生在民主墙上贴过类似的大字报,也不以为意。“这是他们的自由,还有人贴为什么不能在宿舍做爱呢。”
在学校里,蒋楠见到了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学生会选举。为了选举,学生们会提前一个月准备。演讲、发册子,设计吉祥物,做专门的竞选服装,甚至有学生穿着超人的斗篷满校园跑。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学生们都在学校里宣传,蒋楠吃饭路过时,总是会被拦住。“天天为你宣传竞选理念,支持他们,你会得到什么好处。”这是蒋楠从来没见过的。
“在国内选学生会干部,就是上去演讲一下,最后还得老师定。在这里,每一票都需要争取。”竞选结束后,没选上的学生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要求公开学生会的账目。“我对他们是钦佩、羡慕的。在内地谁会问每个人交的十块钱班费哪儿去了啊。”
香港中文大学的兼职讲师梁启智说:“政治的问题现在解决不了,但还是有很多人努力去处理生活的问题。在中文大学,我们很鼓励学生学粤语,又会安排内地生和本地生一起做义工,探访老人院、少数族裔等等。我们的看法是,让内地生和本地生一起去发现香港一些他们以前不知道的角落,可以让双方也谦卑一点,知道自己过往认识的盲点,日后的冲突或者可以减少。”
一个学期过去了大半,蒋楠正在努力适应香港的学习生活。周六、日没有课,但蒋楠基本都在小组讨论、写作业和看论文中度过。蒋楠正在积极地学粤语,希望通过努力,改变别人的看法。“毕竟我们是来学习的,你自己努力一点,别人就会尊重你一点。”蒋楠说,她的感觉很真切,和本地同学的相处也好了许多。“通过合作报告可以消解一些误会,他们也会和我们联合对付其他小组的local(本地生)。”
“你要比他们更努力,才能赢得尊重。”蒋楠说,“要学会包容,不仅包容习惯上、性格上的不同,也要包容别人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之前做过让人不喜欢的事情。人家是否认同你,取决于你的强大,而不是你的强硬。”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