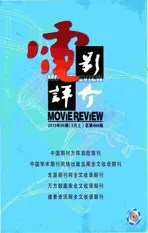见或不见:解析电影《胭脂扣》结局设置的巧妙之处
2013-11-21刘子垚
是“相见不如怀念”还是“日日与君好”,在爱情中每个人都有关乎得失的疑惑。而在关锦鹏导演的电影代表作之一《胭脂扣》中,也有见或不见的疑惑。原著小说中是“相见不如怀念”,电影中却是得以一见,我认为,影片“见”的结局设置十分巧妙。
《胭脂扣》于1988年上映,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胭脂扣》。电影以跨时代的叙事手法,讲述如花、十二少缠绵的爱情,更值此把二、三十年代的塘西风貌搬上银幕,题材、布局都十分新鲜,令影片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如花的妓女死后成为一冷艳女鬼来报馆寻人的故事。小说的结局是如花苦苦寻找,除了知道陈振邦尚在人间,仍未寻得十二少,女鬼如花也无影无踪。
改编后的电影仍然保留了原著中时空交错的叙事方式,电影与小说的最大差别在于结局的设置。小说中,如花没有找到十二少,如花也消失在现代人袁永定的生活中,仿佛没有来过,结局任由读者想象。而电影中,最后如花见到了十二少,此时的十二少已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糟老头,没有当初的俊美与儒雅。如花一声声“负情”的质问,老年十二少沙哑地喊着“原谅我”。最后,画面定格的是如花美丽的面庞,像是在告别,像是在笑,又似笑中含着泪。见或不见之间,我认为电影中“见”的情节设置有其巧妙之处。
改编是影视创作的重要来源之一,电影从其摆脱“活动照相”的那个阶段开始,也就是电影学会了向观众叙述一个故事开始,电影便开始向戏剧或小说借取原材料,电影改编也随之出现。
《胭脂扣》的原著作者李碧华是香港文坛大名鼎鼎的才女,她的小说选材冷僻刁钻,最擅长写情,她笔下的情充满了浪漫、激越、凄艳的色调,李碧华的小说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可供发掘且质量颇高的素材。
毋庸置疑,文字形象是可以转化为银幕形象的,但电影和文学又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这就是说改编不是照搬而是艺术的再创造,改编电影不必也难以完全忠于原著。文学用语言构成文学形象,电影则用镜头构成银幕形象,虽然二者构成的都是艺术形象,但这两种形象无论是在作家思维上还是在读者或是观众的感受上都是不同的。小说的构思可以不必至始至终都在头脑中塑造形象,作者可以做概括性的叙述,也可以发表议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电影的构思要求在整个过程中都运用形象思维,而且是造型的形象思维。对于读者,由于读者个人经历以及审美趣味的不同,对于同一篇小说的理解是不同的。电影则不一样,它与客观世界的成像相关联,由于视觉具有确定性,银幕形象通常是单纯的,不像文学运用隐喻、转义等多种表达方式,往往不具有同文学一样的多义性。文学形象是联想性和感受性的。因而在《胭脂扣》小说的结局中,如花最终见或没有见到十二少不必清楚明了地表述出来,因为那被如花丢弃了的胭脂扣、那首爱情名曲《卡门》、袁永定的疑虑等等所构成的信息量已经很大,足够读者细细品味了。而电影形象是具有确定性的,在电影中,小说结尾的种种是难以用形象语言表达出来的。银幕形象的确定性要求影片在结尾给观众一个答案,也给这场跨越时空的寻找划上一个句号,因而我觉得如花必定是要见到十二少的。影片本身的线索就是如花寻找十二少,本片不是悬疑片,却一直在给读者设置悬念——如花是怎么死的?十二少是死是活?十二少现在身处何方?如花寻找的结果是怎样?随着影片的放映,悬念一个个解开,观众也渴望知道最后的结果。最终,在影片的结尾,美丽依旧的如花见到了垂垂老矣的十二少,十二少道歉,如花说不再等,这结局对观众的震撼程度是非同小可的。影片结局的妙处之一在于,不仅清楚交代了最终的结果,又深深震撼了银幕前的观众。
而对观众的震撼源于对观影观众心理的正确把握。改编要考虑观影观众的心理。观众观看电影有着双层心理动机:一是依恋自己,在电影中体会自己热爱并熟悉的生活;二是寻找自己,通过电影中角色的同化,在心中重建自己失去的对象,满足对自己没有得到的客体的拥有欲望。观众的观影心理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是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集合。从情感的角度来看,最受中国男性观众爱慕的银幕女性形象,一般在外貌和言行上都符合中国伦理对女性的要求,有着东方女性特有的道德美感。但从另一个方向上来看,那些对旧道德、旧伦理深觉压抑的观众却欣赏叙事主人公对旧秩序的反抗与超越,他们通过对主人公的认同,实现了他们在现实中无法超越的束缚的突破。《胭脂扣》这部电影,对于男性观众来说,如花符合男性对情人的所有想象:她专情,肯为爱情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她又多情,懂得如何取悦男人;她美丽,有着很多种样子,叫人看不厌也如迷一般;她又脆弱,苦苦等待那一个男人却还是痴心枉付。但是在男性观众眼里,十二少是不值得如花如此付出的,如花的一片深情应该倾心于更有担当的男人身上,而不是只会风流却贪生怕死、不学无术、最终败光家财的十二少。因而结局中,十二少的落魄给了嫉妒十二少的男性们些许安慰,而如花的美丽依然更是男性观众所期望看到的。对女性观众来说,女性渴望轰轰烈烈的爱情,就如小说中的阿楚,但她们又痛恨薄情的男人。如花与十二少的爱情缠绵悱恻、坎坷重重,最终殉情收场,如此轰轰烈烈的爱情真是嫉妒死旁人,阿楚就一遍一遍地问袁永定“你会不会为我自杀?”。但最终十二少是多情而又怯懦的,他偷生了,这让女性观众忍不住指责十二少的负心,同情如花的深情错付。影片结局中,十二少的悔恨,如花的绝尘而去,使女性观众大为解恨。如果不见到十二少,没有最后的这一幕而任凭读者想象,女性观众也是不甘愿的。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影片的结局也是必须如此的。人是电影的主体,电影的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无论何种电影都必须把人作为创作的透视中心。电影要通过人物的外部言行、内心活动、命运遭遇、性格冲突,来揭示生活的哲理,反映人民的意志,表达作者的体验,愉悦观众的身心。影片和小说对于如花形象的塑造并无太大的差别,二者都形象地刻画出了痴情、偏执、柔弱的烟花女子如花,最大的差异在于十二少。小说中并未过多提到十二少,虽然十二少也是故事的中心人物,但十二少的出场多是通过如花的回忆,且这种回忆在文中所占篇幅不大。电影中十二少多次出场,从影片开头的风流倜傥,到离家的艰苦度日,一直到影片末尾的垂垂老矣,十二少的形象较之原著小说要丰满得多。在小说的结尾,也提到了陈振邦,但只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个普通人,或许是十二少,或许不是,十二少最终在茫茫人海中不知所踪。如果没有影片末尾两人的相见,留在观众视野中的如花还是那个痴情的女子,十二少还是那个风流、儒雅的富家子弟。而有了影片结局的这一安排,如花给观众的印象不仅仅是痴情,更让观众认识到她是对爱情有着至高要求的女子,苦苦等待之后发现等的那个人并不愿与自己同生同死,便毅然决然地放弃。而如果如花没有见到十二少,没有了两人相见时的冲突情节,也不能凸显十二少的懦弱和悔恨。如此安排结局,如花的形象得以更鲜明,十二少的形象得以更丰满,影片的故事结构也得以更圆满。
随着影片的结束,见或不见的问题也有了圆满的答案。见与不见之间,所获得的效果是不同的。电影《胭脂扣》的编剧李碧华和邱刚健并没有完全照搬原著小说,而是在影片的末尾给如花的寻找一个明确而又震撼人心的答案——见,这正是影片结局设置的巧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