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彩墨画的概念范畴以及历史定位研究——以王爱君的彩墨山水画为例
2013-09-08顾凯军
顾凯军/文
关于彩墨画的概念范畴以及历史定位研究
——以王爱君的彩墨山水画为例
顾凯军/文
CONCEPTUAL CATEGORY AND HISTORICAL POSITIONING OF INK AND COLOR PAINTINGS——A CASE STUDY ON WANG AIJUN’S INK AND COLOR PAINT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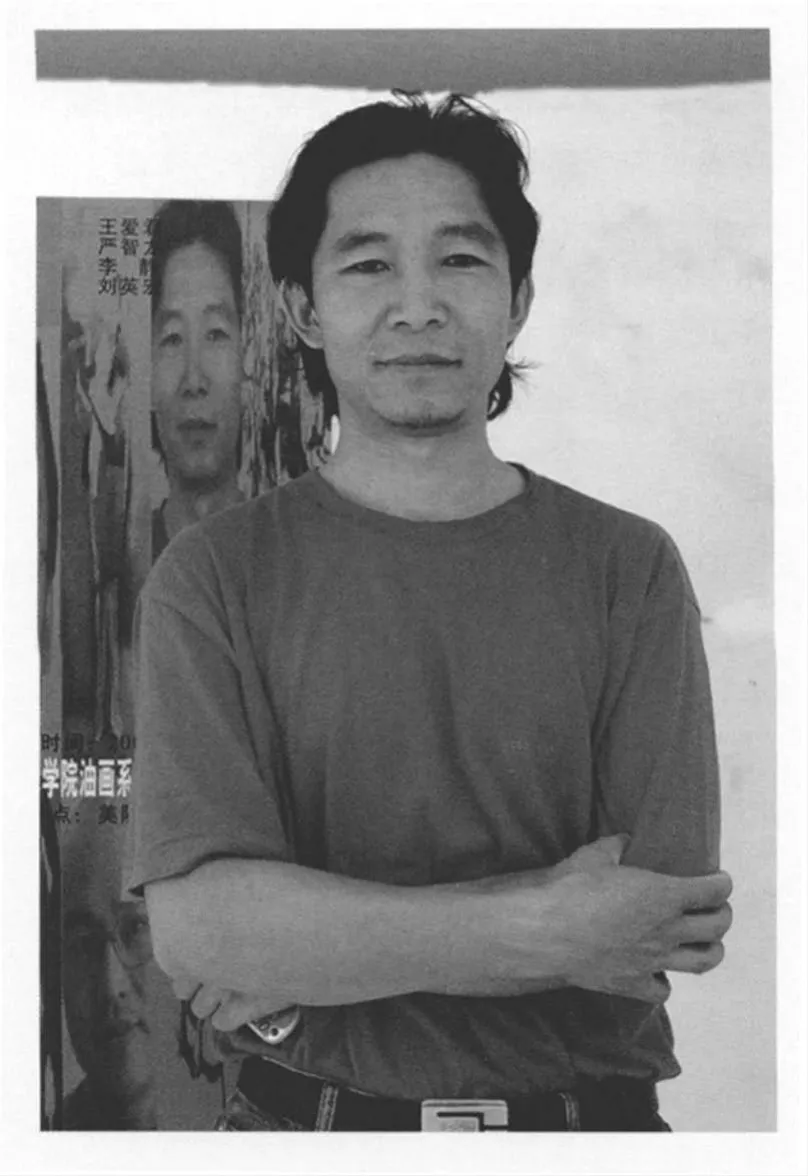
王爱君,1968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1995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2001—2003年于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攻读硕士学位。2002—2003年于法国土昆美术学院交流学习。2004至今任教于天津美术学院。现任天津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
“彩墨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关注彩色的、具有现代实验精神的现代中国画的一个新称谓。当代有学者如牛克诚将“彩墨画”与“工笔画”和“重彩画”并列统称为“现代彩绘”。根据他的观点,近代绘画史就是一个色彩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例如:日本的近代绘画史就是一个色彩的日本画代替水墨画的过程,在西方则有印象派引领了艺术史的革命,而在中国这种转换却迟迟没有发生。这样的思路非常敏锐,可是我还是认为用“现代彩绘”作为一个总的称谓,可能过于宽泛、笼统了些,失去了对中国画特质的定位。因为那样的话,日本画、水彩画、丙烯画、工笔画、重彩画等都可以称为“现代彩绘”,失去了中国的个性。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首先“工笔画”和“重彩画”在技法上有重叠的地方,都是“先钩后涂”法,即是先钩线后填色,它们都易产生死板、匠气的特征。在这一点上,现代日本画也有同样的弱点。其次“彩墨画”虽然大量使用了色彩,可是它从材料技法到理论都走向了综合,尤其是在技法上与“水墨画”出现了兼融并蓄的局面。所以我直觉里有一个观点:是不是可以用“彩墨画”来代替“现代彩绘”这个概念,也即“彩墨画”既是三者之一,也是三者的统称。这个做法在中国并不是没有先例,在中国所有的乐器都统称“琴”,而“琴”又专指“古琴”,这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古代音律是以琴为准绳的。“彩墨画”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在探讨“彩墨画”的时候必然涉及到“气韵”、“意象”、“笔墨”(彩墨画也有笔墨,只不过“墨”已转换为“彩”)等传统画论的核心概念,但同时它又是极当代的,与传统的文人画从形式感到技法都拉开了距离。因为“彩墨画”从格调到理论都远远高于“工笔画”和“重彩画”,而且其概念外沿的宽度和广度都远远高于后两者,所以将三者并称,并不相类,也尤为不妥。

不焦虑的风景NO.18 宣纸水色 73cmx200cm 2013年 王爱君

不焦虑的风景NO.13 宣纸水色 120cmx240cm 2013年 王爱君
“彩墨画”这个概念的发生虽然只有三十年,可是若我们从中国绘画史的长河中去考察,便会发现“彩墨画”的技法表现形式竟然和先秦、两汉、魏晋至唐早期的绘画在技法上有着更强烈的亲缘关系,和唐宋以后的工笔画、重彩画的亲缘关系却疏远很多,这是为什么呢?我的分析如下。

不焦虑的风景NO.19 宣纸水色 73cmx200cm 2013年 王爱君

不焦虑的风景NO.11 宣纸水色 120cmx240cm 2013年 王爱君
我们都知道“汉宫承楚制”,从建筑到礼器到绘画技法都是承继楚制的。楚画灵动飞异,真气弥漫。精气能幻化出各种精怪瑞兽、祥花异草的图形,这些图形既是写意的,又带有抽象装饰的意味。尤其是楚漆画的技法与两汉魏晋的绘画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这一时期的绘画不排除色彩,甚至可以说是以色为主,以墨为辅。从技法上来考察正好印证了孔子的一个著名的艺术观点“绘事后素”,正符合这一时期的作品面貌。孔子认为,再妍巧的色彩,最后也得以素色、墨或中性色来规范它。就如同我们看一个少女,她的着装打扮再好看、再艳丽也得用合乎礼的修养和身姿来打动人。从技法的角度来考察,先秦人画画除了墨稿粉本之外的作品,应该都是“勾涂结合”甚至“先涂后勾”的,这个表现方法不是后来的先勾轮廓线然后再从淡到浓的层层渲染,一笔下去直接就是物体的大形状或者是云气纹的动态线,然后再以中性色或墨色局部勾勒轮廓线,原先粗犷的色彩线突然活了,充满了精怪的灵异色彩。这种方法其实就是谢赫六法里的“骨法用笔”,“骨法用笔”和“绘事后素”所体现的先秦绘画技法是一脉相承的。

不焦虑的风景NO.17 宣纸水色 73cmx200cm 2013年 王爱君
根据谢赫的观点:只有取之象外才能参列神品,而陆探微“事能言象”故能名列古今第一品、第一人。古今莫出其右。他认为“古画之略,卫协始精”。虽然卫协没有陆探微形妙,但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而当朝人极度推崇的顾恺之在谢赫的《古画品录》里只名列第三品、第二人,说他“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迨意,声过其实”。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谢赫认为只有“骨法用笔”才能传神。到了魏晋时期,绘画在技法上从先秦的“先涂后勾”(先涂色后勾线)为主开始过渡到“勾涂结合”了(有的地方先勾线,有的地方先涂色)。所以谢赫会说:“古画之略,至协始精。”根据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所记载的师资传授源流,我们能看到这个师承脉络:卫协师于曹不兴,顾恺之师于卫协,陆探微师于顾恺之,张僧繇师于陆探微(推论,因张彦远没有明说张师承于谁),吴道子师于张僧繇。也就是说谢赫明知道陆探微是师于顾恺之却将顾恺之名例第三品第二人,陆探微排列古今第一,为什么?在张彦远《论顾陆张吴用笔》中我们看到:陆探微师从顾恺之后,吸收了张芝的“一笔书”,借今草之体势独创了“一笔画”,笔势如今草,笔断意不断,连绵不绝,故名“一笔画”。“陆探微精利润媚,新奇妙绝,名高宋代,时无等伦”。而张僧繇“点曳研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顾陆之迹是属于密体,而张吴是疏体,所以张彦远说:“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根据张彦远的观点,如果懂得画有疏体、密体之分,才可以论画,否则只有点头应付一下便走。这里有一个问题,陆与张分别被划分在密体与疏体两个阵营,可是这两人又有共同点,他们都借鉴了今草的笔法。顾的人物造型因为笔法的缘故,可能会缜密写实一些,陆因为借鉴了今草的一笔书,所以造型更夸张传神一些,而画法至张僧繇可谓是真正大变,因为张借鉴了草书的“点曳”之法,线条向写意传神更迈进了一大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张借鉴草书的“点曳”之法是对先秦“先涂后勾”中骨法用笔的线条的一种高度回归。见过楚文字的人无一不惊叹于楚文字善于运用侧锋、偏锋的神妙,这种用笔和后来的草书的“点曳”之法无异。这种用笔在两汉的墓室壁画里自不必说,在魏晋时期的敦煌墓室壁画更是如此,轮廓线一般都是只勾一半,是典型的疏体。
到了唐代就不行了,因为唐代佛画的流行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受印度佛画“凹凸体”的影响,中国的佛画从张吴的疏体迅速滑向写实和流俗,并且受此画风影响,直接产生了后来所谓的“工笔画”。印度绘画是典型的“先勾后涂”法,虽然它也重视线条造型,可是都是密体,而且用色都有明暗,紧贴着线条,丝毫没有中国疏体灵动的张力。这种匠气的画法,在线条上与顾的“高古游丝描”,陆的“一笔画”相结合,在用色上借用了印度佛画的凹凸明暗技法直接导致了“工笔画”的产生。张吴之迹几成绝响!
吴道子的画作有摹本传世,可是张僧繇的画作连个摹本都没有传下来,是画史上的一个悬案。不过张的画迹有《山海经》的木版画再摹本传世,这个世人很少知道。有史料记载,宋代舒雅曾经临过张僧繇创作的《山海经图》,收入内府库藏。明代胡文焕版刻本《山海经》中的插图,据当代学者马昌仪的研究,就是以舒雅本的再摹本翻刻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胡本《山海经》能间接一窥张僧繇画风的原貌。另据马仪昌研究,日本有一种彩色手绘本《山海经图》更接近舒雅临作的原貌,这个版本我在马的著作中见过,就采用“勾涂结合”的画法,是典型的疏体面貌。
还可以从唐代长沙窑的瓷画上考察这种“勾涂结合”的技法。在长沙窑的瓷画中,动物或花卉的清晰的外轮廓线很少,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明朗线条,有时画师一笔下去,你很难说它是线,是面,是体,还是色,技法非常丰富,画面的色彩部分毛绒绒、湿漉漉,线条以侧锋摆动法为主,动作极快,正是张彦远所谓:“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画面没有泾渭分明的色、线、形,但这三者又是高度统一的,好多地方是“先涂后勾”的,有的地方留白,甚至有的地方有如京剧脸谱一般出现了正负形,色、线、形之间是阴阳相生的。画面里的色和形,包括留白都充满了骨感,这种技法正是谢赫所谓的“骨法用笔”。这才是中华绘画技法的正根,后来的院体画和工笔画都走向了“歧路”,色彩上被印度的明暗凹凸技法所左右,与顾陆的密体画嫁接产生了工笔画。可惜长沙窑的这种技法只在民间画师中传承,没有被后来的工笔画和水墨画继承,也成为绝响,这些都是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所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太大了,直到近代“彩墨画”作为一个画种概念的提出,这个古老的传统才有了被激活,恢复新生的可能。

不焦虑的风景NO.20 宣纸水色 73cmx200cm 2013年 王爱君
工笔画、重彩画的特点正如金鸿钧认为的:先勾墨线,后施以淡彩渲染,然后浓彩渲染,最后局部施以重彩。这种画法就是典型的凹凸法,与中国画从先秦流传至南北朝的古技法完全不相类。从哲学的高度上我认为工笔画和重彩画作为画种和样式与有着强烈中国特色的“彩墨画”相提并论非常牵强。行文至此,我想最笨的读者也知道我说的“彩墨画”指的是什么了。“勾线填色法”作为印度样式像一个幽灵一样在吞噬着中国画家的智慧、灵感和创造力,使得中国古典工笔画从宋元以降一直到明清、民国近代,都易陷入匠气、流俗的单一性样式。技法的僵化限制了中国特色艺术风貌的健康发展。日本的浮世绘也是同类的典型,这些都难以代表东方艺术的最高成就。
也许有人会说:现代工笔画已经融合了明清抒写性的精神观念,加强了工笔画中的主观性、写意性、表现性等人文因素的发挥,将水墨画的技法和境界融入了进来。可我还是要说这只是“换汤不换药”,是杂糅,不是原生态的中国技法。因为这些所谓的“新工笔画”不管它怎么变,“先勾后涂”这个技法上最致命的先天缺陷并没有被去掉,所以我说这种改良是无效的。
然后又有人说了,既然你强调上古技法源流的重要性,那你的当代性体现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不要给画家这个画种、那个技法的条条框框,只要他创作出不同于工笔画、水墨画的新面目来就行。到了我们这个与文化传统断裂的时代,要激活一种古老的传统只能用创新这个办法了。正如刘骁纯所言:越是具有个人创造性的就越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创造出来的,民族性在个人创造之中。

不焦虑的风景NO.15 宣纸水色 180cmx240cm 2013年 王爱君
王爱君的《山石系列》是当代彩墨山水画创作中的成功作品。在他的画面里没有明显的形、线、色的区别,他画山水几乎不勾外轮廓线。他用色的方法和水墨画的墨分五色法正好相反,他先调五种以上颜料在水里,让它们变得很稀薄,调成一种老汤,这个老汤是画面基调色,可能灰,也可能黑,但是很少用一种颜色上去,一般都是三个颜色,画到最后可能出现四个颜色。这种方法其实和石涛表现黄山有雾霭时的天空差不多,里面有非常丰富的颜色变化。可是王爱君的技法走得更远,他用丰富的色彩画石头,因为基调色是灰的,所以他敢大量使用泼彩的方法,可是用笔又很细微,局部看是大写意,什么都没有,可是从远处看什么都有,色、线、形都隐藏在画面里。因为他是用老汤做基调色,所以他的泼彩和张大千的泼彩截然不同。张的泼彩是在泼墨的基础上再泼以浓烈的纯色如天蓝色去表现霞光雾霭,而王爱君的泼彩是没有明显颜色倾向的灰度色,他画画往往从一个局部一边泼彩一边点染,就像一个植物一样长成一个画面,这个石头的外形长成什么形状往往不是他事先设计好的。
在王爱君的画面里你找不到光源,和西画不一样,他的画面没有明暗,所以让人产生了一种心象学上的心理空间。那光线很像是从宣纸的背面透过来的。在用色上可以说,王爱君是我看到的将工笔画色彩的凹凸感超越得较彻底的画家,你无法将他的画归入工笔画,也无法归入水墨画,与西方水彩画相比也是两个画种,完全没有关系。只能说这是一种当代新彩墨画,与传统的汉代墓式壁画、敦煌壁画、长沙窑瓷画也都不同,是新时代的新样式。王爱君从他个性的创作出发,不小心触碰到了中国画除了工笔画、水墨画之外的一个更大的、更为古老的“彩墨画”传统,又无意识地将他在西画里学到的造型和色彩训练巧妙地与中国画的技法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当代彩墨山水画的新样式,在技法上智慧地融合了疏体和密体的矛盾关系。在“笔墨”问题上我不能说王爱君突破了什么,可是在对色彩与形和线的关系上,在色彩的表现力上,王爱君单枪匹马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样式。

不焦虑的风景NO.16 宣纸水色 180cmx240cm 2013年 王爱君
2013年5月16日于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