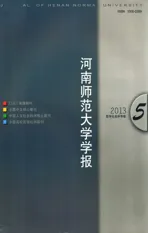小额诉讼制度完善的进路分析
——对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解读
2013-04-12李峰
李 峰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小额诉讼制度完善的进路分析
——对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解读
李 峰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小额诉讼立法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单纯禁止上诉,另一种是分化出专门的小额诉讼程序。在我国,强化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仍然是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程序设置原则化有着长期影响,司法活动并不适宜程序分化所要求的精细操作,民事诉讼法修订中采纳了第一种模式,在简易程序中作出禁止上诉的特别规定。根据我国民事司法发展的阶段性,今后完善小额诉讼的重心不是案件处理过程的专门程序体系化,而是围绕小额案件的确定标准以及当事人的选择权、救济权保障等展开符合国情的设计。
小额诉讼;禁止上诉;程序分化;模式意识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62条对小额案件审理作出规定,诉讼标的额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者,一审终审,对此不少人认为我国正式确立了小额诉讼程序。然而,小额诉讼与小额诉讼程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针对小额案件审判的司法活动,后者是指小额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行为在特定时空的安排,并与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并列的程序制度。显而易见,我国并没有设置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只是新增了有关小额诉讼的制度规定。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极为简略,势必面临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北京、浙江、江西等省市高级人民法院相继制定有关小额案件审理的规范性文件,明确使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并制定有关小额案件的范围、审理方式、审理期限、审理程序转换等内容,俨然有构建体系化、独立化的小额诉讼程序之趋势。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的立法本意,对今后制度完善的走向和司法实践意义重大。
一、小额诉讼立法的两种模式
小额诉讼立法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反映出各国对小额诉讼本质的认识和司法改革目标理解的差异。
(一)单纯禁止上诉模式
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采用此模式,不在立法上设置单独的小额诉讼程序,而仅规定小额案件一审终审。德国一直通过上诉权限制来防止当事人滥诉,加快诉讼程序。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11条第1款规定,对于初级法院的第一审判决不服的,如果申明不服的标的价额在1500马克以下,禁止上诉。需注意的是,此条款所指的标的价额不是当事人讼争的全部标的价额,仅指对初级法院一审裁判不服的部分,与其他国家判断是否属于小额案件系以全部诉讼标的价额来衡量明显不同。此外,“许可上告”制度也是德国对第二审裁判不服而上诉的一种限制,这由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46条所规定。法国同样在立法上体现出限制上诉权的思路,甚至规3500法郎以下的小额案件禁止上诉。意大利也规定滥用上诉权的罚款、损害赔偿等制裁措施[1],对5万里拉以下的案件禁止上诉[2]。限制上诉权在司法实践中取得良好成效,上诉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在德国,不少学者认为,1500马克的标的价额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耐人寻味的是,2001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时,立法部门并未响应学者的呼声,反而将禁止上诉的标的价额标准降到600欧元以下(约合1200马克),说明德国对禁止上诉这种较为极端的制度设计始终保持审慎态度,以免限制当事人的上诉权超过应有限度,诉讼权利保障仍然是民事诉讼立法的基准。
(二)程序分化模式
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采用此模式,在立法上设置单独的小额诉讼程序,使小额诉讼程序从其他程序中分化出来并与之并列,一审终审只是该程序中的一项内容。设置小额诉讼程序的包括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国家地区,由于法律传统的区别,各国家和地区的小额诉讼程序具体内容有较大差异,但基本保持程序体系的完整性、独立性。在程序启动上,一般都依赖当事人的选择。日本规定启动小额诉讼程序须在当事人提出诉讼时依申请为之,法官不会依职权启动程序。在审理法官方面,一些国家没有将案件审理权力的行使限定于正式法官。美国小额法庭可以由正式法官、聘用法官、临时法官审理案件,正式法官由各州选举或州长任命,临时法官由法庭之其他人员担任,临时法官通常由当事人同意的律师担任[3]。在审理规则方面,都突出案件审理的快捷性要求,简化审理规则,英国还规定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法官可以迳行裁判;在上诉权的限制方面,大部分国家原则上禁止上诉,但有例外规定。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27.12条规定,对于程序严重违法或者法律适用错误的,当事人可以上诉。可见,通过程序分化设置小额诉讼程序的国家,因小额程序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以及其他程序并列,小额程序中有关程序利用条件、审理法官、审理规则、上诉规则等方面规定明确具体,从而使程序体系更加丰富、复杂。
(三)两种立法模式的比较
不同的模式选择反映了小额诉讼立法思路差异。德、法等国将小额案件放在上诉权视阈下考虑,英、美、日等国从程序结构体系和功能视角对小额案件作出制度上的系统安排,两种不同做法均有其各自的诉讼传统和特定原因。德国、法国从来不承认当事人拥有不受约束的绝对上诉权,上诉须以上诉利益存在为前提,上诉利益是当事人上诉成立的实质要件,认定标准一般采用“形式不服说”[4]。为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即有对上诉合理控制之必要,这构成上诉利益制度的正当性基础。限制上诉权自然是上诉利益理论在立法上的体现,小额诉讼案件一审终审只是整个限制上诉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对一审、二审裁判不服的上诉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因为限制上诉权始终面临违宪的风险,且司法资源的供给能力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上诉权的限制程序保持一定弹性和适当调整的可能性。德国2001年调整有关禁止上诉之诉讼标的价额即为印证。采用程序分化模式的国家实际是将小额程序作为过于正式化的通常程序之补充[5],形成繁复与简略互相支持的程序体系。小额程序既是多元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一环,亦是保护小额请求的具有特殊程序构造之制度[6]。与单纯禁止上诉模式的重心为上诉权限制不同,程序分化模式的着力点是程序构造,针对小额案件尽可能设置适宜的程序规则体系,明确当事人程序地位、审理规则、证据规则、救济规则等,以求更加顺畅的分流案件,确保民众“接近正义”。正因为一审终审不是程序分化模式的重心,对上诉权的限制就不那么严格,救济条件比单纯限制上诉模式更加宽松。另外,该模式使小额诉讼程序置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快捷审理程序等复杂的诉讼程序体系之中,并有具体的内部程序构造要求,在个案的程序选择和程序运作上比单纯禁止上诉模式更加复杂。
二、单纯禁止上诉模式选择的合理性
通过小额诉讼立法模式的类型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2条只是规定了小额案件实行一审终审,本条规定纳入简易程序之中,作为对简易程序的补充,并没有专门针对小额案件做出具体的程序设计,在立法选择了单纯禁止上诉模式,不存在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这种立法方案虽不排除为权宜之计,但背后蕴含的立法思想和合理性值得认真分析。
(一)程序权利保障任务的长期性
近些年来,针对民事诉讼案件居高不下的状况,司法改革的重心逐渐移向案件分流、审理快速化方面,在能动司法理念引导下积极探索民事速裁、诉调对接等机制,为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提供经验积累。与之相伴的是,民事司法中确实存在不当简化程序环节,片面追求结案率的情况,小额诉讼立法观点上也有过于注重程序再简化的倾向,但主流思想仍然高度警惕能动司法大潮下对当事人程序权利可能带来的损害。最高法院以及各地法院在制订有关速裁、诉调衔接、小额诉讼的规范性文件中,大多强调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或者明确禁止削减重要程序环节。这说明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程序正当化建设所形成的观念影响,案件繁简分流、审理快速化的改革尝试并没有清除程序保障观念,但效率工具主义极易借助本阶段民事司法改革重新泛滥,部分地区的过分追求调解率、快速结案率等做法显示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仍然是需要长期努力完成的任务。小额诉讼程序以全面限权为根本特征,法官审判权及当事人程序保障权皆受严格限制,甚至有专家认为小额程序虽作为一种诉讼程序的称谓,倒不如认为是一种替代性解决机制。美国不少州的小额案件一旦进入上诉审查,就对案件全面审查,形同未经审判一样[7]。全面限权为特征的小额诉讼程序不宜作为现阶段的立法选择,如果从程序构造上对当事人的证明权、辩论权、异议权、上诉权给予全面限制,势必使民事纠纷解决程序运作整体上趋向严重的非正式化,目前来之不易的程序保障观念可能在这种立法思想的冲击下逐步弱化。我国小额诉讼立法存在一种特殊的背景,就是程序保障观念尚未完全根植于社会,程序保障建设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与全面限权的程序分化模式相比,不构建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适当关照小额案件处理简易化的客观需要,采取部分限权的单纯禁止上诉立法路径更符合实际。
(二)程序设置原则化的影响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体系向来呈简便、粗疏的特点,程序设置原则化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一方面,新中国立国之前长期贯彻服务民众、争取民众的思想,力争使民众对执政思想有清晰、直观的认识,法律制度必须为社会各阶层所能够理解和运用,繁琐精细的程序设置与该法律观念背道而驰。马锡五审判方式之所以得到长久青睐,其中蕴含的司法观念在社会转型时期重新焕发生机,与简化司法程序、便于民众利用的目标追求有着直接关系。在“接近正义”的司法改革世界潮流影响下,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并没有走上全面精细化道路,仍然坚持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基本架构的程序体系,维持了简便、亲民的风格。另一方面,新中国废除了原中华民国源于德国的繁琐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立法直接师从苏联,同时也没有全部照搬苏联民事诉讼制度,而是有取有舍。依据固有的程序设置原则化思路舍弃了苏联民事诉讼法中的不间断审理原则,并在司法改革中放弃强职权主义模式,实际引入一个“减配版”[8]。反观国外设置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的国家,其立法目的重心不在于繁简分流和减轻法院的案件压力,而是对固有的正式化、专业化、精细化程序体系之补充,以增加当事人程序选择的机会,提高民众便于利用司法程序的可能性,我国民事诉讼法早就已经具备这些特性。如果设置复杂的小额诉讼程序并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并列,案件审理就需在三种基本程序中做出选择,会增加程序协调和运作的难度,因此程序分化的小额诉讼程序立法模式在我国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使程序体系更复杂,更不易利用。
(三)保留进一步选择的可能
断定我国最终选择了单纯禁止上诉的小额诉讼立法模式难免有些武断。民事诉讼法修订中没有采取独立小额诉讼程序的程序分化模式,学术界的反对意见是一重要原因。司法机关对小额诉讼程序立法相对积极,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虽然强调小额速裁并非为现行制度框架下的独立诉讼程序,但却明确试点的目的是为将来修订民事诉讼法、创设小额速裁程序积累审判实践经验,并且就案件起诉、受理、审理、裁判等重要环节作出体系化的规定,各省市在试点工作中的规定更加具体。与实务部门创设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的强烈冲动相反,学术界不少学者主张采取审慎态度,反对一步到位的立法冒进。认为我国目前还处于“建设法治”“深化法治”阶段,不同于德法等国的“简化法治”阶段,首要价值目标是构建公正的民事司法体系[9]。与国外相比,我国民事案件审理速度并不低,并且速度越来越快,加之案件受理费很低,实际在鼓励当事人将纠纷提交法院,巨量案件涌入又不得不迫使法院进一步加快审理速度,一些必要的程序被简化省略,削弱当事人的程序保障[10],以案件分流和提高效率为出发点构建小额诉讼程序与现实不符。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设置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也不是完全一致地反对,也有观点认为,在小额诉讼程序存在之前不能靠推理判断其弊端,任何程序利弊皆有,该程序积极的一面是毋庸置疑的,应当构建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11]。由是以观,对小额诉讼只作单纯禁止上诉的规定,并不一定是最终的选择,很大可能是为平衡意见分歧而采用的传统做法,即立法上只对小额诉讼做出粗略的、原则的规定,视法律适用情况再予以完善,保留进一步选择的可能性。
三、我国小额诉讼制度完善的进路
单纯禁止上诉的立法模式选择事实上已经确定现阶段我国小诉讼制度完善的进路。不论是通过司法解释或者进一步的立法完善,都应在此基础上针对当下小额诉讼的背景和条件做出符合国情的设计。
(一)司法解释应依循现有立法思路
本次民事诉讼法修订中增设了诸多新的诉讼制度,新的制度依然延续原则化立法的传统。按照以往的处理方式,为满足司法实践中的制度具体化需求,一般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相信小额诉讼制度的完善依然会沿用此做法。不过,针对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的司法解释,不应理解为立法做出原则规定和司法解释实现具体程序体系设置的分工。在小额诉讼立法存在巨大观念分歧、制度构建局限于小额案件一审终审的现实面前,意味着现阶段在简易程序中对小额案件做出特殊规定的方案已经确定,排除了立即构建独立小额诉讼程序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在制订司法解释时必须克制程序分化的冲动,避免对小额诉讼进行体系化的程序设置,形成事实上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关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北京、浙江等地在民事诉讼法修订后制订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已经走上建设独立小额诉讼程序体系的道路,与修订后民事诉讼法的小额诉讼规定严重背离,使小额诉讼制度溢出简易程序的框架范围,导致简易程序异化,进而混淆了程序分类标准,埋下当事人程序权利被肆意剥夺的巨大隐患。即使立法并没有排除将来选择构建独立小额诉讼程序的可能,目下司法实践中采用小额诉讼程序的表述,并制订本属立法权范围的小额诉讼程序内容,实属轻率和急功近利。申言之,小额诉讼案件的一审终审只是对一些特殊案件的上诉利益从法律上予以去除,以平衡有限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因而禁止上诉,这实际是两审终审的例外,我国案件分流的现实需求也不足以使其通过独立的程序设计而发展成为普遍状态。有关小额诉讼的司法解释只能依循现有立法思路,不得与简易程序的基本规定相冲突。
(二)以小额案件确定标准作为司法解释的重心
小额诉讼制度立法只确定了小额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和一审终审两个基本内容,由于一审终审的规定非常刚性,司法解释的重心只能在诉讼标的额的认定方面。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的小额案件是指诉讼标的额为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的案件,“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何所指?需要加以明确,否则会造成小额案件确定标准的混乱。关于年平均工资有社会平均工资和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两种表述,前者包括社会劳动适龄人员平均报酬,其中劳动适龄人员是指在工作岗位上的从业人员、15周岁(含)以上的无业人员。后者统计范围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等,但不包括城镇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国家统计公报发布时将两者合二为一,只公布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其中又分为在岗平均工资和合计其他种类人员的平均工资。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统计数据,2011年全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而合计其他种类人员的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1799元,两者之区别显而易见。以统计的涵盖面和真实反映平均工资水平的效果来看,合计多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更为可靠,应当作为计算诉讼标的额的依据。再者,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确定小额诉讼案件标准,目的在于解决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问题,没有确定全国的统一数额标准,但是各省、自治区内仍然有地区发展水平不一的问题。依小额案件标准分地区确定的精神,应当允许各省、自治区高级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本行政区划内各地区的小额案件诉讼标价额的标准。
(三)立法完善的主要对象是当事人选择权及救济权保障
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的本身确实还存在一些严重缺陷,有待将来立法中予以完善。其一,当事人的选择权。程序保障是现代民事诉讼的根基和灵魂,除非有充足的正当理由或者当事人依法对民事程序权利给予恰当处分,不得减损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域外小额诉讼制度多负有弥补通常程序过于精细化、正式化缺陷的任务,依理更应具有强制适用的积极性。反观之,大部分国家在小额诉讼立法中却赋予当事人选择的权利,而非绝对强制适用小额诉讼规定。这说明小额诉讼制度的固有风险足以使立法者慎之又慎,适当控制利用的机会。我国目前采取强制适用小额诉讼制度的态度,彰显积极利用的立法宗旨,小额诉讼制度或许成为助推司法向非正式化发展的又一利器。鉴于现有民事诉讼制度简便、亲民的基本特色没有改变,小额诉讼制度不具有国外矫正程序体系过于繁琐精细的功能,应当将其视为基本程序体系中的例外规定,确立严格的适用条件,以当事人选择适用更为恰当,尊重其上诉权利处分的自主意志。其二,小额案件的救济措施。“有错误者必须有救济”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更何况缺乏程序权利保障是小额诉讼的先天不足[12]。本次增设的小额诉制度缺乏对裁判救济的规定,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即使在采用单纯禁止上诉模式的国家,也不是彻底剥夺当事人对小额案件裁判的上诉权,而是作出例外规定。德国禁止小额案件上诉的例外有两种情形:即案件有原则性意义,或者判决与联邦法院的裁判或与联邦最高法院联合法庭的裁判相抵触,并以此抵触为判决依据的[13]。凡符合这两种情形之一的,就不受禁止上诉的约束。日本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为当事人选择为前提,绝对禁止上诉,但却设置了另一种救济方式,即赋予当事人对小额案件裁判的异议权,如果当事人对裁判提出异议并且异议合法的,诉讼恢复到口头辩论终结前的状态,并转换为通常程序来审理裁判。具体的救济措施设计与是否赋予当事人适用小额诉讼制度的选择权有关,如果以当事人选择为适用条件,意味着当事人在选择时已经放弃上诉权,宜通过裁判异议制度予以救济;如果未以当事人选择作为适用条件,则应通过例外规定予以弥补,赋予当事人在特定条件下的上诉权。不管做何种设计,救济程序的启动条件均应以程序违法或者裁判违法为前提。
结语
单纯禁止上诉的小额诉讼立法方案是符合现阶段法治发展实际的选择,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体系立法过于激进和冒险,制度完善不可偏向程序分化的路径。因此,立足于简易程序的制度框架,以上诉原理及制度为视角,完善当事人的选择权、救济权等重要内容,俾使小额诉讼制度能够与现有基本程序形成互补、协调有序的关系。
[1]罗结珍.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Z].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112-113.
[2]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M].汪一凡,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516.
[3]马强.美国小额法庭制度与借鉴[J].比较法研究,2011(5).
[4]廖中洪.“上诉利益”若干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07(9).
[5]傅郁林.小额诉讼与程序分类[J].清华法学,2011(3).
[6]肖建华,唐玉富.小诉讼程序制度建构的理性思考[J].河北法学,2012(8).
[7]傅郁林.繁简分流与程序保障[J].法学研究,2003(1).
[8]段文波.一体化与集中化:口头审理主义的现状与未来[J].中国法学,2012(6).
[9]周翠.全球化背景中现代民事诉讼法改革的方向与路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4).
[10]李浩.宁可慢些,但要好些:中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J].中外法学,2010(6).
[11]王亚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程序分化[J].中国法学,2011(4).
[12]廖中洪.小额诉讼救济机制比较研究[J].现代法学,2012(5).
[13]谢怀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Z].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26,127.
[责任编辑孙景峰]
ApproachAnalysisofSmallClaimsSystemPerfection——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162 of Civil Procedure Law
LI Fe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Legislation of small claim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modes: one is pure prohibiting appeal, the other is differentiated specific procedure of small claims. In China, strengthening the safeguard of the parties’ procedural rights remains one of the main tasks in current phase, procedural designing relay too much on principles has a long-term impact, required precise operations caused by differentiation of procedure are not suitable for judicial activities. The amendments to Civil Procedure Law has adopted the former, special provisions were made for prohibiting appeal in summary proceeding. According to limited stage of civil judicature in China, the consummation of small claims in future should focus on standards of small claims cases, parties’ right of procedural election and safeguard of relief of right other than Systematization of special procedure dealing with cases’ process.
small claims;prohibiting appeal;differentiation of procedure;mode of consciousness
D915.2
A
1000-2359(2013)05-0068-04
李峰(1966-),男,河南潢川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研究。
2013-03-21